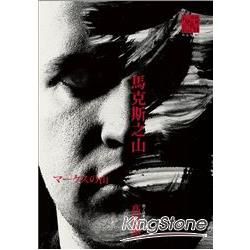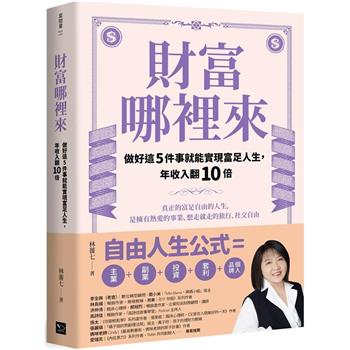山,究竟是什麼?
組織,又是什麼?
這群男人活在只要踏錯一步便會粉身碎骨的冷冽世界裡,
懷抱著得不到答案的疑問,追尋著隱藏在茫茫霧靄中的真相,
他們真能找到出口,見到彼端的那道陽光嗎?
高村薰生涯代表系列第一作
日本暢銷百萬冊,永遠的警察小說最高峰!
榮獲1993年第109屆直木獎,第12屆日本冒險小說大獎
「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1994「週刊文春推理小說BEST10」1993雙料冠軍作
「山究竟是什麼──合田在某個時期明白了自己為何一再挑戰更高更危險的激烈山巔,若能遏止某種自我毀滅的可怕衝動,打從一開始就不會登山了。登山伙伴之間共有赤裸裸的生死,到底從中產生了多麼強烈的感情?身體的麻痺與生命興奮的剎那間,萌生了多少倒錯的執著?──山到底是什麼?」
1976年的南阿爾卑斯的風雪中,發現了一具登山者的屍體。那具屍體讓一顆罪惡的種子落了地,16年後在東京綻放出了腥紅的犯罪之花……
一名前黑道分子被發現陳屍於文教區,幾天之後,另一名現任的法務省官僚則死在自家門口。以合田雄一郎為首的搜查一課刑警拚命調查,只發現兩人的生活背景毫無接點,唯有一致的傷口可以證實他們死於相同的犯人之手。然而,不明的勢力豎起了一道高聳的牆壁,將刑警們阻絕於真相之外。被隱匿的情報、被阻擋的調查,讓刑警們憤怒、焦躁,苦無發洩的出口。
與此同時,彷彿要嘲笑毫無頭緒的警方,犯人接二連三地痛下殺手,究竟這些被害者之間有什麼關連?他們和阻擋刑警腳步的勢力又是什麼關係?
難道一切的真相都隱藏在16年前的南阿爾卑斯的風雪中?
追蹤著犯人的腳步,合田來到了那座擾亂了所有人的人生的巍然山峰。
他將會在山頂上看見什麼……
作者簡介
高村薰 TAKAMURA Kaoru(1953-)
出生於大阪,目前也仍定居大阪。國際基督教大學畢業後,進入外資公司工作。原本對推理小說一無所知的她,因為想要寫商業文書之外的文章,便以曾經去旅行過的北愛爾蘭為背景,寫下了以多國特工橫跨歐亞兩洲展開的情報大戰為主軸的間諜小說《李維拉》(後改名為《追殺李維拉》出版)入圍了一九八九年第二屆日本推理懸疑小說大獎的決選。
隔年則以《抱著黃金飛翔》獲得第三屆日本推理懸疑大獎,正式出道。高村一出道,便轟動日本文壇,作風純熟圓融,被盛讚一出道即為完全體。
高村以冷硬、粗獷的文字,細膩描寫的各類男性形象及其內心複雜難解的糾葛,與格局龐大的作品獨步日本文壇。其中蘊含的哲學思索和批判社會問題的力道,也讓她成為日本的重要意見領袖。
出道二十年的高村素以寡作聞名,至今只有十部長篇單行本,本本厚重,但都深具讓人一讀就上癮的魅力,一旦進入高村的筆下世界,將終身無法離開。
譯者簡介
劉子倩
政治大學社會系畢業,日本筑波大學社會學碩士,現為專職譯者。
譯有小說、勵志、實用、藝術等多種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