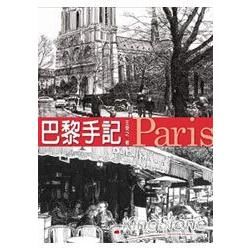這本小書其實是我在巴黎的一些劄記和速寫的集合,這些年來,因公因私,出入巴黎多了,有時候在博物館泡半天,有時候就到里沃利大街的英文書店挑書。帶部數位相機、一個速寫本、一支鋼筆,一部手提電腦,把所見所聞記錄下來,就慢慢成了一本書了。因為就是自己的看法,不是一本旅遊手冊,也不是巴黎正傳,個性很強,我自己覺得還是很有趣的。
雖然想寫這本書的念頭不自今日始,但本來還會拖些時間才動手,因為我手頭上還有好些事情沒做完。但是弄這本書的想法去年我曾和母親談過,她老人家很喜歡我的畫,因此說「你既然有這個計畫,就早點動手,早點出版了,也讓我看看」。沒有想到的是她突然在今年7月4日去世了,傷心之餘,我出於對母親的紀念原因,把這本資料已經大致備齊、但是還沒有動手寫和畫的書稿提前動手,文字、速寫、插圖、照片和在一起,在這裡一方面奉獻給喜歡藝術、建築的讀者,一方面也表達自己對母親的追思,希望她老人家在天堂能夠看到和喜歡這本書。母親的追悼會開完之後,回到美國,我就動手編這本書,有個很積極的目的和動力,因此書很快就出來了。
對不同的人來說,去巴黎的目的是不同的,遊客自然去羅浮宮、凱旋門、協和廣場、凡爾賽,坐著旅遊團的空調大巴,在景點上爭先恐後的拍照留念,巴黎人有點躲他們,喜歡自己慢慢看的人其實也在躲他們。在羅浮宮,你看見上百個穿金戴銀的韓國農民、或者中國那些全身名牌服飾的暴發戶們排著隊在〈蒙娜麗莎〉前面拍照,真是唯恐避之不及。其實也不怪他們,他們來一次不容易,再說你要他弄懂法國文化,下輩子吧。有些小資自助旅遊,拿本導遊書,買張地鐵通行票,樂在其中;藝術家們擠在博物館裡,設計師擠在大道區的名牌店裡,文化人在左岸咖啡館裡,談戀愛的躲在塞納河邊路下麵的林蔭下,那麼大的一個城市,地鐵四通八達,真是各有各的樂園。
在巴黎出差的時候,我經常住兩個地方:如果和學院的美國同事一起去,就會住在左岸聖熱曼區的一個旅館公寓中,叫列諾克斯(Lenox Hotel),那是在巴黎的第五區,和拉丁區很近,是很有文化的一個地方。那裡離開塞納河才一個街區,傍晚順著塞納河散步,河邊有很多的舊書攤,那裡有各種各樣的舊書舊雜誌,五花八門,琳琅滿目。我總在那裡駐足,在舊書的氣味中翻尋歷史,我特別喜歡那些舊巴黎的照片,它們保留了歷史,把歷史凝固在畫面上,總給人很多遐想的空間。巴黎的新與舊在照片上,在你的周圍,既雋永,又生動,它們構成了巴黎的時尚。
如果自己去,就住在離開共和國廣場一站路的一個美式自助酒店了,主要是舒服一點,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年,總是希望房間大一點,寬敞一點。加上那裡離地鐵站很近,出入就方便了。還有一層考慮,就是那裡離中國人的市場才三站地鐵,去吃碗餛飩麵之類的,方便得很。不過那裡中式飲食的水準,和我們熟悉的洛杉磯、溫哥華、多倫多就沒得比了。那個區比較平民化,比起列諾克斯酒店,差了幾個等級,反而覺得更加自在,可見自己真不是個做貴人的料。
今年春天去巴黎,到榮軍院去參觀法國軍事博物館,門口站個漂亮的女士官,穿套淺灰色的薄呢子制服、短筒裙,金色的頭髮綰起,戴頂小巧的軍帽,完全像個模特,漂亮得不可方物。她旁邊幾個海軍陸戰隊計程車官站在那裡和守衛的士兵聊天,斜著眼睛看去參觀博物館的美女,有兩個拿著手機的打電話,每個人都叼根香煙。完全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這種軍風紀,在美國絕對是看不到的,我去過愛德華茲空軍基地、聖地牙哥的太平洋艦隊基地、佛吉尼亞的安納波里斯海軍學院、紐約州的西點軍校參觀,見到的美國軍人總是風紀嚴謹,像這樣吊兒郎當的兵和官,在美國軍隊內大約早就開革了。
的確,法國軍人是很吊兒郎當,看看軍事博物館也就知道,他們也就這個水準,法國軍隊最後一次大勝仗還是1805年前後拿破崙帶領他們打的奧斯特里茨戰役,之後從來都是敗仗連連,在北非、在越南被打得大敗不用說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馬恩河也僅僅是靠著英國軍隊過海峽來幫忙頂著才沒有完全喪失國土,美國軍隊1917年參戰才解了他們的圍,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開始就把國家失給德國人了,基本沒有什麼抵抗,這個國家的軍隊,就是人好看,浪漫,制服漂亮,打仗是不行的。
古怪的法國人。
試想有個國家,那裡的人一年才工作34個禮拜,一年有7個禮拜帶薪放假,中午吃飯要一個半鐘頭到兩個鐘頭,他們的飲食是全世界吃的油膩膩的乳酪、乾酪、高膽固醇的鵝肝和蝸牛、大塊的紅肉,中餐和晚餐都要喝酒,除了上班走路之外,基本不怎麼運動,但是他們的壽命是西方國家最長的一個;一個民族對方便快捷的超級市場沒有多大興趣,卻喜歡像中國的老人家一樣每天逛市場買菜,回家自己燒飯吃,工作時間短成這個樣子,還整天罷工,說勞動時間太長了;他們卻享有世界上最好的醫療福利制度,看病基本不花錢,很多大企業是國營的,基本連連虧損,工會卻強硬得很,動不動就罷工怠工;他們的私人企業中工會力量在整個西方最弱,但是私人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在西方國家卻最高;雖然整天看見這個國家的人一堆堆的在街頭咖啡座上閒聊,喝口紅酒,連打手機電話的人都不多,幾乎沒有見到有什麼人拿手提電腦做事。早上出門時,看到這批人,下午回來時,他們還在那裡,整天坐著胡扯,悠閒得厲害,但是這個國家公民的人均收入卻是西方國家中最高的之一。你說這不有點天方夜譚嗎?你不感到古怪嗎。
如果你習慣了美國、德國、加拿大這樣的國家,在法國待得越久,就越覺得他們的確是很另類的。他們大部分人都對「慈善捐贈」這個詞,對「慈善家」這個詞沒有什麼概念,很少有人會在街頭捐錢給慈善機構幫助窮人,因為他們認為幫助窮人是政府的事情,美國人開著汽車把自己的舊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機,甚至舊汽車捐給救世軍,幫助窮人,成群結隊的捐錢捐物海嘯、颶風災民,成千上萬的做義工去幫助災區重建,在下著鵝毛大雪的耶誕節前幾個禮拜開始,就看見那些穿著制服的救世軍義工每天站在刺骨的寒風中,站在熙熙攘攘的百貨公司、購物中心門口搖著鈴鐺,那些剛剛買完聖誕禮物的美國人就魚貫地將手頭的零錢投到他們前面的紅色小桶裡面,給窮人集中買聖誕禮物,這都差不多成了美國聖誕一景了。可你在法國基本看不到這樣的現象,你問他們為什麼不做,他們冷冷的說一句:「哪政府幹什麼啊?」
人人都說法國美食,法國總統在為巴黎爭取2012年奧運主辦權時,還以法國飲食之精美來調侃英國佬,可你去法國餐館坐下來吃頓飯試試,那裡的服務態度可以媲「美」中國國營餐廳水準。我在西方各個國家來來去去,很少見到比法國人的服務更加差勁的,服務員牛成那個樣子,好像你進來吃飯倒是欠了他似的。我在拉丁區的「雙叟」咖啡館喝咖啡,就問了一句:「怎麼你們的咖啡比其他附近的咖啡店貴那麼多」。那個小鬍子刷的光光的男服務員拉長著臉、連笑容都沒有的回了一句:「你知道你坐的這個座位有誰坐過嗎?沙特!好像是因為我坐了當年沙特和西蒙波娃的椅子,咖啡就要貴那麼許多一樣,特別是那個態度,好像我是簡直不堪入目。你也甭氣,他不是專挑你來刺的,對誰都一樣。法國人對這樣的態度也逆來順受慣了,已經沒了感覺。你也不用埋怨服務態度不好,巴黎的商業網點是全世界最集中的,因此你大可以隨便換一間再試試,咖啡絕對好,不像美國的餐廳,服務生客氣得很,但是咖啡就好像洗鍋水一樣難喝。就算是美國餐廳,到了巴黎也得入鄉隨俗,地鐵站旁的麥當勞也得弄到十點才開門,太陽都升得老高啦。
在法國,你發現四分之一的就業人口是打的政府工,也就是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公務員,比我們整天埋怨的中國公務員比例高多了。這批公務員,是整個西方國家的公務員中效率最低,而工會權力最大的,在法國,可以說政府的走向、決策、表現全部是工會在控制的,比社會主義還社會主義。四分之一的人口當家作主,整個國家就懶懶散散了。巴黎那些衙門美輪美奐,到裡面辦個什麼事情都難得不得了,你去找部長秘書、甚至找部長,也幫不了什麼大忙。其實你找錯了,應該找這個部的工會主席才對,工會一言九鼎,動不動就全體罷工,一下子全城的巴士停開,一下子學校教員罷課,反正好像一個停停走走的鐘。自從拿破崙被放逐到聖海倫納島上之後,這個國家就沒有過什麼令人印象深刻的效益。說到停走的鐘,又讓我想起千僖年的前夕到巴黎,在協和廣場上看到特別裝置的為千僖年倒數計時的大鐘,居然停著不動!一問之下,才知道已經停了兩天了,問「為什麼沒有人來修呢」,答曰「管他呢」,真是典型的法國做風。
去巴黎去得越多,我就越困惑。好多在其他國家是常理的事情,到了這個國家就全反過來了。營養學家告訴你:在西方國家中,這個國家的公民抽煙最厲害、喝酒最多、油膩的食品吃得最驚人,但是壽命卻最長,在街頭基本看不見胖子,心臟病比率也比美國低得多。大家叫這種現象為「法國謎」(French Paradox),或者我叫的法國「魔盒」。反正是搞不懂。
法國有西方最高的稅收、有西方最邋遢的文官群、有整個歐洲最繁瑣無效的制度、有整個西方國家最高的債務、有政府管得太多太細的經濟活動,繁文陋習多得數不清,失業率長期在兩位元數字徘徊,政府卻拿不出刺激企業發展的政策。這麼個國家,卻在21世紀屬於全世界生產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單位時間產值最高的國家之一,世界第三大的出口國,全世界第四經濟大國,在歐洲可以和德國相提並論,世界經濟七雄中絕對少不了他的座席,但是他也絕對不按照國際經濟發展的模式邁步。你如果看《華爾街日報》、《經濟學家》和《幸運》週刊,所有的經濟成長所需要的原則法國好像都不具備,《紐約時報》經濟評論家湯瑪斯.佛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自己的著作《淩志車和橄欖樹》(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說:「如果國家是份股票,法國股一定是我立刻要賣掉的那種。
」
我就是這麼困惑,因為佛里德曼的書對我的影響太大了,在英文作家中,最不遺餘力批評法國體制和法國人的莫過於這個人了。而他的書屬於那種擲地有聲的權威著作,在《紐約時報》寫的經濟專欄也是言之有理、令人信服的。我去法國好幾次,每次回來都帶會浪漫的印象,還有就是一大堆自己無法解釋的現象,此人的著作,其實更加增添了我的疑惑。法國人的這種矛盾性,複雜性,實在令人撲朔迷離。在美國,讀遍所有所謂的主流雜誌和報紙,好像《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新聞週刊》、《時代》週刊等等,卻根本沒法在這些美國輿論中找到解釋。有個作家比喻說:看法國人就好像看駱駝,平時看,怎麼都覺得有問題,比馬差多了,跑不快,背上還有那麼個累贅的駝峰,等你到沙漠裡面,才知道為什麼是駱駝。法國人也是要在法國這塊土地上,才顯示出他們與眾不同的地方,出了法國就不行了,就是駱駝了。自從拿破崙以來,屢戰屢敗,就是好例子。你看法國的武器,樣子都不錯,打仗卻不行,什麼幻影2000,從來沒有什麼戰績,就是在訓練的時候老掉下來;法國的拉法葉驅逐艦,據說是具有類似美國神盾級水準的性能,雷達看不太見,臺灣花了好多錢買回來以後才發現性能不怎樣,雷達上看的清清楚楚,幾無隱形性,這就是法國人的可愛地方。
我一直在找有關法國人的書看,都太學術化,看完了,還是搞不懂。最近在巴黎的里沃利大道上(那裡有兩家恐怕在歐洲非英語國家也是頂級的英文書店)找到一本很過癮的小書,是兩個學者、記者寫的,叫《六千萬法國人不可能錯》(Sixty Million Frenchmen Can’t be Wrong),副標題更叫絕,是「Why we love France but not the French」,翻譯成中文就是「為什麼我們喜歡法國但是不喜歡法國人」。你說有多逗。
這本書好看得很,兩位原加拿大記者,一個叫納道(Jean-Benoit Nadeau),另一個叫巴婁(Julie Barlow),他們兩位原受「當代世界事務研究院」( the Institute of Current World Affaiers )的資助,專門花了兩年時間在法國研究法國人的這種矛盾性。真要感謝外國的研究機構能夠出資贊助這樣貌似空泛的研究專案,在我們國內是絕對沒有人會讓你這樣去「浪費」研究資金的。兩人都來自加拿大法語區,法文講得溜溜轉,英文寫的也漂亮,從頭到尾都是故事,結論雖然未必能說服所有的人,但是研究的內容卻引人入勝。他們還開列了一個長長的參考書目,我就按圖索驥,一本一本找來看,受益很大。
一個民族,如果能夠好好研究自己,如果能夠被別人好好研究,是幸事。因為知道自己是最大的幸福。
我看好多發達的國家都有這樣批評自己的書,在倫敦的諾丁山,我買到一本英國人寫的類似的書,是講英國人矛盾性的,叫《盯著英國佬》(Watching the English),作者是凱特?福克斯(Kate Fox),也是看得你放不下手。在美國書店裡,罵美國人的書比頌揚他們的多好多倍,那才叫絕呢!你到韓國看看,全是說自己好話的書,但凡外面有人寫什麼不利他們的,批評他們的,絕對千夫所指,國家不禁民眾自禁。臺灣的柏楊寫了本《醜陋的中國人》,就鋃鐺下大獄了。
讀完這幾本書後,我心裡癢癢的,就想立馬去把法國人搞清楚一點,不是專業,無關學術,純屬興趣,純屬好奇。估計國人當中,有這種好奇心的為數不多,中國人崇拜法國還來不及呢,連天子腳下的國家大劇院還非得找法國人來做不可!但人真是種奇怪的動物,那點子好奇,還就是按捺不下去。
我去法國好多次,不斷的多方接觸,四處遊歷,書買得多,資料也查了不少,不過要搞懂法國人,還真是不容易。第一是我的法文爛的很,勉強能看,講就困難,靠英語是靠不住的;第二是法國人最討厭美國人,因為美國在經濟上、軍事上、市民型的通俗文化上實在比法國人強太多了,法國人哪裡能夠嚥下這口氣啊!因此一說到是從美國來的,遭白眼的機會就少不了啦。
我對法國其實有好感,因為喜歡它的藝術,她的時尚,喜歡巴黎,喜歡那種什麼都不憂愁的自在生活態度。因此,縱有這麼許多不利條件,還是不斷的瞭解,不斷的寫出自己的感想,也就成了一書,沒有什麼學術意義,就是個興趣吧。
這本書其實是文章和自己畫的插圖、速寫兩者的合一。因為除了我自己的教學和研究、寫作之外,我還喜歡畫畫,但是從來不認為自己有藝術家的天才,還是寫文章多,所以好多人不知道我能夠畫。去年有個某美術學院的設計專業學生,發現我不但能講點理論,還能動手做點設計,已經非常奇怪了,後來看見我在給一個國內的房地產大公司的規劃圖提修改意見,除了寫了一、二、三、四的幾點意見之外,還正在畫一張改進意見的示意草圖,張大了眼睛說「原來你還可以畫兩筆!」我就喜歡這個感覺,自己不是什麼大藝術家,少了多少「大師」的負擔!而自己能夠畫,又多了多少樂趣啊!
法國的趣味,法國的浪漫,在我的這本書和這些畫裡面,可能和別人看到的有些不一樣,有些很有趣的東西,不妨看看,說不定你也喜歡的。
2006年7月25日,於洛杉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