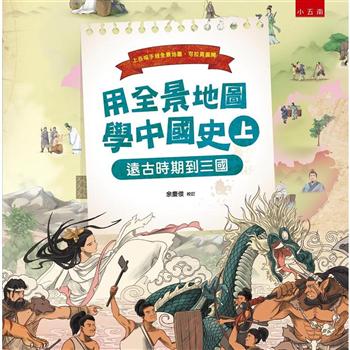前言
一九六○年八月十六日上午七點
約瑟夫.基廷格(Joe Kittinger)高懸在新墨西哥州上方三十多公里空中。十一分鐘過去了,他在吊艙裡面蓄勢待發。那是個開放式吊艙,掛在一顆龐大氦氣球底下緩慢旋轉。儘管太陽早就升起,周圍大氣依舊黝黑猶如午夜。遙望下方,地球的彎曲表面朝遠方延伸,構成一弧地平線,映襯漆黑太空、綻現一圈藍色光暈。
這道光圈就是大氣,地球擁有最寶貴的禮贈。地球的璨藍色澤不是得自海洋,而是染自天空。凡是見過那道細膩光暈的太空人,返航之後都會告訴我們:他們不敢相信,那讓地球顯得多麼嬌弱,卻又無比美麗。 回到地表,沒有了那種崇高視角,大家往往等閒看待我們的大氣層。然而,空氣是宇宙間最奇妙的物質之一。單憑這道黯淡藍線,就讓地球從荒涼岩塊,轉變為充滿生命的世界。而且在地表和要命的太空環境之間,也唯有靠這道屏障,保障脆弱的地球生靈。
基廷格卻越出了大氣保護圈。到了太空邊際高處,大氣十分稀薄,只要壓力衣失靈,不消幾分鐘他就會死亡。首先他的口水會冒泡,接著他的雙眼爆出、腹胃腫脹,最後血液也要開始沸騰。儘管他是美國空軍的試飛員,歷經種種凶險,然而這樣的危險處境卻也是有生以來第一遭。
他獨自待在吊艙裡面,對這種險境瞭然於胸。他有種奇妙感受,那裡的近真空似乎觸摸得到,彷彿有層毒氣團團包裹。黑暗景象令人心驚,他遙望下方雲層屏幕,卻看不穿障壁也完全瞧不見家鄉,這更令他不安。他用無線電和地面管制站通訊。他說:「我上方的天空很不友善,人類永遠不可能征服太空。或許可以到那裡居住,但想要征服卻是永無指望。」
他拖著腳步走向艙門,身負七十公斤重的保命裝備、儀器和攝影機,他的靴子略為伸出邊緣,在那裡站了一會兒。他雙腳下方十數公分處有塊標誌,上書「世上最高的階梯」。他從嚴密封合的頭盔裡吸了一口純氧。他說:「求主保守我,」接著便縱身躍下。
剛開始基廷格並不覺得自己向下墜落,他見得到腳下遠方的暴風雲渦漩,卻看不出雲層逐漸接近。由於周圍的空氣十分稀薄,他聽不到聲音,感受不到風吹,也毫無其他線索足以顯示,他正在人類有史以來最凶險的環境中向下急墜。他在空中攤開四肢,心中湧現幾可算是祥和的感受。他飄浮在一片虛無的海上。
儘管那裡的環境危險,卻仍在保護他。太空中的無壓力情況並非唯一風險,那裡還有大半來自太陽的密集輻射,它們不斷轟擊。太陽每天都為地球帶來光和熱,讓我們能夠生活在這裡,但它也同時釋出彩虹頻譜致命的那端———X射線和紫外光。
感謝我們的天空介入干預,這種輻射始終不會抵達地表。基廷格上方約八十公里處,少數空氣原子稀疏散布,它們發揮警戒哨的功能,負責攔截、吸收那批致命X射線。那批原子在這個過程中被撕扯擊碎,加熱到攝氏一千度。它們構成電離層,那層稀薄大氣的主導力量是電。那裡有龐然藍火從雷雨雲的頂部向上噴發,從地表卻見不到這種上下顛倒的雷霆閃電。來自太空的隕石在這裡灰飛煙滅、化為道道燦爛光芒,變成我們口中所說的流星。隕石帶來金屬在大氣中層層潑灑,從而使電流得以在地球上空四處飛竄。無線電廣播便由這處荷電表面反射,朝四面八方彈往全球各處。
再往上看,基廷格上方的空氣還要面對更猛烈的攻勢,那種打擊力量稱為太陽風。來自太陽的荷電粒子噴流以極高速度朝地球射來,時速超過一百六十萬公里,還趁勢劫掠我們的大氣、把氣層向地球後方推湧構成一道尾跡,讓地球看來就像顆龐大的彗星。
不過在此之前,太陽風必須先通過我們強固無雙的精銳防線:地球磁場。磁場拉動羅盤針指向北方,除了這項用途,我們在地表很少注意到它。但其實地球的彎拱磁場影響遠播,及於我們頭頂幾萬公里高空,磁場還迫使太陽風向四方繞道,就像水流受迫繞過船頭;基廷格上方遠處,道道磁性防護拱弧會導開太陽風,不致造成傷害。磁場防護十分周密,只有少數粒子漏網滲入兩極空域並與大氣對撞,帶來舞動極光,照耀南、北兩極。
儘管如此,我們的防護大氣幾乎全都位於地表上方幾公里範圍,而基廷格進行那次劃時代高空縱躍之時,大氣也大半位於他的下方。墜落幾秒鐘後,他踢腿扭身面朝上方,這時就可以見到他那顆白色飽脹渾圓氣球,以極端高速朝暗空直射而去。基廷格知道,這只是個錯覺。氣球仍然在他躍出的位置緩緩飄浮。其實是他自己以接近聲速,由高空向下墜落。
這時基廷格正翻滾穿越地球的另一道重要防護屏障:臭氧層。他的周圍散布一團無形氣體雲霧,所有溜過電離層的無形紫外線,全在這裡被吸收盡淨。臭氧是種奇妙的東西。地表附近的閃電和火星塞偶爾都會生成臭氧,它聞起來像電線失火,還會讓你氣噎。然而在上空高處,臭氧卻十分機敏又很容易再生。基廷格周圍的臭氧分子受紫外線轟擊分裂,接著便沈著重新構組。就像摩西遇見的著火樹叢,儘管烈燄不止,卻永遠不會燒毀。
兩萬五千公尺、兩萬公尺,繼續往下。壓力危機解除,這時就算壓力衣出現破洞,基廷格的血液也不會沸騰蒸散到空中。不過他還要面對最後一項危機:他已經抵達這趟下墜歷程的最寒冷階段,到了那裡,溫度已經降到零下七十二度左右,他的壓力衣加熱裝置也成為最重要元件。
接著就遇上雲層和氣流,基於種種跡象顯示基廷格終於逐漸接近老家了。一萬兩千公尺、一萬公尺,繼續往下。他就要下墜到聖母峰標高以下了。這時若有噴射機恰好飛經附近空域,就會看到一個身著古怪服裝的人,飛竄飆過窗口。他早先在吊艙見到的雲層,那時遮擋視線讓他見不到老家的屏障,現在便急速向他衝過來。儘管他知道雲朵只是一群觸摸不到的細小水滴,卻依舊蜷曲身體,雙腿上抬,下意識預備承受衝擊。他觸及雲朵那一剎那,降落傘同時開啟,這時他知道,自己可以活下去了。「四分鐘三十七秒自由下墜!」他對著語音記錄器發話,「啊?哇啊!」
這時基廷格已經安全下墜到大氣的最低層:對流層。這裡的大氣,與其說是一道防護屏障,倒不如說是促成地球轉變的契機,這是一層濃密的空氣厚毯,還有氣流和氣候現象,為我們的行星帶來生命,也把地球轉化為可居之所。基廷格越過了極度乾旱的太空,這時雲朵染上片片濕氣在他的面罩上。空氣逐漸濃密,他可以感受到那種拉扯。這時天空已經充滿生命,只是他還見不到它們。隨風攀升的菌群黏附於雲霧微滴,在遠離家鄉的地方搜尋新的侵染對象。昆蟲一路飄盪前往新的覓食場所,而種子則飄向更肥沃的土壤。
還有,謝天謝地,兩架搜救直升機就在附近盤旋。隨著地面迅速接近,基廷格持刀奮力切除他的重裝備套件好減輕著陸衝擊,然而最後一條管子,卻是怎麼切都切不斷,他放棄了,改打開頭盔護罩深吸一口新鮮空氣。空氣湧入他的肺部,氧氣躍過細胞膜進入血液細胞,讓它們轉呈帶了燦爛生機的血紅色澤。(其中有些氧氣則著手引發一場歷日曠久、從這輩子吸入第一口空氣開始,便延續不斷的狂躁歷程。這批無賴分子,還會繼續在基廷格臉上留下痕跡,拖累他的身體,持續我們所說的老化進程。)
最後,經過了十三分四十秒飛行時間,基廷格跌撞摔入矮樹叢中,著陸地點位於新墨西哥州土拉羅沙(Tularosa)以西約四十三公里處。醫事、地勤人員、後援隊伍和媒體記者,紛紛湧出直升機,趕往他著陸的地點。他的面罩開啟,對眾人露出笑容。他說:「我很高興回來和大家重逢。」儘管沙漠景致實在稱不上蒼翠,但在這個曾經超越大氣層的人眼中,絲蘭和灌木艾卻是充滿生機。後來他還說:「我在十五分鐘之前到了太空邊緣,而現在就我看來,自己是身處伊甸園。」 美國空軍上尉,約瑟夫.基廷格二世成為墜落地表生還的第一人。這項壯舉無人能及,他從太空邊陲出發,穿越稀薄空氣,進入濃密大氣並回返家園,彰顯出地球的若干非凡特色。
太空幾乎近得觸摸得到。我們頭頂區區三十數公里以上,就是一片風險四伏的駭人環境,我們到了那裡就要被凍僵、燒焦,終至沸騰喪命。然而,我們的周遭大氣,卻提供那麼周延的防護,甚至讓我們對那些凶險都懵然無知。這就是基廷格那次飛行帶來的訊息,也是所有探測地球大氣的先驅人物留給我們的啟示:我們不只是住在大氣中。我們的生命都是拜它所賜。
南極天空
南極洲在二十世紀五○年代還是個險峻的地方,但那裡的研究站,恐怕沒有幾處比英國南極調查署(British Antarctic Survey)設於郝利灣(Halley Bay)最偏遠的前哨站更為艱困險要。郝利灣基地設於一片冰架,和南極點相距約一千六百公里。那裡的溫度從未提昇超過冰點,冬季時還可能陡降低達攝氏零下四十六度。還有個更嚴重的問題,那就是風。強風狂嚎席捲平坦冰架,颺起積雪刮出陣陣雪暴,帶走大量體溫,還把第一批強悍小木屋掩埋到只露出屋頂圁。
郝利灣的古老傳統在世界其他地區早就式微,然而在這裡卻依舊盛行。那裡的男人蓄留山羊鬍子,講的是只適用於南極的晦澀俚語和粗魯幽默。那裡有拉雪橇的狗群,極目四望只見一片平坦的荒涼雪地。那裡沒有溫柔,沒有安逸,也沒有女人圂。
約瑟.法曼(Joe Farman)是個老派英國人,生性沈靜,常叼根菸斗。自一九五七年以來,他就在這處嚴峻前哨站主持研究。每年,在南半球春夏兩季,英國南極調查署的科學家便跋涉前往郝利灣,測量頭頂高空的臭氧含量。 為什麼測量臭氧?為什麼去那裡?最早是想要利用臭氧動態來測繪上層大氣的氣流,到了二十世紀七○年代,莫利納和羅蘭的氯氟烴發現進一步刺激這項研究,提供了更多推力。不過沒關係,反正法曼遲早還是會做完研究。雖然測量有趣的大氣成分並留下長期紀錄,最後往往能發揮高度用途,但整理紀錄通常不是一件討好的工作,而整理的人通常無從曉得這時下的功夫到底能成就什麼。法曼做這項計畫沒有拿到很多錢,不過成本也沒那麼高,而且總是有充分志願人手來進行測量。
一九八四年年初,法曼的撥款單位老闆來訪,又一次問他,為什麼那麼固執、堅持記錄那種冷門資料。法曼回答:「氯氟烴產業的規模很大,還有人寫文章說臭氧正在改變。所以只有坐在這裡不斷測量,才能看出臭氧是不是真的改變了。」他的老闆回答:「你這些測量結果只能留給後代。那你告訴我,後代對你能有什麼貢獻?」
法曼關於氯氟烴的說詞有些不老實,有個祕密正在他心頭醞釀,他私藏這個機密已經三年。但是同一年稍後,他決定對外透露。剛開始法曼不怎麼相信這組經年累月記載的長串測量數值,它們顯得有些古怪。從冬季黑暗月份到陽光再次照耀之間,郝利灣的臭氧總是有些微變動。不過,從一九七七年開始,情況出現變化。每年在十月初春階段,臭氧會急遽減量。這種驟減情況一年年惡化。一九八三年,法曼依照常態趨勢預期臭氧含量應達三百單位,結果他所見讀數還不到兩百單位。
剛開始,法曼和另外兩位同事都保持緘默。他們不想被世人當做傻子。過去五年期間,美國航太總署有一顆衛星持續對南極上空全面測量臭氧,也始終沒有注意到任何差錯。或許是法曼和他的團隊使用的儀器古怪,也或許是郝利灣本身就有點古怪。所以從一九八三到八四年那個季節,法曼運了一件新儀器到郝利灣。他還檢視了另一個英國研究站的紀錄,那個基地位於更偏北超過一千六百公里的阿根廷群島(Argentine Islands),根據這兩處研究站的資料可以確認郝利灣的紀錄正確無誤。這時每當南半球進入春天,臭氧都要消失百分之四十。天上有個破洞。
當法曼看出這點,便把他的英國式審慎態度拋到九霄雲外。他和兩位同事合著一篇論文投遞到《自然》雜誌,在聖誕夜送達雜誌社,並於一九八五年五月刊出。莫利納和羅蘭的文章幾乎沒有激起絲毫即時效應,法曼卻掀起一場騷動。其中最感驚愕的是唐納德.希斯(Donald Heath)的研究團隊。希斯研究團隊隸屬航太總署戈達德太空飛行中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負責協調該署雨雲七號(Nimbus-7)衛星的臭氧測量任務。他們從資料看不出破洞。法曼團隊在講什麼啊?
希斯團隊匆匆調出他們的資料重新核對。結果令他們羞赧難堪。按照資料回復程式的設計功能,所有亂真數值都會先被剔除,研究員檢視結果時根本看不到,這樣才不會受到惱人的測量誤差干擾。凡是落於一百八十以下的臭氧測量值,顯然都很荒謬,於是就這樣被倒進陰溝。衛星確實看到法曼的臭氧破洞,但因為他們熱心過頭的程式,研究人員什麼都沒看到。這時他們使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的正確資料,看出南極上空出現了一個美國本土大小的破洞。就某些情況而言,臭氧含量還減至一百五十單位以下。
希斯團隊學到一個地球大氣方面的重要教訓。就算你信心滿滿、自詡通曉空氣汪洋的運作方式,最好還是要有心理準備,你隨時有可能面對始料未及的情況埌。 同時,臭氧研究學界方寸大亂。連莫利納和羅蘭的最悲觀論述都沒有料到這等極端慘況,還這麼快就應驗。沒有絲毫跡象顯示全球其他區域有這種破洞,所以這肯定和南極洲的極端環境有關。但那是什麼因素呢?
全世界各大學的研究實驗室和咖啡區,討論焦點開始向南極平流層的第一項特點,也是最顯眼的特徵匯聚:那是地球上空最孤立的大氣區域。每年冬季四方風起,沿著那片冰封大陸邊緣吹襲,最後構成一圈巨大渦旋,氣牆區隔開南極空氣和偏北空域有微風吹拂的較暖大氣,南極空氣被這圈龐大旋風陷捕,溫度穩定下降、愈來愈冷。接下來,南極洲上空就出現了一個新式雲種。
普通的雲都是由液態水滴構成,也得以在對流層幾乎所有高度形成。對流層是地球大氣的最底層,也就是我們體驗風霜雨雪的生活範圍。當你穿過這層大氣逐漸攀升,氣溫也穩定下降,一直到對流層最高處溫度降到最低點。超越這點,緊接著就是平流層。這裡有臭氧分子攔下陽光並暖化空氣,於是氣溫開始提昇。這兩層大氣之間的極冷點,會陷捕所有水汽並轉為雲朵、化為雨水落回地表。這是一道密不透水的屏障,就像一疋壯闊防水布延伸環繞全球,讓底層大氣保持濕潤,上層大氣則完全乾燥。因此平流層幾乎從不出現雲朵。
然而,平流層仍有些許水分從底層滲漏上來,而且當氣溫夠低,水分會凝固成微細冰粒。南極平流層在冬季就會發生這種現象。
這種雲朵很漂亮,散發鮑殼內側那種彩虹光澤,展現種種不該在天空見到的桃紅、紫色和璨藍色彩。到了春天,極地長夜過去,太陽重回天空,這時彷彿無中生有,冰粒在日出或日落時分憑空出現。其實,雲朵始終都在那裡,不過要等到太陽逆轉地平線的明暗兩側,才能勾勒出雲朵的身影,這時的陽光就像一盞聚光燈,以最後一道陡峭光束照耀雲層。接著,天空突然閃現光輝,就像灑滿了孔雀羽毛。早期探險家以細膩水彩創作來表現那種效果。他們全沒料到,後來那會變得多麼危險。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大氣:萬物的起源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3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26 |
二手中文書 |
$ 284 |
自然科學 |
$ 284 |
氣候/氣象 |
$ 306 |
科學科普 |
$ 317 |
中文書 |
$ 317 |
天文/地球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大氣:萬物的起源
認識大氣科學的第一本書!
隨著全球氣候劇烈變化、生態環境面臨危機、冰山漸漸消融,大氣科學成為和我們最切身相關的學科。本書帶你一窺大氣科學研究的歷史和全貌,總覽你我必備的大氣基礎知識。
空氣不只讓我們呼吸,還發揮奇妙作用、轉變為觸摸得到的食物,若非如此,地球上的生物全都無法活命;大氣包覆地球,構成一席保溫毯;飄懸高空的金屬構成一面鏡子,無線電信號才得以反射傳遍世界;地球的外層大氣保護我們免受太陽閃燄摧殘,那種日面磁爆威力猛烈,把全世界的核子彈頭全部擺在一起都相形遜色。沃爾克以生花妙筆寫成這本著作,抽絲剝繭介紹地球層層大氣,講述發現氣層祕密的人物事跡。
一位浮誇的文藝復興義大利人,發現空氣出乎意料地沉重:好比卡內基音樂廳內所含空氣,重達三萬兩千公斤。
一位獨眼特技飛行家,發現空中有一股颶風般強勁的空氣洪流,在八公里高空洶湧奔騰。
一位貧困美國農夫,用乾草叉在穀倉門板上刻寫方程式,構思出暴風迴旋繞行的原因。
一位用意良善卻命運多舛的發明家,製造出奇妙的化學物質,結果險些把臭氧層給毀掉(他還構思出一個點子,把鉛擺進汽油)。
一位隱居鄉間,偏愛把腳趾甲塗成櫻桃紅色的數學奇才,設想出一項科技成果,讓鐵達尼號的乘客獲救生還。
《大氣:萬物的起源》是頌揚地球大氣的精彩著述,也是讀來不忍釋手的科普力作。
章節試閱
前言一九六○年八月十六日上午七點約瑟夫.基廷格(Joe Kittinger)高懸在新墨西哥州上方三十多公里空中。十一分鐘過去了,他在吊艙裡面蓄勢待發。那是個開放式吊艙,掛在一顆龐大氦氣球底下緩慢旋轉。儘管太陽早就升起,周圍大氣依舊黝黑猶如午夜。遙望下方,地球的彎曲表面朝遠方延伸,構成一弧地平線,映襯漆黑太空、綻現一圈藍色光暈。 這道光圈就是大氣,地球擁有最寶貴的禮贈。地球的璨藍色澤不是得自海洋,而是染自天空。凡是見過那道細膩光暈的太空人,返航之後都會告訴我們:他們不敢相信,那讓地球顯得多麼嬌弱,卻又無比美麗。...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嘉貝麗.沃爾克
- 出版社: 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08-08-07 ISBN/ISSN:9789866571152
-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384頁
- 類別: 中文書> 科學> 天文/地球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