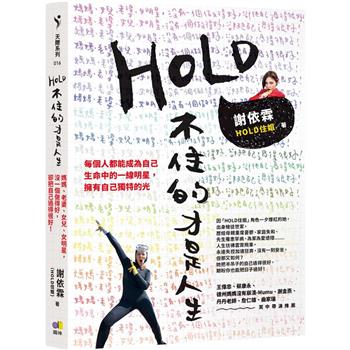瞭解小說藝術奧祕,從事小說寫作、文學批評與賞析者的必讀經典。
本書共分九章,就小說的七個層面:故事、人物、情節、幻想、預言、圖式、節奏,以作者細膩的觀察,優美與洗鍊的筆調,分析並探討小說的內容。佛斯特認為,小說家的任務即是熟練地駕馭這些面向,做到「面面俱到」,而小說家的功力,就表現在他是否有能力涵容並調節這些面向。
作者簡介
愛德華.摩根.佛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1879-1970)
一八七九年一月一日生於倫敦。自小由寡母和姨婆扶養長大。一九○一年自劍橋大學畢業,接下來的十年,在海外遊歷,先後住過印度、義大利和其他國家。這些異國經驗,為佛斯特的小說提供豐富的素材。
佛斯特曾參與過一個由作家、藝術家和知識份子組成的人文社團──「布倫斯伯利社」(Bloomsbury Group),其中的成員都是熠熠閃耀的藝文人士,包括:維吉妮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音樂家班傑明.布瑞頓(Benjamin Britten)、評論家羅傑.佛萊 (Roger Fry)和麥卡錫(Desmond MacCarthy)、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布倫斯伯利社」是知識份子的泉源,也為年輕小說家提供文化刺激。
佛斯特的作品包括許多短篇小說與六本長篇小說:《天使裹足之處》(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1905)、《最長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 , 1907)、《窗外有藍天》(A Room with a View, 1908)、《霍華德莊園》(Howards End,又譯《此情可問天》,1910)、《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 1924)、《墨利斯的情人》(Maurice, 1971)等。其中《印度之旅》備受肯定,被譽為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小說之一,該書出版後,佛斯特將重心轉向講學與文學評論,一九二七年他應邀到劍橋大學主持克拉克講座,這一系列演講成為他最受歡迎之論文集《小說面面觀》的基礎。
一九四六年,佛斯特接受劍橋大橋研究員一職,此後,他一直待在劍橋,直到一九七○年過世為止。
譯者簡介
蘇希亞
政治大學新聞系碩士。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人社系博士班。譯有《不得立法侵犯》、《世界宗教理念史卷二》、《人,生而平等》、《粉紅色童話》、《貪瀆者》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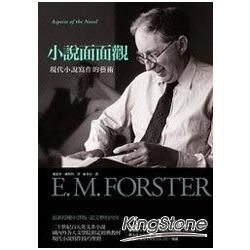
 2009/10/26
2009/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