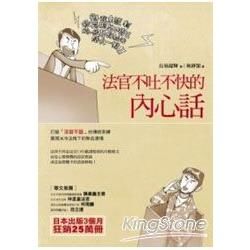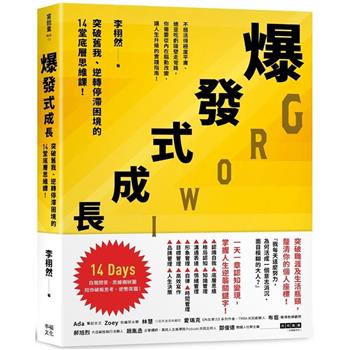【推薦序】
法官不語?
文∕新聞評論人 范立達
端坐在審判席上的法官,要如何面對台下的被告?該疾言厲色的狠狠痛斥被告一番,最後卻以「被告也從此次事件得到教訓,相信應無再犯之虞」而予以輕判?還是面無表情、不苟言笑的按著程序指揮訴訟,卻在宣判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痛下殺著,判處連旁聽席上民眾都駭然的重刑?
法官如何在一念之間決定被告的生死、罪刑的有無及輕重?手握一份充滿文言文及法律術語的判決書,除非受過嚴格的法律專業訓練,否則,真沒幾個人讀得通。但是,拿著判決書問法官,意欲探求真意時,常常接獲的回答卻又是,「法官不語」、「法官要表達的意見全都呈現在判決書上。」
法官不語。這是司法界的傳統,是司法界的鐵律。
法官的意見全都呈現在判決書上。但,真的呈現了嗎?判決書真能精準的傳達法官的心聲嗎?
早年,民智未開,人民多半不知道可以透過訴訟程序保障自身權益。也因此,當年法官承辦的案件量,或許不多。若以為如此,法官就能好整以暇的撰寫判決書,那就錯了。因為,早年科技相對不發達,法官撰寫判決書,須用毛筆一字一字書寫,因此,於能夠言簡義賅之處,法官絕不贅言。到了現今,法官利用電腦,透過「全選」、「複製」、「貼上」的三步驟,很容易就能完成一本厚達上百頁的判決書,但或許剪剪貼貼的功夫多了,真正肯花心思把個人推理的過程都展現在判決書上的法官,反倒不見了。更何況,現在法官承辦案件量之大,令人驚駭。法官忙到過勞死,亦時有所聞。除了極少數幾位精力過人的法官,願意天天挑燈夜戰,耗盡生命在撰寫判決書上,將個人對案件的認知及邏輯推演一五一十的紀錄下來外,其餘絕大多數的法官們,僅將犯罪事實、構成要件及適用法條臚列出來,就已經算是功德圓滿了。在法官都幾乎已經淪為「結案機器」的悲慘環境下,期待出現一份擲地有聲、震古鑠金的判決書,似乎是痴人說夢。判決書,哪能充分反映法官的想法?
法官的真意,不能求諸判決書,那就只好聆聽法官在審判中的一言一語了。
的確如此。特別是近幾年來,對於法官在審判席上必須「法相莊嚴」的要求,已不再像早年那麼的講究了。偶然間,的確可以聽到法官在審判席上發出正義的怒吼。例如說,承辦力霸掏空案的台北地方法院庭長李英豪,他在庭訊時,就曾對著一干金管會官員痛斥「公權力就是這樣被你們玩完的!」、「要這些公務員幹什麼!」這麼正義?然的激烈言詞,真令人耳目一新呢!甚至有人聽了之後說道:「看來,台灣的司法還是有希望的……」
那麼,日本的法官呢?
閱讀本書即可發現,喜歡「一鳴驚人」的日本法官,好像也還不少。而日本法官的這些話語,也確能發人深省。
例如,法官在爭扎著要不要判殺人犯死刑時,就忍不住脫口而出:「犯人殺人很簡單,但是,國家要做出死刑的判決,卻是件很嚴重的事。」這種心態,歐陽修在「瀧岡阡表」一文亦曾道盡:「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對生命,應該尊重。法官要判決一名被告死刑,當然更加慎重。但每天上演的交通事故,卻往往如此輕易的就奪去了被害人寶貴的性命。難怪法官要嘆曰:「在交通事故審判中被害者生命的重量,就像車站前分發的面紙包一樣輕。」
此外,面對冥頑不靈、甚至是喪心病狂,犯後毫無悔意的罪犯,法官不該痛斥嗎?「狗糞尚且能做肥料,難道你們不是比產業廢棄物還糟的無用之物嗎?」、「你已踏進禽獸之道了。既然是人類,就早點回歸人類之道!」對被告這麼精彩強烈且淋瀝盡致的抨擊,聞者只怕都要鼓掌叫好吧!
的確,法官應該是滿腔熱血的,充滿正義的,除了在法律容許的範圍內,妥適的斟酌如何適用法律,並決定量刑輕重外,法官對於案件以及牽涉其中的人與事,不該無動於衷。要求法官按照證據、法條,冰冷冷的作出裁判,而不在裁判以外吐露一言一語,這樣的人,我以為他不是法官,而是法匠。
這本書的專欄的部分,也很有意思。例如,有一篇專欄文章的標題是「自己的事,卻自稱『法院』喲!」的確如此,以我之前採訪司法新聞的親身體驗,在審判庭裡,常常聽到法官說:「法院現在問你……」、「法院要調查的是……」當時,我就很狐疑,為什麼法官問話時不說「我」或「法官」,而要自稱「法院」呢?當然,後來我對此疑點獲得了解答。倘若讀者仍不明暸,就可以看書中是怎麼說的了。
另一篇專欄「檢察官決定審判的國家?」文中提到,日本檢察官起訴的定罪率高達99.92%,這樣的數字,似乎凸顯了日本檢察官起訴的精確性(文中稱為「精密司法」)。但作者擔心的是,這種制度會不會成為「有罪至上主義」,若然,審判會不會變成徒具形式?「公正的審理」這個刑事審判制度的根幹,會否受到動搖?
作者的質疑,亦是我心中最大的疑問。我國司法實務界對於檢察官考評的依據之一,竟是「定罪率」及「折服率」,這不免令人憂心,檢察官對於起訴卻被判無罪的案件,之所以一再上訴,始終不鬆手,會不會是為了怕自身的考績受影響,所以明知理虧卻仍然一再死纏爛打?如果真是如此,那麼,真要問,纏訟於其間,清白卻致訟累的人何辜呢?二○○九年四月間,監察委員李復甸公布「第一銀行押匯弊案」的調查報告時即直言,「本案歷經更十二審,自六十八年起,於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三名被告無罪定讞,共計二十七個審級歷時二十八年半,耗費司法資源,枉顧當事人之司法人權」、「依現行監察法之規定,對於司法院審判工作並非監察權得以糾正,惟罔顧司法人權,侵害當事人基本人權,自應予嚴正譴責,以儆來茲。」李委員所直指的,不正是司法積弊的核心嗎?
不過,對日文或司法實務不是那麼熟稔的讀者,閱讀本書時,可能會覺得有些門檻。另外,由於本書提到的都是發生於日本的實際案例,但絕大多數案例的來龍去脈,在台灣的讀者可以說是全然不知的,僅從作者簡略的描述中,其實很難讓讀者快速進入法官不吐不快時的情境,因此,要在閱讀時立即產生感同身受的體驗,似乎也沒有那麼容易。
但無論如何,一本不是以判決書內容為主,卻是以紀錄法官在庭上的珠璣為重點的法律書,倒也罕見。透過這本書,讀者應可發現,法官,雖然時時刻刻在扮演神的工作,但終究,他們都還是人,還是存在著七情六慾。在審判席上,法官有時刻意,有時脫口而出的話語,其實仍有很多發人深省之處。
終究,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引自霍姆斯言)
【前言】
知道佐田雅志的《贖罪》嗎?
「有點唐突,但你們應該聽過佐田雅志的《贖罪》這首歌吧!這首歌,就算只讀歌詞,便可了解為什麼你們的反省答辯,無法打動人心了。」
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東京地方法院的山室惠審判長,向兩個因傷害致死嫌疑而遭起訴的少年宣判了「三年到五年」的不定期徒刑。少年們如果早點表現出改惡向善的樣子,三年後便可提早出獄,但仍然是個不折不扣的實刑判決。
執拗地折磨酩酊大醉之人的犯行狀態,是非常惡質的。儘管被害人這一方也有一定的過失,但卻不足以構成被告奪取他人生命的理由。......宣讀完畢以前述內容為主旨的判決理由後,山室審判官開口所說的就是一開始的那段話。
「你們這些傢伙,好好地向我道歉!連個對不起也不會說嗎?」
深夜的地下鐵車內響徹男人的聲音。怒吼的對象,是四個十八歲的少年。遊玩了好一陣子直到深夜的他們,當在東急田園都市線.涉谷站乘車之際,就在那時候碰觸到了某個人的身體,亦即牧顯先生的腳尖。
「踩到腳啦!安靜點!」
四個人並沒有顯露厭惡的樣子,依舊興致勃勃地聊天,把牧先生的話當作耳邊風。
那一夜,牧先生以酒醉的狀態回家。原本的性格就很討厭不合理事情,一旦酒醉,天生的正義感受到了增幅作用。據說,他曾在小酒館內,因為注意到某個態度惡劣的客人的強烈語氣,而引起對方極度不滿。
在涉谷的下兩站的三軒茶屋站,牧先生一度下了月台。可是,或許到那時為止所蓄積的不滿,已到達了臨界點,突然間他回過身來,兩手按著已經關起來的車門,對著車內的少年,又大聲吼叫。
接下來的一瞬間,車門開了。可能是因為車掌以為牧先生還要搭車,所以就按了「開」的按鍵吧。於是,四個人影走下月台,將牧先生包圍起來。
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凌晨十二點十分,三軒茶屋站發生暴行事件。警視廳世田谷署將逃亡中的四人做成全身畫像,要求人們提供情報。警官在涉谷站周邊散發的傳單,好像超過了一萬張以上。
五月四日的早晨,牧先生死於那個收容他的醫院中,享年四十三歲。死因是頭部外傷引起的蜘蛛膜下出血。
在神奈川縣警相模原署與警視廳町田署,各自出現兩名少年的身影,是同一天晚上的事。據說,四個人因為看電視報導而知道牧先生死亡,進而互相聯絡,商量妥當而出面自首。
「是我做的......」
對著出現在相模原署,嘴裡咕咕嚕嚕的無職少年,警官詢問說:「做了什麼呢?」可是,除了前面那句話,就再也沒了。沒有辦法之下,說出「是三軒茶屋那件事」以及實情的卻是跟著一起來的父親。
少年四人當中,對牧先生又踢又打暴力相向的那兩人,基於情節重大,所以不在家庭裁判所,而改在地方法院的公開法庭中進行審理。其餘兩人,因為對另兩人的暴行「只是觀看而已」,由於罪嫌不足,所以當時便釋放了。
在東京地院的刑事法庭中,「非常對不起」「反省中」「深感抱歉」等,被告的少年只顧地重複這些謝罪的言詞。可是,他們的態度卻是淡淡的,實在讓人無法感覺到他們真正接受了「奪走人命的嚴重性」這樣的事實。
一開頭的「佐田雅志的說諭」,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出來的東西。審判官具體地舉出歌曲名稱來教誨被告,這倒是個異例,因此,這件事在電視和新聞上也都成了話題。
「因為以法律來裁判人的心,是有其限制的......」佐田先生聽到判決後說了這句話。
判決的隔天,在東京看守所裡的少年,接到了一封信。寄信人是叔母。偶然發現自己的CD中收錄了《贖罪》這首歌,於是抄錄下來寄給他。
而來探望的母親說:「事情從現在才開始吧。即使經年累月,拼命地努力,如果不能展現誠意給遺族看,也是沒用的。請求別人的原諒,不是那麼容易的。」少年回答說:「我知道。」少年們並未提出上訴,因此實刑判決就確定了。
歌詞來自真實故事的《贖罪》,是敘述交通事故的肇事者,犧牲自己的幸福與興趣,以必死的決心去賺錢,從不間斷地每個月把錢寄給受害人的太太的一首歌。
審判官只應該說「法律的聲音」嗎?
倘若追根究底的話,法律這種東西的結構,除了「數位式」以外無他。亦即「有」或「無」兩項對立的組合。
當完全滿足法律條文所寫的「要件」時,即所有的「開關」都在「開」時,訴訟才能成立。未能滿足「要件」,即使只是一個「開關」置於「關」上面,訴訟就會遭退回,就是這樣而已。
儘管也有些條文,在任何階段都有許多開關而讓人看起來覺得很困難,可是,原理是很單純的。其實法律這種東西,單純是有其必要的。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到底哪個違法,哪個合法,便不能給予明確的答案了。
對於任何人,都能平等又明快地回答、不傾向過於瑣碎的考量、融通性低,這些都是法律的宿命。如同使用砍切銳利但又長又重的日本武士刀,在小黃瓜或紅蘿蔔上雕刻花樣,確實會讓人產生不耐煩的感覺,而日本的審判,製造了大量乾燥無味的判決書,這簡直把當事者當成了木頭雕像,所以類似這類的批評,也就是從這個地方產生出來的。
然而,在這個數位式的法律結論之中,偶爾也會有類比式的表情出現。這就是法官的話語。原則上,雖然法官被當作「只應該說法律的聲音」,可是,在法庭中偶而也可以聽到法官自然的聲音。當個人的感情無法壓抑時,不知不覺地就流露出真心話來,正如同一開頭的山室法官一樣,特意借用能與人心直接產生共鳴的「歌詞」和「名言」,這樣的事也是有的。
本書試著收集像這種平常不太容易聽到的法官的發言。除了在新聞媒體等所報導的東西之外,也包含我在旁聽審判時所聽到的一些印象深刻的話語。
爆笑、苦笑.失笑或者感動落淚,有時候憤慨......對於這一個個
的說辭,想必每位讀者抱著各自不同的看法吧。以「很意外地像法官這類人也會說出這麼有趣的話」這種輕鬆態度來欣賞,當然是無妨的。此外,「使用法律這個工具,讓人來裁判人」這是怎麼一回事?民主主義國家的審判應該如何才是?將來如果自己成為審判人員將如何行動?對以上這些事情,若能驅策讀者做些許的思考,真是身為作者莫上的榮幸。
能聽到審判官的訊息的機會
在公開的場合,能夠聽到來自法官的貴重口信的機會,就在以下所列的狀況下。
【補充質問】
審判進行中,檢察側與辯護側從各自的立場,向在證人席的證人與被告人提出質問,即使問了一陣子話以後,當覺得「想聽得更多」之時,法官就會提出這種質問。
有時候,與其說是質問,也會出現只是對被告人的助言或者說教的言語,然而許多人來旁聽審判,正是以此為目地的。
【判決理由】
判決書中,敘述如何到達主文(例如刑事事件,則是有罪無罪。有罪的時候,則加上相關的刑罰)之結論的理由。從證據及證言等,認定什麼樣的事實,根據什麼樣的法律條文,而導出這個結論,雖然判決書上顯示出這些東西,但偶爾在某些地方,也會出現法官們各自具有特徵的文辭使用法和價值觀。這一部分也是很有魅力的。
【附言.感想.旁論】
多數在判決理由的結尾部分,會有來自法官向社會的建議等。尤其雖然沒有強制力,但也有因為遵循這個附言,而使國家和地方自治體加速行動的事例。
例如,有關通過未加熱處理的血液製劑為媒介,主要在白血病與肝炎患者之間擴散的「藥害HIV問題」的故事。一九九六年一月,就任厚生大臣的菅直人眾議院議員,徹底地揭發足以顯示行政疏失的資料,同時因為向犧牲者的遺照下跪謝罪等事,而獲得了處理迅速的評價。據說,一九九五年的十月,當東京地院與大阪地院共同提出藥害HIV訴訟的和解案之時,在所附的「所見」之中,曾嚴厲指責國家對處理此事的遲緩,因而促成情況的改變。
【說諭】
以刑事.少年事件為對象。審判時,在讀完主文與判決理由之後,另行對被告的將來給予些許的勸告。開頭的「佐田說諭」就相當於這個。
這決不是法官一時興起的發言,而是在刑事訴訟規則二二一條中規定的、受到尊重的法令行為。原本正式的名稱叫做「訓誡」,然而在本書中,則採用一般習慣的媒體用語──「說諭」。
【休庭後的行為】
法官在宣布休庭之後,在法庭上非正式的事情。這或許是一時興起。
【其他(法庭之外)】
法院的代表人(長官.所長),以司法記者俱樂部為對象所舉行的記者會。也有「犯罪遭逮捕的審判官,對於警察.檢察官的調查所供述的筆錄」之類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