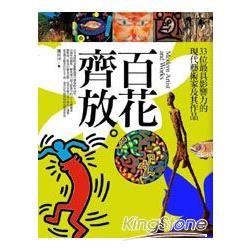第一個進入現代地獄的人
孟克 Edvard Munnch 1863-1944
愛德華.孟克似乎提供了一些末世般的圖像,他將梵谷和高更的色彩表現推向更為廣闊的境界。孟克的色彩,和心理節奏、心理事實聯繫得極為緊密,往往指涉那些神經質、陰暗的事物。但是,孟克並非刻意去尋求矛盾、分裂事物的普遍性,而這普遍性是從那些具濃郁自傳色彩的作品中所輻射出來的。
孟克個人,使我們清晰地瞭解到他困惑的心理現實,然而,這種個人困惑的心理,在 19 世紀末的歐洲卻明顯地被大家所接受。早在 1890 年代,歐洲各種新思潮風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尼采的超人思想、齊克果的存在主義學說等,都在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孟克的價值觀。
孟克的繪畫介入黏質的情感因素,因而使他更傾向於描繪焦慮、抑鬱的色彩和形象,而這些色彩和形象也相應地具備某種精神分析的特質——它們對稱於孟克陰晦的內在世界。他的繪畫,自始至終(晚年有所變化)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潮濕的「溫度」,這種「溫度」以低沈、焦灼的呼吸,在視覺上強烈地吸引觀者的注意力,並使人很容易陷入進去,因為它也對稱於我們敏感的、共通的心理結構。
孟克曾說過:
我要描寫的,是那種觸動我心靈之眼的線條和色彩。我不是畫我所見到的東西,而是畫我所經歷的東西。我絕不描繪男人們看書、女人們織毛線之類的室內畫。我一定要描繪有呼吸、有感覺,並在痛苦和愛情中生活的人們。
孟克的繪畫,也從另一方面揭示其「經歷」與作品主題之間的必然關係。他告訴我們,「要熱愛自己的經歷,而不要害怕它」。孟克的藝術邏輯,與他的家庭背景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來說,個人命運決定了畫家的藝術性格和基本質地。孟克的個人史和繪畫史幾乎是一體的,「我的家庭是疾病與死亡的家庭,的確,我未能戰勝這種厄運。這對我的藝術產生決定性的影響。」1863 年,孟克出生在挪威洛滕的一個名門望族,家庭成員多是政界或軍界要員。
祖父是一名頗具聲望的神職人員,父親是軍醫,伯父為歷史學家。孟克的母親在他5歲時因病去世,他15歲時,姐姐蘇菲亞又死於肺病,他自己從小也體弱多病。孟克成年後,父親和一個弟弟又相繼離世。因此,孟克繪畫中的情感成分,常常建立在對童年和少年時代的記憶中。
16 歲時,孟克聽從父親的意旨,進入技術學校學工程;後來進入奧斯陸的工藝美術學校,受教於挪威畫家克魯格。克魯格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又是歐洲現代主義藝術的提倡者,孟克的早期作品《病童》就受其作品主題的影響。1884 年,孟克與奧斯陸現代派藝術家結識,翌年,獲國家獎學金赴法國學習。
評論家約翰.拉塞爾認為,孟克能夠以一種既不誇張也不自憐的方式,和我們一起分享他的生命經歷,他還賦予這些經歷普遍的含義(一位後來的畫家——奧斯卡.柯克西卡說過,孟克是第一個進入「現代地獄」,並回來告訴我們地獄情況的人)。
繪畫之於孟克,如同戲劇之於史特林堡,其意義是:「一部貧民的《聖經》,或圖畫中的《聖經》。」他可能說過,史特林堡也可能說過:「在殘酷而激烈的鬥爭中,我們找到了生活的樂趣。」
即在宣洩由鬥爭產生的巨大精神能量中,找到了生活的樂趣。在處理這些「殘酷而激烈的鬥爭」時,孟克就像在做愛行為中的人體那樣,一絲不掛,他也讓感情赤裸裸地表現於作品之中。
在孟克的作品中,關於「殘酷而激烈的鬥爭」的部份—— 疾病、死亡、性吸引、暴力,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其餘則是關於自然風景、人物肖像、自畫像等,較為平和輕鬆的日常事物。自畫像也是作者一種「殘酷而激烈的鬥爭」的分泌物。孟克總是把自己的形象置於一個受難者的角色,這個角色始終保持著自省、清醒的承受力。
孟克 23 歲時開始畫《病童》,這是畫家1885年間第一幅有一貫性主題的作品。
無疑地,這幅畫在形式與內容上,都源自於他個人的早年經歷,這是孟克自傳式畫作的開端。孟克這類自傳式的作品,是受到19世紀80年代風行於奧斯陸的波希米亞運動的影響,這一運動主要在於回應作家漢斯.耶格爾的呼籲——寫下你的生活。
在挪威,如果誰背離了自然主義者所主張的解剖學精確法則,或違反幻想主義者那種纖毫畢見的精密畫法,那他的作品既不被視為初學者的弱點,也不被認為具有藝術含義,毫無疑問地,會被斷定為惡意破壞善良風俗。這種認為他的畫作粗劣不堪的責難,實際上就是批評他這個人是懶散的、易變的、膚淺的,簡言之,就是:無能的。這類責難,糾纏孟克達10年之久。
《病童》一開始,就沒有逃脫這類的責難。
《病童》與其說是關於疾病的記憶,倒不如說是針對死亡的一種注視。畫中的少女,坐在母親的身旁,母親低下頭,看不清臉龐,她的手握著少女的手,少女的頭斜側,目光沒有具體地看什麼東西,更像「瞳孔向後縮了回去」,臉部的表情麻木、空洞,手和臉蒼白,與自己和母親的衣服以及右側黑色的區域,形成強烈的反差。
在這幅《病童》中,孟克使「少女」這一形象負載了雙重意義:既是少女的現實,同時也是孟克的現實;既是疾病的現實,同時也是死亡的預言。童年和少年的經歷,使孟克對於這個主題一直保持著本能的鍾愛,或許是恐懼和記憶在有力地驅使他的這種行為。
大約每隔10年,孟克就會創作出不同的《病童》。畫家在此使用的繪畫方法,和挪威自然主義者所採用的傳統方式有所區別。他用抹布和畫筆的柄,把還是濕的或已完全乾了的色塊刮掉、擦磨、做凹痕、搗碎。這些刮過的地方遍及畫面,有的部分再塗上顏料,有的部分則保持原狀,造成一種具象徵意味的效果:那(幅畫)碎裂的肌膚,原是屬於一個具有特殊造型(圖畫)的身體。
孟克在一次又一次的色彩和筆觸的試驗中,尋找和接近他曾經認識的死亡經驗。孟克以為它顯得太過於蒼白、也太過於灰暗了,看起來有如鉛一般地沈重。《病童》透顯出一種衰弱、失敗的臨界點,這個臨界點卻以它相反的跡象來表明孟克背負的疾病痛苦——沈重有力的基調和極力克制的情感。
在孟克的一生中,《病童》是一個揮之不去的記憶和精神深處的縮影,它是一條非常重要具有導航性的基準線,不斷拓展他後來更為開闊的心理和視覺圖像。孟克說:
我第一次看見那個滿頭紅髮的孩子病弱地靠在白色大枕頭上時,我立刻得到了一個印象,這個印象在我畫這幅畫時一直停留在我的腦際。我的畫布上呈現了一幅佳作,但卻不是我想要表達的。
這幅畫在一年之中我重複了好幾次,我把它刮掉,又重新塗上顏色,不斷尋找我的第一個印象——那透明而蒼白的皮膚,那嚅動的嘴,那顫抖的雙手。
嫉妒、欲望、性吸引、性壓抑和陰沈的暴力感等主題,都在孟克的繪畫中貫串始終。孟克的女人形象充斥著「邪惡的欲望」,女巫般的誘惑性:墮落伴隨著毀滅。不祥的女人彷彿控制著一切。
「波特萊爾在1857年的《惡之華》一書中,幾乎每一頁都打上了女性誘惑的印記,女人的誘惑作為一種基本要素,一種自然力量,是無法迴避、不能抑制的。」同樣的觀點也出現在「華格納的《帕西法爾》中昆德麗這個人物身上,滲透在杜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娜塔西婭.彼特羅夫娜這個人物的行動中」。
孟克並非迷戀於女性的誘惑和不祥的形象,在他的繪畫中,我們發現它們是某種被極度壓抑的心理所導致的一種釋放,除卻孟克對女人的整體認知,恐怕這些因素跟他早年陰晦的心理和精神狀態,密不可分。似乎只能在其畫作中,孟克才能夠更加成功地把握他筆下的女人形象。
而從相反的角度看,恰恰在現實生活中,他可能是個失敗者。因為在他的繪畫裡,女人墮落和邪惡的形象,是被現實擠壓出來的,他甚至用一種厭棄和批判的眼光來觀察女人,或者說,他企圖用誇張的色彩和扭曲的線條在畫布上去征服她們。
在孟克的觀念中,女人具有三重角色:處女、娼婦和修女。她們融為一體,集人類生命的神秘於一身,對男人來說,永遠是個謎。
1895年《女人的三個階段》(164 × 250㎝)這幅畫,就是這個觀念的最好例子。在孟克看來,女人是聖潔和墮落的混合物,她們的身體中可以分離出完全相反的特質,既矛盾又統一。孟克在此,將三種不同的女人形象,和困惑、迷茫的男人形象並置在一起,在一個幽暗、略帶恐懼感的環境中,一切都變成活生生的現實。誘惑和排斥的複雜心理,嚮往和懷疑的矛盾因素,永遠存在於男人和女人之間。性和欲望同樣依循本身的自然法則,含混、曖昧,既上升又下落,它們的本質和孟克關於女人的觀點是一致的,在「天堂」和「地獄」的辯證法中獲得一種平衡,一種於混亂當中整理出來的秩序。
1893 年,孟克畫了《吶喊》。
從這一年起,孟克開始了組畫《生命》的創作,以象徵和隱喻的手法,來解釋他的人生觀。「生命」、「愛情」、「死亡」是這一組畫的基本主題,《吶喊》則是這一系列中最為著名的作品。
孟克繪畫中具有典範式的「波浪狀」曲線,在《吶喊》裡,使其畫面的空間充滿了運動感。血紅的色彩、速度、透視所帶來的距離,以及騷動、緊張不安的氣氛,構成這幅作品濃郁的「悲劇」意識。主角的頭顱猶如一顆倒立的梨,更像是一個骷髏,發出刺耳的呼號,似乎他發現了天大的秘密。
《吶喊》中扭動的筆觸以及強烈的色調,對應於主角發出的聲音,好像是他的叫聲產生了畫面所呈現出的一切因素。畫面充斥著掙扎的聲音,這些視覺效果往往會造成觀者心理極度的不適應,並引起強烈的震動。它同樣有另外的作用:強迫性地使你陷入自省和沈思的環境。
我以為,這幅看似簡單的作品中的形象,可以被看做孟克繪畫中所有醜陋和淒慘形象的標誌,只不過,在其他作品中,醜陋的形象常常顯示迷茫、不安、壓抑和暗含暴力氣息的成分。《吶喊》在感情色彩上帶有作者的自傳性因素,它就是孟克變體的自畫像。這也就是在孟克繪畫中將個人情感推向普遍化的例子之一。即使在今天,這幅畫的意涵,仍適合於任何一個處於焦慮、彷徨心境的人。1908 年,孟克的精神分裂症病發,在丹麥哥本哈根的一間療養院接受治療。
病癒後,他回到挪威,過著一個人的生活。他在自己的院子裡弄了一個露天畫室,一年四季總在這裡作畫。老年的孟克,突然對大自然與勞動者的生活產生興趣。這一期間,他畫了許多關於礦工、建築工人、農場工人的勞動場面。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百花齊放:33 位最具影響力的現代藝術家及其作品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99 |
二手中文書 |
$ 315 |
藝術設計 |
$ 325 |
中文書 |
$ 326 |
藝術家 |
$ 333 |
藝術理論 |
$ 333 |
總論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百花齊放:33 位最具影響力的現代藝術家及其作品
以多角度的思維解讀現代藝術的多面性
以獨特的觀點,解析現代最具影響力的三十位藝術家
解碼康丁斯基的抽象思維、感受卡蘿自我分析的心跳聲
迫近傑克梅第的存在主義、漂浮於馬格利特的超現實世界
二十世紀以降的現代藝術家,創作往往出於哲學思維,他們的創作是個人與社會、宇宙萬物間的作戰與對話。有發自肺腑的吶喊,有沉痛的呼籲,有時是實驗,有時是遊戲。
社會事件深深地烙印在藝術家的作品中,現代藝術也塑造了今日的社會。作品中展露了人文思潮的演變、個人與社會間的對抗、人類自我挖掘的深度、人類對自我存在的省思。
認識現代藝術,是一趟現代人類自我認識的旅程。
不同於一般美術史的書寫方式,作者跳脫線性的時間軸,以長年浸淫於藝術史所澱積的私觀點,精選現代三十位最具影響力的畫家、雕塑家、行動藝術家,加以介紹。傑克梅第、培根、康丁斯基、盧梭、卡蘿、克利、高更、馬格利特……沒有一位不衝擊你的大腦,沒有一位不震撼你的心靈,沒有一位你可以忽視。
作者簡介:
魏尚河
1973年生,1995年於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裝飾藝術系學習裝飾繪畫。2002年與渣巴發起成立「histry」(他嘗試)藝術小組,histry拍攝影像作品《甘肅》。2003年《甘肅》參加北大在線新青年主辦的「京西何兮」展、「中國首屆紀錄影片交流周」。藝術評論散見《天涯》、《江蘇畫刊》等刊物。
章節試閱
第一個進入現代地獄的人
孟克 Edvard Munnch 1863-1944
愛德華.孟克似乎提供了一些末世般的圖像,他將梵谷和高更的色彩表現推向更為廣闊的境界。孟克的色彩,和心理節奏、心理事實聯繫得極為緊密,往往指涉那些神經質、陰暗的事物。但是,孟克並非刻意去尋求矛盾、分裂事物的普遍性,而這普遍性是從那些具濃郁自傳色彩的作品中所輻射出來的。
孟克個人,使我們清晰地瞭解到他困惑的心理現實,然而,這種個人困惑的心理,在 19 世紀末的歐洲卻明顯地被大家所接受。早在 1890 年代,歐洲各種新思潮風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尼采...
孟克 Edvard Munnch 1863-1944
愛德華.孟克似乎提供了一些末世般的圖像,他將梵谷和高更的色彩表現推向更為廣闊的境界。孟克的色彩,和心理節奏、心理事實聯繫得極為緊密,往往指涉那些神經質、陰暗的事物。但是,孟克並非刻意去尋求矛盾、分裂事物的普遍性,而這普遍性是從那些具濃郁自傳色彩的作品中所輻射出來的。
孟克個人,使我們清晰地瞭解到他困惑的心理現實,然而,這種個人困惑的心理,在 19 世紀末的歐洲卻明顯地被大家所接受。早在 1890 年代,歐洲各種新思潮風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尼采...
»看全部
作者序
在鄉村──代序
寫這樣一本書,比我預想的要困難得多。好些時候,有限的理解力就會被抽空,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是多麼的微弱。書中我喜愛的畫家、雕塑家和行為藝術家,他們有的影響了我,並改變著我。從某種角度來說,本書是向卓越的藝術家及其作品的致敬,也是一種自我清理。
當我嘗試著進入他們的作品時,我更加懂得了一個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所需要的耐心、不斷地自我折磨、專注的力量和無名的持久性。我努力接近繪畫的「語言」,而事實是當我開始寫作時,文體已經消失為零。我只好老老實實地去寫,盡可能寫得平實、準確、充分和深...
寫這樣一本書,比我預想的要困難得多。好些時候,有限的理解力就會被抽空,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是多麼的微弱。書中我喜愛的畫家、雕塑家和行為藝術家,他們有的影響了我,並改變著我。從某種角度來說,本書是向卓越的藝術家及其作品的致敬,也是一種自我清理。
當我嘗試著進入他們的作品時,我更加懂得了一個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所需要的耐心、不斷地自我折磨、專注的力量和無名的持久性。我努力接近繪畫的「語言」,而事實是當我開始寫作時,文體已經消失為零。我只好老老實實地去寫,盡可能寫得平實、準確、充分和深...
»看全部
目錄
在鄉村──代序
傑克梅第 ‧消失,出現
莫蘭迪 ‧最終之物
基佛 ‧廢墟下的悲劇和再生
紐曼 ‧呈現,自我呈現
培根 ‧培根的面孔很「荒誕」
馬哲威爾 ‧《西班牙共和國輓歌》
康丁斯基 ‧抽象的甦醒之路
波克 ‧繪畫實驗的魔術師
羅斯科 ‧元素,能量,內心的戲劇
波依斯 ‧死兔子和荒原狼
馬諦斯 ‧享樂主義者的色彩深淵
基亞 ‧雜交之後……
孟克 ‧第一個進入現代地獄的人
席勒 ‧徹底裸露的頹廢主張,與你對視
托馬斯 ‧對記憶的知覺
莫迪里亞尼 ‧適度誇張的繪畫程式
卡蘿 ‧畫筆下的自傳編年史
德.庫寧 ‧它很...
傑克梅第 ‧消失,出現
莫蘭迪 ‧最終之物
基佛 ‧廢墟下的悲劇和再生
紐曼 ‧呈現,自我呈現
培根 ‧培根的面孔很「荒誕」
馬哲威爾 ‧《西班牙共和國輓歌》
康丁斯基 ‧抽象的甦醒之路
波克 ‧繪畫實驗的魔術師
羅斯科 ‧元素,能量,內心的戲劇
波依斯 ‧死兔子和荒原狼
馬諦斯 ‧享樂主義者的色彩深淵
基亞 ‧雜交之後……
孟克 ‧第一個進入現代地獄的人
席勒 ‧徹底裸露的頹廢主張,與你對視
托馬斯 ‧對記憶的知覺
莫迪里亞尼 ‧適度誇張的繪畫程式
卡蘿 ‧畫筆下的自傳編年史
德.庫寧 ‧它很...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魏尚河
- 出版社: 華滋出版 出版日期:2012-05-23 ISBN/ISSN:978986662056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52頁
- 類別: 中文書> 傳記> 藝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