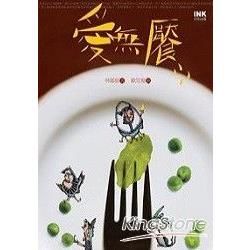說個故事給我聽…
和D交往了一陣子,激情逐漸平息下來。
從法國帶回來的惡習之一是開胃酒與小菜,真的遇上了對手,則不知開的是哪個胃口。我們在窗邊擺了個小咖啡桌,飯前常常兩個人開瓶酒對酌,配著醃橄欖、義大利香腸;奢侈點兒,我會叫他買瓶香檳帶來,慣有的菜色外再加上一盤鶯紅柳綠的水果,然後,坐在他腿上把草莓一顆顆送到他嘴裡,或是要他拿櫻桃餵我。兩人的眼神笑語在香檳泡沫之間交錯,情慾隨它盤旋上升,不須多時,那兩個香檳杯便冷落在桌上,而我們已經在床上繾綣。現在,他還能耐到吃完晚飯以後,兩人稍事休息,相敬如賓地推讓著浴室的使用權;等到所有的儀式都結束了,爵士音樂低低的旋律中,在彼此身畔躺下來。
感覺上像是泡了一會兒的茶,不再燙口,卻不失其甘醇。
就是這個時候,他開始要我說故事給他聽。我說你要聽什麼故事嘛!他說你是小說家,一定滿肚子的故事,說個我聽聽。我說我最會製造場景營釀氣氛,但是叫我編故事,一時編不出來。他說這樣好了,我給你提供一個故事,你來想細節:故事發生在巴比倫時代,巴比倫的公主愛上一個奴隸,要有懸疑刺激浪漫的情節。我先去洗澡讓你好好想一想,出來你再講給我聽。
我再怎麼想就是沒辦法把這故事的陳腔濫調轉化為神奇,自己也想不出更好的故事;最後,當他從浴室出來時,我拿了薄伽丘(Boccaccio)的《十日譚》(Decameron),開了床頭小燈,念了一個猥褻異色的故事,然後兩人在嬉鬧中做愛。可是《十日譚》大部分的故事都太長了,念完二十頁可能還要喝口水才能上床,而且並非隨時都是聽黃色笑話的心情;所以我們開始找情色小說裡的露骨描述,卡沙諾瓦回憶錄的片段,沙赫馬梭克(Sacher-Masoch)《毛皮大衣裡的維納斯》(Venus in Fur)哀愁的憧憬偏執作為睡前故事的題材。床頭那盞燈在入寢時分都是亮著的,不是我戲劇性就是他溫柔低沈的聲音,講著今晚的故事。
伊莎貝拉.阿言德(Isabel Allende)在《春膳》(Aphrodite)裡提到故事的確是很好的催情劑,還引用她小說的一幕烘托那情境。在那個場景裡,男女主角剛做過愛,正互相依偎著休息,男人告訴女人,他想起了以這個題材所作的一幅畫,而在畫中:
男人的眼睛閉著,一隻手放在胸膛,另一隻手在她大腿上,是一種親密的共犯關係。那個鏡頭是一再重演而不會改變的:男人臉上永遠是平靜的微笑,女人永遠那麼慵懶,床單的縐褶永遠一樣,房裡陰暗的角落,從同一個角度照著她胸部和頰骨的燈,以及永遠那麼纖巧滑落的披肩與黑髮,都是一樣的姿態。
我每次想到你,看到的就是這樣的你,看到的就是這樣的我們,永遠地凍結在那畫布上,超越於消褪的記憶。我會花上難以數計的時間想像我也在那幅畫裡,直到感覺自己進入那圖像的空間,不再是個觀察者,而是躺在女人身邊的男人。整個畫面的平衡就此被破壞,我耳邊也響起個聲音。
「說個故事給我聽。」我對著你說。
「說什麼故事?」
「說個你從來沒告訴過別人的故事。為我編一個故事。」
看到這兒,已經在我生命中完全消失的D突然又浮上心頭,那個原本在我消褪的記憶裡逐漸磨滅的面孔和笑容,再次無比清晰地出現在眼前。我終於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麼。始終沒有那個勇氣告訴他自己編的故事,希望呈現給他的永遠是個完美的形象,所以無法忍受一個平庸的故事。我因而永遠期待著某天那個完美的故事能自己出現,到那時我會多麼欣喜地與他分享,而在這之前,就讓我先告訴他別人編出來的完美故事吧!
於是,我這生註定不再有機會在枕邊低語著我為他編的故事。
而你,我的讀者,在這裡看到的是我所想像的,可以在曾有的寂靜夜裡,為他編出來的各式各樣的小故事。它們都不長,念完一個故事,熄了燈,還能有充分的時間與空間,在枕畔等著你的那個人懷裡,寫下另一個動人的故事。
〈Asparagus 蘆筍〉 從那時開始,她發現她的蘆筍必定在晚上消失,白天又安然無事回到冰箱的寶座…
A小姐滿心愉悅望著堆得滿坑滿谷的蘆筍,不管是晶瑩如玉的白蘆筍、鮮翠碧綠的青蘆筍、還是標新立異的紫蘆筍,那一根根從水盆裡探出來爭相向她打招呼的可愛頭兒,吱吱喳喳此起彼落地喧譁著,「買我吧,買我吧!」她倒覺得為難了,選哪個好呢?
即使是同樣的青蘆筍,也有細如鉛筆和粗如水管者。最後她選了粗的,倒不一定因為粗大便是美,只是純粹好奇,想知道這比台灣超市標榜的「原裝進口美國蘆筍」還大好幾倍的蘆筍,究竟是如何地美國原味。
她沒有趁鮮馬上烹煮。想起在台灣超市這種使土產蘆筍黯然失色的進口蘆筍天價,讓她決定絕不能辜負這蘆筍,雖然在美國超市裡它是難以想像的賤價,無論如何她得想出別出心裁的精緻烹調法,好好提昇蘆筍的美味才行。她告訴室友今天買了新鮮蘆筍,只得到不甚熱絡地,「哦,是季節了嗎?」A小姐對如此冷淡的反應大為不解。
那天晚上,她翻出所有食譜,參考任何蘆筍建議食法,在蘆筍湯蘆筍沙拉蘆筍通心粉蘆筍雞蘆筍慕斯間神遊,心悸不已,看到情動之處,忍不住跑到廚房打開冰箱,想看看她可愛的蘆筍晚上是否睡得好。出乎意外地,她的蘆筍居然不翼而飛。
她以為自己眼花了,或者記錯地方,翻箱倒櫃徹底搜尋一遍,還是不見芳蹤。那天她睡得不太好,想著今天在超市和蘆筍的邂逅與定情,難道只是春夢一場?
第二天悵然若失地打開冰箱弄早餐,正想著再去買一把吧,赫然看見蘆筍從冷藏櫃裡對她展露笑顏。她把它們拿出來,一根根數,一根根檢查,並沒有任何異狀。
從那時開始,她發現她的蘆筍必定在晚上消失,白天又安然無事回到冰箱的寶座。這到底意味著什麼?難道蘆筍染上了夢遊症,晚上會自己打開冰箱在她們兩人的小公寓四處探險嗎?
A小姐一向尊重個人隱私,從不過問室友的生活,或趁她不在進她房間翻東翻西;但這次,她覺得事出蹊蹺,有必要好好研究一下。於是等室友前腳一走,後腳就溜進她房間。
室友大學念的是美術系,這個斗室曾經堆得到處都是顏料彩筆畫布畫框。自從她在室內設計公司找到了工作,那些可以讓她想起八歲塗鴉年代開始有的畫家夢想的道具全收得乾乾淨淨,只留下牆上還吊著幾幅名字簽得大大的名作。A小姐環視一周,沒看到可疑跡象,只發現桌腳字紙簍好像塞滿了垃圾。
她走近一看,大多數是素描紙,上面繪滿了大大小小各種角度各種形狀的蘆筍,心下當場釋然。早說不就好了嗎,也不用害她擔這個心,這女孩也真是,說一聲她還可能大大方方給她一根讓她畫個夠,何必這麼偷偷摸摸地!
她隨手從字紙簍抽出幾張,想看看室友這兩個晚上的成果如何。她發現這小妮子的確有她兩把刷子,筆下的蘆筍個個風姿獨具,就那麼簡單幾筆,神韻風骨竟勾勒無遺。
她一張看過一張,興起還把字紙簍裡丟了揉了的全拾出來一張張觀賞,直到看到真有點兒蹊蹺的東西。
看到後來,越來越覺得看到的不是蘆筍,而是男人身上那玩意兒。她不相信地擦擦眼,想著是自己心有邪念產生的幻覺嗎?但她沒有看錯,最後那張整張都是挺立的陽具,都像蘆筍一般尖端朝上,如雨後春筍冒出地面;其中一個本來還掛了兩個小球,後來她大約覺得不太搭調又把它們塗掉,另一個上面帶著毛的,被她打了個大叉,整個抹滅。但說它們是陽具,每個尖端又帶著點蘆筍的形狀與紋路,讓她幾乎想問了,這是蘆筍陽具的素描嗎?
她小心翼翼把這些撕下來的素描紙再放回去,不忘記稍微整了一下,免得留下被人翻動過的痕跡;心裡那個謎不斷擴大,到底她的小畫家心裡在想什麼?就只是單純的思春嗎?
她看到合在桌上的素描簿,抑制不住地把它翻開。這大概是她大學時代留下來的,課堂上描畫的靜物裸體,課堂外的風景人物,歷歷在目。然後,她看到一張像是魔法仙境的速寫,肯定是近作:如寧芙仙子頭戴花冠身著飄逸長袍的美女在原野間漫步,透過樹蔭縫隙照在她身上的陽光,讓那薄紗輕衣把她曼妙豐腴的肉體襯得若隱若現,極是動人。但整個畫面有一突兀的地方,就是那滿地冒起的蘆筍,而仙子竟也能在蘆筍間凌波微步;任她形狀美好的裸足輕撫蘆筍,飄然似騰雲駕霧。
下一張仙子玉體橫陳,側躺在蘆筍之間,秀髮披散,星眸宛轉,薄紗服貼在身,那腰臀美好的曲線畢露無遺。而在萬萬千千蠢蠢欲動的蘆筍中,已經有幾根變形為那不知是男人還是蘆筍的陽物,仙子的玉手,就落在其中一根身上,看來無限溫柔。
她翻到下一張,仙子就這麼跪著,花冠已揉碎桃紅散滿地,紗袍敞開著,她微向後仰的身軀把裸露的乳房飽滿弧線帶得更圓潤。在紗袍中不可見處,想必是侵入她肉身的蘆筍吧!
那天晚上她把蘆筍燒來吃了,最後還是水煮沾美乃滋,原先那些花俏新奇的食譜都棄之不用。她很遺憾地發現那粗大的蘆筍質地也粗,完全沒有想像中的超凡美味。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愛無饜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54 |
二手中文書 |
$ 252 |
愛情小說 |
$ 253 |
中文現代文學 |
$ 281 |
中文書 |
$ 282 |
小說 |
$ 288 |
現代小說 |
$ 28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愛無饜
從食材出發,圍繞著各色蔬果打轉的,便是眾生芸像、世間百態;蘆筍、葡萄、奇異果、松露、茄子、洋蔥看似沉默,卻以無比豐富的表達力低訴世間男女的瞋怨悲喜、慧狎愚癡、因緣魔障。從A到Z的敘列,在英文裡是所有字辭源起的小宇宙,26幅小素描,不多不少,作者藉由一篇篇奇想極短篇,素筆勾勒一幅幅的愛慾圖像。
這本書的彩圖虛實交錯,一部份是作者採買食材、烹調、品嚐的忠實記錄,一部份是歸化台灣女婿的法國插畫家歐笠嵬(Olivier Ferrieux)綺麗想像勾勒出的幻境。那些看似平實的食材演繹出人心世態的新聊齋故事,讓滿肚子小妖怪的歐笠嵬餵上一幅幅甜美中帶幾分詭譎、純真卻不失世故的插畫,更加生色。有素有葷,百味參雜的人生,獻給所有愛吃的讀者。
謹誌美食人生,美味愛情。
作者簡介:
文字/
林郁庭
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巴黎索邦大學博士候選人。喜愛文學、電影、音樂,亦美食品酒,研究志怪傳奇、現代文學、十九世紀英國法國文學、小說、浪漫主義、文化研究。作品散見各報章雜誌,2007年獲得第二屆人間新人獎。著有長篇小說《離魂香》。
插圖/
歐笠嵬(Olivier Ferrieux)
1963生於法國里昂市柏宏鎮,格勒諾勃(Grenoble)及里昂高等藝術學院畢業。
1985起陸續在法國、瑞士、日本等地舉行多次個展、聯展。1995年來台,曾參與「伊通公園百人聯展」、台北美國文化中心個展、誠品畫廊「單數?複數」聯展及「捕風捉影」素描展。
97-99年間在漢口街擺小畫攤。
在台出版品有《一百的故事》(橘子)及最新作《漢口街的小意外》。
法國第三電視台及Kanari Films曾拍攝相關紀錄片《小妖怪》及《歐笠嵬在台北》。
喜歡喝綠茶。
章節試閱
說個故事給我聽…
和D交往了一陣子,激情逐漸平息下來。
從法國帶回來的惡習之一是開胃酒與小菜,真的遇上了對手,則不知開的是哪個胃口。我們在窗邊擺了個小咖啡桌,飯前常常兩個人開瓶酒對酌,配著醃橄欖、義大利香腸;奢侈點兒,我會叫他買瓶香檳帶來,慣有的菜色外再加上一盤鶯紅柳綠的水果,然後,坐在他腿上把草莓一顆顆送到他嘴裡,或是要他拿櫻桃餵我。兩人的眼神笑語在香檳泡沫之間交錯,情慾隨它盤旋上升,不須多時,那兩個香檳杯便冷落在桌上,而我們已經在床上繾綣。現在,他還能耐到吃完晚飯以後,兩人稍事休息,相敬如賓...
和D交往了一陣子,激情逐漸平息下來。
從法國帶回來的惡習之一是開胃酒與小菜,真的遇上了對手,則不知開的是哪個胃口。我們在窗邊擺了個小咖啡桌,飯前常常兩個人開瓶酒對酌,配著醃橄欖、義大利香腸;奢侈點兒,我會叫他買瓶香檳帶來,慣有的菜色外再加上一盤鶯紅柳綠的水果,然後,坐在他腿上把草莓一顆顆送到他嘴裡,或是要他拿櫻桃餵我。兩人的眼神笑語在香檳泡沫之間交錯,情慾隨它盤旋上升,不須多時,那兩個香檳杯便冷落在桌上,而我們已經在床上繾綣。現在,他還能耐到吃完晚飯以後,兩人稍事休息,相敬如賓...
»看全部
推薦序
一本充滿想像力的戀人詞典
最大膽、最有趣、最令人想入非非的創作
詹宏志、楊澤、韓良露 品味推薦
蔬果的色香味,在《愛無饜》中,象徵著男女關係的慾愛情。林郁庭拿手調理蔬果的形色,茄子、蘆筍、葡萄、玫瑰桃,都能刻劃出色慾的原相。至於愛的氣息,松露、香瓜兩篇寫得特別勾魂,讀完之後仍有隱約飄盪的迷香。或許林郁庭對情為何物仍有不解,她筆下的蔬果之情味都不是甜美入口的,波羅蜜、草莓吃來苦澀,有情有味的人生得來不易啊!這是一本充滿想像力的戀人詞典,由現代高等知識女性,而非後宮嬪妃訴說的一千零一夜的性愛傳奇。
─...
最大膽、最有趣、最令人想入非非的創作
詹宏志、楊澤、韓良露 品味推薦
蔬果的色香味,在《愛無饜》中,象徵著男女關係的慾愛情。林郁庭拿手調理蔬果的形色,茄子、蘆筍、葡萄、玫瑰桃,都能刻劃出色慾的原相。至於愛的氣息,松露、香瓜兩篇寫得特別勾魂,讀完之後仍有隱約飄盪的迷香。或許林郁庭對情為何物仍有不解,她筆下的蔬果之情味都不是甜美入口的,波羅蜜、草莓吃來苦澀,有情有味的人生得來不易啊!這是一本充滿想像力的戀人詞典,由現代高等知識女性,而非後宮嬪妃訴說的一千零一夜的性愛傳奇。
─...
»看全部
目錄
◆ 蔬果齋誌異──飲食男女A-Z
說個故事給我聽...
Asparagus 蘆筍
Blood Orange 血橘(櫻桃橙)
Carrot 胡蘿蔔
Daikon 蘿蔔
Eggplant 茄子
Fennel 茴香
Grapes 葡萄
Honeydew Melon 香瓜
Iceberg Lettuce 西生菜(捲心萵苣)
Jackfruit 波羅蜜
Kiwi Fruit 奇異果(獼猴桃)
Lime 萊姆
Mango 芒果
Nectarine 玫瑰桃
Onion 洋蔥
Parsley 香菜
Quince ?桲
Raspberry 蔓越莓
Strawberry 草莓
Truffle 松露
Ugli Fruit 優克力果
Vanilla 香草
Wintermelon 冬瓜
Xiporius Fruit 載波果
Yuk...
說個故事給我聽...
Asparagus 蘆筍
Blood Orange 血橘(櫻桃橙)
Carrot 胡蘿蔔
Daikon 蘿蔔
Eggplant 茄子
Fennel 茴香
Grapes 葡萄
Honeydew Melon 香瓜
Iceberg Lettuce 西生菜(捲心萵苣)
Jackfruit 波羅蜜
Kiwi Fruit 奇異果(獼猴桃)
Lime 萊姆
Mango 芒果
Nectarine 玫瑰桃
Onion 洋蔥
Parsley 香菜
Quince ?桲
Raspberry 蔓越莓
Strawberry 草莓
Truffle 松露
Ugli Fruit 優克力果
Vanilla 香草
Wintermelon 冬瓜
Xiporius Fruit 載波果
Yuk...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林郁庭、歐笠嵬
- 出版社: INK印刻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8-06-01 ISBN/ISSN:978986663101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68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