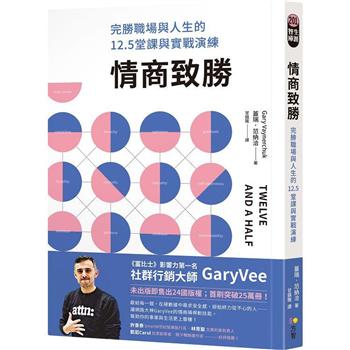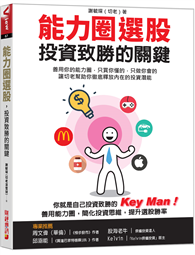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編輯弁言〉終於回到台灣,一生漂流後,他選擇記錄台灣,已是老人的故事……
一派自持與溫雅的文風,字如其人,看似沒有激揚之情,但其內省與自覺的泉源,卻是汩汩湧升無休。馬森所創作的文學,是要不斷掘深那窪拋棄禮教束縛、脫離西方宗教原罪觀後,個人自由與存在意義的活井。
視似卡繆《異鄉人》人際疏離、缺乏實存感的莫名所以;也像卡夫卡的《變形蟲》,將想像附生於動物,拉低人的位階正視獸性本質;也有湯瑪斯曼《魔山》中說理論辯的形式,由陷於困境的角色直抒胸臆。在馬森的小說語法中,不難看見西方現代主義與存在主義的哲理邏輯,使其文本透顯不同於其當代小說的興味,不論在形式及題材上,表現出濃烈的前衛實驗性格。
最早的《巴黎的故事》,以人類學田野調查之心,就文學之筆寫成,竟能擴及不同膚色的族群,堪稱現代文學中極難得見的異鄉底層人物的生活面貌實境;反應其巴黎生涯的《生活在瓶中》,則企圖追隨意識的流動,觀照「反省」與「解悟」對人的意識所產生的作用。《北京的故事》以中國文革為背景,是寓言,也是殘酷劇場;《孤絕》即為Isolation,說出繁華現代社會中,個人心靈的荒瘠之感;《海鷗》思索背叛自然享有絕對自由的人類,所背負的重擔;最為人知的《夜遊》,則像是對年輕的靈魂投下了震撼彈般,「不要活過二十歲」,是怎樣惡狠狠的慘綠年少,是怎樣的對青春年華的眷慕啊!《M的旅程》是以其擅長的象徵手法,外在變形、轉換時空,內心背離原鄉卻又負疚;《府城的故事》則終於回到台灣,一生漂流後,他選擇記錄台灣,已是老人的故事。
作家不免漸老,文字卻能代代如新,尤其經典之作,在當初時代或許只有少數人賞識,卻在時間推移後顯出其孑然風華。為免遺珠之撼,我們整理「馬森小說集」八部作品出版,依寫作時間序列,讓讀者看到這位走在文學之河先端的作家,如何在齊河、濟南、北京、淡水、宜蘭、大甲、蘇澳、台北、巴黎、墨西哥、溫哥華、倫敦、台南的不斷播遷流離的生涯中,在中文、日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等不同的語境與文化範疇裡,創造出一個個不停想、不停看、不停要掙出人世重圍的人物,及他們的故事。如高行健所說:「畢竟是神遊的馬森,毫不戀棧,東方西方,來去自由,何等瀟灑!」毋論作家優游何處,那口源源不絕探求生命底線的深井,則會繼續留在他的小說裡,留在台灣,待讀者掬飲。
〈附錄〉從天涯到台南──年輕小說家賴香吟專訪「賢拜」小說家馬森
一九八七年的夏天,在結束了長達二十餘年的國外遷徙生活之後,馬森接下了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的聘書,按道理,八月該是去上任的時間了。馬森正在打算著怎麼去台南,聯合文學發行人張寶琴對他說:我們正要到成大辦個文藝營,你就來幫我們做個專題演講吧,我們有車,連人帶行李,送你下去。馬森想這倒也方便。因此,那一年聯合文學文藝營,開幕式過後的專題演講,馬森就站在台上講現代小說。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馬森,也是我熟讀《孤絕》、《夜遊》以及《海鷗》這幾本小說的青春時期。那個夏天之後,馬森落腳台南,悠悠十來年,而我則考上外地的大學,毫不猶豫離開了台南。
二○○四年第一天,我穿進巷子,找到馬森位於台南開元寺旁的住家。在按下門鈴之前,不免躊躇片刻。過去不是沒有機會認識馬森,但卻習慣保持距離。這是為什麼呢?馬森未必神祕,在同年代的文友圈裡,他顯得優雅明朗,在年輕學生眼中,他和善可親。但也可能就是因為這些形象,節制而禮貌地區隔了我心中關於馬森的印象;我很少與人提及我讀馬森小說如何如何,且等自己不免也開始寫起小說之後,更是避免與舊日熟讀的作者作品,素面相見。沒想到就在我回到台南的初始,巧合被派來採訪馬森。十六年的時間,掐指算過,幾秒鐘而已。
宜蘭佛光大學在二○○二年為馬森辦了一場「馬森作品學術研討會」,並為他慶賀七十大壽。這個數字讓許多人乍聽之下吃了一驚。我印象中的馬森,始終是五十幾歲的學者姿態,和我那幾本讀舊了的小說集,一起留在台南老家的書架上;當時我把馬森的小說與朱天心、蘇偉貞等年輕作品一起捧讀。時隔多年,我在他家屋內,看到許多舊日的文學選集,看到亮軒給他寫的字墨,看到龍應台一九八五年題字贈書的《龍應台評小說》。他的開場白是,他第一次來到台南,是一九五五年的事情。那時候的台南印象是,這城市真小。說到這裡,他問我,那時候妳在台南嗎?我忍不住笑,這離我出生的一九六九年還有好大一段差距。後來馬森又提到,一九七○年代初,《中國時報》高信疆寫信來邀他寫稿的時候,大約把他想像成長輩,信中文白夾雜,用了頗多敬語,而龔鵬程寫文章也說讀馬森早年著作《莊子書錄》,以為他是竺心舊學的老先生。
這些錯雜的印象,反映不同世代對馬森的陌生。馬森出現在台灣文壇的時間,說來不太秩序,每個時期,他且扮演不盡相同的角色:搞戲劇的學生、有條有理的方塊評論家、現代主義小說作者、大學教授。這使得他的讀者區分成好幾個群落,且讀者與讀者之間未必有交集;年長的文化人跟他有上一代的風雅交情,昔日文藝青年案頭上多半有幾本他的小說,而再年輕點的,後來做了他的學生,跟他生活噓寒問暖。
※
我是一九三二年出生的,那時北伐之後有一段繁榮的和平日子,在我印象裡邊,五歲以前,日子非常好過。不過七七事變,一打戰,我們那地方很快被佔領了,日本人沿著河北山東,很快就下來。因此,打從五歲起,我可說進入日據時期,受日本教育,學校裡頭有日本教官,學日文,一天兩個鐘頭,很重的課,就跟國文作文課一樣重。
這是馬森自己的話。地點是山東齊河,他的出生故鄉,時間是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馬森五歲到十三歲。好不容易戰爭過去了,勝利了,可是緊跟著國共內戰,東逃西逃,又四年。
經你這樣一問,我才發現自己的確跨越了好幾種時代。當年我經過幾次解放,可以說跟著解放跑。那時候,我們很怕共產黨,因為聽多了鬥爭清算解放這些手段。我父親是在國民政府裡做事的。一家人往濟南跑。在濟南買了間小房子,預備住下來,我也在濟南上學,可是才過幾年,濟南就解放了。先是共軍炮火把我們房子打垮,佔了周邊,第二天,國軍來打共軍,我們又變成轟炸目標。我母親便要我們往外逃,她留在家裡守著。我和一些叔舅弟侄輩逃出來,也沒來得及告訴母親,便臨時決定去北京找我父親。從濟南走到北京,走了一個星期,好幾千里。
在北京又繼續上學。後來國共和談,父親先去青島。幾個月後,他派了一個親戚,回到北京來接我。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我離開北京,到青島會合父親和表哥,往上海,然後坐船到台灣。在基隆下的船。
我追問:母親沒能一起出來?
他說:沒有。那是後來。很睌以後的事了。
於是,馬森來台的時候,已經是個十六、七歲的少年了。很快又離開了同來的父親,輾轉唸淡水中學、宜蘭中學;學校裡大陸學生不多,幾個人克難住校,課堂上老師說的多半是日語或台語,聽不懂。
馬森的青少年生涯,幾乎可作為一個分析戰爭與政治動盪的豐富取樣。可是他對這段經歷,之前吐露不多。那是一段不得不流離的啟蒙歲月。六年中學,換了七、八個學校,長期沒有跟家人在一起。我以為他可能從這段生涯說出什麼苦澀的故事來,孰料他卻一語輕輕帶過:「這樣也好,比較獨立。」
然而這個少年並非原來就是堅強的孩子。作為家中唯一的獨子,父親不在,抗戰去了,他很依賴母親,很內向,母親也保護得緊。他提到,大概是四、五歲的時候,才第一次踏出家裡院子,到外面街上去:「在門口碰到一個小孩,跟我說了許多不好的話,罵我的意思,我馬上就哭回來了,怎麼外面世界這麼恐怖?」
母親不許他游泳,不許他跟野孩子混在一起,她總說:你身體沒他們好。那時他又瘦又小,放學走在路上,老師還怕一陣風就把他吹跑了。他不服氣想要鍛鍊身體,想要壯大,住在濟南的時候,晚上摸黑跑到護城河去學游泳,誰想水又冷又涼,一下子就感冒了。他真正學會游泳,是在台灣的淡水。「那時候沙崙海濱很乾淨,在海裡邊很簡單就學會游泳了。後來就經常去游,身體也隨之長高長壯;長得比父母都高大了。」
※
這個內向的孩子,有一個話不多,喜歡看些章回小說打發時間的母親。她也經常給獨子講故事,有些可能是她的生活經歷,有些也可能是她添油加醋,總之,馬森很愛聽她講故事,有些很神奇的地方,甚至有點魔幻寫實的味道。馬森在七十歲年紀回憶這些久遠的兒時往事,記憶仍然非常清晰,他說到打開父親書箱的經過:
小學四五年級,父親不在家呀,我發現屋子裡邊有一間房,書箱是父親留下來的,但是大概沒有人翻動過,我就把它打開,裡邊有好多書,有魯迅,有巴金,有茅盾,有沈從文,還有莎士比亞劇本的翻譯,《羅密歐與茱麗葉》,我很早讀的,還有安徒生童話集什麼的,那大概是我父親上學時喜歡所以收集來的。他去抗戰,書就留在家裡。那時候翻了魯迅,似懂非懂,但是巴金倒容易看,是些愛情故事。
如此讀了不少二、三○年代的中國新文學。在濟南、北京唸中學時候,馬森比較明顯地喜歡兩個作家,一個老舍,一個曹禺;一個小說,一個戲劇。轉到台灣宜蘭中學之後,馬森開始給報紙投稿,大抵寫些詩與散文;師大國文系時期,《中央日報》更時常可見他的文章。然而,比起有些作家很早即清楚立志要當一個作家,馬森並沒有那樣的想法,也沒有特別計畫。當時他只是個喜歡讀寫實主義小說,尤其喜歡屠格涅夫的年輕人。生活裡多數時間,他其實更熱中於學校裡和李行、劉塞雲、白景瑞等人的戲劇演出,他甚至去參加了一個演員訓練班。如果真要找出開始寫小說的往事來,他是這樣說的:
我想我開始寫小說,應該是一個文學獎的關係。一個紀念國父誕辰的大專生文藝創作比賽,第一次辦,是由學校訓導處把我們的文章匯了去,送到徵文處。最後一天,訓導長來宿舍問我怎麼沒有寫,因為他知道我常在報上登文章,他說我應該寫一篇,我說那什麼時候交稿呢?今天下午。那怎麼來得及?他說,你現在就開始寫。那是早上十點多的事。我寫到下午三四點鐘,寫好了。那篇文章後來得了首獎,當時詩組得獎的好像就是余光中。因為第一次辦,記者還來訪問,報上也登得很大,還拍了畫面,不過那時候還沒有電視,是放在電影預告前面的新聞片播放的。記者問我,你是不是將來就預備寫小說了,我說,沒有這樣想法,不過,這倒也給我丟了個問題。那是第一次寫。
那是一九五二年左右的事情。之後,馬森的確在小說上作了一些嘗試,但是沒有完整發表的作品。成績不斷的還是戲劇。他就像他自己所形容:「剛開始可能是強迫自己,後來就演出興趣來了。欲罷不能。上癮似地。」一九五四年,馬森從師大國文系畢業,當兵走過他與台南的第一次淵源之後,回到師大唸研究所,作《世說新語》研究,同時在師大國語中心兼任講師,接觸不少外國學生,其中與一位比利時修女學法文的經驗,以及那年剛來台徵選的法國政府獎學金,聯繫了他去巴黎的因緣。
※
對比早期少談的戰爭流離生活,馬森在巴黎之後的國外遷徙歲月,透過文學作品,透過每本書末的著作資料,反而較為一般讀者熟悉。他前後在巴黎待了七年,學語言,習電影,唸漢學,同時和一些留學生創辦了在當時頗具影響力的《歐洲雜誌》。日後將近二十年光陰,馬森始終沒有回過台灣。《生活在瓶中》主人翁對藝術前途的不確定,對國家身分的茫然,某一程度代言彼時他在巴黎的生活。時隔三十幾年,他還能毫無遲疑立刻說出《生活在瓶中》的命題:
像一朵花插到瓶裡,水沒有了就是沒有了,它沒有根嘛,無根的生活。那時候我深深感覺到失土失根的痛苦。畢竟從中國到台灣的這些流離,並沒有真正離開的根和土。即便台灣也還是根和土。我的根土,指的是廣義的文化。而到巴黎就是真正離開了……。
一九六七年,他千辛萬苦把母親從大陸接到了巴黎,可同時,他又收下了來自墨西哥學院東方研究所的聘書。分離二十年的母親在療養院養身體,說得很無助:「你人去了,我在這兒怎麼辦呢?」結果他仍然決定一個人先去。在巴黎已經成家立業的他,生命有點蠢蠢欲動,想要擺脫壓抑,試著冒險,他說:「不管了,我還年輕,不需要太大的保障,有這一年合約就可以去了。」在墨西哥陌生的旅宿裡,他提起筆來,寫出了後來收進《馬森獨幕劇集》的第一個劇本。
馬森曾將墨西哥的六年生活,形容為「急流中的湖泊」。他幾乎是在這裡踏進他文學創作的第一座山谷茂林。他的妻子、孩子與母親,在六個月之後,也來到墨西哥定居。在有僕人有親人的家庭生活,以及墨西哥風情殊異的文化刺激之下,他在這個湖泊,寫成了《生活在瓶中》,此外有《馬森獨幕劇集》以及《北京的故事》。在這之前,除了一系列由真實材料剪編而成的《法國社會素描》(後易名《巴黎的故事》)之外,可以說,馬森還不曾如此專心致意在文學的領域裡耕耘過。這其間不能不提的人物是,當時在台北主編《大眾日報》副刊的金溟若先生,他不僅邀約催促馬森寫作獨幕劇,且為其量身製作了大版面的戲劇專刊,其後,《生活在瓶中》也是在《大眾日報》副刊發表的。
這些作品,以馬森自己在一九八四年為《北京的故事》作序所言:是所謂「經歷心理革命稍前的作品」。他對這一時期的作品,有這樣的自評:「我扮演的是一個批評者的角色,而不是一個參與者的角色。我時常運用了魯迅式的嘲諷,卻缺乏更深一層的同情與悲憫。」
然而,這心理革命指的是什麼呢?
※
「《生活在瓶中》,可以某一程度代言您在巴黎的生活嗎?」我問馬森。
「某一程度是可以的。」他先是這樣回答,接著,又說:「然而我又是非常喜歡巴黎的。《生活在瓶中》只是某一個面向的感受,消沉的面向。許多時候,我是很能享受巴黎的歡樂文化氣氛的。」
類似的兩面或多面陳述,後來不斷出現在我們的談話裡。剛開始,我不免以為這是一種迴避或稀釋問題的方式。關於馬森,我向來只是一個偏食其小說,不完全的讀者。但因為這次訪談,比較全面讀過他的劇本、散文與文學評論之後,不僅沒有呈現出一個更完整的馬森,相反地,我由小說所讀到的馬森形象,不時與其他文體的馬森構成矛盾費解之處。於是,我對他提出的問題,總不免站在小說讀者的立場,預設其生活與個性可能較貼近於小說的描寫,也不免追問:明朗、樂觀的評論口吻;冷靜、深刻的戲劇安排;濃鬱、熱情的小說人物;究竟哪一面形象,才比較接近內在的他?
然而,他往往不會給我一個肯定,卻也絕非否定的回答。他的說話,有條有理,避免任何抽象的描述,看似開誠布公,十分坦然,然則,幾句話便輕輕鬆鬆繞過了不明的核心,直接到達簡明而不偏不倚的結論。
一個創作的人總是很複雜的。個性裡總有幾個傾向,一個是我,另一個也是我。
我可以告訴你,我的哲學是悲觀主義,但我在生活上抱著樂觀主義。這並不相違背,一個悲觀,一個樂觀,在我來說,是很統一的東西。
妳要是問問我太太的意見,她會說,我這個人就是喜歡熱鬧,沒有電話就不能生活,我是絕不會把電話拔掉的,因為我需要朋友。
我們都笑了。他這些話的口吻,當場聽起來並無敷衍之意。在進行過幾回合的問答之後,我不得不試著修正我的印象,眼前這個自我介紹是B血型天秤座的馬森,似乎真的不受各種個性的矛盾衝突所擾,糾葛在小說裡那些飽受生命往事與熱情所惱的角色們,好像一批馴良豢養的獸,唯有在創作之際才會放肆各尋出口。
其餘的時間,他是個理性而穩定的人,「每天可以保持在差不多的狀態,沒有什麼高潮低潮。」關於個性,他經常使用「個人自覺」這四個字:覺察到了弱點或欠缺,便通過後天的訓練去改變。他提到兒時正是因為自覺過於內向,口齒不清楚,不會表達自己,所以才硬著頭皮報名參加演講,而後還把自己推到了舞台上,通過劇中的人物來盡情表現自己。
※
馬森的墨西哥生活結束於一九七二年。他決定到加拿大去重做學生,同時把母親送回台灣定居。也是在這一年,他在香港出版他的第一本書《法國社會素描》,同時,應高信疆邀稿,開始在《中國時報》寫稿。在好幾篇陸續發表的短篇小說當中,一篇題為〈癌症患者〉的作品,先後被高信疆、朱西甯收入《當代中國小說大展》、《中國現代文學年選》而受矚目。
我的癌症不是肉體上的,可是我清清楚楚地感覺到有些地方不對勁兒。有些地方的先天組織破壞了,毒化了。這毒又慢慢地向著別的地方蔓延。終於有一天我會整個地潰掉。
這篇以癌來譬喻思想心疾的小說,後來收在《海鷗》的第一篇。這本小說雖然晚至一九八四年才出版,但其中許多篇章和《孤絕》都差不多寫就於一九七○年末期,兩本短篇小說集明顯含有現代主義的成分。馬森創造的「孤絕」一詞,成為他小說風格的一個標記,也轉成詮釋現代主義的好用詞彙。這麼多年過去,馬森談到現代主義,有一種沉澱後依舊肯定的態度:
我到西方去有一些轉變,一是我比較了解基督教,研究了死亡與贖罪的問題,二,我也比較了解西方人的思想,現代資本主義的情境。此外,幾個對我影響很大的東西,一是佛洛依德的心理學,它是讓我認識人性的一個工具,一個路向。另一個就是存在主義;存在主義的一些說法,跟其他說法比起來,我還是覺得它是比較接近真理的一個東西,比較看到人生真相的,比基督教,比儒家、道家,都接近人生的真相。存在主義的確是很悲觀,的確是把人生看得很沒有意義,我基本上贊成人生是沒有意義的,沒有一個歸向,說起來,人活著沒有一個價值、意義,但是你實在也必須自己給人生產生一個價值,製造一個意義。
這時期發表的短篇小說,在形式與結構,馬森有意識作了不少實驗與表演;這是一個亮眼的登場,小說家馬森的形象很快確立。這距離當初大學時代記者問他是否打算當一名小說家,已經過了二十餘載。
明眼讀者想必都注意到這一波小說創作的高峰。雖然在創作時間上緊接著墨西哥時期,但這次馬森走進的山谷茂林卻是全然不同的景色。這一時期的小說,雖然在色調上經常是灰暗的,但這灰暗往往正是生命燃燒所造成的光影所致,這些小說,對於生命的野性與激情,保持著一種寬容與理解,甚至是歌頌的態度。馬森在獨幕劇力守的節制與均衡,此時似乎張散開來,任憑角色與情節湧入。特別是他拿到博士學位,又從學生變回教授之後所寫作的長篇小說《夜遊》,其中許多角色,都不是可用常理眼光來看待的,但馬森對各種人物的理解與描寫,卻有情而動人。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這是個大謎題。馬森經常的回答是重作學生,心理上有二度青春的自由感覺。再者,加拿大這個國家的開放性,也讓他的生活圈裡的確出現不少率性冒險的人物。此外,馬森與我提到他的前妻安妮,她是個比較容易信任別人,敢於開放,然而情緒也相對起落分明的女子,馬森透過她,看到了中國文化加在自己的束縛與拘謹,他覺得應該改變自己。馬森與安妮最終以分居收場,他對這場婚姻的自我檢討、內在苦澀,說來也是創作《夜遊》的背景之一。
從加拿大之後,我想,我沒有再回頭,也就是說,沒有再變成一個保守的人,我覺得在我生命歷程裡邊,加拿大是一個關鍵性的時期,一個關鍵性的階段,在那以前,我是非常學院派的人,學院派的意思指的是:當學生,教書,上班,照顧家庭;非常傳統的一個人,不會越出這個規矩,甚至也不會特別同情規矩外的人,而是帶一點批判眼光看他們。可是,從加拿大之後徹底改變了,我完全能接近這樣子的人,雖然我沒有變成這樣子的人,但是我理解這樣子的人。
這段話,對照他一九七六年,身處溫哥華,為《馬森獨幕劇集》一書所寫的序:
到了加拿大以後,不管在研究寫作上,還是在生活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變成了一個與前大不相同的人。我好像重新獲得了一次生命,又投入了生活的急流中,無暇休歇了。從此開始了我生命中另一個截然不同的階段。
兩段話都點出了分水嶺的意思。馬森甚至十分清楚地說:「如果我沒有去加拿大,就不會有《孤絕》與《夜遊》那些小說。」然而,更具體的往事經緯,他沒有說得更多。
※
《夜遊》寫好之後,馬森把稿子寄給白先勇看,白看了《夜遊》之後,非常激動,寫了好幾封信給馬森,也提了意見。《夜遊》於是就在復刊的《現代文學》上連載。這樣一篇有關嬉皮、吸毒、性別的小說,在當時還不常見。一九八四年,《夜遊》出單行本,市場反應出乎意料的好,據說接連在爾雅銷了二十版,還有人提過要拍電影。
我就是在這個時候讀到馬森的。馬森加入(或說是重返)台灣文壇的時間這樣晚,以至於年輕讀者不會察覺這作者其實已經年過五十。他的文學,往前一點,沒被來得及納入留學生文學或現代文學的討論裡,往後一點,又離後來發展的都市文學、同志文學還有距離。他在溫哥華時期所寫的幾本小說,彷彿不按排序亮起的幾顆明星,獨自閃爍在八○年代中期的台灣文學天空裡。
現實生活的馬森,這時已經隻身離開加拿大,轉到倫敦教書。一九八○年,睽違二十年,他第一次回台灣,覺得台灣政治氣氛漸漸在改變之中。一九八三年,他應姚一葦之邀,在藝術學院新成立的戲劇系客座教書。這一年,真是把他忙透了,又導戲,又看小說獎決審,同時在報紙寫專欄。
說來龍應台寫「野火集」其實是我介紹的。那時我每周在時報寫兩個專欄,「東西看」和「述古道今」,一個用文也白的筆名,一個用筆名牧者,經常接到讀者來信罵人。認識龍應台之後,我覺得她在《新書月刊》寫的書評非常犀利,應該寫專欄,就給她介紹金恆煒,我說我已經寫了兩年,該換個新人來寫。我的最後一篇文章緊接著龍應台的第一篇,我還在文章裡寫著:現在接著有龍應台的「野火集」,我就下臺一鞠躬之類的句子。結果這「野火集」一上台,就燒起來了。
因為《夜遊》、《孤絕》暢銷所帶來的熱鬧生活,對馬森來言,也許是一波所謂「生活的急流」。但無論如何,與藝文界朋友如張曉風,隱地,席慕蓉,蔣勳等人的交誼很使愛熱鬧的他感到愉快。他提到,對比冷漠的英倫生活,台北似乎是通過朋友們熱情的臂膀在歡迎著他。他終於起了回台定居的念頭。
一,失土失根的感覺漸漸讓我覺得倫敦待不下去了,我對英國印象並不挺好,英國人冷,不容易交朋友。二,天氣不好,冬天陰沉沉的,讓人心情老不愉快。那幾年經常回來,覺得台灣情形改變了,跟以前兩蔣時代不太一樣;我真正回來是一九八七年,解放報禁那一年。再說,也是父母年紀大了。母親原來住在豐原,我回來後接到台南住。我母親是在這間屋子裡去世的。
※
時間,地點,倒回台南。這一場閱讀時空的迷走,大致理出了頭緒。
我繞著馬森的人生打轉,除了是想澄清自己腦中馬森錯雜的形象,同時也想從他的口中聽到更多關於小說的背景往事。然而,沒有,沒有太多。彷彿一片落葉,在時間壓過之後,只留下了枝梗。馬森笑說,他幾乎也不太讀從前的小說了。我不得不面臨到,對年老作家的訪談,通常跳不出文學史料的框框:何時何地發生了何事,除此之外,多半是雲淡風清的回答。
我們提議去馬森新作小說出現的開元寺走走。
一生遷徙:齊河,濟南,北京。淡水,宜蘭,大甲,蘇澳,台北。巴黎,墨西哥,溫哥華,倫敦。台南恐怕是馬森住得最久的城市。
他當初選擇來台南,部分原因就是因為它小鎮的安靜,離台北核心的繁忙遠一點。這麼多年下來,台南的確像一塊柔軟的海綿,靜靜吸納了十幾年的光陰。馬森在成大中文系待到退休。《M的旅程》是他在台南所創作的唯一一本小說集,九個寓言幻境短篇,思索的仍是之前小說的主題:傳統與家族倫理的羈絆,自我認同,理想與夢的追尋,只不過,我們終究在這裡微微告別了青年馬森,儘管主人翁M仍然像極了一抹單薄孤獨的現代主義影子。這本書沒有創造如《夜遊》、《孤絕》那樣熱烈的銷售數字,可卻是馬森極為鍾愛的系列作品。
今年(二○○三)夏天,我和家人到溫哥華去,我帶了一個手提電腦,溫哥華沒別的事,就起了寫小說,寫台南的小說的念頭。府城的故事,當中有好幾篇是今年夏天在溫哥華寫的。
巴黎的故事,當時候寫,有一點用人類學的角度來寫,有很多人是真實的,有很多事也是真實的,我只是稍微改一下,使之有文學的味道。至於北京的故事,則完全是寓言。而府城的故事,既不是記實,也不是寓言的。
我的目的並不是要寫府城的歷史。但也可能關涉到一些。現今台北是愈往國際化走了,府城則留了一些台灣的原貌。我想一面寫府城,一面研究府城。這個系列故事,有些還沒寫出來。
我又回到台南,因緣機會讀到了馬森這一系列小說。一些發生在府城的人的故事。
我在這幾篇小說,讀到了老境。
這幾年,似乎整個一代人都在體驗「父親」的逝去,生命的無常與老境,對我們來說,漸漸顯出它的奧妙來。年長作家的書寫變得可貴,工整手稿,三言兩語,往往有令人難以勝受的功力。
馬森是一個少見以電腦寫作的文學前輩;他總是有些使人驚奇的地方。我跟著學生輩稱呼他為馬老師,多少將我對馬森的印象拉回現實,加上寫作生涯的梳理定位,我比較看得清楚,那個佇立在《孤絕》、《海鷗》書後的作者,確確然走到了人生的老境與歸鄉。馬森其實已經稱得上是個健談的人,可他的小說說的往往比他口中說出來的又更多一些,具有血肉的肌理。
如今馬森說他經常忘記眼前的事情,但許多年代久遠的回憶,卻歷歷分明。
對比與他同代的作家,由村野與家族入手,寫作大時代下的戰爭與人生故事,小說家馬森一開筆就直接跳到現代的疏離情境。他的童少生涯,他笑稱的日據時期生活,因而像過早曝光的底片,沒有現出具體可辨的影像。幸好,他透露,他正寫著一系列母親在濟南的故事;這的確是馬森文學的重要人物。以及,一九四九年夏天,那個十六歲少年,留下家鄉的母親,從北京到上海,登上船,在基隆港上了岸。那雙少年的眼睛所錄下的世界,以及他在這南方島嶼的流離青春,應該也是一片還沒有爬梳開來的厚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