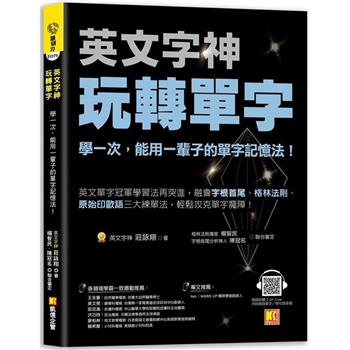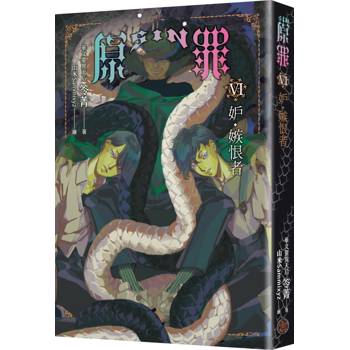重新開始,手很生疏,像兒童一樣筆筆描著,倒也有初學者的稚情。他記起老師的教導,繪畫以生物為基礎,以生命為開始,以生活為實質,一張畫完成,透露的無非就是這幾件事。
於是以後我們常見到軍官背著畫袋,拿著拐杖,在林泉之間徘徊踟躕,似乎在尋找某種景觀,構思某種圖案。或見他有時呆呆地站在那兒,好像在觀察某種物相,或者細讀某種形體。也見他選 擇一個角落,搭穩架子,要麼就手拿著紙和墊,依著石頭坐下來,聚精會神。
周圍生機洋溢,處處都是寫生的世界,生命並不缺乏。軍官的眼睛一向犀利,看得到物的特徵和細節,捉得住靜態和動態,一段時間以後,筆已運用的很熟練。見到他的寫生的人,都還以為是為專業畫家畫的呢。 ──李渝〈踟躕之谷〉
六○年代即開始創作的李渝,第一本小說集《溫州街的故事》,寫巷弄裡花木掩映間纏祟著戰爭與政治的,一樁樁繁華又滄桑的煙雲故事,已然是台北文學重要的一頁。之後,從《應答的鄉岸》與《金絲猿的故事》,再跨到《夏日踟躕》,作家美術史的專長一顯無疑,〈江行初雪〉裡已經出現的菩薩塑像、唐代服飾,宋代彩繪,到了〈無岸之河〉,藉小女孩的眼,描一隻「翅邊鑲著金色的羽毛」的鶴,展翅翱翔過豐腴富足的唐朝婦女,和綺麗憂鬱的徽宗工筆;騰飛過蘇軾的赤壁,也驚嘎一聲突出了黛玉的寒塘花魂。作家的筆下畫面層出,每翻轉一次,就是一個永恆的畫面,這個畫面,是文學的,也是藝術的。
其〈踟躕之谷〉,以一位自情治系統中退下,轉任開路工程的軍官為主角,寫他如何在經歷殘酷戰爭與暗流浮動的傷害下,體驗到「生命終究是無光的」,在白日酣暢於炸山爆破的快感,與魔魘於「夜半醒來的時候,密審的暗室,昏黑的刑場,驟然臨置,變成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的刑場」 間搏鬥著。又如何在一次暴烈的炸山錯差中殘廢,除去軍職,留居山林,並拿起筆畫出形相以外的,心內的線條與圖像。小說裡寫軍官初遭大難,某天黃昏時走到峰頂,恰見:
山岳迤邐,重重巒頭拱擁著峽谷,餘暉這時正妍妁,從山頂到山腰映得光彩,樹林株株斑斕挺立,顏色像翡翠一樣地明媚,樹梢的地方又給鍍染得比金縷還要纖美,景觀真是華麗又遼曠。
從山腰以下,日光卻遲遲不能移度下來,光質猶豫了,沒有給谷帶來亮度,反而使它失去色調形狀,變得晦黯而曖昧。尋找谷的盡底,似有底不見底,憂邃得無法 計,魍魎的煙嵐瀰漫飄蕩,不可知的氣氛浮沈著,盤旋著。
李渝行筆至此,不僅僅是描繪了一幅氤翠鑲金的畫面,還帶出一個畫家,由此位畫家,再帶出中國山水畫牽延百年的寫意寫實題目,和她身兼美術史專業與小說家身分背後的信仰;一個中國傳統山水畫的現代化進程,以及小說家李渝的現代主義美學,於焉鋪漫開來。
寫於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九三年間的,李渝關於美術的評論,後集書成《族群意識與卓越風格》,其中包括她對中國繪畫的民族主義與「現代」定義;山水畫的「外相」與「心源」的看法,拉丁美洲文藝在二十世紀後半期遭遇到的文化入侵、弱勢風格的壓抑與復興等議題,都有精闢獨到的看法。更令我們眼睛一亮的,是其中別出章節的四篇,她對畫家余承堯其人其畫的專論。小說家在此,一改她小說節制與舒緩的敘事腔調 ,換裝成專業美術評論者,對余承堯半生戎馬,中年轉畫,以素人之姿 ,卻直承宋、元山水典範的驚人成績,予高度肯定。李渝使用語言熱情澎湃,文字精煉嫵媚,一如畫家直畫石理岩紋,千山萬壑氣勢磅礡堆疊觀者眼前,不容呼吸,只能屏息;李渝的描繪與評論,亦以相同姿態,將畫家畫作引介讀者眼前,大有驚呼聲就要奪出,說:看,「代表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繪畫的一位畫家,就在眼前這裡了。」
儘管小說家曾提到,故事的本身或有所本,但提昇後,往往才達到一個超昇的世界,也就是一個寫小說的人真正想講的世界。 不可否認地,〈夏日踟躕〉一篇,確確疊合了畫家余承堯的身影,透過理解這位獨立於畫廊與評論界之外的畫家,我們或可一窺小說家李渝如此細寫畫家藉筆墨找尋救贖的經驗,是否隱含了某種對自己小說美學的回眸眼神?
余承堯,一八九八年生於福建省永春縣,出身於典型的耕讀家庭,父親早逝,曾學木匠與漆器,習做櫥桌,畫「勾欄」,能於木料上鉤畫雕花、彩繪。近代畫家齊白石早年亦曾有過木匠經歷,或許相同經驗都曾使得他們在書畫、造型與美感取向,留下一定程度的影響。 二○年代初期,余得友人支助,赴日就讀,原習經濟,後轉入日本士官學校就讀,自此開始他的軍旅生涯,直至對日抗戰勝利,四十八歲的他,已累官中將,此時,余卻毅然做出退休決定,原因紛多,其中以「二十多年的征戰生涯裡,他雖未親手殺過別人,但卻間接的與無以數計的生靈的死有關」 ,最接近李渝〈夏日踟躕〉主人翁的心理鋪陳。一九四九年,台海關係一夕變色,余隻身獨留台北經商,從事藥材生意,此後四、五年間,他並且開始他的南管推廣工作,開始逛畫廊。〈鐵甲與石齒的幻生〉說到畫家首次萌生提筆的念頭:
幾次畫展看下來,他胸中的『成山』使他對諸多畫家所作的山水頗覺不滿。他覺得他們的山水太貧乏、太單調,一點都不像他所體會到的奇妙、複雜與雄渾。於是余承堯首度拿起畫筆,讓他胸中的『成山』在紙上現形。
這年,他五十六歲,這一動念,牽引出他後半生的畫藝傳奇。
林詮居《才情‧隱士‧余承堯》收入畫家大量畫作,其中一幅跨頁水墨,即使是印刷品也讓人震動。這是余承堯畫於一九七一年的兩幅鉅作之一:「山水八連屏」 。近七百五十公分的幅寬,山的形體氣勢,簡潔磅礡,以幾個大塊分割營造,互相襯托呼應,山勢走向一氣呵成,當視角偶然停留畫面的某一點某一處,目光自然被牽動,不由得隨山的波折,隨蜿蜒山路,再行再走,攀高或入河谷,在蹊徑飛瀑間目光又順勢流瀉而下。在此八連屏中,畫家甩開已成套式的中國傳統的皴法規則(如江南岸渚用披麻皴、黃土高原用雨點皴、溪澗泉石則用帶水斧劈皴等),余承堯的不師古人用心在此一顯無疑。前文述及他所以萌生作畫的念頭,正因不滿傳統山水的紙上煙雲,於是他由心、眼出發,從他的軍事地形學出發,自創亂筆,既不講究毛筆筆法,也不管前人心法,「結構完整,層次分明」,他想畫出他曾行腳的大江南北十八省分,以及「實實在在的山」(余承堯語)。在四連屏、八連屏之後,畫家的創作更入佳境,「山高更應大」、「奇峰疊翠」、「連峰直聳破雲端」、「群峰拔秀立空中」、「庚申秋日作山水」等畫作 ,畫家由細碎筆跡組成崎峻山岩,再由大塊分割構圖組成全畫的余式畫風,愈見複雜成形,亂筆,竟組合出生命力旺盛的憾人山水。
李渝說:
看余承堯畫,如果對中國繪畫不太陌生,也許會從記憶裡遙喚出兩種山水典型來,一是以范寬為代表的北宋山水,一是吳彬、龔賢等人作品中所看見的十七世紀「變形主義」山水。
這是李渝面對畫家余承堯時最驚懾的一事:
何以在五十餘歲的高齡開始,竟能有這樣緊密的結構意識?畫家自己說:「從來沒有學習過過去人的畫」,何以一出手,就這樣接近如范寬、李成、荊浩等北宋山水典範呢?
中國傳統山水畫的興起,與漢末以降,至魏晉而大興的玄學、道家思想有直接關係。政治的亂象使創作者企圖以老莊的「自然」與名教相抗衡,但更多人選擇韜晦遺世、避入山林;表現在文學上的,是玄言詩趨轉成肆意遊遨的山水詩;詩人寫下:「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輝。……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畫家則走入溪澤峻嶺中,山水畫開始從作為背景的人物畫中獨立出來。六朝畫家宗炳的〈畫山水序〉提出書畫專論,強調「山水質有而趣靈」 ;唐代王維則從詩與畫、理論與創作上雙重實踐,「破墨」與「皴筆」,實質改進山水畫只靠濃淡、容易單調的表現方式,「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則加入了禪意境界,山水畫成了寄託文人胸臆的所在。
從這裡開始,有荊浩氣勢雄峻的北方重巒《匡蘆圖》;有董源岡巒清潤、嵐色鬱蒼的江南《夏景山口待渡圖》及蒼蓊深邃、樸茂華滋的《夏山圖》﹔再有巨然淡墨輕嵐,景色幽深的《萬壑松風圖》。到了南朝後主時的趙幹,繪長江初雪季節,漁人水中作業,入冬時特有的空曠與凋零,畫家用白粉彈作小雪,雪花飛舞就要融入水中。《宣和畫譜》說此畫「樓觀、舟船、水村、漁市……散為景趣,雖在朝市風塵間,一見便如江上,令人蹇裳欲涉而問舟浦漵間也。」 山水畫發展至此,已見氣候。一入宋代,李成、范寬,一個「雨點寒林」,一個「對景造意」,一個平遠,一個高遠;《晴巒蕭寺》與《谿山行旅圖》,畫出宋初山水的兩種風貌,充分體現了山水實景與畫家內心秩序再現之間的關係。這是宋人典雅莊重、和諧蘊藉、節制含蓄的美學,發為文,形諸筆墨,造型藝術,全無二致。詩文如此,書畫如此,瓷器亦同……(未完)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鬱的容顏-李渝小說研究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0 |
二手中文書 |
$ 174 |
文學人物傳紀 |
$ 194 |
中文書 |
$ 194 |
華文文學研究 |
$ 198 |
作家傳紀 |
$ 198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19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鬱的容顏-李渝小說研究
小說家的心裏﹐同樣有一張圖﹐那張圖的顏色蓊鬱蒼青﹐線條不肯同俗﹐不願被框架﹐因為有沃土﹐於是可以憂鬱且豐饒。 ──鄭穎
「溫州街,一條禁錮的、壓抑的,卻又風華絕代的街道。」
李渝寫溫州街巷弄裏花木掩映間纏祟著戰爭與政治的,一樁樁繁華又滄桑的煙雲故事,已然是台北文學重要的一頁。從保釣運動回歸藝術史專業與小說家身分的李渝,敘事腔調節制舒緩,文字精鍊嫵媚,自早期現代主義式的苦悶與悸動,到後期對歷史、藝術的反思觀照,如詩的構句下,蘊含一種超越時空、想要將歷史傷害或暴力扭曲篡奪了人的尊嚴、自由、美的靜謐時刻還原、超越、昇華的浪漫意志。
《鬱的容顏》從李渝的美術評論出發,藉余承堯到趙無極的中國山水畫,探索小說家心源內境的美學起點,並就其戀物癖式的靜物觀微素描,「多重渡引」的複雜敘事技巧,分析其美學、執念、纏擾與思辯,在近乎山水畫的靜謐遠景下,看見暗藏其中的「歷史輪迴卻無聲的暴力與卑微」。
作者簡介:
關於:李渝
一九四四年生於重慶,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藝術史博士,赴美求學期間曾與作家丈夫郭松棻共同參與保釣運動。李渝的創作始於六0年代,被歸為現代主義的創作者。著有小說集《溫州街的故事》、《應答的鄉岸》、《夏日踟躇》、《賢明時代》,長篇小說《金絲猿的故事》,藝術評論《族群意識與卓越風格》,畫家評傳《任伯年──清末的市民畫家》;譯有《現代畫是什麼》、《中國繪畫史》等。
關於: 鄭穎
一九六九年生,台灣省澎湖縣人。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現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著有《野翰林──高陽研究》。
章節試閱
重新開始,手很生疏,像兒童一樣筆筆描著,倒也有初學者的稚情。他記起老師的教導,繪畫以生物為基礎,以生命為開始,以生活為實質,一張畫完成,透露的無非就是這幾件事。
於是以後我們常見到軍官背著畫袋,拿著拐杖,在林泉之間徘徊踟躕,似乎在尋找某種景觀,構思某種圖案。或見他有時呆呆地站在那兒,好像在觀察某種物相,或者細讀某種形體。也見他選 擇一個角落,搭穩架子,要麼就手拿著紙和墊,依著石頭坐下來,聚精會神。
周圍生機洋溢,處處都是寫生的世界,生命並不缺乏。軍官的眼睛一向犀利,看得到物的特徵和細節,捉得住靜態...
於是以後我們常見到軍官背著畫袋,拿著拐杖,在林泉之間徘徊踟躕,似乎在尋找某種景觀,構思某種圖案。或見他有時呆呆地站在那兒,好像在觀察某種物相,或者細讀某種形體。也見他選 擇一個角落,搭穩架子,要麼就手拿著紙和墊,依著石頭坐下來,聚精會神。
周圍生機洋溢,處處都是寫生的世界,生命並不缺乏。軍官的眼睛一向犀利,看得到物的特徵和細節,捉得住靜態...
»看全部
目錄
江行出雪
──從傳統山水畫到余承堯,藉李渝畫論看其小說美學與自我救贖
由「多重渡引」論李渝小說中的現代性與歷史書寫
──從《溫州街的故事》到《賢明時代》
凝視與回望
──李渝的現代主義小說實踐
憂鬱且豐饒
──從李渝畫論,探其身為小說創作者的心源世界
附錄 在夏日,長長一街的木棉花
──從傳統山水畫到余承堯,藉李渝畫論看其小說美學與自我救贖
由「多重渡引」論李渝小說中的現代性與歷史書寫
──從《溫州街的故事》到《賢明時代》
凝視與回望
──李渝的現代主義小說實踐
憂鬱且豐饒
──從李渝畫論,探其身為小說創作者的心源世界
附錄 在夏日,長長一街的木棉花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鄭穎
- 出版社: INK印刻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8-09-24 ISBN/ISSN:986663125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0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華文文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