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昌南也,為製瓷之地,宋代之後易名為景德鎮,西人如是稱呼瓷器,又如是稱呼中國。
可見瓷器不只是用火和土燒成的?更是血與淚。
好瓷凝聚的可是情感。無有情感,無有瓷魂。
而瓷器與愛情是這世間最容易破碎的兩樣東西。
故事從十八世紀的西方開始,一位礦物學者愛上有夫之婦,於是以槍戰決鬥斷定愛情結果,孤單的學者死裡逃生,傷心之餘,他出發到中國,邈遠的東方,為男爵尋找製瓷祕密。漸漸地,他深入這片廣曠的土地,以其科學知識與習得的中文,甚至進入皇宮內苑,成為皇上的寵臣。他沉溺於瓷器與愛情的找尋,並誓為其奉獻生命……
陳玉慧奔途於台灣、北京、慕尼黑三地,以「那個站在東西之間的人」,將靈魂與血汗如投入瓷窯熾熱紅火中,所虔意鍛製煉情煉字煉心之絕美長篇。
跨越迢遙東西距離,連接現今與從前,交流異國文化語言,作者讓中西美學與價值觀對話,真假虛實新古相錯,以意識流的剖白寫法,穿梭男人與女人身體,像要穿過所有最遠的隔閡最堅固的核心最難的謎,只為找尋永世恆存、無以倫比的「美」。
我看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打算從這裡出發。我是那個站在東西之間的人。我在東方,我也在西方。
想像一個西方遇見東方的故事,因為想說,畢竟西方無法體會東方,而東方一樣也不能了解西方。英國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不都說過了?
整部東西文化交流史其實是一部誤會史。
瓷器在麥森被稱為薩克森血碗。可見瓷器不只是用火和土燒成的?更是血與淚。好瓷凝聚的可是情感。無有情感,無有瓷魂。
而瓷器與愛情是這世界上最容易破碎的二種東西。
我自己是在麥森街道上遇見了這位十八世紀的礦物學家,他從這裡開始一段驚心動魄的冒險旅程。挑戰是空前的,因為小說以第一人稱寫成。而他是男子,不但是古人還是薩克森人。因為太不可能了,所以就完全有可能。我便是魏瀚,我真的是。
他曾愛上這裡的女子,為其中一名女子決鬥差點而死,一生註定要為愛情付出。
我也是?
他的愛非關感官,非關精神,他只是需要被喚醒,被激發,他可以愛上所有的無限。
他愛女人,女人的胴體正像瓷器或者玉,他陷入,沉溺,
女人像瓷器般可以包容盛載他的靈魂,他愛上詩歌,他讀過Novalis。
他愛瓷器,他愛中國。
還要再談一次性別嗎?我是女性?男性?中性?或無性?又或者,都是?
我只有在離別後才像個女人。
請你原諒我的心猿意馬,我如果難以抉擇,
那是因為命運開我們的玩笑,他在暗巷中偽裝成另一種面貌。
我的人生因此在彼時有了另一種風景。
所有要說的都說了,事關China……
事關瓷與愛。──摘自陳玉慧著〈薩克森血碗〉
作者簡介
陳玉慧
在台北讀中文系,去巴黎學戲劇表演,到紐約外外百老匯當導演,後來留在德國擔任《聯合報》駐歐特派員。法國國家社會科學研究院文學及歷史系碩士。曾獲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香港浸會大學「紅樓夢獎」決審團獎,及台灣新聞評議會主辦的傑出新聞人員獎等。當過演員和編劇,也導演過許多膾炙人口的大戲,如與明華園合作之《戲螞蟻》。去過許多戰爭和國際新聞的現場,訪問過無數國際領袖與菁英,多年來不定期為德語媒體《南德日報》及《法蘭克福廣訊報》撰稿。被舞蹈家林懷民譽為當代最動人的散文家,文學評論家陳芳明稱以台灣的「世界之窗」,著名德國作家史諦曼(Tilman Spengler)認為是「德國文壇最值得期待的新進作家」。暢銷作品《徵婚啟事》曾改編成舞台劇及電影,轟動一時;而影射台灣百年歷史的長篇《海神家族》已在德國出版,且將搬上國家戲劇院舞台。
陳玉慧在印刻的作品:
海神家族
慕尼黑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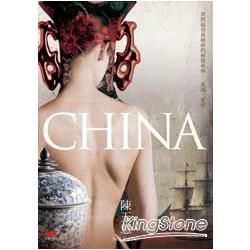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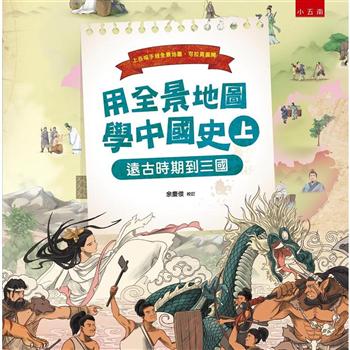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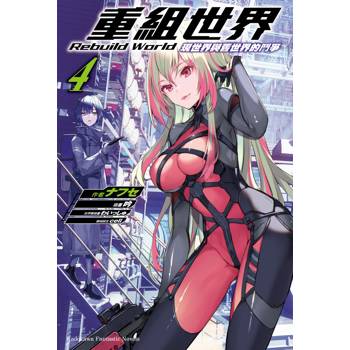

首先,我想不諱言地說:我有些失望。以我對《徵婚啟事》的欣賞,我認為這本書可以寫得更好。 這絕是可引人入勝的題材:瓷器、愛情、中國和一個來自西方世界的目光,拉出距離感卻緊緊相扣。在開頭的部分,處理得不錯,對於主角身邊的失意、灰暗,遙遠的東方神秘、繽紛,充滿期待,這時的景深是很有層次的。 帶進主題:瓷器,這個中國已經發展千年的技藝,早已和中國合一。尋這一脈絡進入中國,幸運地以難遇的速度進入中國的政治核心,並且不屬於任何一個組織,作者為主角安排了一個絕佳冷眼觀望的位置,然後開始用西方的眼光,看清朝乾隆晚期中國的矛盾、封閉和狂傲。 使用書信的方式,交代主角在中國所見所聞,這提供了一個在故事現實之外快速交代情節的捷徑,做為瓷器這個比較生硬、脫離日常生活主題一個拉開距離的描寫,使人不覺得突兀,甚至在閱\讀時可以直接跳過一些和情節無關的書信往來。雖然全書幾乎以日記體的方式敘寫,使用書信來交代事件好像無可厚非,但不得不說,這樣的方式,常常在閱\讀時將讀者帶離原本已進入的情緒,對於整個架構來說其實是不利的,而且由於書信往來的情況全書都有,也就使得整本書的結構顯得鬆散許\多。 以日記型態敘述主角對思慕者的心緒,在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裡已經有很好的典範,在這部分,作者要面臨的挑戰是:歐洲人的口吻。歌德可以駕馭自己的語言馳騁,盡情表現維特的熱情、反省、愁悶到激動、狂喜,無論用什麼文字都不顯得突兀,甚至令人感到一種少年的義無反顧與才能,但在《CHINA》中,這種描寫是必需自律的,必須以非中國式的文字情感來表達,在許\多時候,我認為作者有意識到這件事,但還是有些失誤,以下舉出一個明顯的例子: P.239 宅院裡一棵古老的槐樹,從外面看起來,宅第已開始露出衰敗的跡兆,門上的油漆早已剝落,一抹陰氣散之不去。 槐樹的樹影重重。 第一段所用的文字,就主角旅居中國的時間來看,寫出這樣的句子還算符合實情,然而第二段:槐樹的樹影重重。實在是個失誤。樹影重重的意象是非常中國的,並非一個外國人隨意可以寫出的句子,加上槐樹這個意有所指的樹種(主角是礦物學家,對植物的辨識恐怕不會特別留意),槐拆開為「木鬼」,在中國由字型化為引申含意的代表之一;於是,讀到槐樹的樹影重重一句時,一種和主角剝離的感覺湧來,覺得很不舒服。這樣的感受在書中一些地方像是棍棒一次一次的敲擊著腦袋,我認為這是可以再寫得更好的地方。 另外是愛情的情節不足。或許\我們得體諒作者已經在處理瓷器和歷史背景上著力甚多,以至於在愛情的主題上,成了連結這些事件的附屬品,在情感的流動上,沒有很好的一致性,澎湃時不見細膩、細膩時不見熱情,而情感的轉變也在書信中完成,少了角色間互動而產生轉變的張力,這是很可惜的──如何去調和西方男子情感的熱情、外放與東方女子感情的神祕、內斂,真得是很難的課題,我認為以作者對男女情感的觀察,其實可以做得更好。 書末的附錄,讓我們見識到一本書的難成,身為作家的努力,但我不禁要問,當千辛萬苦而得書成之後,是否畫成了自己原本所想達成的模樣?──這要問問讀者吧?再問問成為讀者的作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