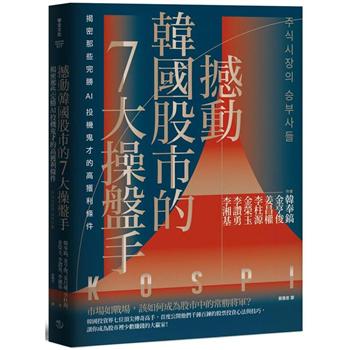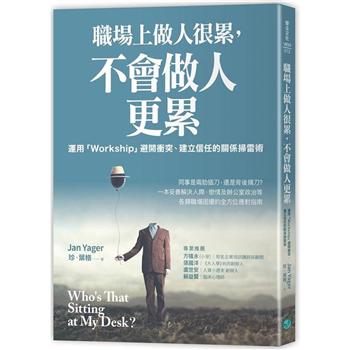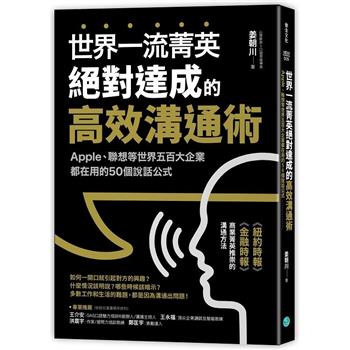一百年前如星塵飄落古老清末宮廷霧翳景片
西洋鏡流水般緩緩捲動時代的兩度春秋
最懾心動魄的兩段不可思議愛情故事
1903年春天,清朝駐法公使裕庚的女兒們,年輕、漂亮、聰慧的德齡和妹妹容齡,本來有機會跟著上個世紀初最偉大的舞蹈家、現代舞蹈之母伊莎朵拉.鄧肯繼續習舞,卻在回到中國時,機緣湊巧,走進充滿秘密、風雲詭譎的皇宮裡,成為全中國權力最大卻也最孤獨封閉的一群人身邊面對廣大新世界的翻譯者,窺見沒落王朝衰亡前的最後掙扎。
經歷、價值觀都堪稱「中西合璧」的這對絕代雙驕,對愛情、國家同樣存有熱情與幻想,也為這個彷彿深不見底的清宮大內帶來一次次東西方文化撞擊的活力,但她們越來越不確定,牽動自己與未來中國命運走向青春幻滅的,是怎樣茫茫不可知的巨力?
有什麼在那巨力下靜靜潛伏、茁長:德齡跟美國醫生凱.懷特之間的祕密愛情,容齡跟念念不忘死去珍妃的光緒之間的純真情愫,跨越膚色、階層、理念間的友情,險象環生的幾次宮中危機,至親間的扶持與牽掛,慈禧太后或是光緒帝從不向外人傾訴的心事和愁緒……
「德齡,我們都是一樣有幻想的人……但是這些幻想還是改變不了皇爸爸。」
舞蹈,染髮,照相,化妝,咖啡,花草茶,電影,婚禮,牙醫,打針,點心,話劇,精神分析解夢,肖像油畫,洋裝,報紙,鋼琴,座鐘,音樂盒,手槍,飛行器模型,腳踏車,汽車………見證世紀之交邂逅的文化與愛情。
那徹底覆埋陳舊中國的,是那些充滿奇技淫巧的「古怪新奇玩藝兒」?還是不能撼動不能戳孔的保守心態?
並不具有真正公主身分的德齡姊妹,卻在短短兩年間看盡慈禧、光緒與宮眷們扮上的與卸下的角色妝扮都同樣複雜難以言傳的靈魂機關;在懷抱著引介域外新事物改變舊中國的期望同時,也深刻感受到有什麼脆弱的東西也隨之而去了。夢想畢竟還是夢想,但卻留下了許多不會再有的珍貴回憶與友情,與誤闖危局詭局的凶險經歷;以及,那些不常擁有真正歡笑的人們的赧顏與側臉暗影,和夜明珠般散發幽光的幾滴眼淚。
純淨卻曲折的愛情,層疊纏祟的恩怨,凝實的文化內蘊,靈動富麗的京味語言,更大膽重新定位歷史人物形象與評價,可說是當代傑出女性說書人跨越時空寫下另一位女性眼中清末宮廷生活的精緻多寶格袖珍櫥窗。
2006年8、9月間,《德齡公主》作家親自編劇,由中國中央電視台製作電視連續劇集,於黃金檔時段播映。
關於「德齡公主」裕 德齡:
清裔正白旗貴族,1886年生於武昌,著名旅美作家。其父為前清駐法公使裕庚。1895年,德齡9歲,隨父出使日本,後赴巴黎,成為現代舞大師伊莎朵拉.鄧肯入室弟子。1903年,裕庚任滿回國,17歲的德齡偕么妹容齡隨全家返抵北京,入宮覲見後獲得慈禧太后寵信,封為御前女官,擔任傳譯,後受封為郡主。至1905年3月因父病請旨出宮到上海。
1907年5月,德齡與美駐滬副領事懷特結婚,1915年移居美國,開始用英文寫作,著有《清宮二年記》、《清末政局回憶錄》、《御苑蘭馨記》、《瀛台泣血記》、《御香縹緲錄》等多部回憶錄與紀實文學作品,並於作品中署名Princess Der Ling,在海外名噪一時。抗戰期間,參與宋慶齡在港發起的「保衛中國同盟」,鼓吹海外華人、華僑共同資應抗日戰爭。1944年11月,在加拿大車禍喪生,終年58歲。
以德齡為主角的作品,至少包括2006年在中國播出的電視連續劇《德齡公主》,以及以回憶錄為本的話劇《慈禧與德齡》。
作者簡介
徐小斌
原籍湖北,出生於北京的知識分子家庭,曾上山下鄉,1982年畢業於中國中央財政金融大學,現為中國中央電視台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一級編劇、中國作協會員、北京作協理事。
1981年起發表文學作品,迄今創作逾400萬字。中篇小說〈雙魚星座〉獲中國首屆魯迅文學獎;長篇小說《敦煌遺夢》獲第8屆中國全國圖書金鑰匙獎、年度中國十佳長篇獎;短篇〈請收下這束鮮花〉獲《十月》雜誌首屆文學獎,中篇〈異邦異族〉獲《鍾山》雜誌優秀中篇小說獎;散文〈海幻〉獲中國全國青年散文大獎賽創作獎。1998年獲中國首屆女性文學創作獎。部分作品被譯為英、法、日、義等國文字,在海外發行。
著有長篇小說《海火》、《敦煌遺夢》、《羽蛇》、《海妖的歌聲》,中短篇小說集《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迷幻花園》、《雙魚星座》……等十餘冊;散文隨筆集《世紀末風景》、《薔薇的感官》《繆斯的困惑》、《出錯的紙牌》……等。並有作品選集《徐小斌文集》5卷出版。另有美術作品集《華麗的沉默與孤寂的饒舌》;電影編劇作品《弧光》(獲第16屆莫斯科電影節特別獎,由中篇小說〈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改編),電視劇編劇作品《德齡公主》等多部。
徐小斌的BLOG:blog.sina.com.cn/xuxiao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