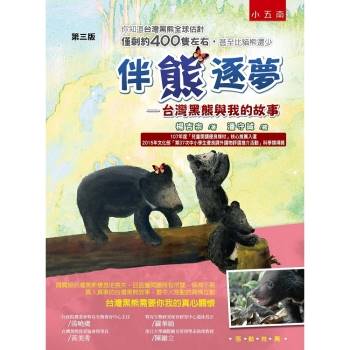本書以「蔣中正的一九四九」為題,並不準備對蔣中正在一九四九年的各項作為進行研究,而是將重點置於蔣中正自一九四九年一月下野至一九五○年三月復行視事一年多的時間中,探討他如何再起?再起的過程與機遇。全書除前言、結論外,分為五章:第一章「第三次下野」,探討蔣氏決定下野的原因,以及下野之經過;第二章「從溪口到臺北」,敘述蔣氏下野後,居留溪口的生活,以及轉赴上海、舟山、臺灣等地之過程;第三章「建立黨政關係常軌」,分析蔣氏在杭州會談、成立非常委員會,以及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院長等事中的地位;第四章「維護大陸最後據點」,探討蔣氏兩度至西南的情形,以及其在李宗仁出國後,角色如何轉換,從幕後走上前台;第五章「在臺復行視事」,探討蔣氏個人對於復任總統問題的認知,以及復職一事進行之經過。
本書重點在探討蔣中正在一九四九年下野之後,如何重新再起,復任總統的過程,以及他個人對相關問題的思考、判斷。資料方面以蔣氏所留存相關資料,包括國史館庋藏《蔣中正總統檔案》、《蔣經國總統檔案》與蔣氏家屬所保存《蔣中正日記》; 及史政單位所收集或保存之蔣氏相關資料,如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總裁檔案》、《會議記錄》等為主。此外並參閱相關當事人留存之資料,如張群之《中行廬經世資料》,邱昌渭往來函電,張群、吳忠信、徐永昌、閻錫山、居正、胡宗南、丁治磐、雷震等日記,以及李宗仁、黃旭初、程思遠、蔣經國等回憶錄。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常有一些年代具有歷史轉折的特殊意義,而成為歷史研究的主題,一九四九年即是其中之一。在國共戰爭的較量中,中國在一九四九年出現重大的變化。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華民國首都南京陷落,政府遷到廣州;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布成立,開啟了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局面。而中華民國政府在軍事失敗一路轉進的情況下,從廣州、重慶、成都,於十二月初播遷臺北,形成此後將近一甲子的海峽兩岸對峙局面。有研究者稱一九四九年為「中國的關鍵年代」,謂: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得到勝利並沒有帶來和平。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年間,戰後中國政局演變至為激烈,國共的慘烈鬥爭隨著東西冷戰的形成而益趨複雜。此期間一九四九年的變局:中共建國、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臺灣、加上接著發生的韓戰,造成其後半世紀海峽兩岸的長期對峙,實是歷史上的一大轉折。
亦有研究者認為這一年是「中國社會的大變革」,表示:
一九四九年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並不只是一個政權代替了另一個政權、一種政治力量代替了另一種政治力量,而且是一場中華民族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大變革。
更有研究者如此形容一九四九年的重要性:「一九四九,不僅是一種符號,更是時代的爆破點,它造成了前所未見的歷史海嘯。」但是不論如何陳述,從本質上來看,一九四九年是一個動盪的年代。
作為一個動盪的年代,一九四九年可以討論的人與事很多,但是相較於西方學界對於戰後國共關係或失去中國的研究,或許一九四九年所具有的特殊意義,海峽兩岸學界關於「一九四九年」的學術研究,在一九九九年之前是較為少見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一些過去視為敏感的議題不再是禁忌時,一九四九年相關的人與事逐漸成為歷史研究的主題。
一九九九年為「一九四九年」的五十週年,是年十二月,臺北與北京各自舉行一場以「一九四九年」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推動了一九四九年的相關研究,會後分別出版《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及《劃時代的歷史轉折-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兩本會議論文集,呈現出關於「一九四九年」的初期研究成果。此後,以一九四九年為主題的研究陸續出現,如傅國湧從十四位知識份子一九四九年的日記,探討他們個人在這一年的生活、感覺;張仁善從軍事、經濟、城市、農民、知識份子、學校、工商界、媒體及社會問題等九個方向,探討一九四九年的中國社會變遷;陳錦昌以「遷臺」為主軸,參閱相關史料及論文,建構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臺灣的過程;吳興鏞根據其父吳嵩慶遺留的資料及相關檔案,探討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中央銀行庫存黃金運臺的經緯; 林桶法以「大撤退」為題,探討蔣中正暨政府機關與人民於一九四九年遷臺的經過等。
此外,亦有以一九四九年國共軍事戰略、知識份子抉擇為主題的相關論文。日本學者也注意到「一九四九年」在民國史研究的重要性,自二○○二年起進行連續四年的研究計畫,並於二○○六年十二月出版久保亨編著的《一九四九年前後之中國》,從「斷裂與延續」的角度探討一九四九年前後的中國,為一九四九年研究提出一個新的思考方向。
在一九四九年的研究中,蔣中正及其相關人與事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主題。蔣中正身為中華民國總統,雖然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宣布下野,但是仍然擔任中國國民黨總裁,政治上的影響力並未因此而減弱。而代行總統職權之副總統李宗仁一再指稱他在幕後操縱政局,甚至要求其出國,更顯示他在這個關鍵年代的特殊地位。在蔣中正的相關傳記中,對於他在一九四九年前後的相關活動,大多闢有專章,作相當篇幅陳述,但是以此為主題,進行討論之學術論文或專著並不多見,反而有不少非學術性作品出現,以類似小說的筆法敘述蔣氏在這一年的經歷。
對蔣中正而言,一九四九年是他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年。他於一九四九年日記之總反省錄中回顧一年來身受各種遭遇,記道:
本年一年中之生活,所見所聞與身受各種遭遇,無非為人唾棄,為世譏刺,恥辱悲慘,於茲為甚。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重閱一九四九年之日記,記道:
重閱三十八年日記,更覺當年環境與形勢之可怕,至於悲慘與侮辱之經歷,則不足道矣。
至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一日,回憶一九四九年底西南失陷的情形,記道:
回憶三十八年杪,渝蓉陷落之情勢,匪軍縱橫,所向披靡,敵騎未至,疆吏早降,民心土崩,士氣瓦解,其敗亡形勢,不惟西南淪陷莫可挽救,即臺灣基地亦岌岌欲墜,不可終日。當此之時,共匪定余為戰犯,欲得而甘心,而一般叛將敗類,設辭攻訐,更予人不堪之侮辱,乃以中正為仇寇之不容,而反以共匪為可君矣。
從這三段日記來看,蔣氏不僅在一九四九年當年,即使在時隔數年之後,對於這一年各種經歷的記憶,依然是「悲慘」、「侮辱」,顯示一九四九年對他而言,有著難以磨滅的悲憤。
除了日記上的自我反省外,蔣氏亦曾多次在對中國國民黨黨員講演中,以「亡國」兩字形容一九四九年的處境,表示:「本黨的革命事業到了今天可以說已經失敗了!總理領導我們艱苦奮鬥建立起來的中華民國,已經在我們手裡被敵人滅亡了!」並強調自己不僅是帶罪之身,而且是以「亡國之奴」的心情來對同志講話;藉此激勵黨員同志。
在一九四九年一直隨侍蔣氏的長子蔣經國,於一九五九年撰寫之〈危急存亡之秋〉,以「日記」體裁,陳述個人在這一年的經歷,但就其內容而言,充分呈現蔣中正在一九四九年的心情與處境,為蔣氏一九四九年日記未公佈前的忠實記錄。他在該文〈自序〉中稱:「民國三十八年,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在這一年之中,國家民族所遭遇的危險困難,以及我父親所處的地位環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惡劣和複雜。」
蔣中正對於一九四九年雖然感到屈辱、悲憤,是革命生涯中最大的挫折,但是從他一生事業來看,一九四九年亦是他人生另一個階段的開始;雖然被指稱為「失去中國的人」,卻是建設臺灣的奠基者。論者嘗謂蔣中正是一個「大冒險家」,若就一九四九年的挫折與再起來看,確實如此。蔣氏從一九二四年五月出任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至一九七五年四月病逝於中華民國第五任總統任內,執掌中國軍政大權達五十年之久,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具影響的人物之一。
在這五十年中,可以一九四九年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五年,蔣氏的活動空間在中國大陸,從領導北伐、剿共、抗戰至戡亂,是他生涯中的第一個階段;一九四九年底,國共戰爭失敗,政府播遷臺灣,從一九五○年至一九七五年的二十五年間,蔣氏在臺灣,創造了他生涯中另一個階段。但是蔣氏如何扭轉他個人的命運?
蔣中正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下野之後,除了在溪口的三個月,生活較為安定外,其餘時間大多是奔走於政府所控制的各個地區,從上海、舟山,到達臺灣,再以臺灣為基地進出大陸,至福州、廣州、重慶、成都、昆明、廈門等地,力挽危局;期間還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份,赴菲律賓及韓國訪問,結合反共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下野之後,沒有任何政府的職務,只是中國國民黨總裁,依憲政體制,執政黨的領導人應遵守黨政分際,不應亦不宜干預或主導屬於政府部門的軍政事務,但是以他掌握中國軍政大權二十餘年,所累積的政治實力與能量,實不容許他置身事外。蔣經國曾引述蔣中正的話語說:
本年憂患艱危忍辱茹辛,在內奸外敵重重包圍夾擊之下,幾乎無倖存之理,而乃竟能出死入生堅忍不撼。
蔣經國亦說
父親自三十八年初,第三次下野以來,一直到舟山撤退為止,可說是最艱苦的時期;然而用最大的忍耐力,把這個最嚴重的難關渡過了。
蔣氏為何「忍辱茹辛」?為何「用最大的忍耐力」?他如何在黨、政之間取得他的位置,持續在軍政事務上的影響力?如何能「以在野之身對內對外」?以及如何復任總統?筆者認為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