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抄襲的知識社會學─民國以來史學界最大的集體舞弊疑雲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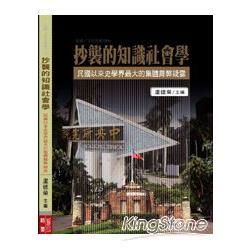 |
抄襲的知識社會學─民國以來史學界最大的集體舞弊疑雲 出版社:時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9-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08 |
中文書 |
$ 308 |
史學理論 |
$ 315 |
社會學總論 |
$ 315 |
歷史概論 |
$ 315 |
科學科普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本文針對台灣的抄襲文化,對「抄襲」一辭勢必無法迴避,特別我身為教師以勸勉學生不許抄襲為業,歷有年所。本文所稱抄襲,不是指逐字逐句的呆板方式,而是指文章外貌經過精心改裝、變裝,但骨子裡的原創意內容卻出自李敖著作,但不表明出處的一種文化活動現象。在學術界,此種行為因為違反學術倫理、以及公平正義原則,已足以令社群認定是違規、會推翻社群前提的行為,屬於可受可評之事。至於在法院,實務上,本文所提及三人之行為是否構成侵權,並非本文論述的基礎。本人認為以上現象事關台灣史學界存亡之公共利益,不得不予以揭弊,也請史界中人、及所有讀者一起參與判斷和檢視,以導正歪風。本人所提三人乃中研院的資深研究人員,其中有兩位已論及院士桂冠之頒授,可說動見觀瞻、影響深遠 。中研院乃國家學術重鎮,自是應比一般大學教授還要高的道德標準以相繩,遑論以法律層級屬於最低道德標準的東西來作為自律的規範。
為了杜絕中文世界行之數百年的抄襲歪風,我建議全民公審此一現象,敬請給本刊回函以示該三人所為是否抄襲,本刊會保存這些回函,以供各界改進之參考。
壞的開始是失敗的全部。已經失敗了還在那裡拖死狗,於是我們看到五個學術世代的集體大墮落,外加大學閥集團的營私舞弊案。整個史學體制就像一位行將就木的鴇母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還有人不斷地給她戴桂冠、贈以花圈,這鴇母家的門外一條長達一公里的人龍是各地湧來的朝聖致敬團。用『物必自腐而後蟲生』都不足以形容現代中國史學體制的源頭,遑論其現狀是杜xx所加諸其上的創意腐化工程呢。
本期的主題是抄襲成風及其共犯結構。在先進史學國家,莫說犯了抄襲是唯一死罪,肇事者沒得話說,連教授在課堂膨風、好吹大牛者亦被視同學術詐欺的行為。最有名一個案例是某大學教授在課堂講述越戰,講著講著說他在越南戰場如何英勇,後來該教授被查出,根本沒去過越南。當謊言拆穿之日,就是這位假越戰英雄消失史學界之時。學術不可詐欺,是觀察一個個國家是否一流的一大重要指標。學者的職守是生產知識,倘若在這一個程,吹噓、造假,無惡不作。國人如何仰賴這些所生產的知識用以建設國家、提升國家呢?告訴國人一個重大資訊:一流國家罕有抄襲事件,故爾沒有抄襲問題。只有我們三流國家因抄襲成風,根本無力解決此一嚴重問題。比這還糟的是,我們還頒發學術桂冠給抄襲者,直到東窗事發才摘下其桂冠。一流與三流之差異,相差何啻霄壤?
台灣的史學體制傳承自20年代中國大陸由胡適、傅斯年所建造的那套史學體制。胡、傅均留洋,卻未悉西方現代史學底蘊就束裝返國,之後很快就搶佔主流權力位置。傅、胡先後跟著國民黨撤退來台。於是,那套自以得西方嫡傳的史學體制又在台灣生根、繁衍起來,史學體制的司令部就設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台灣大學歷史系這兩個聯盟機構。傅很快就去世,這個體制的幫主寶座傳給傅事業的夥伴李濟,這是台灣擁有史學的第一代,即傅、李兩人。
這個體制充滿著落後性與腐敗性,積弊叢生到不行。它早就淪為與法國大革命前夕那個即將被打倒的舊體制沒有兩樣。台灣民眾逕稱它為舊體制可也。舊體制到了台灣,根本收不到優秀的學生,好不容易收到一位,卻被他給溜走。此人就是李敖先生,他在就讀台大歷史系之時,即聞到舊體制的屍臭味,中途綴學之後提筆為文要求史語所和台大史系的兩位負責人,李濟和沈剛伯交出棒子。在1961年,李敖的〈老年人和棒子〉一文清楚照出舊體制的腐朽和不堪。五十年後的今天,李敖所批舊體制的沈疴如今不僅仍在,而且病勢愈發加重。
1990年代,台灣史界有三路人馬湊巧地把中國文化的學術議程給端出枱面來,這三路人馬分別是杜xx集團、李敖個人,以及盧建榮個人。各自經十年的努力,李敖將主要成果結集成《中國迷信新研》,盧建榮主要是「台灣五部曲」和「唐代五部曲」共十本專書。只有杜xx該派成員這一路最不成才,領有國家天文數字的獎助和公家機構的設施和資源(史語所一所年度預算從1990年破億起,逐年扶搖直上,已歷二十年),結果,成員個個做不出來,只好把李敖的辛苦創意給全抄了。這些成員還因此獲獎無數(幾十萬、幾十萬白花花銀子在頒贈),如今真相大白,這些高額獎金理當全歸李敖所有。杜xx集團秉承師門交付的血仇,絕對要與羞辱其師門的李敖勢不兩立,沒想到一代不如一代到向李敖交心到完全拜服在李敖腳下。
敬請讀者給我們指教和鞭策,大家一起來關切嚴重的抄襲積弊問題。本刊相信台灣是個有救的社會,一定要設法阻止它自尋死路。
最後,本刊有三篇報導揭弊文章,承蒙李敖先生事先過目,並惠予指教。至為感激。
專號‧序――台灣史界的深層崩壞
我對研究社會/文化現象的聲明
台灣史界集體抄襲疑雲事件
案例一:台灣權勢集團抄襲成風――杜正勝麾下青澀學究不恥
下抄民間學者李敖/盧建榮
案例二:一路獎不完的院士高徒,原來是史上最大文抄公/盧建榮
案例三:國立大學文學院長,竟是玩票文化活動者/盧建榮
社論‧抄襲政治學與其共犯結構
⊙自由論區
古中國災異論述之建構過程――以《史記》殷、周二〈本紀〉文本
為中心之探討/沈柏宏
千面「甘露」及其多方打造的歷史――兼論祥瑞文化在百科全書中
取得欄目並定型過程/宋天瀚
閱歷蓬萊...
- 出版社: 時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9-01 ISBN/ISSN:978986665355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史學理論
|









![2026【補充延伸實務趨勢與議題】觀光資源概要(包括世界史地、觀光資源維護)[華語、外語領隊人員][二十一版](領隊華語人員/外語人員) 2026【補充延伸實務趨勢與議題】觀光資源概要(包括世界史地、觀光資源維護)[華語、外語領隊人員][二十一版](領隊華語人員/外語人員)](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6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