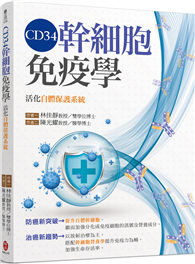從原鄉到他鄉,從南到北,從台灣到人類世界……詩人隨著命運的流轉、青春的行踏,在桃園落地生根。他為島嶼書寫頌歌,對地景的凝視,對時間的體會,對生命的感受,對現實的關懷,每個瞬間,都化為樸實而雋永的詩句。
本書為林央敏2007年以後的最新詩集,共收錄近十年來所發表的百行以下的小品詩共54首。內容大多以其生活的家鄉景物為焦點或起點,再擴及台灣和世界。由於林央敏志在溶合中、西的即景詩傳統,因此文字風格異於一般以「風花雪月山水情」為主的傳統即景詩和地景詩,而是在寫景、抒情之外,也含有歷史人文與社會現實的寫真或諷喻,更有少數篇幅較長的作品猶如微型敘事詩。多數作品特別講究語言的聲韻之美,將自由體的白話現代詩賦予某種格律和韻律,為詩人對聲音美感的追求,更是沉澱十年、細心雕琢的一片詩風景。
◎本詩集由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贊助出版
作者簡介:
林央敏,1955年生,嘉義縣太保市人,現居桃園市。曾任小學、大學教師、台語文推展協會會長……。現任《台文戰線》文學雜誌社發行人。曾獲聯合報文學獎第一名、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及詩獎、散文獎、小說獎、評論獎、文化獎等多項文學獎,是台灣民族文學的代表性作家。
1965年即寫古詩、’72年首次發表新詩、’83年開始台語寫作。首倡台灣民族文學,是戰後台語文學運動的倡導作家及台語文學理論的主要建構者,也是首位將台語散文由說理引入純文學領域的詩人。’86~’97年間熱衷民主人權、民族解放、本土文化、母語文學、教育改革等社會運動。作品因觸犯官方禁忌屢遭查禁封鎖。
寫作品類豐富,風格、技巧與主題多樣,另有作曲與電腦軟體,被稱為全方位作家。有百餘篇作品分別選入詩、散文、小說、評論的各類選集百餘種,並選入大、中、小學教科書中,部份作品被譯為英、日文發表於外國書刊。著作三十餘冊(詳見本書附錄),其中11萬字的詩體小說《胭脂淚》是台語文學第一部史詩(EPIC),也是台灣文學史至今最長的敘事詩;詩作〈毋通嫌台灣〉被譜成24種不同的曲子,對催化台灣人意識與民主運動皆有深遠的影響。
林央敏文學田園網址:http:// blog.roodo.com/tw_poem
章節試閱
桃園地名有感
這塊土地
曾是凱達格蘭的故居
山中仍是泰雅在掌理
從「虎茅庄」到「桃園市」
是荒蕪到熱鬧的距離
兩個名字相隔三百年
1905才定型「桃園」
身分卻像漂泊的浮萍
在新竹與台北間擺盪
1950自立成縣,名字
曾用來命名村鎮街區
也用來標記郡縣廳市
落霞與孤鶩齊飛
直轄與一區同名
桃園是全台唯一
地名繁衍,轄區漫延
一如「大員」伸展成「台灣」
又如「艋舺」擴大為「台北」
如今大員改名叫安平
艋舺依舊駐足老街區
只有桃園是青青河畔草
能夠伸長綿綿的遠道
在全區與全市間蜿蜒
從前的桃仔園留在小桃園
現在的桃園市已成大桃園
村庄長胖,城市長高
土地的神經有感地名沒變
*******************
千塘之鄉
當你乘風回台灣
想念家園的眼睛往下望
會看到大大小小的藍水晶
鑲在一片疊高的平原上
那是辛勤耕作的桃園郎
用二百年汗水滴成的埤塘
雖然桃花凋謝,桃子省略
整片失踪的桃仔園,還留
這些鏡子映照先民的心血
遠古時候,大漢溪從石門奔離
大江西去,將桃園沖積成台地
後來陷落的台北把河流拉過去
叫望水興嘆的農民自己興水利
他們開鑿看天池,一陂又一陂
雨季後讓天空掉入這些軟玻璃
夜裡就讓星星化做珍珠來寄居
終於創造出荒漠變良田的奇蹟
擺放千顆水晶的密度世界第一
現在兩條動脈 伸向二千八百塘
用支流編織灌溉生命的微血網
是稻米飲水解渴的銀行
是魚蝦與飛禽悠閒的天堂
更是市民放鬆心情的地方
龍潭連士校、八德接茄苳
都像青塘園那般生態盪漾
這麼多美目在巧笑倩兮
唯有桃園地──千塘之鄉
*******************
擁擠的河──桃園大道記
台1線流來流去,
北越龜崙嶺,南出楊梅壢,
是一條縱貫桃園的大河。
盤踞兩岸的堤防高矮不齊,
會伸出腹地,把河道推得更擠。
車龍如水如船隊,紛紛噴霧氣,
二腳獸只能穿行縫隙,
喇叭聲像人工天籟彼落此起,
危險夾在紅綠燈的交換閃爍裡。
靠近奇士美廠房的路口
有車受傷,後方變身停車場。
屁股貼著NoKiss的飛羚
觸倒一匹125CC的野狼,
狼騎士的血被朝陽舔乾,
如兩片凋落的玫瑰花瓣。
塞滿公車的上班族蠢蠢不安,
速度熄火,時間還在動,
想用什麼理由搪塞打卡鐘!
電線桿早已取代行道樹,
離地1.5米處的腿部
長出一片片五花八門的皮膚,
上有刺青:「吉屋租售」最醒目。
為了建構美化道路的政績,
許多盆栽點綴在市區的路邊,
希望移植一些零碎的春天,
被緊張氣氛灌溉的花木多可憐,
來不及枯乾的也獨自蔫蔫。
大病院過去是大工業區,
中間有瀕臨丁字路的平交道,
長官們研議20年的陸橋還沒建好,
已換成鐵路高架和地下化在爭吵,
柵欄頻頻垂低,怨氣時時升高,
警衛當雕像,靜觀人車搶道,
一輛載鐵條的貨車被火車撞倒,
貨車甩尾,鐵條抓破自強號,
只有火車時刻表重傷,真是幸好!
幸好在這條桃園大道兩側
開了國1、國3大運河,
南來北往的遠行客
不用再受困擁擠的河。
現在官廳膨脹,市長升格,
不知權力能否升級為氣魄,
將擱淺的水聲改寫成快歌?
桃園地名有感
這塊土地
曾是凱達格蘭的故居
山中仍是泰雅在掌理
從「虎茅庄」到「桃園市」
是荒蕪到熱鬧的距離
兩個名字相隔三百年
1905才定型「桃園」
身分卻像漂泊的浮萍
在新竹與台北間擺盪
1950自立成縣,名字
曾用來命名村鎮街區
也用來標記郡縣廳市
落霞與孤鶩齊飛
直轄與一區同名
桃園是全台唯一
地名繁衍,轄區漫延
一如「大員」伸展成「台灣」
又如「艋舺」擴大為「台北」
如今大員改名叫安平
艋舺依舊駐足老街區
只有桃園是青青河畔草
能夠伸長綿綿的遠道
在全區與全市間蜿蜒
從前的桃仔園留在小桃園
現在的桃園市已成大桃園
村...
作者序
讓即景小品溶合中西傳統
在交通不便、以農立國的時代,故鄉/家鄉與他鄉/異鄉絕對是涇渭分明的兩個概念和兩種感情。到了工商為主的現代,發達的交通網路打破土地籓籬並用速度把距離縮減了,使家鄉與他鄉有連在一起的感覺而不知何處是他鄉,我想1980年代以後出生的台灣人,當他們搬家或離開生長的地方後,不會有濃厚的鄉愁,因為他們的「故鄉感」淡薄如絲了。
我生長在安土重遷的農業時代末期,故鄉感自然很重,不過因為謀生的關係,也長年客居他鄉,結果就像古人所吟的,先是「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變成「夢裡不知身是客,直把異鄉做故鄉」,最後是落地生根客居久,異鄉已成新故鄉。對我來說,嘉義和桃園都是我的家鄉,前者是命,後者是運,命運使我有了第一故鄉和第二故鄉,我的名字也只有寫在這兩個縣市的戶籍簿裡。這是以較小的鄉土情懷定義出來的家鄉,要是從較大的國家意識或國際觀來看,整個台灣就是我的家鄉,本書作品的背景有十分之九都屬台灣,其中大部份的地景都在桃園和嘉義境內,因此以「家鄉」為名。
而為何取名「即景詩」呢?這就得說明寫作這些作品的理念和作品產生的動能了。
如眾所知,所謂「即景詩」,通常指「因時生感,即景言情,興到筆隨」的有感而發之作,所以又叫「即興詩」(extempore poetry),所表現的內容多屬描寫景物和因景而生的感情。既為即興偶得,自然大多數都是袖珍型的小品詩,觀之包括中國與台灣在內的整個漢語文學可說都是如此,這裡頭不只作者有明言是「即景、即興、偶得」的作品,如宋代朱淑貞和明代王冕的〈即景〉,前者為七言絕句,後者為七言律詩,都是古典詩的小品,其他絕大部份的短詩在性質上其實也是即景詩,曹植的〈七步詩〉、鄭板橋的「送賦」和「吟蟹」固是有名的即興之作,幾個傳為美談的文人雅集如蘭亭修禊、金谷酒數、龍山落帽、桃李春宴、福台閒咏等等,每位參與者其實都在寫即景詩,李白、杜甫、白居易……這些古代詩人的小詩也差不多每一首都是見景、臨場、感時而起興的詠嘆攄懷,其中最長的也許應屬《紅樓夢》第五十回裡的那篇「蘆雪庵爭聯即景詩」,以五言寫成,前後共70句,但它是曹雪芹寫賈寶玉和寶釵、湘雲、黛玉等十二金釵在玩賦詩接龍的文字遊戲而已,不能算是一首完整的即景詩。
台灣詩壇應是深受傳統漢詩的影響,格律解放後的現代詩人所寫的自由體白話新詩也如出一轍,雖不叫即景賦詩,但實為即興小品,而且十之八九的作品,內容不出風花雪月鴛鴦夢和悲歡離合兒女情,這類小品詩人多如過江之鯽,密度不下於埤塘裡的烏尾冬,大概也是因為這類題材好寫,容易產生詩情畫意,所以多數詩人才熱衷於雕琢一己私情,而為了避免文字顯得陳腐,便亟亟於扭曲文法、轉化詞性,競相弄巧爭奇,結果便是字義模糊,內容不著邊際,使讀者如墜五里霧,彷彿讓詩產生這種晦澀效果才叫意象新穎或文句獨創。這種好耍文字拐子花的現象倒是最近半世紀才格外火紅興盛,迄今不衰,這種現象讓一些講究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古代詩人看了,相信他也會自嘆弗如。
如前所述,觸景寄情儼然已成為漢語即景詩的傳統,至少是最大宗的一種典型,但我覺得即景詩不該拘泥於此,不能只有寫景、詠物和抒情,我認為即景詩也可以擴大篇幅,加入歷史、文化、思想、社會、政治等土地與人文的素材,並且可用於寫實紀事,使它的內容更豐富,更有歷史感或現實感,在這方面,我以為西洋即景詩的寫實紀事傳統值得我們借鏡和學習。說到西洋即景詩,我首先想到的是英國桂冠詩人丁尼生(Afred Tennyson, 1809-1892)的《國王即景詩》(Idylls of the King),這篇可說是即景詩發展的終極型態,由12首描述亞瑟王傳奇的敘事詩組成,因此又被稱為「國王敘事詩」。由此可見即景詩也可以在寫景詠懷之外加入說故事,丁尼生這篇詩曾經給我靈感,在史詩《胭脂淚》裡讓角色觸景生情想起往事,敘說一段故事。但我又想,我們也不必把即景詩都變成敘事詩,畢竟用詩說故事是文學創作上絕頂的難,不是真正的大詩人無以為力。因此我又想到古羅馬詩人佛吉爾(P. Virgil, BC.70-19),他的小品詩《牧歌》(The Eclogues)和《農事詩》(The Georgics)都是描寫自然、吟詠田園之作,可做為改造並深化漢語即景詩的最佳類型,前者較短,優婉感性;後者較長,描寫田間的生活與工作,具有寫實風格,而為了增加趣味,有時會帶入一個掌故或一段神話。
佛吉爾寫作田園詩(pastoral poetry)正是師承希臘亞力山大時代的西洋即景詩的奠基者狄奧克利多斯(Theocritus),狄氏的即景詩讀來就像在欣賞民間風俗畫,甚至可說是一篇民間風俗小劇,背景有田野、城市或海邊,內容偏於寫實,加上他個人的詩才及敏銳的感受性,使他的小品詩同時具有真實和理想的美。狄奧克利多斯的寫實紀事風格使即景詩成為一種重要詩體,不只影響佛吉爾,也影響後世文藝復興時期的許多意大利和法蘭西的即景詩人,到十八世紀法國古典主義末期的詩人謝尼葉(André Chénier, 1762-1794)都是他的傳承者,有希臘血統的謝尼葉情感奔放,對美、正義和真實的愛好極為熱烈,很推崇狄奧克利多斯的寫實精神,他寫詩不避諱對時代、對政治的口誅筆伐,不幸的是因參加法國大革命而下獄,在恐怖時代結束的前兩天被送上斷頭台,斷掉31歲的熱情。
我希望台灣現代詩人寫作小品詩,尤其寫作即景詩、田園詩,不要只侷限於寫景抒情,有時也應寫實紀事,或者溶合二者,作品才能反映時代、落實土地。其次,現代詩人寫作白話詩已不興韻律,但我覺得韻律仍相當重要,可以強化一首詩在聲音上的美感,前面提到的古代詩人,無論中西,他們雖處於詩律尚未解放的時代,在文句韻律上有不得不爾的要求,但即使不存在傳統的韻律格式,我相信他們也會重視詩的音樂性,而自發性的講究文字韻律,尤其佛吉爾。以上這些,就是我在1990年以後寫作小品詩、即景詩所秉持的主要理念。
這本詩集裡的小品詩,大半以某處景物為描寫焦點或起點,因此這類作品也可稱為地景詩或地誌詩,它們之中,有純粹寫景和寫景兼抒情的,也有在景色之中加入歷史人文與社會現實的,而少數篇幅較長的,猶如微型敘事詩,具有事件和情節。大概也受到前述:詩要講究語言聲音美的導引,在寫作當下,或自然或有意的讓詩句產生或多或少的押韻,其中最顯著的莫過於〈角板山一韻究竟〉這首,全詩從題目到末句共67行,全部只押一個韻。
本書收錄長短不一的小品詩共54首,除二首曾經收到我的第一本詩集《睡地圖的人》以及〈蘭潭即詠〉這首七言絕句之外,其餘51首都是2007年到2017年間的新作,距離我的上一本個人詩集《一葉詩》恰好十年,多數華語,少數台語,這反映最近十年我有意重新磨練華語創作力的企圖,自然也暴露出我做為詩人的慚愧──十年磨一劍,只得一本詩。當中有七首其實各有台、華語版本,為省篇幅,只取原作,不收後製的譯文版,但有二首例外,一為〈大坪印象〉和〈太平印象詩〉,後者乃前者的改寫版,是筆者有意呈現改寫的痕跡,另一首是〈台灣新褒歌〉與〈台灣頌歌〉,由於我對這塊安身立命的土地總是愛之深而責之切,這首是少有的頌詞,樂於讓她雙語同在。
全書按即景之地分為五輯,前二輯寫我已經居住四十年的第二故鄉桃園市,其一是我立身桃園時曾經或目前所居的生活區域,自是最常活動的地方;其二是閒暇時的出遊之地。第三輯是嘉南即景,是我此生除了桃園之外最熟悉、也最常活動的平洋曠野,多數地景都在我的第一故鄉嘉義,即使關子嶺也算是,因為關子嶺早年地屬嘉義縣,現在雖屬台南市,卻是我從小至今佇足老家門口時,只要晨昏東望總會看到的一座山頭、一座地標。第四輯所錄諸詩寫的是桃園、嘉南除外的其他縣市,它們的場景也屬前述國家意識或國際觀之下的家鄉。收在第五輯裡的詩所關注的對象未必發生在台灣地,因此取名「方外即景」,不過仍屬人類事務,也和台灣社會、台灣人有密切連結。
最後我要感謝桃園市文化局及圖書館,去年起開始辦理文學閱讀推廣活動,本書有幸受到補助,這是我迄今四十多年的文學創作生涯中,第一次受到官方的出版補助,別有意義和感覺,同時也激起我出版這本詩集的欲望和動能。
讓即景小品溶合中西傳統
在交通不便、以農立國的時代,故鄉/家鄉與他鄉/異鄉絕對是涇渭分明的兩個概念和兩種感情。到了工商為主的現代,發達的交通網路打破土地籓籬並用速度把距離縮減了,使家鄉與他鄉有連在一起的感覺而不知何處是他鄉,我想1980年代以後出生的台灣人,當他們搬家或離開生長的地方後,不會有濃厚的鄉愁,因為他們的「故鄉感」淡薄如絲了。
我生長在安土重遷的農業時代末期,故鄉感自然很重,不過因為謀生的關係,也長年客居他鄉,結果就像古人所吟的,先是「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變成「夢裡不知身是客,...
目錄
自 序|讓即景小品溶合中西傳統
第一輯 桃園即景生活篇
桃園地名有感
千塘之鄉
初見大溪
會記得尾寮(台語)
擁擠的河──桃園大道記
在中壢街頭
龜山公園天淨沙
壽山巖聽蟬
山在富庶──記桃園虎頭山
南崁溪流過去
第二輯 桃園即景遊歷篇
角板山一韻究竟
石門行
集結獨裁者──走過兩蔣園區
大溪觀音亭
來到靈潭陂──兼致鍾肇政先輩
平鎮素描
楊梅老樟樹
八塊厝樓──八德記憶
自君出國門
白沙岬燈塔
永安夕照
桃園古廟短詠
蘆竹五福宮(台語)
龜山壽山巖(台語)
桃園景福宮(台語)
桃園神社(台語)
新屋范姜祠堂
第三輯 嘉南即景
水牛厝出世記(台語)
溪河夢
蘭潭即詠
閒釣仁義潭
天地雙琴──詠大埔湖濱之地琴木
大坪印象
太平印象詩
萬鷺朝鳳金萱園(台語)
觀音水濂(台語)
西拉野求雨祭(台語)
遊仙詩(台語)
想見關仔嶺
月娘津落目屎彼暝──鹽水夜遊記(台語)
福爾摩沙商籟吟(台語)
第四輯 台灣即景
台灣新褒歌(台語)
台灣頌歌
石岡水壩吟(台語)
台灣農民吟
紅星照耀滿地紅──記者吳望台日記
治國賽神仙(台語)
水蛙吐喟(台語)
開挖中國家
千面埋伏──聞高雄氣爆
第五輯 方外即景
瞻頭看耶穌(台語)
美美的痛楚──讀賈平凹《秦腔》
炫美與羞醜
火災(台語)
楓橋日泊(台語)
月娘是中國領土
沙漠染綠
附錄一|火的河流──導讀林央敏的五首詩 李若鶯
附錄二|林央敏著作簡表
自 序|讓即景小品溶合中西傳統
第一輯 桃園即景生活篇
桃園地名有感
千塘之鄉
初見大溪
會記得尾寮(台語)
擁擠的河──桃園大道記
在中壢街頭
龜山公園天淨沙
壽山巖聽蟬
山在富庶──記桃園虎頭山
南崁溪流過去
第二輯 桃園即景遊歷篇
角板山一韻究竟
石門行
集結獨裁者──走過兩蔣園區
大溪觀音亭
來到靈潭陂──兼致鍾肇政先輩
平鎮素描
楊梅老樟樹
八塊厝樓──八德記憶
自君出國門
白沙岬燈塔
永安夕照
桃園古廟短詠
蘆竹五福宮(台語)
龜山壽山巖(台語)
桃園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