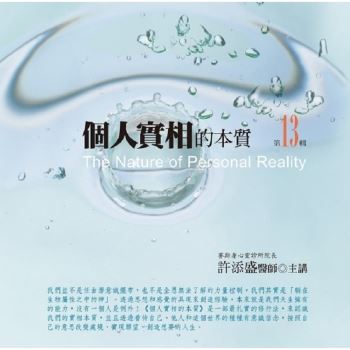一九九五年夏天,「全美伊斯蘭聯盟」領袖法拉坎呼籲全美黑人,於十月十七日至華府的國會林蔭大道前,參加「百萬人民大遊行」。國會林蔭大道向來都是大規模政治示威活動的場地,金恩博士正是在此發表「我有個夢想」的演說;其他在此集結的大型示威活動,包括反越戰、墮胎、婦權、同性戀人權等等。許多在林蔭大道舉行的遊行都曾引發爭議,不只因為各集會的政治訴求,也因為集會人數多寡的問題。想當然爾,針對集結人數,示威活動策劃者會提出偏高的估計值;畢竟,人數越多,代表他們的動機引起廣大民眾的支持,也代表示威活動組織完善,辦得很成功。相較之下,負責維持該地區秩序,並受命於國會,負責提交集會人數官方估計值的美國國家公園警察隊,通常會提出偏低的估計值。舉例來說,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華府所舉行的同性戀人權大遊行,主辦單位預估有超過一百萬人參與示威,而公園警察隊預估只有三十萬民眾參加。
示威活動的主辦單位會和公園警察隊意見相左,這並不難理解。宣稱有大批民眾參加,對示威活動的主辦單位有利,但是在面對大批群眾時,很少有主辦人有辦法計算群眾人數。反之,這些年來,公園警察隊想出了比較精密的方法,可以估計示威群眾的人數。他們用空中照相來顯示林蔭大道上布滿群眾的區域,既然已知林蔭大道的面積,他們可以計算出群眾集結的區域大小;接著,公園警察隊再將這個區域面積,乘以預估每平方公尺可容納的平均人數,所得出的結果,就是群眾人數的估計值。
「百萬人民大遊行」正突顯了估計群眾人數的政治本質。光是這個遊行活動的名字本身,就已經設立了一個該遊行能否算得上是「成功」的目標;隨著舉行遊行的日期越來越近,主辦單位堅信到時候的參加人數一定會有一百萬人,而批評人士則預測這是不可能的。(根據公園警察隊的統計,目前只有兩個活動的參與人數達到百萬人:一九六五年詹森總統的就職大典慶祝活動,和一九七六年美國建國兩百週年紀念活動)。在遊行活動當天,主辦單位堅稱目標已經達成;當法拉坎發言時,他宣稱現場的人數介於一百五十萬到兩百萬之間。相比之下,公園警察隊估計群眾人數約為四十萬人(這已是民權示威活動的最高紀錄)。
主辦單位和公園警察隊在人數估計上的差異,符合我們常見的模式:法拉坎憤怒地回應,譴責說「種族主義、白人優越感,以及對我法拉坎的痛恨,使他們不願相信我們所說的」,並且揚言要控告公園警察隊。波士頓大學有一群專門分析空照的專家(不過,他們的專長是大自然空照,而非群眾空照),他們檢視公園警察隊的空照圖片後,提出自己的估計值:約八十七萬人,誤差幅度為百分之二十五(也就是說,根據他們的說法,當天參加的群眾確實可能達到一百萬人)。公園警察隊則是提出更多的資料反駁,包括額外的照片和大眾運輸系統的紀錄,證明遊行當天只有稍微高一點的交通流量湧入華府中心,這使得波士頓大學研究人員重新修改估計人數,微幅下降至八十三萬七千人。
公園警察隊與波士頓大學研究人員的估計值之所以不同,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雙方用來計算群眾數量的乘數不同。波士頓大學研究人員假定人潮十分擁擠,每平方公尺容納六個人,相當於每個人占○•一六平方公尺,這大約是電梯中擠滿人時的擁擠程度。在大量的人潮當中,人和人之間似乎不太可能會站得這麼近,而且還連續好幾個小時,直到集會結束。相比之下,公園警察隊採用該擁擠度的一半,即每人平均約占○•三二平方公尺。對於聽眾而言,這已經算是十分擁擠了;大部分聚集聽講的群眾分布四處,平均為每人○•五一平方公尺至○•七六平方公尺。
很明顯地,「百萬人民大遊行」吸引了大批的人潮。聚集的群眾是否實際達到一百萬人,或少於一百萬人,真的很重要嗎?在這個例子,群眾的人數多寡其實還代表了一些象徵性的議題,包括法拉坎在黑人心目中的聲望和影響力,以及公園警察隊估計值所反映的種族歧視和其他偏見的程度。法拉坎顯然有為一百萬這個數字辯護的使命感;而批評他的人士則樂於宣稱示威運動未達目標,抨擊法拉坎誇大事實。波士頓大學研究人員的估計值,使得公園警察隊的估計程序受到質疑,儘管公園警察隊對於人群密度的假設似乎更合理一些。此外,估計群眾的人數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因為這些估計值大多偏低,因此讓主辦單位感到憤怒;有些新聞媒體在報導波士頓大學研究人員的估計時,暗示公園警察隊可能心懷偏見。在國會新的指示之下,公園警察隊宣布此後將不會再提供任何示威活動的人數估計。
這個爭論關注的焦點,是一個十分簡單的統計問題:「百萬人民大遊行」實際有多少人參加?這個問題有三種不同的答案。法拉坎和其他主辦人士主張,群眾總數高達一百萬人之多。他們估計人數的方法,想必和其他倡議者計算示威活動(及社會問題)的規模一樣,都是用猜測的。既然遊行吸引了這麼大批的群眾,他們猜測必然有高達一百萬的支持者參與,正如林蔭大道上其他大型示威活動的主辦人一樣。第二個估計值當然來自公園警察隊;他們用既定的空照方法,計算群眾集結的區域面積,再利用乘數(每人約○•三二平方公尺),來估計聚集群眾的人數。第三個答案來自波士頓大學研究人員,他們的方法和公園警察隊相同,但採用不同的乘數(每人約○•一六平方公尺)。(顯然,只要採用不同的人群密度估計值,也就是說,改變乘數的數值,就有可能導出各種群眾總數的估計值。)問題實在是非常地簡單:在人群當中,人們可以站得多近?令人訝異的是,雖然新聞媒體關心群眾人數的爭議,但是記者在報導這則新聞時,通常只有報告相互競爭的數字;很少有記者試圖瞭解這些數字如何產生,更別提去評估哪些假設最有可能計算出最正確的估計值。媒體的焦點,反而著重在提出這些估計值的人背後的動機:公園警察隊是否心懷偏見?
「百萬人民大遊行」這個例子提供了兩個重要的教訓。第一,要瞭解統計爭論的主要爭點,就算只是粗淺的輪廓,而非技術上的細節,我們是辦得到的。第二,在增進我們對統計爭論的瞭解上,媒體通常做得不夠多。新聞記者通常沒有解釋不同團體如何導出不同的數據,更不用說是去評估這些數據了。事實上,媒體的報導常常局限在這個團體提出數字 X,而那個團體提出數字 Y 來反駁。這完全無助於讀者和聽眾詮釋不同的估計數字。
「百萬人民大遊行」爭議涉及的利害關係,主要是象徵性的。因為法拉坎承諾要將一百萬人聚集在一起(也因為他堅決認為他辦到了),於是一些評論者將人數的統計,轉化成對他的影響力及可信度的衡量。無論如何,不管是否真有一百萬人參加,它都確實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示威抗議活動。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統計數字:是事實,還是謊言?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70 |
二手中文書 |
$ 187 |
社會人文 |
$ 194 |
中文書 |
$ 194 |
社會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統計數字:是事實,還是謊言?
數字確實會說話,但它更會說謊。當數字說謊時,你分辨得出來嗎?
死於槍口下的兒童數目每年以倍數的速度增加?厭食症每年奪走十五萬名年輕女性的生命?白種男性只佔新勞動力的六分之一?令人怵目驚心的統計數字形塑我們對社會議題的思考。但這些數字多半是錯的。本書教你如何看出有問題的統計數字,並以批判的方式來思考它們。對於任何看或讀新聞的人,以及任何仰賴統計數字來理解社會問題的人,還有大學學生,這本書都不可不讀。
貝斯特從各種在媒體上備受關注的社會議題切入,包括墮胎、網路色情、遊民、百萬人遊行、青少年自殺等,藉由來自《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及其他主要媒體的例子,他為我們揭開了統計數字的使用、誤用與濫用的祕辛。
貝斯特鉅細靡遺地向我們解釋了壞統計數字出現、散播並形塑政策辯論的原因與方式,也告訴我們看穿壞統計數字、批判思考「統計戰爭」的具體方法。你並不需要高深的數學知識才能讀懂這本書,因為裡面談的,全都是最基本、最易懂的統計,例如百分比、平均值、比例。
這本平易近人的書告訴我們,除了天真地全盤接受統計數字或犬儒地認為它們毫無意義外,我們還有另一種選擇:面對著在社會科學以及我們飽受媒體轟炸的生活裡氾濫的統計數字,我們可以當個聰明、批判、具權的閱聽者。
章節試閱
一九九五年夏天,「全美伊斯蘭聯盟」領袖法拉坎呼籲全美黑人,於十月十七日至華府的國會林蔭大道前,參加「百萬人民大遊行」。國會林蔭大道向來都是大規模政治示威活動的場地,金恩博士正是在此發表「我有個夢想」的演說;其他在此集結的大型示威活動,包括反越戰、墮胎、婦權、同性戀人權等等。許多在林蔭大道舉行的遊行都曾引發爭議,不只因為各集會的政治訴求,也因為集會人數多寡的問題。想當然爾,針對集結人數,示威活動策劃者會提出偏高的估計值;畢竟,人數越多,代表他們的動機引起廣大民眾的支持,也代表示威活動組織完善,辦得...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喬.貝斯特
- 出版社: 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08-01-30 ISBN/ISSN:9789866662096
-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208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