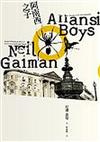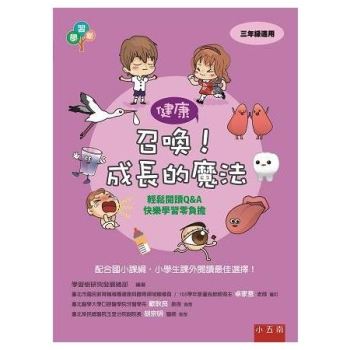當神話侵入現實,人生開始失控……
你的老爸是惡作劇之神,
熱愛開玩笑,讓你的童年囧到不行;
有個從沒聽過的兄弟上門來相認,
他擅長假冒你,還把走了你的未婚妻!
衰運連連,一切都是爸爸在搞怪?
切斷父子手足的牽絆,就能順遂一生?
《美國眾神》暢銷作家尼爾.蓋曼與非洲故事之神阿南西攜手合作,獻給讀者最詼諧、機智、溫暖、歡樂的都會奇幻冒險!
體面的死法一定有十萬種,舉例來說,從橋上跳到河裡去拯救快溺斃的小孩;單槍匹馬勇闖歹徒巢穴,死在槍林彈雨下。這些都是體面之極的死法。有些死法雖然不怎麼體面,但也不會太令人難堪,例如人體自燃。
但,胖查理的爸爸偏偏不是其中任何一種死法。他是這麼死的:他正在臺上高歌,同時對臺下的金髮美女大獻慇懃,全場氣氛熱到最高點之際,忽然露出古怪的表情,一手壓住胸口,一手向前伸,然後從臺上摔了下來,倒在一名正妹身上,又從她身上跌到地上,沒人能摔得這麼緩慢、這麼優雅。倒地時,手上還抓著一樣東西──剛剛還穿在正妹身上的無肩帶小可愛。
這麼令人難堪的死法,正是胖查理老爸的正字標記。諸如此類的窘境,充斥著胖查理的童年回憶。
其實胖查理一點也不胖,但這綽號一旦從他老爸口裡冒出,就一直緊黏住他不放,不管他怎麼自我介紹,別人自然而然會開始叫他胖查理。和他同病相憐的是鄰居一條冠軍拳師狗,原本趾高氣昂不可一世,在老爸隨口叫了聲「小笨笨」之後,聲名一蹶不振,人人都說牠一臉蠢相。
父親的葬禮上,難堪指數再度攀升。不過這也不算什麼,隨後揭露的家族祕密才是真正的打擊:一、他老爸是神!卻是個專司說故事、唱歌和作弄人的惡作劇之神!二、他竟然有個親兄弟!為什麼他毫無印象?
無論如何,父母皆已過世,這素未謀面的兄弟是他僅存的親人了。這一相認卻是胖查理人生開始失控的起點!這位兄弟個性跟爸爸如出一轍,享樂至上,缺乏責任感,更冒充他去招搖撞騙!怪的是還處處逢源,不僅唬過他的上司,更把走他的未婚妻!可憐的本尊沒人理會,落魄街頭,連搭計程車也回不了家。
查理只想過平凡安穩的人生,他的兄弟卻繼承了父親的精神,繼續把他的生活搞得一團亂。這麼糟糕的親情關係不要也罷!他實現了願望──卻引來更大的災難。他要如何收拾殘局?老爸與兄弟留給他的,真的只是災難與羞辱嗎?人生究竟是怎麼回事?
生命的力量來自於說故事與歌唱,尼爾.蓋曼這本饒富幽默感的成長小說便是最佳典範。
本書特色
生命的力量來自於說故事與歌唱,尼爾 蓋曼這本饒富幽默感的成長小說便是最佳典範。
尼爾 蓋曼似乎很喜歡阿南西這個神!不過看完本書後一切謎題都解開了!說故事的神與說故事的作家,都在編織人生啊!
《阿南西之子》幕後花絮:事實上,早在1996年《美國眾神》誕生之前,尼爾 蓋曼就已經有了《阿南西之子》的故事雛型,也動筆寫下幾頁劇本草稿(當初他想的是戲劇或影片的形式),但一直沒有進展。後來在寫《美國眾神》時,他靈機一動,便讓尚未在《阿南西之子》中具體成形的南西先生(胖查理的父親、非洲蜘蛛神阿南西)客串演出。隨後《阿南西之子》的寫作方向便從劇本轉為中篇小說,然而他的編輯聽他說完書之後卻斬釘截鐵說:「這是本長篇小說!我是編輯,我說了算!」於是,就有了現在的《阿南西之子》。
《阿南西之子》小道消息:據說《阿南西之子》、《無有鄉》皆有改編電影的計畫。只是,由於電影公司在選角的看法上與作者有出入,因此《阿南西之子》的拍片計畫可能暫時中止。
其實蓋曼的故事都很適合影像化呢!人物生動、情節曲折、故事幽默,很有大眾緣。想像一下《阿南西之子》的夢幻卡司!胖查理-威爾史密斯飾演;蜘蛛-克里斯塔克,或由威爾史密斯一人飾二角;阿南西爸爸-摩根費里曼!一定超過癮的!
作者簡介
尼爾.蓋曼(1960~)
當代奇幻大師,被譽為「美國之寶」,史蒂芬.金更封他為「故事寶窟」。
他有如「文壇的達文西」,從漫畫、散文、小說、電影劇本、歌詞創作、兒童故事,到奇幻、科幻、驚悚小說,均無一不精的鬼才作家。
27歲時,他便以漫畫「Sandman」系列崛起,著名的黑暗幽默在九○年代風靡了歐美大眾,更獲獎無數,成為歐美漫畫迷心目中的最愛與經典。小說創作也迭獲佳評:長篇小說《星塵》獲創神獎、中篇故事《第十四道門》獲星雲獎;《美國眾神》堪稱他的文壇代表作,不僅獲得多項大獎,也囊括紐約時報等各大暢銷榜;此外更有不少精彩短篇小說創作。蓋曼才華洋溢,創意驚人,擅長融會現代都市文明與古老奇幻傳說,交織人性的幽暗與瑰麗,想像力大膽豐富,筆觸簡練詼諧。2007年電影《貝武夫》劇作即出自他手。
著名獨立音樂女歌手Tori Amos屢在創作歌曲中讚揚蓋曼,並引用他作品中的意象。Google總裁Matt Cutts更是蓋曼的超級書迷,曾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公開表示:「如果你不認識尼爾蓋曼,我為你感到遺憾;但我也為你高興,因為你可以從頭閱讀他的作品。」(另有八卦一則,事關Matt為了尼爾.蓋曼向蘋果電腦嗆聲,見繆思部落格blog.yam.com/musesbooks/article/11480967)
尼爾.蓋曼專屬網站: www.neilgaiman.com
譯者簡介
林嘉倫
台大學外文系畢,輔仁大學翻譯所碩士。目前專職法律翻譯。譯有《機長,我有問題──解開你對航空旅行的所有疑問》、《圖解繩結完全指南》、《未來世界》、《煙與鏡-尼爾.蓋曼短篇選》、《魔是魔法的魔》、《巴黎,賽啦》等書。喜歡旅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