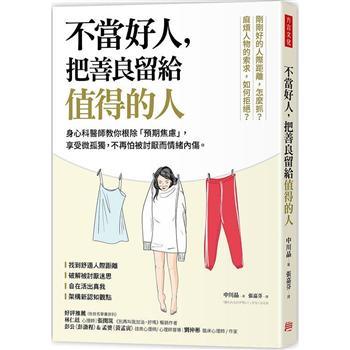「母親……」江說:「母親沒有想過勸阻父親嗎?沒有想過阻止父親不要背叛舅父大人嗎?」
阿市苦笑,搖了搖頭,說:「那是不可能的事。男人們一旦決定要戰爭,那就是勢在必行的事情了。」
「舅父大人認為父親背叛了……」
「織田信長就是那樣的男人。」姊姊初吐出這句話。
江繼續追問母親:「但是,母親大人……沒想過告訴舅父大人,父親要幫助朝倉家的事嗎?」
「那怎麼可以呢?」
阿市制止大聲說話的初,靜靜地笑著說:「你們的父親也這麼說過。」
江驚訝地看著母親。
「他說:你可以告訴兄長大人我的決定。但是,聽到你們的父親那麼說後,我就決定了。我決定跟隨你們的父親。我選擇做淺井長政的妻子,而不是織田信長的妹妹。」
大姊茶茶和二姊初小聲地啜泣了。
織田家與淺井、朝倉兩家的戰爭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經過在小谷城附近的姉川會戰,淺井軍固守易守難攻的小谷城後,戰線便轉移到攝津、比叡山一帶。信長被迫陷入苦戰,便說動當時的天皇──正親町天皇和將軍義昭,促成雙方和解。當時是元龜元年(一五七○)的年底,淺井家的次女初,便是在這個時候出生的。
「戰爭沒有因為這樣而結束嗎?不是已經和解了嗎?」江問。
阿市輕輕搖搖頭,說:「是兄長大人讓義昭大人坐上將軍大位的,但是,義昭大人只是形式上的將軍,掌握將軍實權的人其實是兄長大人。兄長大人想要的是操控將軍與天皇的兩種權威,讓天下諸大名聽令於自己。……義昭大人知道了兄長大人的野心後,便寫信給諸大名,要求他們討伐兄長大人。這是將淺井家再度逼上新的戰場,也是最後戰役的關鍵……」
元龜三年,義昭大人與兄長之間的戰事擴大了。在義昭大人的煽動下,甲斐國的武田信玄也參與了討伐兄長的戰爭。南下到信濃、遠江的信玄軍逼近德川家康的居城──濱松城,輕易地在三方原擊敗德川軍。四面皆敵的織田信長此時亦無法派兵支援德川軍。對德川家康而言,此戰是他一生中唯一敗戰,而且敗得很慘。
天正元年(一五七三),江出生的這一年,信長時來運轉。四月,淺井與朝倉所期待的武田信玄,竟在參戰的途中病沒。七月,興兵討伐信長的將軍義昭因為失去援軍,不敵信長,只好投降,並被信長趕出京都,室町幕府就此滅亡。同年八月,信長進軍岐阜,攻打越前,逼迫朝倉義景自殺。朝倉氏也被信長消滅了。
接下來的八月二十七日,織田軍開始對小谷城進行全面攻擊,以波濤洶湧之勢強力攻打。很快的,八月二十八日長政的父親──久政便被迫自殺。
「那天晚上,長政大人叫我前去,命令我帶著你們姊妹三人離開小谷城,他要把我們送到織田軍的陣營。他是這麼對我說的……」
阿市拚命反抗長政的意思,並且數度哀求,希望能與長政一起死。但是長政無論如何都不同意。終於,阿市和姊妹三人還是離開了小谷城。
雙方激戰了許久,長政雖然被逼到小谷城的本丸了,仍然奮勇持續抵抗了兩天,最後在兵卒盡失的情況下,切腹自殺了。和信長持續對抗了三年多的小谷城終於被攻陷,淺井氏也滅亡了。長政享年二十九,死時正值英年。
「……說完了。」
說完這麼長的一段話,阿市好像虛脫了般,放鬆了雙肩。但是,江覺得還沒有結束。父親遭受舅父討伐而死之事,給江帶來很大的衝擊。
「這件事……以前……為什麼不告訴我呢?」
阿市注視著女兒,說:「離開小谷城的時候,你才剛出生不久。……因為覺得這件事對什麼也不知道、在伊勢城裡平靜地長大的你來說,或許是太殘酷的事情。」
「我想知道……我希望可以更早知道這件事……」
江的眼眶裡微微浮現了淚光。聽到江的話後,初又說了重重打擊了江的話。
「不要說這種不負責任的話!」
「姊姊……」
「為了不讓你有悲傷的記憶,大姊和我一直一直在忍耐,但你現在卻一臉無所謂的說想早點知道父親的事。……我好幾次都想乾脆告訴你好了。可是,每次我想說時,卻都被母親阻止。你看我,看看我呀!」
初嚴厲地看著江說。她的眼裡已經充滿了淚水。
「你知道嗎?江。我們這一切都是……都只是為了不讓你生活在怨恨舅父和害怕舅父的日子裡呀!」
初終於忍不住掩面哭了。江不知如何是好地看著掩面而哭姊姊。
不知道……。江什麼也不知道。
從剛才就一直緊閉著嘴巴沒有說話的茶茶,這時平靜地說了:「江,你也覺得很難過吧?但是,江,你不要難過了,這不是你的錯。」
「茶茶說的沒錯。如果有人錯了,那麼就是一直不讓你知道此事的母親錯了。」
阿市說著重重地嘆了一口氣,又說:「沒想到是秀吉製造了讓我說出這件事的機會……」
「莫非這是無法避免的惡因果……」
江抬眼看著說這句話的茶茶。茶茶以低沈而不帶情緒似的聲音繼續說:「攻打小谷城時的先鋒,就是猴子──木下藤吉郎秀吉。」
江想起那個卑微地伏在地上行禮,小小的臉上有著許多皺紋的男人。
「他現在好像改姓羽柴了。以織田家老臣丹羽大人與柴田大人姓氏中的各一個字為姓。」阿市補充說明著。
初從旁插話說:「他是一個狡猾的人……。確實像猴子般的狡猾。」
初吸吸鼻子,眼帶淚光地看著江,繼續恨恨地說:「把父親大人逼到絕境的,就是猴子帶領的軍隊。……打敗父親後,他因為戰功而獲得小谷城與北近江之地的賞賜。但是,他說山城不便居住,所以捨棄了小谷城,在淡海附近蓋了新的居城。」
小谷城現在已成廢墟,沒有人住了。江想起在天守閣的高欄時茶茶所說的話。初口沫橫飛似地又說:「不只父親大人被逼死,年長我十歲的異母兄長萬福丸也被殺了。」
「初!」
阿市喝止初繼續說下去。但是初不顧母親的阻止,仍然繼續說:「兄長被捉走,在關原被處死了。這也是猴子做的事。」
「啊……」
江驚訝地轉頭看阿市。只見阿市無言地低頭看榻榻米。母親的沉默表示姊姊說的是事實。
「但是,江,殘酷的人並不是只有秀吉一人,舅父大人的作為比猴子更令人難以猜測,他也做了許多殘酷的事情。」
「初,不要再說了。」
茶茶尖聲阻止初繼續說,可是初沒有聽進去。
「既然已經說到這裡了,最近還有一件事也應該讓江知道。」
「……本願寺的事嗎?」
茶茶和初看著母親阿市。看到阿市端正了坐姿,江也下意識地重新坐好。
「兄長大人不僅把各藩國的大名視為對手,更把石山本願寺視為主要的敵手。」
阿市說,元龜年間讓信長陷於苦戰的反對勢力的中心,就是石山本願寺。如今淺井、朝倉兩家已經滅亡,信玄也已經亡故,但信長與本願寺持續了將近十年的戰爭,如今卻還在繼續著。
「可是……與寺院為敵…。」江勉強說了幾個字,就覺得口乾舌燥了。
茶茶平靜地說:「不管對手是誰,一旦違背自己已經決定的事,就絕不輕饒。世人都說這就是織田信長的作風,非常可惜怕。因此伊勢長島之戰時,織田軍殘酷地殺死了兩萬起義的軍隊;在越前之戰中被織田軍殺死的人數,有人說是三萬人,也有人說是四萬。」
上萬……到底是多少?那是江無法想像的數字。初在一旁越說越激動:「江,舅父大人把比叡山的延曆寺整個燒掉了,只因延曆寺在戰爭的時候,藏匿了淺井家或朝倉家的士兵。那是對自己沒有信心的人,才會做的事情吧!」
阿市緩緩地開口說:「夠了!一下子說這麼多,江承受不了的。要替江想一想。」
「讓我說,我只要再說一件事就好。」
初說,但茶茶的表情變了。初現在想說的,就是最不該說的事情。然而初已經停不下來,她比手畫腳地說:「舅父大人還把父親的頭蓋骨當作酒杯,和家臣們共飲!祖父大人、朝倉義景大人的頭蓋骨也一樣──」
「不要說了!」茶茶出聲制止初的同時,也一巴掌打在初的臉頰上。
「大姊……」
江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情景。初被茶茶一巴掌打倒在榻榻米上,發出哭泣的聲音。
「夠了,不要再說了。母親大人和我都不想聽了……」
茶茶也哭了,她的手按著初掩著臉頰的手。阿市也默默地流著眼淚。但是江沒有哭,她哭不出來。她感到無比的訝異與疼痛,這兩種感覺不斷在她的內心裡膨脹,並且互相擠壓。
江搖搖晃晃地站起來,走到屋簷下。她屈膝看著黑暗的地面,突然頭向前伸出,窒息的感覺讓她嘔吐了。
□
江一點想睡的感覺也沒有。因為心情激動,她的腦子非常的清醒。
這時,江躡腳走在城內黑暗的走廊下。月亮所散發出來的微光照不到前路,只能靠點亮在各個角落的微弱燈光,勉為其難地摸索著向前走。
江想去找信長,她有許多事想要直接問信長本人。信長舅父有多麼可怕,看他白天時毆打那個叫猴子的男人,和從母親與姊姊們的言行裡,江已經有所了解了。但是,她就是控制不了想要自己去了解的念頭。
靠著些微的印象,江在走廊上的某個轉角處轉彎,果然看到走廊深處──城中的某角落,發出昏暗的光芒。
那裡是拉門,看來門內的人還沒有睡覺。
江朝著點著燈的那個房間,小心翼翼地走在走廊上。然後,她把指尖放在拉門上,悄悄地推開一點點縫隙。就在她推開拉門的那一剎那,銳利的喊聲傳進江的耳中:「是誰?」
江被這個聲音嚇了一跳,手一抖,本來關著的拉門反而被她順勢拉開了。江無處可躲,心想反正一定會受到責備,乾脆大方地環視拉門大開的房間內部。
信長在房間裡面。寬敞的房間正中央有一張書桌,背對著牆壁掛軸的信長穿著窄袖便服,正面對著書桌在看書。不知道侍候信長的人是不是在隔壁的房間裡,這個房間裡不見任何侍者的影子。
「是阿江嗎?進來。」
聽聲音不像在責備。江依照信長說的,走進房間裡。
「過來這邊。」
江反手關上拉門,像踩在雲裡一樣地走近信長,跪坐在信長的正對面。信長看也沒看江一眼,視線仍然投向已經翻開的書本上。
「那個……為什麼知道是我……?」江忘了打招呼的禮儀,開口就問。
「憑感覺和腳步聲。」信長終於抬頭看江。
「黃昏見面的時候,我已經確認過你呼吸的氣息與體型的大小了。找我有事嗎?」
江緊張地吞吞口水,張開乾燥的嘴唇說:「舅、舅父大人,我有幾個問題想問您。」
「等一下。」信長把放在榻榻米上的托盤子移到書桌上,拿起水壺注水入杯中。「我不想聽到那樣的聲音。喝吧!」
信長的聲音有著讓人無法拒絕的力量。江伸手拿起杯子,咕嚕咕嚕地喝光了杯中的水,然後便盯著信長看。信長也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江。
「說吧!」
「是。……我想知道舅父與我出生的淺井家之間的戰爭。」
江一邊回想母親說的話,一邊努力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說到父親長政切腹之事時,江忍不住眼中閃著淚光。
「你說的都是事實。」信長冷冷地說,然後視線回到剛才的書本上,一副想要就此結束談話的樣子。
「但是,聽說逼迫家父切腹、處死我兄長的人,是羽柴秀吉。」
「沒有我的命令,臣下不敢妄為。逼長政切腹,處死萬福丸的人,就是我信長。還有別的問題嗎?」
江一口氣又問了關於石山本願寺之戰與焚燒延曆寺之事。她擔心自己稍一猶豫,就無法把話說完。信長雙手抱胸,游刃有餘地回答江的問題。
「一向門徒的極樂之國應該在另一個世界,卻對現世的政治處處有意見,涉入太深,分明是想要得到現世的權力。你不覺得他們那樣很奇怪嗎?」
江發現自己正在點頭。並不是她理解信長的言論,而是舅父自信滿滿的聲音,讓她覺得舅父所言是正確的。
「延曆寺的事情也一樣。應該專心學問的佛道中人卻吃肉喝酒,讓女人進入寺院的領地,這不打緊,竟然還組織了攜帶武器的僧兵,參與戰爭。是他們做了非分之事。面對非分之事,我不能置之不理。」
信長兩眼炯炯有神,並且閃爍著冰冷的光茫。信長冰冷的眼光讓江感受到無比的壓力,好不容易才又說:
「那麼,舅父大人並沒有排斥信仰嗎……」
信長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移轉了話題,說:「你知道『天下布武』嗎?」
「知道。聽說舅父大人用這幾個字做了印。」
江的回答似乎頗讓信長訝異。於是信長看著江,說:「那麼,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
「我知道。那就是要以武力統一天下的意思。」江想起不知道是從姊姊們那裡聽來的,還是從侍女們那裡聽來的話,便這麼回答了。
「錯了。」信長立即否定江的回答。「當今之世有三股勢力,那是武家、公家和寺家。我所說的『天下布武』的意思,是要以武家為主體來統一天下。」
「舅父大人認同宗教嗎?」
「我不是世人所說的鎮壓宗教者。我不是同意了天主教的佈教嗎?」
江想起城中天守閣內有許多和宗教有關的繪畫。
「也許舅父大人遇到了新的神佛,那些神佛與流派、宗門無關。是這樣的嗎?」
江急切地問。信長的臉上掠過似有似無的苦笑,說:「我不知道神佛。我只相信我自己。」
「只信自己……」
「你也要記住這一點。要活得快樂,就要只相信自己。」
江不太懂這句話的意思。因為只相信自己,所以在制裁別人的時候,不管造成多大的傷害,也無所謂嗎?……就在江這麼想著的時候,腦海裡突然浮現一個圓而扁平形狀物體的影像。是頭蓋骨。
江很害怕這次舅父的反應。但儘管如此,江還是鼓足勇氣,開口問:「最後還有一個問題。舅父大人,關於用家父的頭蓋骨……」
「用頭蓋骨喝酒之事嗎?」
「是……」
信長的聲音因為憤怒而發抖。
「那不過是個謠傳。」
「謠傳……」
「戰爭結束後的正月,我替長政大人、久政大人和義景大人的頭蓋骨做了『薄濃』的處理。」
「薄濃……?」
「就是塗金漆。我為他們的頭蓋加工,做了金漆的處理。」
江的臉色慘白。
「那是對已故者表達敬意的禮節。」
「禮節?」
信長說真實的情況是他與家臣們進行酒宴對飲時,將長政三人的頭蓋骨,分別放在托盤之中,擺放在繞著外廊的屋簷下。
「敵對的雙方對戰時,本來就會有勝有負,這是無可避免的事情。但是戰爭既然已經結束,好好的裝飾一下他們,一起迎接新的一年,不是很好嗎?至少我是這麼想的。但是,不知道是誰把這件事謠傳成用他們的頭蓋骨盛酒。不管我做什麼事情,都會遭到惡意的扭曲。」
信長冷靜下來,平淡地述說著,但江覺得自己看到信長孤獨的一面了。
「您不覺得氣憤嗎?」
「氣憤?」
「那種不實的傳言,不是很令人氣憤嗎?」
信長也直視著目不轉睛看著自己的外甥女。
「讓想說的人去說吧。」
「可是──」
「還是那句話,除了相信自己之外,別無他法。……阿江,要不要相信剛才我說過的話,都由你自己決定。重要的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
江一直看著舅父,思考了一陣子後,終於以很清楚的聲音回答道: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相信您說的話。而且,不管您的理由是什麼,我都不會原諒害死了我的父親、我的兄長的織田信長。」
江瞪著信長。信長的雙眸發出冷光,江不禁打了個寒顫,縮了縮身體。然而,接下來信長說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話。
「有趣。」
「有──趣?」
「能夠這樣直接對我說心裡想法的人非常少。和敢直視我的人一樣,都是非常少的。」
「我什麼也沒有說!」
信長沒有回應江的這句話,卻笑笑地說:「看來,你這孩子和我有點像。」
「像舅父大人您嗎……?」
「不錯。如是男兒身的話,或許會成為了不起的武將。」
「我才不想當什麼武將。」
「是嗎?不想當武將嗎?」信長很開心地笑了。
「而、而且,您好像也對我母親說過相同的話。您也說我母親如果是男兒的話,會是很好的武將。」
「阿市嗎……」信長的聲音突然一沉,說:「她一定很恨我吧!」
「母親恨您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是您讓她的丈夫失去性命。不過……」
「不過什麼?」
「……不過,我覺得母親不管多麼怨恨舅父大人,內心裡還是喜歡舅父大人的。」
信長露出難以理解的表情。
「否則,不管您怎麼邀請,母親都不會來安土城的。母親就是那樣的人。」
信長看著江,微微笑了。
「你真的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女孩子。」
江正想回答什麼,但被信長制止了。信長接著說:「阿江,聽聽我對你的期待。」
「……期待?」
「你擁有寶貝。」
「寶貝?」
「那寶貝就是你與生俱來的稟性。……阿江,你會長大。要相信自己,儘量按著自己的想法過生活。這就是我的期待。」
「……我明白了。」
江只能這樣回答。但是,為什麼我的稟性是寶貝呢?她卻完全不懂。信長再一次問江:「那你呢?喜歡我嗎?」
「……不知道。」
「是嗎?這個也不知道嗎?」
信長笑出聲了。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江:公主們的戰國〈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46 |
日本文學 |
$ 468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江:公主們的戰國〈上〉
2011日本NHK大河劇50週年紀念作之同名原創小說
「野田妹」上野樹里化身率直公主,詮釋以男性角度敘述的歷史中未曾細論的重要人物
女子的戰爭,是無論如何都要活下去!
日本戰國時期最特立獨行的公主,
就像她的名字一樣,如水一般貌似柔弱實則剛強,
曲折又波瀾萬丈的五十年人生大戲。
幼年喪父,逼迫父親走上絕路的是親舅舅織田信長;
十二歲奉命出嫁,不到一年便硬生生被姊夫豐臣秀吉拆散。
第三次婚姻,嫁給小自己六歲的德川家康之子,生下七個孩子,
繼而成為後水尾天皇的岳母,協助德川幕府建立兩百五十年泰平盛世!
「阿江,聽聽我對你的期待。……你擁有寶貝。那寶貝就是你與生俱來的稟性。……阿江,你會長大。要相信自己,盡量按著自己的想法活下去。這就是我的期待。」
戰國時期,群雄並起,打著「天下布武」口號的織田信長為了圓統一日本之夢,不惜迫使妹婿淺井長政兵敗自盡,妹妹阿市因此帶著三個女兒茶茶、初與剛出生沒多久的江,返回織田家居住。
一直不清楚父親真正死因的江,直到七歲那年,才明白自己的親舅舅竟是不共戴天的殺父仇人。茶茶與初始終無法諒解舅舅的冷酷無情,唯有江願意接受信長的說法與理念,並把「相信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下去」這段話牢記在心,做為她的生存之道。
數年後,織田家大將明智光秀舉兵反叛,發動本能寺之變,織田信長身亡,阿市與三姊妹頓失依靠,再次走上離亂之路。自此之後,江的人生將會走向何方?三姊妹之間又會遭逢怎樣的衝突與別離?
作者簡介:
田渕久美子
1959年出生於日本島根縣,著名劇作家、小說家。曾撰寫《妻子的畢業典禮》、《女神之戀》、《鑽石之戀》、《離婚女律師》等多部高收視話題連續劇劇本,2003年以NHK電視劇本《櫻》獲橋田賞,2005年以NTV電視劇本《冬季運動會》獲放送文化基金賞電視作品賞。擅長描寫積極向上的女性,往往能引起觀眾的共鳴。
2008年執筆NHK大河劇《篤姬》劇本,描寫一名堅強樂觀的女子,如何在動亂的日本幕末時期,帶領江戶城平安度過戰禍的危機,感動了全日本,創下自大河劇開播以來最高的收視紀錄。2010年再接再厲完成小說《江:公主們的戰國》上下二冊,為隔年NHK大河劇50週年紀念作的原創故事,再次引發日本全國性的討論。
譯者簡介:
郭清華
淡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畢業。第一個工作就是出版社的日文翻譯,一直沒有離開翻譯的崗位。譯有《我愛廚房》、《殺人人形館》、《殺人黑貓館》、《北方夕鶴2/3殺人》、《魔神的遊戲》、《天璋院篤姬》及《龍馬傳》等書。
章節試閱
「母親……」江說:「母親沒有想過勸阻父親嗎?沒有想過阻止父親不要背叛舅父大人嗎?」
阿市苦笑,搖了搖頭,說:「那是不可能的事。男人們一旦決定要戰爭,那就是勢在必行的事情了。」
「舅父大人認為父親背叛了……」
「織田信長就是那樣的男人。」姊姊初吐出這句話。
江繼續追問母親:「但是,母親大人……沒想過告訴舅父大人,父親要幫助朝倉家的事嗎?」
「那怎麼可以呢?」
阿市制止大聲說話的初,靜靜地笑著說:「你們的父親也這麼說過。」
江驚訝地看著母親。
「他說:你可以告訴兄長大人我的...
阿市苦笑,搖了搖頭,說:「那是不可能的事。男人們一旦決定要戰爭,那就是勢在必行的事情了。」
「舅父大人認為父親背叛了……」
「織田信長就是那樣的男人。」姊姊初吐出這句話。
江繼續追問母親:「但是,母親大人……沒想過告訴舅父大人,父親要幫助朝倉家的事嗎?」
「那怎麼可以呢?」
阿市制止大聲說話的初,靜靜地笑著說:「你們的父親也這麼說過。」
江驚訝地看著母親。
「他說:你可以告訴兄長大人我的...
»看全部
目錄
序章
第一章 信長
第二章 光秀
第三章 阿市
第四章 宗易
第五章 阿寧
第六章 秀吉
第七章 茶茶
第一章 信長
第二章 光秀
第三章 阿市
第四章 宗易
第五章 阿寧
第六章 秀吉
第七章 茶茶
商品資料
- 作者: 田渕久美子 譯者: 郭清華
- 出版社: 如果出版 出版日期:2011-10-25 ISBN/ISSN:978986670293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日本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