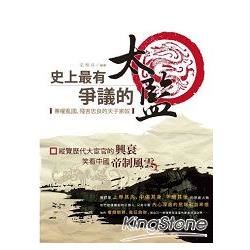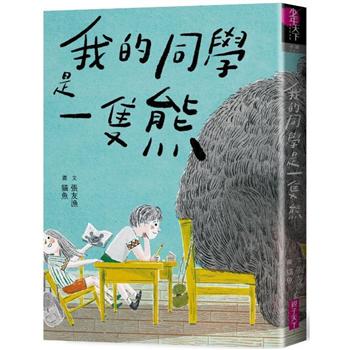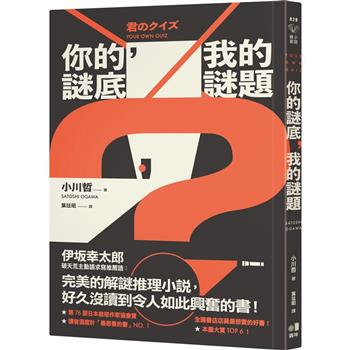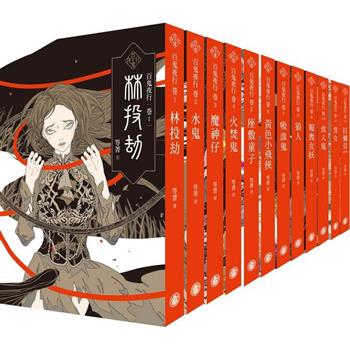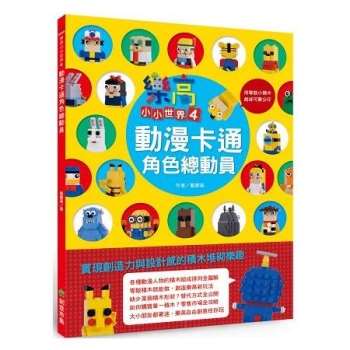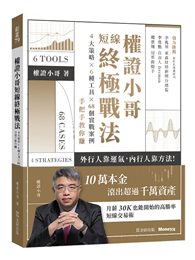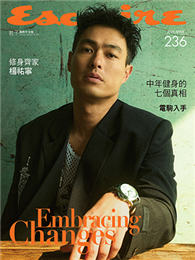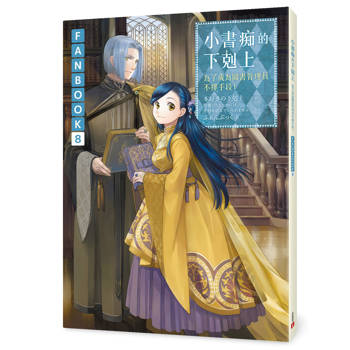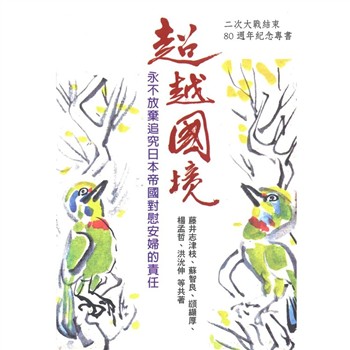【縱覽歷代大宦官的興衰,笑看中國帝制風雲!】
他們是上辱其先,中傷其身,下絕其後的悲劇人物;
他們是遭閹割的可憐人,只為平衡內心深處的屈辱和自卑感;
他們權傾朝野、瘋狂斂財、將自己一併埋葬在滾滾的歷史洪流之中……
本書為您揭露一幅幅血淚斑斑、荒謬絕倫的歷史畫面——
太監,就是皇宮中的侍者,他們缺少某種重要的零件──沒有男性特徵,用現代的用詞來說,他們是沒有「雞雞」的男人。
提到太監,由於受電視劇的影響,很多人腦海中的太監彷彿永遠都是那麼壞。看看歷史:漢有十常侍,唐有仇士良,宋有童貫,明有魏忠賢,清有李蓮英,說起這些人,讀者無不咬牙切齒,而著名的「黨錮之禍」、「東林黨爭」等事件,也給這群人戴上了一頂醜陋至極的帽子,以致於一提起太監,人們或恥笑,或戲謔,或謾罵,或悲憤,甚至罵上他們祖宗十八代。
本書選取中國歷史上最具爭議的太監,敘述了他們在皇權中的榮辱浮沈。皇權為他們帶來了榮譽和財富,也帶來了恥辱和殺戮。他們為皇權提供了服務與保障,也造成了王朝的更迭與顛覆!
本書特色
1.本書特別選出宋明清以及更早的朝代,分別精心挑選出「心最狠」及「貪最多」的大太監,敍述了他們在皇權中的榮辱沉浮。
2.歷代宦官專政對於皇室王朝帶來的恥辱和殺戮,將宦官權勢推至登峰造極之境的荒誕行徑。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史上最有爭議的太監:專權亂國、殘害忠良的天子家奴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46 |
歷史人物 |
$ 246 |
歷史人物 |
$ 252 |
人物群像 |
$ 252 |
清史 |
$ 288 |
文史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史上最有爭議的太監:專權亂國、殘害忠良的天子家奴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史明月
文化研究者。自幼對歷史有很深的文化情結,而這綿遠深沉的歷史文化情結,又源於他內心深處對歷史文化的癡迷和熱愛。正是這種執著,讓他有一種文化使命感。多年來,史明月致力於歷史文化的推廣與出版,並獲得了很不錯的效果。其他代表作品有《明馮夢龍智囊(圖文本)》《歷史上最有爭議的后妃》《李鴻章為人處世的方圓經》等。
史明月
文化研究者。自幼對歷史有很深的文化情結,而這綿遠深沉的歷史文化情結,又源於他內心深處對歷史文化的癡迷和熱愛。正是這種執著,讓他有一種文化使命感。多年來,史明月致力於歷史文化的推廣與出版,並獲得了很不錯的效果。其他代表作品有《明馮夢龍智囊(圖文本)》《歷史上最有爭議的后妃》《李鴻章為人處世的方圓經》等。
目錄
第一監 趙高:指鹿為馬 禍國殃民
他善於在秦始皇面前阿諛奉承,因而逐漸獲得權力,為他後來篡改遺詔、扶立庸主、當上丞相打下了基礎。他從一名小小的宦官起家,卻在秦王朝最後的幾年翻雲覆雨,整個天下曾離他不過一步之遙。他一手將秦帝國千秋萬代的春夢引向破滅,也將自己一併埋葬在了滾滾的歷史洪流之中。
◎處心積慮博得始皇寵信
◎秦始皇去世後祕不發喪
◎偷樑換柱詐稱遺詔
◎濫殺無辜,恣意妄為
◎「指鹿為馬」欲取秦而代之
◎結束罪惡滔天的一生
◎後人話趙高:陰謀的化身
第二監 李輔國:超乎常人的厚黑高手
他相貌奇醜無比,四十歲之前無所作為。安史之亂期間,勸說太子李亨繼承帝位。唐肅宗即位後,被加封為元帥府行軍司馬,開始掌握兵權,並改名為輔國。之後又因擁立代宗即位,被冊封為司空兼中書令。大權在握後李輔國更加為所欲為,最後被人刺殺身亡。
◎假傳聖意,權傾朝野
◎一手遮天,殘害忠良
◎作惡多端終難逃一死
◎後人話李輔國:標準的奸佞,亂臣賊子
第三監 劉騰:廢後戮相,倒行逆施
他幼時因罪被閹,入宮做了宦官,補小黃門。因善於觀察,心藏計謀,能通解人意,因而特蒙恩寵,很快由小黃門轉補中黃門。他原本是遭閹割的可憐人,因其內心深處的屈辱和自卑感,產生了種種報復、殘忍、貪婪、凌虐的變態行為。
◎善於察言觀色而得到升遷
◎瞅準皇上心腹博取寵愛
◎左右逢源,恃權胡為
◎開棺戮屍,可悲下場
◎後人話劉騰:倒行逆施的心理變態
第四監 仇士良:欺君抑相,竊國弄權
他一生弄權干政,穩步高升,從一個侍侯太子的一般太監,歷任監軍、內外五坊使、左神策軍中尉、驃騎大將軍、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知內侍省事等要職,封楚國公,死後追贈楊州大都督。仇士良檀權攬政二十餘年,一貫欺上瞞下,排斥異己,橫行不法,貪酷殘暴,先後殺二王、一妃、四宰相,使當時朝政變得更加昏暗和混亂。
◎得勢後乘隙控制軍權
◎甘露事變失事,重臣慘遭殺戮
◎皇帝被其操縱,心狠手辣行惡
◎貪酷殘暴終落個削官沒籍
◎後人話仇士良:仇視賢良的一代奸奴
第五監 童貫:史上唯一被封為王的宦官
他的經歷,充滿了傳奇般的悲喜劇色彩。他的一生中,開創了幾項中國歷史之「最」:中國歷史上握兵時間最長的太監;中國歷史上掌控軍權最大的太監;中國歷史上獲得爵位最高的太監;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出使外國的太監。
◎「仗義疏財」,媚迎事主
◎控制軍權,虛功受獎
◎宋金結盟抗遼——金變被動為主動
◎潰敗潛逃,終將伏法
◎後人話童貫:閹割過的王爺不孤獨
第六監 王振:禍國害民的文人太監
他是明朝第一個專權的太監。原本是一個失敗的教書先生,卻自閹進宮,得到了明英宗的寵倖,開始擅權,結黨營私,干涉朝政,揭開了「太監帝國」的序幕。為了建立所謂的豐功偉績,根本不知作戰為何物的他,慫恿皇帝親征來犯的也先,結果是皇帝做了俘虜,自己賠上了性命。
◎採取兩面手法,獲得寵信
◎黨同伐異,大耍淫威
◎土木之變,終落得可恥下場
◎後人話王振:把皇帝賣給敵人的絕世太監
第七監 劉瑾:「八虎」之首「立皇帝」
他六歲時被太監劉順收養,後淨身入宮當了太監,遂冒姓劉氏,侍奉太子朱厚照,即後來的明武宗。他善於察言觀色,隨機應變,深受信任。太子繼位後,他數次升遷,爬上司禮監掌印太監的寶座。一旦大權在握,便引誘武宗沉溺於驕奢淫逸中,自己趁機專擅朝政,時人稱他為「立皇帝」,武宗為坐皇帝。他排斥異己,陷害忠良,朝中正直官員大都受他迫害。但他最終落得個凌遲處死、千刀萬剮的下場,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
◎悅主受寵,奪得大權
◎瘋狂報復,打擊異己
◎專權擅勢,納賄自肥
◎多行不義必自斃,終被剷除
◎後人話劉瑾:史上最富有的太監
第八監 魏忠賢:空古絕今的九千歲
他本是一市井惡少,目不識丁,卻諳熟拍馬絕技,入宮不久,得太監王安提拔,又與皇孫奶娘客印月打得火熱,並接近萬曆皇帝,地位和權勢與日俱進。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後,他和客印月開始攬權幹政。他恩將仇報除王安,逼走魏朝,杖殺朝臣,大興冤獄,捕殺東林黨,私植黨羽,自稱「九千歲」,為歷代閹官專權亂國的最高峰。他不僅獻春藥慫恿皇帝淫逸,還自己娶妻納妾,搶奪天下民女,害死多少薄命紅顏。
◎淨身入宮,察色邀寵
◎平步青雲,謀害異己
◎擅權亂政,殘害東林黨
◎多行不義,自縊而亡
◎後人話魏忠賢:「騎在萬歲頭上的九千歲」及其另一面
第九監 李蓮英:清代厚黑第一閹
他在清宮長達五十二年。是慈禧太后最寵愛的貼身太監,也是清代品位最高、權勢最大、財富最多、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大宦官。他對主子的奴才嘴臉,和對同類的兇狠殘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狐假虎威,有恃無恐,置諸侯於腦後,視軍機大臣為等閒,朝中大員及外省督撫,無不對其巴結奉承,仰其鼻息。舉凡國政朝綱、清廷要務,無不與聞,無不干預。
◎自閹進宮,受到寵信
◎權力日盛,肆意妄為
◎朝臣抨擊,暴病而亡
◎後人話李蓮英:亦正亦邪,陪伴女主子一生
第十監 小德張:皇后的主心骨
他幼年家貧,遭人恥笑,奮而自宮做了太監。小德張入宮之後,左右逢迎,依靠隆裕太后對自己的寵愛,逐漸從一個低級的小太監做到了太監總管的位子,成為繼李蓮英之後的又一個清宮權宦。
◎自宮入皇門,慈禧賜名號
◎為討慈禧歡心,使出渾身解數
◎兩面逢迎,機靈留後路
◎保隆裕太后之位,身居要職
◎依仗寵信,大肆斂財
◎弄權作勢,窮奢極侈
◎思想空虛,無聊了餘生
◎後人話小德張:清朝最後一代大總管
他善於在秦始皇面前阿諛奉承,因而逐漸獲得權力,為他後來篡改遺詔、扶立庸主、當上丞相打下了基礎。他從一名小小的宦官起家,卻在秦王朝最後的幾年翻雲覆雨,整個天下曾離他不過一步之遙。他一手將秦帝國千秋萬代的春夢引向破滅,也將自己一併埋葬在了滾滾的歷史洪流之中。
◎處心積慮博得始皇寵信
◎秦始皇去世後祕不發喪
◎偷樑換柱詐稱遺詔
◎濫殺無辜,恣意妄為
◎「指鹿為馬」欲取秦而代之
◎結束罪惡滔天的一生
◎後人話趙高:陰謀的化身
第二監 李輔國:超乎常人的厚黑高手
他相貌奇醜無比,四十歲之前無所作為。安史之亂期間,勸說太子李亨繼承帝位。唐肅宗即位後,被加封為元帥府行軍司馬,開始掌握兵權,並改名為輔國。之後又因擁立代宗即位,被冊封為司空兼中書令。大權在握後李輔國更加為所欲為,最後被人刺殺身亡。
◎假傳聖意,權傾朝野
◎一手遮天,殘害忠良
◎作惡多端終難逃一死
◎後人話李輔國:標準的奸佞,亂臣賊子
第三監 劉騰:廢後戮相,倒行逆施
他幼時因罪被閹,入宮做了宦官,補小黃門。因善於觀察,心藏計謀,能通解人意,因而特蒙恩寵,很快由小黃門轉補中黃門。他原本是遭閹割的可憐人,因其內心深處的屈辱和自卑感,產生了種種報復、殘忍、貪婪、凌虐的變態行為。
◎善於察言觀色而得到升遷
◎瞅準皇上心腹博取寵愛
◎左右逢源,恃權胡為
◎開棺戮屍,可悲下場
◎後人話劉騰:倒行逆施的心理變態
第四監 仇士良:欺君抑相,竊國弄權
他一生弄權干政,穩步高升,從一個侍侯太子的一般太監,歷任監軍、內外五坊使、左神策軍中尉、驃騎大將軍、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知內侍省事等要職,封楚國公,死後追贈楊州大都督。仇士良檀權攬政二十餘年,一貫欺上瞞下,排斥異己,橫行不法,貪酷殘暴,先後殺二王、一妃、四宰相,使當時朝政變得更加昏暗和混亂。
◎得勢後乘隙控制軍權
◎甘露事變失事,重臣慘遭殺戮
◎皇帝被其操縱,心狠手辣行惡
◎貪酷殘暴終落個削官沒籍
◎後人話仇士良:仇視賢良的一代奸奴
第五監 童貫:史上唯一被封為王的宦官
他的經歷,充滿了傳奇般的悲喜劇色彩。他的一生中,開創了幾項中國歷史之「最」:中國歷史上握兵時間最長的太監;中國歷史上掌控軍權最大的太監;中國歷史上獲得爵位最高的太監;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出使外國的太監。
◎「仗義疏財」,媚迎事主
◎控制軍權,虛功受獎
◎宋金結盟抗遼——金變被動為主動
◎潰敗潛逃,終將伏法
◎後人話童貫:閹割過的王爺不孤獨
第六監 王振:禍國害民的文人太監
他是明朝第一個專權的太監。原本是一個失敗的教書先生,卻自閹進宮,得到了明英宗的寵倖,開始擅權,結黨營私,干涉朝政,揭開了「太監帝國」的序幕。為了建立所謂的豐功偉績,根本不知作戰為何物的他,慫恿皇帝親征來犯的也先,結果是皇帝做了俘虜,自己賠上了性命。
◎採取兩面手法,獲得寵信
◎黨同伐異,大耍淫威
◎土木之變,終落得可恥下場
◎後人話王振:把皇帝賣給敵人的絕世太監
第七監 劉瑾:「八虎」之首「立皇帝」
他六歲時被太監劉順收養,後淨身入宮當了太監,遂冒姓劉氏,侍奉太子朱厚照,即後來的明武宗。他善於察言觀色,隨機應變,深受信任。太子繼位後,他數次升遷,爬上司禮監掌印太監的寶座。一旦大權在握,便引誘武宗沉溺於驕奢淫逸中,自己趁機專擅朝政,時人稱他為「立皇帝」,武宗為坐皇帝。他排斥異己,陷害忠良,朝中正直官員大都受他迫害。但他最終落得個凌遲處死、千刀萬剮的下場,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
◎悅主受寵,奪得大權
◎瘋狂報復,打擊異己
◎專權擅勢,納賄自肥
◎多行不義必自斃,終被剷除
◎後人話劉瑾:史上最富有的太監
第八監 魏忠賢:空古絕今的九千歲
他本是一市井惡少,目不識丁,卻諳熟拍馬絕技,入宮不久,得太監王安提拔,又與皇孫奶娘客印月打得火熱,並接近萬曆皇帝,地位和權勢與日俱進。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後,他和客印月開始攬權幹政。他恩將仇報除王安,逼走魏朝,杖殺朝臣,大興冤獄,捕殺東林黨,私植黨羽,自稱「九千歲」,為歷代閹官專權亂國的最高峰。他不僅獻春藥慫恿皇帝淫逸,還自己娶妻納妾,搶奪天下民女,害死多少薄命紅顏。
◎淨身入宮,察色邀寵
◎平步青雲,謀害異己
◎擅權亂政,殘害東林黨
◎多行不義,自縊而亡
◎後人話魏忠賢:「騎在萬歲頭上的九千歲」及其另一面
第九監 李蓮英:清代厚黑第一閹
他在清宮長達五十二年。是慈禧太后最寵愛的貼身太監,也是清代品位最高、權勢最大、財富最多、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大宦官。他對主子的奴才嘴臉,和對同類的兇狠殘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狐假虎威,有恃無恐,置諸侯於腦後,視軍機大臣為等閒,朝中大員及外省督撫,無不對其巴結奉承,仰其鼻息。舉凡國政朝綱、清廷要務,無不與聞,無不干預。
◎自閹進宮,受到寵信
◎權力日盛,肆意妄為
◎朝臣抨擊,暴病而亡
◎後人話李蓮英:亦正亦邪,陪伴女主子一生
第十監 小德張:皇后的主心骨
他幼年家貧,遭人恥笑,奮而自宮做了太監。小德張入宮之後,左右逢迎,依靠隆裕太后對自己的寵愛,逐漸從一個低級的小太監做到了太監總管的位子,成為繼李蓮英之後的又一個清宮權宦。
◎自宮入皇門,慈禧賜名號
◎為討慈禧歡心,使出渾身解數
◎兩面逢迎,機靈留後路
◎保隆裕太后之位,身居要職
◎依仗寵信,大肆斂財
◎弄權作勢,窮奢極侈
◎思想空虛,無聊了餘生
◎後人話小德張:清朝最後一代大總管
序
前言
太監是何許人也?
提到太監,由於受電視劇的影響,很多人腦海中就會出現這種影像:外觀上,他們滿臉壞笑,諂媚無比,嗓音尖利,面黃無鬚;人品上,他們陰險狠毒、狡詐無比,陷害忠良,攪亂國政;朝堂上,他們和皇帝的關係匪淺,而且遍地爪牙,手眼通天;經濟上,他們身家億萬,富可敵國,卻貪得無厭,因私廢公。
可是中國自盤古開天闢地至今,已走過幾千年的歲月了,而太監身為皇帝身邊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各個王朝所起的或好或壞的作用,是無法忽視的。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一群人?為什麼他們要那樣為人處事?為什麼他們可以掌握政權甚至改寫國家的命運?究竟是什麼魔法可以讓皇帝對他們百般信賴?難道他們真的個個都那麼壞嗎?
或許,通過對這個群體的表現,我們可以得出對歷史的另一類解釋,對人性也會有另一種角度的思考。也許人們在謾罵譏笑他們的同時,卻可以看到,在他們身上,也有我們這群正常人的影子。
本書特別選出宋明清以及更早的朝代,分別精心挑選出「心最狠」及「貪最多」的大太監,敍述了他們在皇權中的榮辱沉浮。皇權為他們帶來了榮譽和財富,也帶來了恥辱和殺戮;他們為皇權提供了服務與保障,也造成了皇權更迭與顛覆。除了展現皇權與太監的關係,也從多方面為您揭開一幅幅血淚斑斑的歷史畫面。
太監是何許人也?
提到太監,由於受電視劇的影響,很多人腦海中就會出現這種影像:外觀上,他們滿臉壞笑,諂媚無比,嗓音尖利,面黃無鬚;人品上,他們陰險狠毒、狡詐無比,陷害忠良,攪亂國政;朝堂上,他們和皇帝的關係匪淺,而且遍地爪牙,手眼通天;經濟上,他們身家億萬,富可敵國,卻貪得無厭,因私廢公。
可是中國自盤古開天闢地至今,已走過幾千年的歲月了,而太監身為皇帝身邊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各個王朝所起的或好或壞的作用,是無法忽視的。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一群人?為什麼他們要那樣為人處事?為什麼他們可以掌握政權甚至改寫國家的命運?究竟是什麼魔法可以讓皇帝對他們百般信賴?難道他們真的個個都那麼壞嗎?
或許,通過對這個群體的表現,我們可以得出對歷史的另一類解釋,對人性也會有另一種角度的思考。也許人們在謾罵譏笑他們的同時,卻可以看到,在他們身上,也有我們這群正常人的影子。
本書特別選出宋明清以及更早的朝代,分別精心挑選出「心最狠」及「貪最多」的大太監,敍述了他們在皇權中的榮辱沉浮。皇權為他們帶來了榮譽和財富,也帶來了恥辱和殺戮;他們為皇權提供了服務與保障,也造成了皇權更迭與顛覆。除了展現皇權與太監的關係,也從多方面為您揭開一幅幅血淚斑斑的歷史畫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