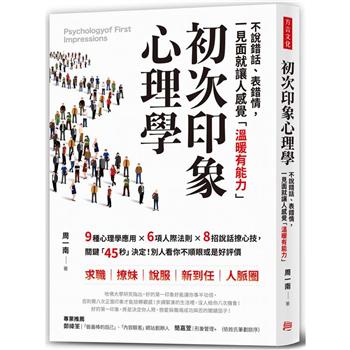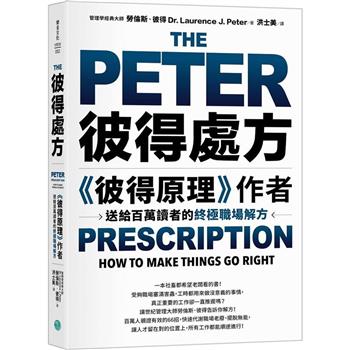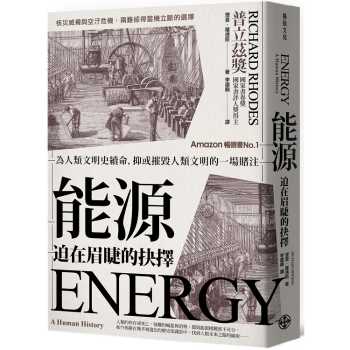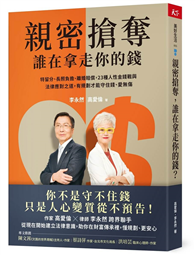推薦序
大命題大圖像的歷史追索--讀賈德的《戰後歐洲六十年》
楊照
「戰後」對台灣讀者,是太簡單的兩個字,簡單到很難一眼理解這本書要處理的是甚麼題材,因為「戰後」做為一個歷史概念,在台灣基本上是陌生的。
這毋寧是一件奇怪的事,因為只要稍微翻讀賈德在書最前面解釋「戰後」概念的說法,我們很容易就發現這樣的概念,對於描述台灣歷史的一些關鍵轉折,多麼有用。
「戰後」的完整說法應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指的不單純是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這件事,以及其後的時間,而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基點,去紀錄、去看待這場戰爭產生了哪些戰爭以外的巨大影響,或者換一個說法,這場戰爭製造了多少不會隨著軸心國投降就結束的後遺症,持續改變這個世界的面貌。
從一個普遍的角度看,我們當然可以說,一九四五年之後,一直到今天,甚至一直到往後的永久,世界的樣態都被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樁歷史事實改變了,所以「戰後」時期可以從一九四五年一直無限往後延續下去,沒有終了。但這不是賈德標舉「戰後」的用意,也絕非引進「戰後」做為一個歷史斷代概念真正的作用。賈德試圖以這本大書論證的,是戰爭的破壞、為了解決戰爭所採取的非常手段,給那個時代的歐洲,帶來了絕大的問題,往後很長一段時間,歐洲各國的變化發展,都受到這套問題的牽制,二次大戰是場拖長、難以醒來的噩夢,一直壟罩著歐洲,花了幾十年時間,歐洲才終於走離「戰後」,將戰爭的敗壞連環效果拋在身後,眼前產生了新的可能選擇。
「戰後」概念成立的第一條件,是第二次大戰造成的空前破壞。包藏在「戰後」歷史的一個弔詭主題,正是人們如何刻意或無心地遺忘了戰爭的恐怖結果。和戰爭剛結束時歐洲滿目瘡痍的情況相比,歐洲人的記憶實在短暫地驚人。一部份因素是戰爭結束後主導國際情勢的強權之一,是在大戰中沒有受到本土破壞的美國;另一部份的因素則是:正因為破壞太鉅、痛苦太深,不論戰勝或戰敗的歐洲人,都是實質的「倖存者」,也就都無可避免活在「倖存者難局」中--唯有遺忘,才能省下應對破壞痛苦的精神能量,也才能鼓起足夠勇氣來重建現實。
後來被遺忘了的,賈德耐心地考掘出來,除了戰爭本身的轟炸、殺戮之外,還包括了正式停戰之後,隨即引發的頻繁內戰和大舉遷徙。歐洲國界在短時間內,被重劃了不只一次,尤其是中歐、東歐國家,他們先要處理被德國佔領遺留下來的困擾,繼而又得面對蘇聯侵占強加的新秩序。德國納粹的種族主義政策,掀開了過去幾百年被勉強壓蓋住的潘朵拉盒子,釋放出了種族分類的衝突因子,不會隨著納粹戰敗瓦解就消散無蹤。劃界、內戰、遷徙,基本上都和種族分類衝突有關。
賈德還原了這部分「不方便」的記憶,無可避免讓我們驚覺:原來緊隨著第二次戰爭結束而來的中國內戰及大遷徙,是和歐洲同步發展進行的,我們也就同時理解了,國共內戰及其後的大遷徙,可以、也應該從二次大戰的後遺症角度來予以分析、理解。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書中,透過引進德國戰後的紀錄,平行對比提醒過我們:二戰結束後,不只有中國在進行人口大遷徙,那是一個大流浪的時代。賈德的書則更全面、更具說服力地刻畫了這樣一個遍地內戰、幾千萬人流離失所的戰後圖像,供我們做更清楚的比對。
這明白顯示了:「戰後」的歷史分析架構,儘管賈德用來集中描述歐洲所發生的事,不過實質上,這個架構對於我們整理中國,乃至亞洲從四○年代中期到至少七○年代結束,這幾十年間的事,也大有幫助。
採用了這樣的分析架構,也就決定了賈德所依賴的史料,以及其敘事風格。《戰後歐洲六十年》書中有大量的統計數字,有複雜的社會動盪描述,後面的篇幅還會有精巧的集體心理討論,然而相對地,沒有太多關於個人--不管是英雄或惡棍--的刻畫。賈德忠於「戰後」的大歷史命題,要提供給讀者的,是一幅經歷半世紀變化距離才得以看清楚的歐洲鳥瞰圖,大塊大塊的色彩塗抹,讓人真的能夠快速領略從戰爭到「戰後」、到走出「戰後」的歷史軌跡。他冷靜堅持,不受誘惑,不會為了煽情的戲劇性效果而破壞統一的敘事風格,不將眼光停留在任何精彩的個人--這段時間畢竟出現了多少我們極為熟悉的精采個人啊--身上。
另外一項對於大歷史命題的難得堅持,表現在《戰後歐洲六十年》書中敘述詳略的安排。因為要解釋歐洲如何一步步從「戰後」走出來,賈德的寫法是愈接近二次大戰剛結束的部分,說得愈是詳細,而且愈是今天被排除在邊緣的,只有放回二戰背景中才能明白其意義的記憶,賈德就愈是用心,不厭其煩地對我們說明。
同樣的命題,落入沒那麼高明的史家手中,很容易就會失去了大圖像大關懷,讓瑣碎卻有趣的細節,尤其是個人角色的表現,搶走了社會結構解讀的鋒頭。也很容易就依照人類記憶的天性,安排成「詳今略古」的寫法。
《戰後歐洲六十年》因而是一本難得、傑出的歐洲左翼史學精華之作。要彰顯的,正是社會、經濟等集體力量,而非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無名的眾人在戰爭中所受的苦難,戰後圖存的複雜互動掙扎,塑造出歐洲這樣一條「戰後」的歷史軌跡,絕非觀察記錄史達林等少數政治領袖所能看得出來的。
在台灣,我們沒有這樣的大歷史命題的視野。甚至連在被「唯物史觀」壟罩幾十年的中國大陸,左翼社會史的歷史關懷竟然也幾乎都被遺忘了,歷史書寫突然全都回到描述個人、凸顯個人的傳統老路子,讓歷史知識範圍大大縮水,歷史研究的技藝大開倒車。在這樣令人遺憾的背景下,我們更應該閱讀《戰後歐洲六十年》,接受賈德歷史視野的刺激,認真思考我們自己的「戰後」歷史命題。
導論
我是在維也納的火車總站—西火車站,換車時,初次決定撰寫此書。時間為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那是大家對未來感到樂觀的時期。那時我剛從布拉格回來,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即領導「公民論壇」的劇作家和歷史學家,正在布拉格著手推翻共產主義警察國家,要把四十年「真正存在的社會主義」(real existing socialism)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在那幾個禮拜前,柏林圍牆已出乎眾人意料被突破。在匈牙利,一如在波蘭,人人忙著應付後共產時代的政治挑戰:幾個月前還呼風喚雨的舊體制,這時漸漸被打入冷宮。立陶宛的共產黨剛剛宣布要立即脫離蘇聯獨立。搭計程車前往火車站途中,車上的奧地利電台傳來羅馬尼亞人民起義反抗尼古拉.希奧塞古任人唯親之獨裁政權的最早報導。政治地震正把二次大戰戰後冰封歐洲的大地震得四分五裂。
誰都看得出,一個時代結束了,新歐洲正誕生。但隨著舊體制的消逝,許多存在已久的認知將受到質疑。原本看來歷久不衰且從某種角度看似乎不可避免的東西,將顯得不再那麼顛仆不破。冷戰對峙;將東、西歐隔開的分裂現象;「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較量;繁榮西歐與其東邊蘇聯集團諸衛星國,各有自己一套論述,彼此不交流:這些全不能再視為意識形態驅策下必然的結果或不可移易的政治鐵律。它們是歷史的偶然產物,而歷史正把它們推進冷宮。
本書講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史,因此以一九四五年為起點:即德國人所謂的Stunde nul,零時。但一如二十世紀的其他任何事物,這段歷史都以始於一九一四年,使歐陸開始墮入浩劫深淵的那場三十年戰爭為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戰本身對所有參與者來說,都是個令人痛苦難忘的殺戮戰場—塞爾維亞十八至五十五歲的男子,有一半死於那場戰爭—但一番打殺後,什麼問題都沒解決。(與當時普遍的看法相反的)德國並未在那場戰爭或戰後協議中被擊垮,否則它怎能在二十五年後就站起來,將歐洲幾乎完全掌控在手裡。事實上,德國未支付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債務,因此,協約國獲勝的代價,超過德國落敗的代價,從而使重新站起來的德國比一九一三年時更為強大。三十年前隨著普魯士興起而出現於歐洲的「德國問題」,至此仍未解決。
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陳述托洛斯基的史觀時,引用希臘詩人阿基洛科斯(Archilochus)的著名詩句,為兩種推理方式做了具影響力的區別:「狐狸懂很多事,但刺蝟懂得一個大原則。」套用柏林的措辭,這本書絕不是「刺蝟」。我在書中沒有什麼關於當代歐洲史的大理論要提出;沒有包羅一切的主題要闡述;沒有包羅萬象的故事要講述。但不能因此認定,在我眼中,二次大戰後的歐洲史沒有貫穿一切的新趨勢。其實它不只出現一個新趨勢。像狐狸一樣,歐洲懂得很多。
首先,這是段歐洲勢力消退的歷史。一九四五年後,歐洲諸國再也無法奢望稱雄國際或建立帝國。惟一的兩個例外—蘇聯和只在某種程度上稱得上是例外的英國—都自認是半歐洲的國家,且無論如何,在本書所述的這段時期結束時,兩國的勢力也都大大萎縮。歐陸上的其他地方,大部分受過戰敗、遭占領的羞辱。這些地方無法靠自力擺脫法西斯的掌控;也無法在無外援下擋住共產主義入侵。戰後歐洲靠外人來解放—或受到外人的監禁。費了很大一番努力,加上數十年歲月,歐洲人才重新掌控自己的命運。歐洲過去的海上帝國(英、法、荷、比、葡),在這些年裡失去了海外領土,全縮回他們的歐洲母土,注意力轉回歐洲自身。
其次,在二十世紀後期幾十年,歐洲史的「主敘述」漸漸式微。這些主敘述是十九世紀恢宏的歷史理論,對進步與改變、對革命與轉型,各提出它們心目中的理想形式,而且它們助長了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將歐洲撕裂的那些政治計畫和社會運動。這一現象也是只有放在泛歐洲的大勢下觀察才能理解,而這個大勢是:隨著西歐境內政治狂熱的消退(只有在知識界裡居少數的非主流人士身上例外),基於某些大不相同的原因,東歐境內的政治信仰也消失,史達林主義遭到唾棄。在一九八○年代,的確有一短暫期間,讓人覺得知識界右派似乎會以同樣屬於十九世紀的計畫—拆掉「社會」,把公共事務丟給不受管制的市場和最小政府去支配—為主軸東山再起;但最後無疾而終。一九八九年後,在歐洲,沒有涵蓋所有面向的左派或右派意識形態計畫可供採用,只有對自由的憧憬,而現在,對大部分歐洲人來說,自由是個已實現的諾言。
第三,偶然間,「歐洲模式」姍姍來遲出現了,為歐洲在意識形態掛帥的過去已死的雄心,提供了不算太差的替代品。這一模式是以社會民主黨、基督教民主黨提出的法案和歐洲共同體(與後來歐盟)的蟹狀外延機構兩者折衷調合而成,是帶有鮮明「歐洲」特色,用以管理社交、國與國關係的方式。這一歐洲路線,涵蓋從孩童保育到國與國間法律規範的種種事物,代表的不只是歐盟和其成員國慣常的治理作為;二十一世紀開始時,歐洲模式已成為爭取加入歐盟者的明燈和榜樣,對美國構成全球性挑戰,與「美國生活方式」一起爭奪世人的垂青。
從只是個地理名詞(和對那樣的說法相當苦惱的地方),轉型為令個人和國家都起心效法、心生嚮往的地方,歐洲這一明顯出乎意料的轉變,乃是個緩慢、層層累加的過程。套用亞歷山大.瓦特(Alexander Wat)針對兩次大戰之間波蘭政治人物的虛妄認知所提出的嘲諷性評論,歐洲不是「注定偉大」(doomed to greatness)。從一九四五年的情勢,乃至從一九七五年的情勢,肯定誰都料想不到歐洲會以這樣的身分冒出頭。這一新歐洲並非依循事先設想好的共同計畫而出現:沒有人著手催生它。但一九九二年後每個人都看出,歐洲在國際格局裡占據這新位置後,與外界的關係,特別是與美國的關係,有了新的面貌—對歐洲人和美國人來說都是。
這也是貫穿這本描述戰後歐洲之著作的第四個主題:戰後歐洲與美國複雜且常遭誤解的關係。西歐人希望美國參與一九四五年後的歐洲事務,但又痛恨那參與和那參與所隱含歐洲衰落的意涵。此外,美國雖在歐洲駐軍,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後那幾年,但構成「西方」陣營的大西洋兩側,彼此仍是大不相同。當時西歐對冷戰的認知,大不同於冷戰在美國所激起的那種相當危言聳聽式的反應,而接下來五○、六○年代歐洲的「美國化」,則在今日常遭到誇大。
東歐對美國與美國屬性的認知,當然大不相同。但在東歐,若過度強調一九八九年前和一九八九年後美國對東歐人榜樣般的影響,同樣會悖離事實。東西歐境內的異議批評者,例如法國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或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維爾,特意強調他們未把美國當作可供他們所屬社會效法的模式或榜樣。一九八九年後的東歐年輕一代,的確一度渴望以美國模式—有限的公用事業、低稅、自由市場—來將他們國家自由化,但這一模式最終未得到普遍接受。歐洲的「美國時刻」屬於過去。東歐的「小美洲」未來,則無疑要在歐洲裡尋求。
最後,歐洲的戰後史是一段被靜默籠罩的歷史;是不再兼容並蓄的一段歷史。歐陸曾如一塊精細複雜的織錦,由重疊的語言、宗教、族群、民族交織而成。其中許多城市,特別是位於新、舊帝國邊界交會處的較小城市,例如的里雅斯特、塞拉耶佛、薩洛尼卡、切爾諾維茨、敖得薩或維爾納,曾是不折不扣的多文化社會。在那些城市裡,天主教徒、東正教徒、穆斯林、猶太人和其他族群共居一地,稀鬆平常。但我們不該把這個舊歐洲理想化。波蘭作家塔德烏什.博羅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所謂的「在歐洲正中心燒得嘶嘶作響那個不可思議、近乎好笑的民族熔爐」,定期因為暴動、屠殺、集體迫害而四分五裂,但這樣的熔爐的確曾存在,且仍存於在世者的記憶中。
一九八○年代起,特別是蘇聯瓦解、歐盟擴大之後,歐洲走上多文化之路。難民;外勞;為了工作和自由而被吸引回帝國首都的歐洲前殖民地的居民;從位於歐洲外擴後之邊陲地區的衰落國家或高壓國家志願或非志願投奔而來的移民,已共同將倫敦、巴黎、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柏林、米蘭和另外十幾個地方,轉變成多民族的世界性都市,不管那些城市是否樂見這樣的轉變。
歐洲冒出這些「非我族類」的新居民—例如歐盟境內現在可能有一千五百萬穆斯林居民,且還有八千萬穆斯林在保加利亞、土耳其等著獲准進入歐盟—不只突顯了歐洲現今對愈來愈多元的未來所感到的不安,也突顯了歐洲是如何輕易就遺忘那些在歐洲的過去裡死掉的「非我族類者」。關於戰後歐洲的穩定是如何倚賴史達林、希特勒的成就這點,在一九八九年後呈現得最為清楚。這兩位獨裁者,在戰時共犯的協助下,一起剷平了如灌木叢生的荒原般犬牙交錯的民族組成,為戰後那個較不複雜的新歐陸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一九八九年起—隨著存在已久的禁忌遭到打破—事實證明,承認為歐洲重生所付出的道德代價(有時是在不顧惡毒反對與否認的情況下)乃是可能的事。如今的客觀環境,使波蘭人、法國人、瑞士人、義大利人、羅馬尼亞人和其他國家的人,較能夠去了解—如果他們有心去了解的話—幾十年前他們國內所真正發生過的事。就連德國人,如今也開始修正此前他們所接受的本國史,並帶來弔詭的結果。如今,幾十年來頭一遭,德國人的苦難和德國人的受害—不管讓他們受難受害者是英國轟炸機投彈員、俄羅斯軍人或把他們驅逐的捷克人—開始受到注意。在某些地方,再度有人試探性的提出,猶太人並非惟一的受害者。
這些探討是好是壞,見仁見智。這些公開追憶的舉動,象徵政治走上正常發展?或者如戴高樂等人所深切了解的,有時,遺忘較為明智?在書末的結語,我會探討這問題。最近這些造成紛擾的追憶動作,在與當前迸發的民族偏見或種族偏見相提並論時,有時被視為是歐洲原罪的邪惡證據:歐洲之未能從過去罪行中得到教訓、歐洲失憶症般的懷舊行為、歐洲愈來愈想回歸一九三八年的傾向。但在此我只想指出,這樣的認知沒有必要。套句美國棒壇傳奇貝拉的話,這不是「舊事重演」。
此刻的歐洲並非在重新進入其紛擾不安的戰時過去,反倒在離開那段過去。今日的德國,就像歐洲其他地方,比過去五十年的任何時刻,更深刻意識到其二十世紀的歷史。但這不表示德國正被拉回那個過去,因為那段歷史從未走開。誠如這本書所試圖呈現的,二次大戰的長影濃濃罩住整個戰後歐洲,但它無法得到完全的承認。對歐洲晚近歷史的緘默,乃是建構歐洲未來的必要條件。如今,在幾乎其他每個歐洲國家境內都爆發了令人不快的公開爭辯之後,不知為何,我覺得讓德國最終也能公開質疑官方出於好意建構之歷史的準則,乃是適當(且無論如何不可避免)的事。對此,我們或許不是很舒服;那說不定還不是個好兆頭。但那是種結束。希特勒死亡六十年後,他的戰爭和那場戰爭的後果正在進入歷史。在歐洲,戰後持續了很久,但終於要走到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