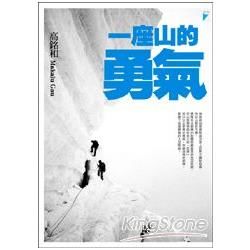他是以「台灣隊」名義登上聖母峰的第一人,也是聖母峰世紀山難奇蹟的倖存者。失去十指與十趾卻用堅韌意志克服身體殘缺的他,更是一個跨越生命難關的勇者!
我沒有死在聖母峰上,撿回了一條命,我是幸運的;我的手指還殘留著一小節拇指,可以做些簡單的事,我是幸運的;雖然我失去了腳趾,但我仍然能走路,我是幸運的。山,讓我的人生充滿遺憾,也讓我的人生充滿燦爛!--高銘和8400公尺的高山、零下60℃的嚴寒氣候、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世界。1996年春天,在成功登上聖母峰頂、站上世界之巔後,高銘和遇上了聖母峰攀登史上最嚴重的世紀山難。那場山難奪走了8位國際登山好手的生命,但他憑著堅強的意志力,熬過徹夜的風雪,奇蹟似的成了從死神手中逃脫的幸運兒。
鼻子、手指、腳趾壞死切除,15次大小手術,失去健康與理想的日子。獲救後的高銘和遭受到嚴重的凍傷,必須切除所有壞死的部位,醫生為他剜下額頭的肉填補鼻子、將雙手縫在肚子以生長新肉,痛楚不堪的手術救治了他,卻也讓他失去了生活的能力,甚至是攀登下一座山的權利。為了再度回到高山懷抱,人生再大的極限都可以超越!高銘和沒有自暴自棄,他花了一年時間努力復健,從最基本的刷牙洗臉學起,到寫字拿相機,只為了完成他多年來的心願--中國百岳的拍攝計劃。終於,他在1998年重返聖母峰,更多次前往新疆、西藏的高山勘察,因為對他而言,山是支持他向前走的最大動力!高銘和樂於與人分享自己的經歷,演講足跡更遍及台灣、東南亞,不但得到了無數的迴響,也激勵了每一個人的心!
作者簡介:
高銘和(Makalu Gau)
台灣從尼泊爾登上聖母峰的第一人,生於1949年,從小在瑞芳長大,對那時的他來說,山是他生活的地方與遊戲的場所。從中原大學土木系畢業後,高銘和便進入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工作,在同事的邀約下,開始登山健行,後來又接觸攀岩,真正開啟了他的登山生涯。短短10年之內,高銘和已爬遍台灣群山,於1982年開始遠征海外,轉往國外高山邁進。
1992年前往西藏攀登聖母峰,但最後未能成功;後來於1996年春季重登,終於成功站上聖母峰頂,卻也因受困暴風雪中,遭受嚴重凍傷而切除了鼻子、手指、腳趾和腳跟。後來,他歷經了15次大小手術和1年的復健,才重拾人生。1997年,高銘和將1996年攀登聖母峰的前後經過,寫成著作《九死一生》。(大地地理出版,2003年曾由秀威資訊BOD印行。)他的故事鼓勵了很多遭遇相近的人,出書之後更廣受邀約到處演講,持續與大家分享他的經歷。高銘和於1991年起開始從事《中國百岳攝影計劃》,為了繼續未完的工作,他在1998年重回熱愛的高山,前往西藏、新疆、四川等地,持續執行《中國百岳攝影計劃》的拍攝工作,並預計在2012年完成。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聯合推薦
2009年聖母峰登頂者/江秀真
2009年聖母峰登頂者/伍玉龍
2009年聖母峰登頂者/黃致豪
台北市教育局局長/吳清山
國際奧委會委員暨國際拳擊會主席/吳經國
玉山國家公園處長/陳隆陞
2009年聽障奧運基金會總執行長/盛治仁
歐都纳董事長/程鯤
營建署署長/葉世文
作家/劉克襄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戴遐齡
名人推薦:◎聯合推薦
2009年聖母峰登頂者/江秀真
2009年聖母峰登頂者/伍玉龍
2009年聖母峰登頂者/黃致豪
台北市教育局局長/吳清山
國際奧委會委員暨國際拳擊會主席/吳經國
玉山國家公園處長/陳隆陞
2009年聽障奧運基金會總執行長/盛治仁
歐都纳董事長/程鯤
營建署署長/葉世文
作家/劉克襄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戴遐齡
章節試閱
【序】勇敢攀登自己人生的高峰
一九九六聖母峰世紀大山難已經過了十多年了,但對親身經歷這場震驚世界的災難而幸運地倖存下來的我,卻仍存在著無限的感傷和感觸。
對喜愛登山的人來說,都會記住當年發生的這樣一件大事;但也都會記取經驗,在後續的攀登活動中,設法避免再度發生類似的山難事件。
近幾年來,我一直有機會與各行各業的人士,分享自己在聖母峰上求生存的經過,也告訴很多人,在受傷住院期間是如何克服心理障礙,以及出院後,又是如何鼓起勇氣重返喜馬拉雅山,最後的結論就是:人是那麼的渺小,所以要懂得謙卑,特別是面對大山大水的時候。
我常學著與山對話,把山當成知己,以柔軟的身段去親近它、了解它,並從中學習更多大自然的法則和尋求快樂的泉源。
每個人的一生,總會遇到許多不如意及讓人遺憾、沮喪的事情;我也是如此意外碰上了。但是要相信,人只要活著就有希望,堅持到底必能成功。我期盼這本書所呈現的故事,可以讓人思考一些不同的人生道路,勇敢地去攀登自己人生的高峰。
楔子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下午一點,那天風不是很大,晴空萬里,我人在聖母峰南峰約海拔八千七百公尺處,只剩下一百公尺不到就可以登頂,雪巴人卻向我提出撤退的建議,讓我當場呆住!
原因之一是雪巴人丹增的氧氣面罩出了問題,不得不下到第四營去,讓深信藏傳佛教的他們心底萌起不祥之感。但因為同時正有三十多人向著頂峰挺進,絲毫沒有撤退的跡象;再加上我背負著許多責任與國人的期許,在停留觀察約半小時之後,我們還是決定登頂,但有一個原則,那就是:快上快下。
三點十五分,歷史的一刻,我終於站上世界的頂峰。倉促地拍下留念的照片之後,便趕緊下山。誰知天氣變化得很快,拍下登頂照片時天空還是一片蔚藍,等我下到八千六百公尺時卻已風雪交加,連站都站不穩,面罩與防風鏡不斷地起霧、結冰,讓我的行動受到許多限制。隨著天色漸漸暗下來,我與雪巴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遠,最後,剩我一人獨自留在漆黑的雪地裡……
原本我以為雪巴人先去找路,會再回頭找我,但隨著時間一點一滴流逝,我放棄了那樣的念頭,心底感到慌亂與害怕,但腦筋卻是異常清醒理智,不停地想著如何渡過這個難關的方法。
這時,留在原地是最好的方式,免得因為走錯方向或滑落冰坡而一命嗚呼;我想挖個雪坑躲進去,但冰斧一碰到冰面就反彈,只好作罷。我知道自己的處境極為兇險,因為,要在狂風暴雪的八千四百公尺處度過長夜,談何容易!
由於意識到情況不太樂觀,我開始想立遺囑告訴我的家人、朋友及贊助廠商,明白交代「我被困在什麼地方?為什麼下不去?」也想到了《中國百岳》無法完成的遺憾。
原本我打算花兩個月的時間在聖母峰南側進行拍攝,因為要拍攝《中國百岳》的山峰,最好能完整呈現山的東西南北側。所以我攀登聖母峰的原因之一,就是想捕捉它南側的面貌,下山之後再接續到西藏,行程早已安排好了。
沒想到,我卻卡在聖母峰頂,下不下得去都還是未知數,何況是《中國百岳》的拍攝。一想到自己沒辦法完成計畫,莫名的幻覺突然都出現了。我隱約看見錦繡的老闆對我說「你這個瘋子!」影像就好像早期收訊不良的電視機般,一下彩色、一下黑白,跳動模糊不定。
我也感覺到一張張黑白的臉孔在對我說話,雖然無法辨識出是誰,但感覺得出來是熟悉的人。之後,影像慢慢清楚,彩色的畫面中出現了等在基地營的隊友,其中的林道明還笑著對我說:「隊長,還不趕快下來,我們要慶功了。」最後甚至連家裡的小孩也出現了。
我聽不清楚孩子的聲音,看到的是他面向窗台的黑白畫面,眼神望向遠方,好像在說:「爸爸去爬山那麼久,怎麼還沒有回家?」這一幕讓我打從心底一酸,想到如果自己真的無法回去,那我的家人怎麼辦?
剎那間,我的心忍不住悸動起來,於是我告訴自己,無論如何都要活著回去。
我分析出會讓自己陷入死亡的幾個原因:不是溫度太低,就是空氣稀薄、腦部缺氧而死。這時我想起尼泊爾第一位登頂聖母峰十次的安力達雪巴曾告訴過我,有一次他被困在聖母峰上,為了保持清醒和體溫,只好整晚不停地拍打全身,於是我就開始不斷地拍打身體,兩隻腳上下擺動,身體像汽油桶般滾過來滾過去,甚至大聲嘶吼、叫自己的名字以保持頭腦清醒。
而為了克服高山上稀薄的空氣,我也盡量讓暴風雪不要包住我的口鼻,一側過臉就用力吸氣。這是個相當累人的動作,做沒幾次就累得想趴下了,但我警覺性高,馬上又起身繼續地做……就這樣,一直撐到天空透出微弱的紅色亮光,太陽就快出來了!直到我聽見有人呼喊我的名字,才終於獲救。
這一場聖母峰有史以來最大的山難,一共有八人喪生,我是唯一受困在八千四百公尺還能獲救生還的人,但我的十根手指、腳趾都已壞死,必須全部切除;而焦黑的鼻子也必須挖掉,不過並不影響呼吸功能。原本我以為只要切一切、縫一縫就好,沒想到竟是一連串「剖骨挖肉」治療的開始;一年內,我總共動了十五次刀,東挖西補,全身上下體無完膚。之後面對的還有長期抗戰的復健工作,但我都堅忍以對,因為畢竟我活下來了!
我從來沒有過「征服」一座山的想法,排除萬難登頂,是為了要征服自己的懦弱與狹隘,現在矗立我眼前的人生大山已經夠險、夠艱難,足夠我用一輩子的時間去挑戰。
(本文由張尊禎撰稿)
我承認,我對山很著迷,朋友甚至戲稱我為「山癡」。
一位老朋友曾在報上如此說我:
人間自是有情癡。認識高銘和十八年,深深了解他對山的愛戀,怎一個癡字了得。這樣一個山癡,寧願輸掉了事業,賠上婚姻,只為了親近那一座座沈默不語的山峰。
他的人也像那些山峰一樣,沈默寡言,只有在提及山時,他變成口若懸河,完全判若兩人。大山小山都是最愛,我常調侃他,對於山的海拔高度可能比家人的生日還記得清楚。老闆不准他請長假爬山,他憤而辭掉熱愛的工程工作;老婆不諒解他愛山比愛她更多,他氣得找我這個老朋友傾訴,其實我知道他心底也是很苦澀,山的愛戀怎能和夫妻感情混為一談?可是在山面前,他真的忘了老婆很辛苦的在家帶孩子,看多了山的四季容顏,他忘掉兩個孩子的長相,天知道他並不是故意的。
對於這樣一位山癡,我能說什麼呢!
──劉雲英《民生報》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一日
什麼時候開始迷上山的,我說不出個確切日期,因為我對山的愛,既不是「一見傾心」,也不是「一見鍾情」,而是漸進式的,一星期、兩星期、一年、兩年,越陷越深,終至無法自拔。
最初接觸山,是剛進入社會的時候,那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每天朝九晚五,埋頭苦幹,除了打球以外,平常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休閒活動。
或許是命中注定吧!公司裡剛好有幾位同事,假日喜歡到台北近郊爬爬山,有一次邀我同往,我想反正也沒什麼事,便答應了。
去過一趟以後,感覺不錯,因為既可以運動,又可以欣賞風景,而且還有一群人可以談談說說的。所以,之後他們每次邀約,我都欣然前往。
每回爬山,又會多認識一些其他山友,結果邀我爬山的人越來越多。
剛開始時,爬的都是台北近郊、一天可以來回的山,像七星山、大屯山。久而久之,我開始爬那些位於外縣市的山,星期六去,星期天回來。
後來我又熱中於攀岩。在國內,一般所謂的爬山其實只能算是健行,靠的主要是腳力,真正要用到手來爬的時候不多。但攀岩卻非常講究臂力和指力,另外,還可以訓練柔軟度、平衡感和膽大心細。你大概不知道攀岩的人指力最厲害可以鍛鍊到什麼程度,我在國外就曾看過這樣的表演:用根小指就可以吊單槓!
我攀岩的地點是北投的大砲岩。當時這裡有位賴長壽先生專門教人攀岩,我跟他學,一學就會,覺得非常好玩、刺激,又很有挑戰性,十分符合我的個性。有好長一段時間,我每個星期天都會坐火車到北投攀大砲岩。
迷上爬山後,我幾乎沒有哪個農曆年是在家裡過的。每每吃完年夜飯,便背起背包,和幾個朋友出門爬山去。家人見狀,每次都只能搖搖頭。因為像過年這麼長的假期,平常少有,所以我不願意錯過。台灣一些真正的高山,像雪山、玉山,我都是利用農曆年假一一爬完的。
打從第一次爬山開始,十年之內,台灣大大小小的山都留下了我的足跡。
爬山就是這麼一回事,越爬胃口越大。當我爬完國內大部分的高山之後,便開始把目標轉向國外,我對國外登山的情況不陌生,因為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都在蒐集這方面的資訊。
為了出國登山,我還特地補習英文並取了英文名字──Makalu(馬卡魯)。這是世界第五高峰的名字,因為音節響亮又容易記,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如果香港、韓國和日本不算在內的話,我第一次出國登山是在一九八四年,登的是位於法國境內、阿爾卑斯山系的白朗峰(Blanc),標高四八○七公尺。白朗峰在國際級的名山中算是座小山,不過已足以讓我體驗到國外登山的滋味。當時,因為高山症的關係,我還在山上的旅館裡吐得七葷八素;下山休息幾天後,又捲土重來,並從另一條路線登上白朗峰。過程雖然艱辛,但我隱隱覺得,山終將可以讓我實現或發現一些什麼東西,雖然當時我並不知道,那將被實現或發現的,就是「自我」。
之後,我分別在一九八五年到美國優勝美地攀岩,到瑞士登馬特洪恩峰(Matterhorn),一九八八年到阿根廷登阿空加瓜山(Aconcagua,六九五九公尺),一九八九年到日本登劍岳(Tsurugi),然後到印度登怒峰(Nun,七一三五公尺),並於一九九○年登喀喇崑崙山脈的莎瑟峰(Saser Kangri,七六七二公尺)。
一九九一年秋天,我登完世界第六高的卓奧友峰(Cho Oyu,八二○一公尺),下山回到拉薩後,西藏登山協會的朋友邀我明年再回來登座高山。
他們最初建議我登的是世界第五高的馬卡魯峰(Makalu,八四六三公尺),我當時還真有點心動,因為一來,中國才開放馬卡魯峰供人攀登不久,還沒有人從西藏方面登過頂;二來,我的英文名字正好是馬卡魯,要是登頂成功,就非常有意思。
不過,沒人爬過就代表沒有這方面的攀登資訊可供參考,自己要當開路先鋒,難度極大。而且,登山活動需要資金支援,馬卡魯峰雖然名列世界第五高峰,但台灣知道此山的人卻少之又少,要找贊助很不容易。思前想後,我終於打消登馬卡魯峰的念頭。
我的朋友又建議不妨考慮聖母峰(Everest)。聖母峰的攀登資訊十分豐富,知名度更是不在話下,世界上千嶺萬岳,有哪一座比聖母峰更為有名?
聖母峰!我眼睛頓時為之一亮!
我從前不是沒有想過,有朝一日要登聖母峰。更恰當的說法是,自從迷上登山後,我從來就沒有懷疑過自己有一天會投入聖母峰的懷抱中。如果把登玉山比作參加區運會,那登聖母峰就好比是參加奧運會,又有哪個朝夕鍛鍊的運動員,不是以參加奧運為終極目標呢?
記得一九八九年,我在朋友家裡看過一部有關登聖母峰的紀錄片,片中記錄了一九八八年中國、日本和尼泊爾三國組隊登聖母峰的全部經過。參與的三個國家共派出一、兩百人,分成兩隊,一隊從尼泊爾方向登頂,一隊由西藏方向登頂,最後在聖母峰頂會合,堪稱是一次史無前例的登山壯舉。
看到聖母峰宏偉壯闊的冰天雪地,看到登山隊浩浩蕩蕩的行列,看到攀登過程的險象環生,我整個人都傻住了!整部片子全長十個小時左右,我從晚上八、九點眼睛眨也不眨地看到隔天清晨五、六點,身體都快累垮了,但體內卻是熱血沸騰,久久不能平復。我心裡只有一句話在盤旋:大丈夫當如是也!
人生常是這樣:有很多事你一直想做卻沒有進行,經旁人輕輕一推卻變成事實。當西藏登山協會的朋友建議我登聖母峰之後,我仔細地考慮了一陣子,想到聖母峰早晚都是要爬的,便毅然決定在隔年一償心中夙願。就這樣,我在一九九一年帶著既興奮又惶恐的心情離開拉薩,因為我知道,下次再來時,將是我挑戰世界最高峰──也是我人生最高峰──的時候。
取道尼泊爾回台灣時,在加德滿都短暫停留期間,我偶然想到,既然已決定明年從西藏爬聖母峰,何不也向尼泊爾申請看看?尼泊爾是個內陸小國,由於政治因素,二十幾年來從來沒有批准過台灣登聖母峰的申請。我向尼泊爾政府提出申請,純係姑且一試,根本不抱任何指望。不過,要是能在尼泊爾登聖母峰,募款一定會容易得多,因為尼泊爾是國際登山舞台,是全世界注目的焦點。
回到台灣後,我就開始準備各種登山及募款事宜。起初,包括我在內,原有六個人打算參加一九九二年的聖母峰活動,由於募款不順利,有三個人被迫退出,非常可惜。
在登聖母峰前,我們到北美洲的最高峰麥肯尼(McKinley)進行了一次易地訓練。麥肯尼峰雖是北美第一高峰,但標高只有六一九四公尺,和八八四八公尺的聖母峰相比,當然是小巫見大巫。其實,不要說是北美洲,就是在其他洲,能跟喜馬拉雅山系山峰相比的高峰也屈指可數。全世界十四座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峰中,單喜馬拉雅山就囊括了九座,所以,西藏和尼泊爾一帶的喜馬拉雅山系,堪稱為登山界的聖地,而聖母峰當然更是聖地中的聖地。
一九九二年八月,我和張清水、陳秋霞兩位山友踏上聖母峰的征途。但很不幸的,我們沒有登頂成功,陳秋霞走到半路,就因為急性肺炎被背下山,而我強登至八○五○公尺後,也不敵冰冷的大風雪而被迫折返。唯一的安慰是,我突破了八千公尺的瓶頸,吸收了很多高海拔冰雪地攀登經驗,同時也成為台灣登山界登到八千公尺的第一人。
雖然勝敗乃兵家常事,而我也不是每次登山都登頂成功,但此次聖母峰的挫敗,還是令我意志消沈。有賴西藏登山隊女隊員桂桑的一席話,才讓我的鬥志重新燃燒起來。她告訴我,早在一九七五年,她就登過聖母峰,可惜在八六○○公尺不慎被開水燙傷了腳,不得不放棄登頂。結果,十五年後的一九九○年,她參加中美蘇三國登山隊,終於如願以償,成為中國第二位登上聖母峰的女性。更令人佩服的是,她在一九九九年又登了一回,成為兩次站上聖母峰頂的藏族女性。面對已有兩個小孩的她,聽著她的故事,看著她堅毅的表情,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我告訴自己:聖母峰,我一定會再回來!
一九九三年,我辭去工程公司的工作。因為,隨著登山的次數越來越多,所花的時間也越來越長,我請的假已接近一個理智的老闆可以容忍的限度,偏偏這時候,我又和錦繡文化企業簽訂合約,要製作一套名為《中國百岳》的攝影集,必須常到中國去實地考察及拍照,此後請的假只會多,不會少。經過再三考慮,我覺得人可以追求自己志趣的黃金歲月實在很有限,便毅然遞上辭呈。
說起《中國百岳》的構想,實在來得偶然。在西藏爬卓奧友峰的時候,我和中國的聯絡官薛雲聊天,他偶然提到台灣出版的《台灣百岳》這本書做得不錯,我就答腔說:「你們中國比我們台灣大得多,山既多且高,其實可以做一本《中國百岳》。」他卻回說:「在中國,要是沒有上面的指示,不可能有人力物力去做這種事。」最後還補了一句:「你們來做怎麼樣?」
雖然這只是脫口而出的一句話,卻像是一粒種子,在我心裡生根萌芽,而且越長越大。
其實,爬了十幾年山,我漸漸有個體會,爬山並不一定只有用兩隻腳走上去、走下來這樣的事可做,不同的山有不同的風土、人情,如果能夠在爬山的同時做這方面的記錄,將可把爬山的活動擴展到另一個更高的層次。況且我也覺得,中國的山,假如透過中國人的思想和眼光來呈現,肯定比外國人更有感情。
回到台灣以後,我整天想的都是《中國百岳》這件事,空閒時便拿出中國的地圖來,圈選我認為可作為中國百岳的一百座山。
另一方面,我開始接洽一些出版商。我找過《台灣百岳》的原出版社,甚至找過日本方面的出版社,但他們在經過評估以後,都以投資太大,市場也不是那麼看好為理由而作罷。最後,經人輾轉介紹,我拜會了錦繡文化企業的負責人許鍾榮先生,他在和我詳談後即表示支持我的計畫,還說了一句令我畢生難忘的話:「世界上許多大事都是瘋子做出來的!」許先生還答應預支我若干前往中國進行實地考察的經費,這在他們公司算是破天荒頭一遭。有了這個奧援,我更專心投入《中國百岳》的工作。
在我圈選的百岳中,有三分之一位於西藏,所以自此以後,我便常常取道尼泊爾,出入西藏。
埋首《中國百岳》工作的同時,我並未忘記聖母峰。基本上,我計畫從西藏方向再登一次聖母峰,不過,我也不放棄爭取從尼泊爾登峰的機會。雖然知道尼泊爾政府會批准的機會微乎其微,但我這人就是這樣,不到黃河心不死。
每次經尼泊爾進出西藏,我都會跑一趟觀光部登山處,看申請有沒有什麼進展,不過卻從來沒有什麼好消息。
有次我乾脆從台灣寫信給觀光部,問他們為什麼不批准我的申請。信中我說:我是個愛山的人,想爬聖母峰是很自然的事,而且我已經爬過那麼多大山,你們為什麼不讓我爬聖母峰?
出乎意料的,尼泊爾政府竟然回我一封信,要我把登過哪些山的詳細資料寄一份給他們。我見事情有了眉目,趕緊把資料用DHL快遞寄過去。沒多久,尼泊爾政府又來了一封信,問我當初在西藏登聖母峰的時候,有沒有帶中華民國國旗。我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便回信說我是個爬山的人,只對爬山有興趣,從不談政治,請他們不要把爬山和政治混為一談!
接著,尼泊爾政府又來信要我繳交一份證明,確認我當初在西藏登聖母峰的時候真的沒帶國旗。我火速打了電話給北京中國登山協會的朋友,請他們開一張證明給我,然後寄給尼泊爾政府。本來我以為很快就會有回音,不料過了一個月,還是音訊全無,我開始懷疑,事情是不是又有了什麼新的變化?
終於,我望眼欲穿的回音還是來了。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真是我人生難忘的一天,因為我收到了一張來自尼泊爾政府的傳真──竟然是攀登許可函,他們終於批准我在一九九六年春季組隊攀登聖母峰!
這個突如其來的訊息使我欣喜若狂。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有一種非把這件事告訴全世界不可的衝動。我拿起電話,打給每一位登山界的老朋友。他們得知此事後,都興高采烈,連說恭喜。其中一個朋友還說:能夠突破台灣登山界二、三十年來的瓶頸,拿到尼泊爾政府的攀登許可,這事真是比登聖母峰本身還難。
【序】勇敢攀登自己人生的高峰一九九六聖母峰世紀大山難已經過了十多年了,但對親身經歷這場震驚世界的災難而幸運地倖存下來的我,卻仍存在著無限的感傷和感觸。對喜愛登山的人來說,都會記住當年發生的這樣一件大事;但也都會記取經驗,在後續的攀登活動中,設法避免再度發生類似的山難事件。近幾年來,我一直有機會與各行各業的人士,分享自己在聖母峰上求生存的經過,也告訴很多人,在受傷住院期間是如何克服心理障礙,以及出院後,又是如何鼓起勇氣重返喜馬拉雅山,最後的結論就是:人是那麼的渺小,所以要懂得謙卑,特別是面對大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