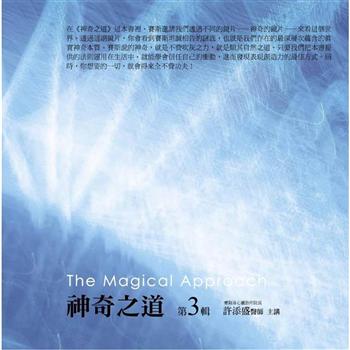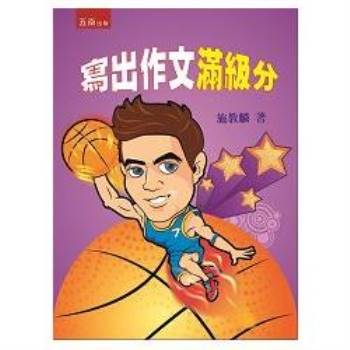在現代和傳統兩造之間欲走還留的鄉村圖景
《福壽春》是一部世情小說,且是一部近期少見的用章回體創作的長篇小說,李師江從世道人心的角度書寫現代鄉村生活。書中,李師江刻畫了一個李福仁家庭兩代人──父母與四個兒子的倫常關係與命運,透過這一家兩代人描述了中國東南海邊鄉村近十幾年來的風土人情,可說是一幅充滿命運感、生命力的風俗畫。李師江並不著急表達這種生活的意義所在,而是用如同工筆畫一般的細膩筆觸,著力對生活本身進行日常化的精細描摹,由此我們看到一個在現代和傳統兩造之間欲走還留的鄉村圖景──又耕田又種花又做海的農民生活,迷信色彩與傳統觀念交織的鄉村精神世界,老一代農民與下一輩觀念斷裂中的痛楚和傷感,一個從農耕社會城市化正在消失的農村。
我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終究是需要故鄉的。即便你無暇回家,只在腦海中回想。
有一種論調,說的是,如果你開始懷舊,就證明你老了。其實我從小學高年級到城裡念書開始,就開始懷舊了。我懷念在河中撈魚的日子,懷念在山上摘草莓的時光,懷念在祠堂改成的小學裡被同學孤立的孤獨,懷念母親抱著我躲避颱風的惶恐,懷念鄉村給我的每一點童趣、恐懼以及喜悅──至今這些元素滲入血液,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氤氳二字:故鄉。──李師江
熟悉李師江這類作品的讀者,肯定會對寫出《福壽春》的李師江感到陌生。在這裡,攔海造田、山上栽茉莉、海邊養蟶子的增坂村取代了北京城;傳統親族倫常與思想觀念取代了現代都會的男女關係;平靜樸實、娓娓道來,帶著農村百姓尋常口語的敘述語調取代了調侃嘲諷中帶著青春憤怒的伶牙俐齒。這部作品以李師江的故鄉福建寧德增坂村為背景,透過李福仁及其兒女家人、鄰里親族的日常生活,寫出李福仁勤懇踏實、子孫滿堂卻老來孤單的一生,寫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村故鄉地景與人心的變化,也寫出李師江對鄉村生活的追憶與眷戀。──蘇敏逸.成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作者簡介:
李師江
1974年生於福建寧德,1997年畢業於北師大中文系。現居寧德,專業寫作。在台灣出版有小說《她們都挺棒的》等四種,是大陸標誌性作家之一。大陸出版有長篇小說《逍遙遊》,並以該書獲得「2005年度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另著有長篇小說《中文系》、《哥仨》、《福州傳奇》,隨筆集《畜生級男人》,歷史傳記《曹操:我這一輩子》。部分作品譯介至英、法、日等國。
章節試閱
人生在世,命有定數。不信命有自個的活法,信命的也有命理可循。西人循星座,中國人信生庚八字,輔以相生相剋之理,禍福時運,都有預料之跡。故爾有風水相師,精通命理徵兆,預言禍福,窺探天機,又以此為職,替人指點迷津,尋求趨利避害之法。又據說那算命先生,因以洩露天機為業,常常命運不濟,遭天譴而折壽,也是人生一大悖論。又有初識些不三不四的理論者,信口雌黃,見人有錢言其好,見人無錢,又以言語相欺嚇唬騙財者,也能魚目混珠,混得好飯吃,因其只騙人不欺天,倒不損害自己壽辰。因而造就這世界魚目混珠,真假莫辨,只能是信命者自己體會,不信者也無礙,宛如那塵埃一般,隨風去也。
卻說算命陳先生,肥胖白淨,有福相。那一身行頭,也頗清楚,上身是一白色短袖襯衫,乾淨齊整可見折痕,下面一條暗色肥大背帶西褲,折痕也歷歷在目。戴一副黑色墨鏡,儼然知識幹部形象。左手拄一根黑色透亮拐杖,右手提一個精緻竹籠,籠中是那嘰喳蹦跳甚是伶俐的算命鳥。他每隔一兩年都會來村中一次,盤桓個十日八日,給村中有興趣的老少算完了才走。他是個瞎子,以拐杖探路,這一日篤篤篤進了一家宅院,那拐杖卻先探到地上一軟物事,接著哼哼兩聲,陳先生嘆問道:「好大一頭肥豬,卻是誰家的?」
正是晌午時分,那厝裡幾戶人在前廳乘涼,閒聊著吹穿堂風呢,一人回應道:「陳先生,是福仁家的養的一口好豬呀!」
陳先生用杖子在豬身上探了探,那豬也不甚理會,自顧沉睡。陳先生吟道:「是好豬,卻不是主人的!」那李福仁也在乘涼呢,憨笑道:「先生開玩笑吧,這口豬好養得很,又不往外跑,數我數年來最好養的一口豬,怎會不是我的呢!」
原來這口豬頗有口碑,打自買回來養起,噌噌噌長肉,自比把普通的豬長得快,習性又好,鄰里嘖嘖稱讚。說來自有奇妙之處,這豬天性不同凡響,吃完了不愛待豬圈睡,愛跑出來在廳堂一臥,跟人待一塊兒,一動不動,似乎聽人聊天,既而鼾聲漸起,如一朵巨大的蘑菇在地上生長。大夥都誇這豬脾性好,年底長到四五百斤,李福仁可以起新厝了。
當下陳先生不再言豬,眾人給他在廳堂讓座,吃茶。他也放下籠子,取出紙牌,放出算命鳥,準備預卜的營生。也有人在眾鄰里之間招呼:「陳先生來算命了。」便有一干婦女小孩也圍來湊熱鬧。陳先生將他人生辰八字與那算命鳥說了,算命鳥便跳出來,在斜攤開的紙牌上抽出一隻,遞與陳先生。陳先生便拈了一顆黃穀餵了,然後細看此牌,娓娓道出那命運玄機,眾人屏息側耳傾聽,此情此景暫不細表。且道這豬,到了年底,長了好大肥實的個兒,不下五百來斤,李福仁叫了屠夫李細嫩,凌晨時分殺了,分了幾擔已到街上擺上架。眾人起來時只見地上有幾灘豬血的痕跡,都奇了,道:「這麼大一口豬殺了也不見豬叫聲,好不清淨利落!」
街道肉攤上,屠夫李細嫩管切肉,李福仁脖子上掛了個褪色的電工包,管收錢。晌午時分兩人都顧不上吃飯,在鄰鋪子裡拿幾個包子往嘴裡一塞。李福仁收錢收到手忙腳亂,一雙常年在地頭忙活的手,算起經濟帳來煞是費勁。日頭西落,看那豬肉所剩無幾,破舊的電工包裡鼓鼓囊囊,李福仁也估摸不清到底有多少錢,只是覺得充實到了心頭,似乎把一口肥豬正鑽在這包裡待著。正尋思今天回去算帳可能要算到半夜,卻見大兒子安春急匆匆趕來,叫道:「爹,二姐肚子疼在地上直打滾,娘叫你快回!」
李福仁脖子上掛著一袋錢急匆匆趕回家,二女兒美葉已經疼得無力。阿吉醫生已到現場,端詳過後道:「可能是急性闌尾炎,須到縣裡動手術。」當下叫了鄰里裡後生四個,抬了竹子擔架來,把美葉放上去,李福仁跟著,就往縣裡趕。其時增坂村還未通馬路,需抬到鄰村廉坑,才能搭上車。
這一住院住了半個月多,李福仁不甚曉得女兒病情,只記得自己成天跑上跑下從電工包裡取錢,而那個電工包,就連睡覺也掛在他脖子上,一天一天地癟了下去。到了出院那天,居然掏空了,李福仁在回家的路上,心頭有所悟,居然覺得這個包頗為棘手,順手扔了。
過了一二年光景,算命陳先生又篤篤篤而來,青山依舊,還是那副白胖樣子。有人記起前事,稱讚道:「陳先生好靈驗,說那豬不是他的便不是他的。」於是慫恿李福仁也來算一次,李福仁木訥,不好求神占卜之事,只是搖頭憨笑。陳先生摸了摸李福仁的額頭五官,喃喃道:「子孫滿堂,老來孤單,你的命是撿回來的,硬得很。」李福仁一介粗人,並不明白其意,旁聽者也並不在意。各人只管得眼前得失,哪會愁煞一生一世。
1
日月穿梭,光陰荏苒,轉眼李福仁已經六十開外,體力不似當年能扛一二百斤擔子,卻仍上山種地,下海種蟶,十分繁忙,家中大小事全由妻子常氏主持。這一日正晚飯時分,家裡來了個不速之婦,身材乾瘦,顴骨突出,臉形如橄欖,眼睛卻有精光。這婦人渾身上下與常人無異,只有一個不凡之處,乃是嘴巴,伶俐刁鑽,誇一個人能比花好比月圓,罵一個人能變狼心成狗肺,端得是難惹。她老公腿腳細長,渾號鷺鷥,因而人叫她鷺鷥嫂。夫妻倆無兒無女,家中生計靠鷺鷥在土裡刨活自給;那鷺鷥嫂仗著能說會道,消息靈通,近年做些說媒牽線的事,因能得個二三十塊媒錢,又能騙到一個豬腿來吃,居然做上手了,打探到誰家未婚男兒未嫁女兒的信息,便能循著氣味上門來了。
常氏不敢怠慢,客氣道:「你到誰家誰家有喜,有閒等到來我家了,必有好事。快坐快坐,要是沒吃飯我就舔雙筷子,不要客套。」當下放下碗,給鷺鷥嫂泡茶。鷺鷥嫂阻止道:「別忙別忙,你吃你的,又不是遠門客。我剛吃了晚飯,老頭子在飯裡多加了紅薯,一出門就放屁,在你家門口放完了才敢進來呢──怕被人說不厚道,嘴上能說屁股還不閒著,見笑見笑。聽人講二春回來呢,這還不信呢,過來看看,還真是回來了,漬漬漬,大變樣了,看來外面水土更養人。」
二春也跟他爹李福仁一樣,寡言少語,埋頭吃飯,聽鷺鷥嫂提到自己了,才點一下頭附和一下,並不搭訕。常氏替他回道:「是呀,昨天剛回呢,是比前些年長得壯實了!」
鷺鷥嫂問道:「去了好幾年了吧!」
常氏道:「前後去了四年了,讓他回還不肯回來,這一對冤家,盼得我心兒都裂兩瓣了。」
鷺鷥嫂道:「父子算什麼冤家!這一回來,不就結了,一家子團團圓圓的多好!」
原來這家中有一樁逸事,卻是村人鄰里都知曉的。四年前,二春也就二十出頭,在家閒著,成日跟一夥浪蕩子弟玩耍,晚上也不回家過夜,把家當了飯館,吃了就走。李福仁是極勤勞的人,最看不慣兒子德行,卻也不知管教,只想把他趕出門去。那常氏是極疼兒子的,做了好人來呵護,讓二春也能混日子。逢著一次,大女兒坐月子,常氏一去伺候了個把月,那李福仁自己在家做飯,偏偏不做二春的份,待其他人吃完,便鎖了家門,不讓二春有吃的門路。那二春在家待不下去,打聽得一個浪蕩朋友的叔叔在廣東磚廠做工,有門路可以介紹過去,便尋思離家去了。沒有盤纏,便假借李福仁的名義,到村中收購蟶苗的販子支了幾十元,因那李福仁三天兩頭都有蟶苗送來,販子也不介意。二春取了錢,到三嬸家借了一個蛇皮袋子,裹了幾件行李便去了廣東。常氏回來,見兒子不知去向,打聽了幾日,才曉得去了廣東,待託人寫了信去,和二春聯繫上,曉得在磚廠勤勞做工,又有同鄉關照,方得放心。這二春心氣高,這一負氣出走,連續幾年都不想回來。後常氏在信中婉言勸了,才在四年之後回了家。
當下鷺鷥嫂開門見山,道:「二春也有二十五了吧,該尋思著討媳婦了。」常氏道:「是呀,正要尋思這事呢,你見識的姑娘多,給我們二春留心著。」鷺鷥嫂笑道:「不留心我能上你家來?就不知二春中意什麼樣的姑娘,二春呀,你說說。凡你能說出個大概模樣、怎樣脾性、如何出身,有個一二三的說道,我包準能將那意中人從人堆裡摘出來。這我可不是說唬話,你娘也知道我說撮合過我不少滿意姻緣的。」二春受了追問,才支吾了一聲道:「不曉得。」常氏插嘴道:「鷺鷥嫂呀,我二春這些年只曉得工作,哪去想這事,你見識廣,搭配不搭配,你可先做主意。」鷺鷥嫂笑道:「我是肯替你搭配哩,可討媳婦這事是千人眼萬人面,最終要自己看準的才覺得好。前些年我給村尾李細玉介紹一個八都的姑娘,別提多好,腰身粗屁股大,不用懷上就知將來能生男娃,要是聽我的,今年早就抱上孩子了。偏是不滿意,後尋了一門蘆杆瘦的媳婦,風一吹能倒,結婚一兩年了,如今不但沒個動靜,且那媳婦兒整日泡在藥罐子裡,他爹媽腸子悔青,斷子絕孫的心都有了!」
鷺鷥嫂站在三春身邊,講得高興,又指手畫腳,身子都快挨到桌子上去,把三春弄惱了,道:「你這唾沫星子老往我碗裡蹦,不讓我吃飯了,走遠點!」常氏忙解圍道:「這孩子,說話沒個分寸。」講得鷺鷥嫂一陣尷尬,退後一步笑道:「是不是給你哥說媳婦把你惹著了,別著急,你哥討了媳婦就輪到你了。」三春道:「笑話,我要媳婦還輪到你找,我豈不是白到縣裡念書了。我決不可能要你手頭那些農村姑娘的。」鷺鷥嫂裝嚴肅道:「好,有本事的話找一個在你哥前頭的,鷺鷥嫂就等著看你能耐,不要到頭來又讓你媽來求我了。」三春道:「又不是有金元寶撿,搶在我哥前頭幹嗎?等我要媳婦的時候,姑娘自己會找上門來!」鷺鷥嫂不服氣道:「果然是讀過些書的,說話的口氣都不一樣,只怕將來做的沒說得那麼容易,我且擦亮眼睛瞧著!」
插科打諢一陣,飯散了,剩常氏和鷺鷥嫂在廚房,兩個婦人竊竊祕語了一陣,鷺鷥嫂道:「我是不打無準備的仗,這生庚帖子都帶了,您瞧瞧。」取出一張紅紙帖子來,上寫:「萬氏,女命,年十九歲,五月初六日子時生。」原來是橫嶼島上一個姑娘,鷺鷥嫂早有心說與二春。常氏喜道:「都說你鷺鷥嫂做事麻利,我二春才回來兩天就有這好事,明日就找阿肥先生合帖去。」那阿肥先生乃是本村的陰陽先生,未娶獨居,時常有侄兒家接濟些糧食,三餐節儉,卻吃得肥胖,通曉易經風水,幫人做些紅白喜事掐日子的活計。次日兩婦人拿了帖子來,阿肥先生淨了手,把男女雙方生庚帖子並排在桌上,閉目掐指算了片刻,輕聲開口道:「有合。」兩婦人都面有喜色,同聲問道:「大合還是小合?」阿肥先生神閒氣定道:「不大不小,中合。大合乃是天合,為天定良辰,萬裡挑一,普通人家只要中合已經滿意。」常氏滿是歡心,道:「既然如此,八字有一撇了,鷺鷥嫂,事不宜遲,且把二春的生庚給送去。」鷺鷥嫂見有成數,也頗興奮,道:「正是,都說好事多磨,咱們得手腳麻利些,休讓什麼給磨住。」叫先生寫了一張二春的生庚帖子,讓鷺鷥嫂捎與對方合貼用。又給了阿肥先生兩元合帖花彩,回去一心等鷺鷥嫂消息。
幾日後,鷺鷥嫂就回了信息,進了常氏的厝裡便叫道:「這兩塊錢真沒白給,阿肥先生的合帖拿十裡八村都有靈驗。對方合帖了,也是有合,就等二春去看女方哩。」嚷嚷呶呶的,似要全厝的人都知道她撮合的媒有成數。常氏道:「好勒,給他辦身行頭,選個好日子你就帶他過去。」鷺鷥嫂煞有介事道:「是呀,我也得算計著騰出日子來呢,這捎帶消息來回跑路的,也要不少開銷呢!」常氏婉言笑道:「你的辛苦,我這心裡一併記著,等事成了一併付你媒錢,哪能忘了你的好處呢!」鷺鷥嫂道:「我倒不是計較這些,只是我那老頭一身老病,三天兩頭湯湯藥藥的,手頭緊得似擰了鏍絲,哪有閒錢跑閒差使。似你這趟差使,我能省就省,不坐車不搭船,直接走路去。」
常氏笑道:「鷺鷥嫂你又說大話嘲諷我,那橫嶼隔著海一二里的,你能走過去不成。」鷺鷥嫂神氣道:「不成就游過去唄,捨得這身皮,才能攢下兩藥錢。跑我這行當,貼錢做義務也有落自己頭上的:去年給李歪鼻家老大說個媒,費我來來回回跑路費,結果到頭一個子兒沒得。」常氏道:「你那媒錢是大錢,人家自然就忘了小頭了,也是常事。」鷺鷥嫂怨道:「哎喲,說起大頭來我就來氣,全是義務,李老八兒子那門婚,我穿針引線忙破了頭,臨成了,居然說是自由戀愛,不認我這個媒人了,哎喲,那個冤呀,在我肚裡堵個十天八天都出不盡。他一個土鼈兒子,拿起鋼筆都會倒個兒,跟縣裡文化人差個十萬八千,懂得什麼自由戀愛?不過為撇下我的功勞趕了個假時髦。明眼人都能看出來,兩家相距十幾里地,非親非故,沒有我撮合能湊一塊兒?還硬說是同學,沒讀過書哪有同學呀?這樣不誠實的人家,結了婚也沒有意義,過幾年準得見報應……」
常氏忙止住了她的話頭,道:「他嫂子,這人心好歹都看得見,用不著去煩惱它,你做了,終歸是好事,人家雖短著你的,心裡也能記得你的好哩。」鷺鷥嫂作勢掌自己嘴巴,吐著唾沫道:「呸呸,我這刀子嘴豆腐心,話吐出來就沒了。做媒人的,打心裡也不願意咒別人的不好,平時別人氣著我我也不說的,這不是見了你說話投機,掏心窩子了都!」常氏給鷺鷥嫂泡了糖茶,又問了對方姑娘一些究竟,鷺鷥嫂又吐了姑娘一些信息:原來姑娘家有四姐妹,排第二。家裡女兒多,到了出嫁的年齡,跟流水似的,得緊著往外趕,對男方家境不甚計較,只尋求一個老實肯幹的後生嫁了出去。兩婦人就著姑娘的話題閒聊下去,暫且不提。
常氏是重門面的,讓二春到縣裡配了一套行頭。買了時下縣裡流行的一身藍色西裝西褲;店主姑娘又建議他配一條白襯衫加一條紅色領帶,煞是鮮豔,去了好幾十塊。臨行,常氏又囑咐要買雙新皮鞋,才能配套。原來二春有雙皮鞋,塗了油也能顯新,常氏要兒子體面,不放心,怕配不得新衣服,又花了十來塊。那二春皮膚白,晒不黑,又身材高挑,眉目清秀,回得家來,這一身行頭加在身上,儼然不像個農家子弟。常氏前後上下打量,只似端詳著剛出生的嬰兒一般,口裡讚如今衣裳做得真是好看!鷺鷥嫂也贊道:「我帶過看親的後生,數你最有派頭,連我都長氣哩。」只是到了臨走前,居然沒有人會打領帶,慌裡慌張,好歹從村裡叫了個去過縣裡工作的來打上。鷺鷥嫂道:「快走快走,誤了好些時間了,遲了人家以為你面子重。他嫂子,這車船費是不是交我手上來。」常氏道:「不急,二春口袋裡有錢,他見過世面,哪裡花錢他懂得主持。」鷺鷥嫂道:「瞧您這好手段,錢抓您手裡跟上了鎖似的,一準想讓二春的婚結得氣派。」
當下從村口坐上三輪摩托斗車,搖搖顛顛而去。前七八年在西陂塘造堤攔海,村口前面的海地灘塗成了田地,又在田地之間修了一條磕磕絆絆的馬路,直通到國道上去,增坂村才有得通車。那車開到渡口,又搭船開了一二里,才到橫嶼,一路無話。到了姑娘家,鷺鷥嫂輕車熟路,躡手躡腳帶了進去,是一座古舊青磚大厝,住了六七八戶人家。姑娘家長接了進去,都知來意,也不說話,只點頭意會,二春頭一回見識,只覺得跟做什麼祕密事。兩人被接引著,在前廳長凳上坐了片刻,未見姑娘身影。女主人客氣,泡了茶。二春正一路口渴,剛要吃茶,卻被鷺鷥嫂輕摁住手腕,悄聲道:「姻緣未定,不能吃茶,任何東西也別放嘴裡,這是規矩來著。」
二春坐立不安,只瞧著天井花盤上種的一棵石榴樹,有一隻伶俐小雀跳來跳去。鷺鷥嫂習以為常,如姜太公釣魚,穩穩等著,一切程序盡在心中。再過片刻,才見一個姑娘從外頭進來,穿過前廳,進了一間廂房去了。鷺鷥嫂轉看二春,似乎在打盹,忙輕聲指著道:「就是這姑娘,回頭出來仔細瞧了!」二春睜大眼睛,不一刻姑娘便從廂房出來,穿過前廳之間,也用餘光瞥了二春一眼。但見這姑娘,不胖不瘦,不高不矮,容貌不漂亮也不難看,一個尋常不過的女兒家。鷺鷥嫂問道:「看清楚否?」二春點了點頭,當下兩人告辭而回。鷺鷥嫂問道:「中意麼?」二春只是愣著,不說話。鷺鷥嫂道:「你也是男子漢人家了,這點面皮都沒有,回頭跟你娘說去,早日把意見傳達了來。」
回得家來,常氏早想問個究竟了,怎奈二春金口難開。問得急了,只說個「不知道。」常氏道:「我兒,你是不是在外邊做工做傻了,怎麼連媳婦都不懂得挑,你是不是嫌對方哪點不好了?」軟磨硬泡之下,二春才開金口吐了兩個字:「太黑。」
恰那鷺鷥嫂又來尋回話,常氏便抱歉道:「恐怕不成哩,二春說那姑娘太黑,我也不知道怎生個黑法,是不是炭那麼黑呀!」鷺鷥嫂慨然道:「他嫂子,我又不缺心眼,怎會介紹個黑炭給侄兒。那黑也就是不太白淨而已,島上的姑娘整日風吹得,都沒那麼白淨,又不是大榕樹上的鷺,池子裡的鵝,一身白毛有啥用,多白也白不成米飯來吃。尋常人家討媳婦,看得順眼就過去,最重要是身材好股盆好,能生仔,先傳宗接代先有福,你說在理不在理?」
常氏道:「我也是這個意思。只是我二春見過世面,眼光挑剔,如今後生的事,咱們也做不了太多的主,不順他的意,將來還不知道有多少為難事。我再說說他,你給費心多張羅張羅,找個你情我願的。你手上的生庚帖子排成隊,註定不是什麼難事。」鷺鷥嫂無奈道:「這麼挑剔的主,只怕做成要扒我兩層老皮了,做好事難呀!」失望之餘,又問道:「那安春的豬欄是不是不養豬呀,要是空著便給我用罷!像我這種無兒無女無依無靠的人,還是養只豬當老本罷了!」常氏道:「那我問問,他應該是不養的,我那大兒媳婦帶著孩子就費勁,從不思量養豬的事。」當下鷺鷥嫂悻悻而回,嘀咕道:「也不知人說他從廣東背回一袋子錢是真是假,姿態這麼高,保不成是真的?」心裡一團疑問咯得慌,找人打聽去了。
人生在世,命有定數。不信命有自個的活法,信命的也有命理可循。西人循星座,中國人信生庚八字,輔以相生相剋之理,禍福時運,都有預料之跡。故爾有風水相師,精通命理徵兆,預言禍福,窺探天機,又以此為職,替人指點迷津,尋求趨利避害之法。又據說那算命先生,因以洩露天機為業,常常命運不濟,遭天譴而折壽,也是人生一大悖論。又有初識些不三不四的理論者,信口雌黃,見人有錢言其好,見人無錢,又以言語相欺嚇唬騙財者,也能魚目混珠,混得好飯吃,因其只騙人不欺天,倒不損害自己壽辰。因而造就這世界魚目混珠,真假莫辨,只能是信...
推薦序
推薦序
讓世界安靜下來
成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蘇敏逸
李師江對台灣讀者來說,也許並不算陌生。他曾先後在台灣出版了《比愛情更假》(2002)、《她們都挺棒的》(2003)、《肉》(2003)等三部小說及隨筆集《畜生級男人》(2004),這些作品大多以李師江混居北京的生活經驗為素材,在他噴薄而出,不吐不快的文字裡,激盪著桀傲不馴的青春野性與玩世不恭的叛逆之氣,隱隱然帶著王朔的調調,而他在2010年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系》,也讓我聯想到上個世紀九○年代王朔的經典作品〈動物凶猛〉。
熟悉李師江這類作品的讀者,肯定會對寫出《福壽春》的李師江感到陌生。在這裡,攔海造田、山上栽茉莉、海邊養蟶子的增坂村取代了北京城;傳統親族倫常與思想觀念取代了現代都會的男女關係;平靜樸實、娓娓道來,帶著農村百姓尋常口語的敘述語調取代了調侃嘲諷中帶著青春憤怒的伶牙俐齒。這部作品以李師江的故鄉福建寧德增坂村為背景,透過李福仁及其兒女家人、鄰里親族的日常生活,寫出李福仁勤懇踏實、子孫滿堂卻老來孤單的一生,寫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村故鄉地景與人心的變化,也寫出李師江對鄉村生活的追憶與眷戀。
一部好的小說是內容與形式相得益彰的高度整合,恰當的形式可以使作品的內容與精神獲得更精準的傳達。《福壽春》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濃厚的中國古典小說氣息,李師江正是以平實的傳統說書的敘述模式,將農村素樸的常民生活與思維方式捕捉、凝練起來。小說題目「福」、「壽」、「春」本身便飽含著中國農民傳統觀念中的吉祥之意,而小說的框架是算命師對李福仁「子孫滿堂,老來孤單」的命運斷語,既符合農村鄉民求神問卜的生活習性,又隱然帶著命運難違的中國傳統智慧。小說以古典白話的平鋪直敘開展李福仁的家族故事,在人際紛爭中展現農民最單純善良的公道是非。
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問題可以說是中國經濟迅速膨脹,社會產生巨變之後,作家們最重要的書寫主題之一。將《福壽春》與李師江以北京生活為書寫背景的作品加以合觀,也可以看見李師江對這個問題的態度。相較於京城生活的躁動喧囂,李師江對故鄉風俗民情的描寫細膩有情。在小說中,李福仁的兩個兒子安春和三春僅是讀了一點書,便厭棄農村的勞動,一心想往城市發展,卻因好高騖遠,不肯踏實苦幹,最後敗盡家財而歸,安春和三春的經歷展現了現代都市社會的物欲誘惑對人心的腐蝕。相較之下,寡言守分的李福仁對土地懷抱著深厚的感情,生活簡單,熱愛勞動,厭惡好吃懶做之人,李福仁看似保守但卻勤懇踏實的生命態度才是人類得以永續發展的關鍵。同時,在全村人依然秉持著「生兒子最重要」的傳統觀念,安春與細春也為了生個兒子,躲避計生組對於超生的追查而遠走他鄉,李福仁卻看得開:「如今我倒覺得生個女兒家也是有情有義的,雖不能傳宗接代,倒是對父母體貼,也是有用的。」在時代的變遷中,李福仁並不固執於傳統思維,是真正智慧通達之人。
大陸版的《福壽春》有李師江所寫的〈創作札記(代序)〉,記錄了李師江在創作生涯中對於寫作問題的摸索、反省與修正,其中有這樣一條:「耐心、笨拙、誠實、細心,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要寫好一個長篇的質素。」李師江正是通過這樣的實踐,讓生命與作品沉靜下來。我個人以為,不僅僅是寫長篇小說,其實「耐心、笨拙、誠實、細心」也是面對這個過於急功好利、喧囂浮躁的現代社會,很重要的美德。
推薦序
讓世界安靜下來
成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蘇敏逸
李師江對台灣讀者來說,也許並不算陌生。他曾先後在台灣出版了《比愛情更假》(2002)、《她們都挺棒的》(2003)、《肉》(2003)等三部小說及隨筆集《畜生級男人》(2004),這些作品大多以李師江混居北京的生活經驗為素材,在他噴薄而出,不吐不快的文字裡,激盪著桀傲不馴的青春野性與玩世不恭的叛逆之氣,隱隱然帶著王朔的調調,而他在2010年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系》,也讓我聯想到上個世紀九○年代王朔的經典作品〈動物凶猛〉。
熟悉李師江這類作品的...
作者序
後記
李師江
從寧德市區到增坂村,十三四公里,沿著一○四國道,送父親回村。道路兩邊的景致倒是不錯,桉樹、香樟四季常綠,其後是村莊、田野、果園,依次從車窗掠過,每次讓我想起侯孝賢《童年往事》、《最好的時光》之類的電影畫面。若是冬日,陽光從車窗進來,車裡暖洋洋的,我有一搭沒一搭地跟父親聊一兩句。
回寧德生活這兩三年,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送父親去看病。他是三十來年的老支氣管炎,有時候十天半月發作一次,有時候一兩個月發作一次,唯一的辦法就是打消炎藥。八十多歲的人了,一般的私人醫生不願意接診,我上午八點左右開車送父親上去,十一點多再接他回增坂村。期間三個小時他在我好友李育文的診所打吊瓶。如此連續五六天,甚是疲憊。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送父親來往的時光,亦可能是人生中最美的時光之一。
父親於我而言,不僅是父親,他承載著我對鄉村的寄託與迷戀。
有一天,在南漈登山,在路邊荊棘叢中發現一隻小貓,大概出生不久,兒子安川很喜歡,於是我們把牠送到老家,安川叫牠湯姆。每次回鄉村,就會看看湯姆,湯姆很快長成一隻壯碩的公貓。我心有所託,似乎不在家的時候牠替我守護家園。有時候牠在後院仰臥著懶懶地晒太陽,有時候抓來一隻老鼠放在地上玩耍。農村的院子,總是鬧過老鼠的,湯姆去了之後就絕少了。去年,由於老院子過於老舊,拆掉重建。在這過程中,湯姆各種受驚(也許主要是搬家時被鞭炮給驚著了),落荒而逃,再也不敢進家門,變成一隻在村裡閒逛的野貓。母親說牠有回來過幾次,看見房子跟原來不一樣,又跑掉了。
前幾個月,跟安川在街邊的車軲轆底下撿了一隻走丟的小貓,又帶回老家,這次取名叫六一,因為是六一兒童節撿的。六一在家住了幾天,後來就被經常到後院偷食的野貓帶走了——野貓生了一窩小貓,跟六一一般大,也許六一覺得跟牠們過更快樂些。
我又想養狗,父親是不太願意的,我就說服他。小時候家裡的一隻黑狗,跟我同齡,陪我上山,陪我走夜路,處處給我壯膽,總是是我童年最好的夥伴,以及最甜蜜的記憶之一。我說,現在如果有一隻狗陪你晒太陽,陪你看家,陪你散步,多好。父親終於被我說服了。我的私心是,我沒有時間或者不能做的事,狗能幫我做到。
我終究是希望一隻貓或者一隻狗,替我維繫與鄉村的關係。
我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終究是需要故鄉的。即便你無暇回家,只在腦海中回想。
有一種論調,說的是,如果你開始懷舊,就證明你老了。其實我從小學高年級到城裡念書開始,就開始懷舊了。我懷念在河中撈魚的日子,懷念在山上摘草莓的時光,懷念祠堂改成的小學裡被同學孤立的孤獨,懷念母親抱著我躲避颱風的惶恐,懷念鄉村給我的每一點童趣、恐懼以及喜悅——至今這些元素滲入血液,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氤氳二字:故鄉。
不會懷舊的人註定是冷血動物。
在前幾天與友人的聊天中,我們得到一個認同的說法:有一個鄉村老家的人,是多麼幸福。
當然,一切終將逝去,一切也將改變。譬如,對剛上小學的安川這一代人來說,也許他的故鄉在諸如迪斯尼樂園之類的場所。他頗為排斥鄉村,一點都不會興趣。當然,主要原因也是他沒有在此長時間生活過。
增坂村的前面是當年攔海造田的大片田地,現在已經成為蕉城最大的工業區。在離增坂村四五公里的海邊,台資闖入的聯德鎳合金項目正在投產,汙染指日可待,並成為成為整個寧德市人民的心頭之患。村莊裡高樓林立,外人租住的人口大量湧入。與我寫《福壽春》之時相比,鄉村以及周遭完全迥異。再過些年,這一片土地變成什麼樣子,不得而知。
可以預知的是,再過多年,我所熟悉的故鄉,將會面目全非,乃至消失——不論是因汙染而背井離鄉,還是因開發而物是人非,「故鄉」,將被快速奔跑的中國遠遠拋棄。那時候,聊以自慰的,只有手邊一本《福壽春》。
後記
李師江
從寧德市區到增坂村,十三四公里,沿著一○四國道,送父親回村。道路兩邊的景致倒是不錯,桉樹、香樟四季常綠,其後是村莊、田野、果園,依次從車窗掠過,每次讓我想起侯孝賢《童年往事》、《最好的時光》之類的電影畫面。若是冬日,陽光從車窗進來,車裡暖洋洋的,我有一搭沒一搭地跟父親聊一兩句。
回寧德生活這兩三年,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送父親去看病。他是三十來年的老支氣管炎,有時候十天半月發作一次,有時候一兩個月發作一次,唯一的辦法就是打消炎藥。八十多歲的人了,一般的私人醫生不願意接診,我上午八...
目錄
讓世界靜下來 蘇敏逸(成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福壽春
後記
附錄:李師江創作年表
讓世界靜下來 蘇敏逸(成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福壽春
後記
附錄:李師江創作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