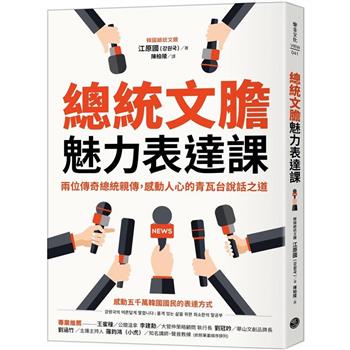名人推薦
我相信凡是讀過此書的人,都會毫不遲疑地肯認「詩的新批評」確是中國現代詩學的重要成就之一,它通過把現代詩歌觀念落實到具體的批評實踐之中,為促進中國詩學的現代化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並由此留下了大批值得認真分析和學習的詩學遺產,而陳越此書作為該領域的第一本系統性的研究專著,其原創之功、搜求之勞和開掘之深,委實值得嘉許。──解志熙.北京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英美新批評在一九二○年代後期就已傳進中國,新批評的首創者之一瑞恰慈,以及瑞恰慈的學生燕卜蓀都來中國講過學,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也在那時譯介到中國。新批評的研究方法在三、四○年代影響了朱自清和俞平伯,也影響了當時不少年輕詩人,如吳興華和袁可嘉,這一段歷史很少人知道,本書都有非常詳實的考察和評論。本書可以說是一部詳實的英美新批評在中國的傳播史。──呂正惠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詩的新批評」在現代中國之建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05 |
華文文學研究 |
$ 405 |
文學 |
$ 405 |
華文文學研究 |
$ 495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詩的新批評」在現代中國之建立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越
男,1978年生於湖北黃陂,2011年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就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文學,已在《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勵耘學刊》、《現代中文學刊》、《新詩評論》、《國外理論動態》、《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等刊物發表論文、譯文多篇,有數篇被《人大複印資料》(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轉載。譯有《《資本論》傳》(中央編譯出版社),編有《清華映像》(合編)(清華大學出版社)。
陳越
男,1978年生於湖北黃陂,2011年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就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文學,已在《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勵耘學刊》、《現代中文學刊》、《新詩評論》、《國外理論動態》、《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等刊物發表論文、譯文多篇,有數篇被《人大複印資料》(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轉載。譯有《《資本論》傳》(中央編譯出版社),編有《清華映像》(合編)(清華大學出版社)。
目錄
「詩的新批評」之重溫(序)/解志熙
第一章 「詩的新批評」在現代中國之建立
第一節 現代詩學與文本批評
第二節 文獻綜述與概念界定
第三節 問題意識與論述框架
第二章 英美新批評詩學在現代中國的譯介與傳播
第一節 瑞恰慈文藝理論在現代中國的譯介與反應
第二節 艾略特詩論在現代中國的譯介與傳播
第三節 燕卜蓀、朱利安.貝爾及奧登一派詩人的詩論
第三章 詩的經驗及其傳達:「詩的新批評」之理論基礎
第一節 瑞恰慈與詩的經驗說之確立:「詩的新批評」之創作本體論
第二節 經驗的傳達與象徵、晦澀:「詩的新批評」之分析話語
第三節 從關注詩人到關注詩:「詩的新批評」之核心方法論
第四章 文學教學與「詩的新批評」之展開
──以朱自清和一個雜誌及一個副刊為中心
第一節 朱自清的現代文學批評觀念
第二節 客觀地分析語義:朱自清新批評的核心
第三節 《國文月刊》、《新生報》與「詩的新批評」之展開
第五章 現代「詞的新批評」三大家
第一節 俞平伯詞釋思想
第二節 浦江清與〈詞的講解〉
第三節 吳世昌詞學批評思想述略
第六章 現代「詩的新批評」之後起之秀
第一節 邢光祖與比較詩學
第二節 吳興華與重審古典
第三節 袁可嘉與「戲劇主義」
第七章 現代「詩的新批評」之核心觀念例說
──以語音、肌理與含渾為中心
第一節 詩的新批評之「詩與語音」問題
第二節 詩的新批評之「肌理」說
第三節 詩的新批評之「含渾」說
第八章 現代「詩的新批評」之典型作品例說
第一節 重審古典世界:古詩新詮例說
第二節 揭開詞的神祕:現代詞釋的代表作
第三節 開闢新詩空間:白話新詩探幽例說
第四節 引入他山之石:西洋詩的譯釋例說
第九章 結語
第一章 「詩的新批評」在現代中國之建立
第一節 現代詩學與文本批評
第二節 文獻綜述與概念界定
第三節 問題意識與論述框架
第二章 英美新批評詩學在現代中國的譯介與傳播
第一節 瑞恰慈文藝理論在現代中國的譯介與反應
第二節 艾略特詩論在現代中國的譯介與傳播
第三節 燕卜蓀、朱利安.貝爾及奧登一派詩人的詩論
第三章 詩的經驗及其傳達:「詩的新批評」之理論基礎
第一節 瑞恰慈與詩的經驗說之確立:「詩的新批評」之創作本體論
第二節 經驗的傳達與象徵、晦澀:「詩的新批評」之分析話語
第三節 從關注詩人到關注詩:「詩的新批評」之核心方法論
第四章 文學教學與「詩的新批評」之展開
──以朱自清和一個雜誌及一個副刊為中心
第一節 朱自清的現代文學批評觀念
第二節 客觀地分析語義:朱自清新批評的核心
第三節 《國文月刊》、《新生報》與「詩的新批評」之展開
第五章 現代「詞的新批評」三大家
第一節 俞平伯詞釋思想
第二節 浦江清與〈詞的講解〉
第三節 吳世昌詞學批評思想述略
第六章 現代「詩的新批評」之後起之秀
第一節 邢光祖與比較詩學
第二節 吳興華與重審古典
第三節 袁可嘉與「戲劇主義」
第七章 現代「詩的新批評」之核心觀念例說
──以語音、肌理與含渾為中心
第一節 詩的新批評之「詩與語音」問題
第二節 詩的新批評之「肌理」說
第三節 詩的新批評之「含渾」說
第八章 現代「詩的新批評」之典型作品例說
第一節 重審古典世界:古詩新詮例說
第二節 揭開詞的神祕:現代詞釋的代表作
第三節 開闢新詩空間:白話新詩探幽例說
第四節 引入他山之石:西洋詩的譯釋例說
第九章 結語
序
「詩的新批評」之重溫(序)
解志熙
陳越的這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的修訂稿,記得此前的題目是「『詩的新批評』在現代中國之建立」,在預答辯的時候有幾位老師擔心「詩的新批評」這個說法過新,且有與英美的「新批評」攀比之嫌,所以建議修改為《「詩的文本批評」的中西匯合》,作為最終答辯的題目。我當然理解這個建議的善意──那幾位老師其實都很肯定陳越論文的學術貢獻,他們的建議只是為了答辯的保險而言。應該承認,「詩的文本批評」這個概念的指稱顯然比較明確,但我私心裡還是更喜歡「詩的新批評」那個說法,因為此類詩評確實借鑑了英美的新批評,才與中國古典詩學的注解賞析傳統劃開了清晰的界限,開闢了詩的文本批評的新階段──倘若折中一下,則「詩的新批評」乃正是運用現代的詩學觀念和批評方法針對「詩的文本」而展開的詩歌批評實踐。也正為了這個緣故,此次出版也便恢復了舊題。
誠如陳越所說,這樣一種詩的新批評乃是「中西匯合」的產物,只有在「五四」文學革命之後才可能發生。事實上,胡適、顧頡剛和俞平伯等在「五四」之初即曾熱烈討論過《詩經》諸篇的詩本義,發表了多篇「說詩」的文字,不過那時的他們只是籠統地運用著來自西方的純文學觀念、努力把《詩經》當做純文學的詩作來解讀,而尚無詩的文本批評的方法論之自覺。到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之際,兩種情況同時發生了:一是新詩壇上有象徵派-現代派詩歌的勃興,此類新詩含蘊著比較複雜深隱的情思和朦朧含蓄的詩藝,不是一般讀者可以一讀就懂的,於是也就迫切要求著批評性的解讀;二是古典詩詞進入大中學講壇,成為文學教學的重要內容,而由於古典語言的隔閡和詩藝的古雅,年輕的學子們也迫切要求著現代性的導讀。正是這兩種情況不約而同的交集,共同推動了針對具體詩歌文本的新批評之開展。
開創了這個詩的批評新路的,既有新詩人和批評家,也有致力於古典文學教學的現代學人──事實上這兩類人往往是二而一的。比如朱自清和俞平伯就既是初期的新詩人和新詩評論者,後來又成為高校的古典詩歌研究專家,這雙重的身分促使他們在致力於詩的文本批評及其方法論的探討時,一方面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代的解詩傳統,並努力使之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印象式鑑賞轉變為分析性的解讀;另一方面則更多地借鑑了西方現代的詩學觀念和詩歌批評方法,尤其是來自英美「新批評派」的詩歌批評方法。恰在此時,英國批評家瑞恰茲(I.A.Richards1893-1979)正好來華任教於清華、北大、燕京等校。瑞恰茲被公認為英美「新批評派」的奠基人之一(另一個奠基人是名詩人T.S.艾略特,他的詩作與批評理論也在此時傳入中國,另一個「新批評派」的代表人物、瑞恰茲的得意弟子燕卜蓀則在抗戰時期來華任教於西南聯大),他的批評理論、語義學研究和文本分析方法,特別適合於詩歌文本之解讀,給清華大學教授葉公超、朱自清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影響,以至於葉公超斷言:「我相信國內現在最需要的,不是浪漫主義,不是寫實主義,不是象徵主義,而是這種分析文學作品的理論。」(葉公超:〈曹葆華譯《科學與詩》序〉,撰寫於1934年,見《科學與詩》,商務印書館,1937年)正是由於葉公超的熱情介紹,朱自清也及時地注意到了瑞恰茲的理論和方法,遂努力將瑞恰茲的意義理論和文本分析方法運用於中國古典詩歌和現代新詩的解讀,陸續撰寫了《新詩雜話》、《詩多義舉例》等關於詩歌文本的新批評論著。朱自清又轉而推動了他的同事俞平伯和浦江清。我們只要讀讀俞平伯這一時期連續發表的解詩之作《讀詞偶得》,就不難體會他在傳統的鑑賞和訓詁之外,顯著地加強了詩詞語言意味的分析,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俞平伯在朱自清的熱情鼓勵下,精心撰寫了〈詩的神祕〉一文,堪稱詩歌文本「新批評」之開創性的方法論文獻。俞平伯承認「詩(詞也在內),有一部分人看它永遠是很神祕的,類乎符咒」,但新的理論方法的自覺使他自信地宣稱:「我們要把詩從神祕之國裡奪出,放在自然的基石上,即使有神祕,卻是可以分析,可以明白指出的。」又謂詩的神祕「只是詩的複雜微妙幽沉各屬性的綜合,似乎一時不能了解,卻終究可以分析,敘述和說明的。「(俞平伯:〈詩的神祕〉,《雜拌兒之二》第1頁、第4頁、第5頁,開明書店,1933年。)
進入抗戰及四十年代,對於詩的文本的「新批評」又有進一步的拓展。此時除朱自清等資深學者外,又有不少年輕學者如林庚、吳世昌、金克木、李廣田、邢光祖、吳興華、程千帆、袁可嘉等陸續加入,並且也出現了專門服務於國文教學的文本批評刊物《國文月刊》、《國文雜誌》(葉聖陶主持)及《新生報》「語言與文學」副刊等,……矚目於詩歌文本的新批評一時蔚然成風,湧現出一批相當出色的成果,如浦江清的《詞的講解》、朱自清的〈古詩十九首釋〉、吳世昌的《論詞的讀法》、李廣田的《詩的藝術》、吳興華的《現代西方批評方法在中國詩歌研究中的運用》、程千帆和沈祖棻合著的《古典詩歌論叢》(該集出版於1954年,但集內的解詩文章多作於四十年代)等,都是詩歌文本新批評的傑出論著。其批評對象,則既包括新詩,也有古典詩詞,甚至涉及外國詩。比較而言,對古典詩詞的新批評最有成效。
在詩歌文本的新批評開展過程中,每個批評者的具體操作方法容或有別,但大的著眼點和方法論是非常一致的,其要旨在朱自清的〈古詩十九首釋〉(此文是朱自清1940年夏至1941年夏的休假期間為《國文月刊》的「詩文選讀」欄撰寫的)前言裡得到了扼要地揭示——
詩是精粹的語言。因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許多人覺得詩難懂,便是為此。但詩究竟是「語言」,並沒有真的神祕;語言,包括說的和寫的,是可以分析的;詩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徹的了解;散文如此,詩也如此。有時分析起來還是不懂,那是分析得還不夠細密,或者是知識不夠,材料不足;並不是分析這個方法不成。這些情形,不論文言文、白話文、文言詩、白話詩,都是一樣。不過在一般不大熟悉文言的青年人,文言文,特別是文言詩,也許更難懂些罷了。
我們設「詩文選讀」這一欄,便是要分析古典和現代文學的重要作品,幫助青年諸君的解,引起他們的興趣,更注意的是要養成他們分析的態度。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實欣賞;欣賞是在透徹的了解裡。一般的意見將欣賞和了解分成兩橛,實在是不妥的。沒有透徹的了解,就欣賞起來,那欣賞也許會驢唇不對馬嘴,至多也只是模糊影響。一般人以為詩只能綜合的欣賞,一分析詩就沒有了。其實詩是最錯綜的、最多義的,非得細密的分析工夫,不能捉住它的意旨。若是囫圇吞棗的讀去,所得著的怕只是聲調詞藻等一枝一節,整個兒的詩會從你的口頭眼下滑過去。(朱自清:〈古詩十九首釋〉,《朱自清全集》第7卷第191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年。)
如所周知,傳統的中國思想和學術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注重直覺印象之談和經驗綜合之論,而不擅長系統性、學理性的分析。這個共同性影響及於古典的詩歌批評,便是面對詩意比較含蓄以至「神祕」的詩歌文本,古人很樂於坦承「詩無達詁」,於是要麼滿足於「釋事忘義」的訓詁性注釋,要麼滿足於訴諸經驗直覺的印象性品評,而長期缺乏綿密深入的分析性批評。朱自清等人所開創的「詩的新批評」,則肯認詩歌作為精粹的語言藝術品並非神祕無解,其精微的意味和精妙的藝術仍可通過語言藝術的分析而得以彰顯和昌明。他們對新詩與舊詩詞文本的精闢分析,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詩是可以分析的語言藝術作品」。這與英美「新批評」對詩的文本批評之立場和方法若合符節,而又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典語文學傳統中的合理因素,如此「中西融合」委實具有開拓中國詩歌批評新時代的重大意義。
然而,很可能因為這種詩的新批評比較注重具體文本的解讀,乍一看似乎關涉度不夠宏大、理論性也不很鮮明,所以當今學界一直很少關注它的歷史和價值。此前只有資深的現代詩歌研究專家孫玉石先生敏銳地意識到此類批評的現代意義,他從1987年開始不斷探索、先後撰發了多篇專論,到2007年結集為《中國現代解詩學的理論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成為這一領域的開創性學術成果,也是迄今唯一的專題論著。按,孫玉石先生所說的「中國現代解詩學」其實就是陳越所謂詩歌文本的「新批評」。孫先生的開創性研究誠然功不可沒,但也有明顯的局限──只把「解詩學」視為針對新詩的解讀性批評,研究的視野一直限制在「中國新詩學」的範圍裡,而未顧及到現代人對古典詩詞的解讀同樣可以納入到中國現代詩學的視野、同樣屬於詩歌文本的「新批評」之列,甚至比新詩的文本批評更為出色。
正是在借鑑孫玉石先生的先行研究的基礎上,陳越的探索更進了一步也更深了一層。陳越自覺超越「中國新詩學」的限制,別具慧眼地從「中國現代詩學」的視野出發,將發生在現代中國的所有運用現代詩學觀念和方法來進行的詩歌文本批評──不論其對象是舊詩、新詩還是外國詩──都納入詩歌文本的「新批評」的考察範圍,著力揭示其現代的理論基礎、方法特徵和具體的批評成就,於是所見更廣、所論更深。當然,與此俱來的學術難度也更大了,為此,陳越付出了艱苦的勞動和辛勤的思考。讀博的幾年間,陳越埋頭窮搜相關文獻、補充相關的中外文學知識、思考相關的詩學理論批評問題,終於用數十萬字的論文,第一次完整地梳理了「詩的文本批評」在現代中國崛起的來龍去脈、深入發掘了此種新批評的理論基礎、批評方法和批評實踐,讓人對詩的新批評潮流的歷史和價值獲得了全面的認識,這無疑是中國現代詩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陳越窮搜文獻的勞績,可以本書第二章為例,該章對英美新批評在現代中國之傳播的梳理可謂集其大成,其中有許多條文獻都是陳越首發的。至於陳越對「詩的新批評」成就的分析之深入,則可以本書第四章為例,該章重點討論了「詩的新批評」在詞學領域的展開,乃以俞平伯、浦江清、吳世昌對詞的解讀為代表,深入發掘其作為詩的新批評的現代意義、具體分析其批評方法的現代性特徵,完全超出了一般古典文學學術史的研究視野、而又扎實地彌補了中國現代詩學研究的一個盲點,所以讀來令人耳目一新。……我相信凡是讀過此書的人,都會毫不遲疑地肯認「詩的新批評」確是中國現代詩學的重要成就之一,它通過把現代詩歌觀念落實到具體的批評實踐之中,為促進中國詩學的現代化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並由此留下了大批值得認真分析和學習的詩學遺產,而陳越此書作為該領域的第一本系統性的研究專著,其原創之功、搜求之勞和開掘之深,委實值得嘉許。
說起來,陳越在本科所學並非文學,只因熱愛文學,乃刻苦自修、考入南開大學攻讀文學碩士,後來又到清華隨我讀博。他的探討吳宓、梁實秋等新人文主義者的碩士論文,仔細追溯西方原典、校正流行比附之見,讓面試的老師們頗為讚許。也正因為他的英文很好,所以在博士論文選題時,最初曾想研討中西現代文學批評觀念的融合問題,後來覺得題目過大,容易失之浮泛,乃將視點集中落實到「詩的文本批評的中西融合」這個專門的詩學問題上,由此銳意探尋,遂有了不少重要的文獻發現和漸趨深入的理論思考。陳越的好學苦讀在清華中文系是出了名的。讀博生活本來就很清苦,陳越又是來自基層的一個窮學生,可他讀博期間卻節衣縮食,購買複印了大量文學詩學書籍,他的小小宿舍實在無法安頓,我只好把辦公室借給他,放了整整一屋子。如此勤學苦讀,給陳越的論文打下了厚實的基礎,答辯時一下子拿出了三十餘萬言的論文稿,其厚重度和完成度讓汪暉兄在答辯會上當面讚嘆說,「陳越的論文是本專業歷屆同學中唯一真正完成了的博士論文。」論學一向嚴格的方錫德兄則破例地在評議書裡讚揚陳越的論文,「是本學科近年來罕見的一篇優秀的博士學位論文,建議通過答辯後,申報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然而,謙虛樸實的陳越並沒有申報這個獎項,畢業後的幾年來他仍然孜孜矻矻地繼續修改和完善著論文。自然,此前的陳越在學術修養上也有明顯的不足,比如對中國古典解詩學傳統不很熟悉就是他的論文的一個薄弱環節。如今翻看這個即將出版的修改稿,在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進和補充。要說這個修改稿的問題,恰恰來自於陳越謙抑的個人性格和嚴格的學術自律:有些重要人物如葉公超本來可以專寫一節的,可是陳越卻因為有人論述在先,他便只註明別人的研究而不再詳論;有些重要文獻本來是陳越先發現的,可是別人後來率先發表了,他就删掉自己而轉注別人。在學術上如此過於嚴格的自律,反倒影響了本書論述敘事的完整性和個人觀點的充分表達。這是讓我很感可惜的。
陳越畢業已近四年,論文終於要出版了。欣悅之餘,乃略為介紹如上,即以此為序吧。
解志熙
陳越的這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的修訂稿,記得此前的題目是「『詩的新批評』在現代中國之建立」,在預答辯的時候有幾位老師擔心「詩的新批評」這個說法過新,且有與英美的「新批評」攀比之嫌,所以建議修改為《「詩的文本批評」的中西匯合》,作為最終答辯的題目。我當然理解這個建議的善意──那幾位老師其實都很肯定陳越論文的學術貢獻,他們的建議只是為了答辯的保險而言。應該承認,「詩的文本批評」這個概念的指稱顯然比較明確,但我私心裡還是更喜歡「詩的新批評」那個說法,因為此類詩評確實借鑑了英美的新批評,才與中國古典詩學的注解賞析傳統劃開了清晰的界限,開闢了詩的文本批評的新階段──倘若折中一下,則「詩的新批評」乃正是運用現代的詩學觀念和批評方法針對「詩的文本」而展開的詩歌批評實踐。也正為了這個緣故,此次出版也便恢復了舊題。
誠如陳越所說,這樣一種詩的新批評乃是「中西匯合」的產物,只有在「五四」文學革命之後才可能發生。事實上,胡適、顧頡剛和俞平伯等在「五四」之初即曾熱烈討論過《詩經》諸篇的詩本義,發表了多篇「說詩」的文字,不過那時的他們只是籠統地運用著來自西方的純文學觀念、努力把《詩經》當做純文學的詩作來解讀,而尚無詩的文本批評的方法論之自覺。到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之際,兩種情況同時發生了:一是新詩壇上有象徵派-現代派詩歌的勃興,此類新詩含蘊著比較複雜深隱的情思和朦朧含蓄的詩藝,不是一般讀者可以一讀就懂的,於是也就迫切要求著批評性的解讀;二是古典詩詞進入大中學講壇,成為文學教學的重要內容,而由於古典語言的隔閡和詩藝的古雅,年輕的學子們也迫切要求著現代性的導讀。正是這兩種情況不約而同的交集,共同推動了針對具體詩歌文本的新批評之開展。
開創了這個詩的批評新路的,既有新詩人和批評家,也有致力於古典文學教學的現代學人──事實上這兩類人往往是二而一的。比如朱自清和俞平伯就既是初期的新詩人和新詩評論者,後來又成為高校的古典詩歌研究專家,這雙重的身分促使他們在致力於詩的文本批評及其方法論的探討時,一方面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代的解詩傳統,並努力使之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印象式鑑賞轉變為分析性的解讀;另一方面則更多地借鑑了西方現代的詩學觀念和詩歌批評方法,尤其是來自英美「新批評派」的詩歌批評方法。恰在此時,英國批評家瑞恰茲(I.A.Richards1893-1979)正好來華任教於清華、北大、燕京等校。瑞恰茲被公認為英美「新批評派」的奠基人之一(另一個奠基人是名詩人T.S.艾略特,他的詩作與批評理論也在此時傳入中國,另一個「新批評派」的代表人物、瑞恰茲的得意弟子燕卜蓀則在抗戰時期來華任教於西南聯大),他的批評理論、語義學研究和文本分析方法,特別適合於詩歌文本之解讀,給清華大學教授葉公超、朱自清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影響,以至於葉公超斷言:「我相信國內現在最需要的,不是浪漫主義,不是寫實主義,不是象徵主義,而是這種分析文學作品的理論。」(葉公超:〈曹葆華譯《科學與詩》序〉,撰寫於1934年,見《科學與詩》,商務印書館,1937年)正是由於葉公超的熱情介紹,朱自清也及時地注意到了瑞恰茲的理論和方法,遂努力將瑞恰茲的意義理論和文本分析方法運用於中國古典詩歌和現代新詩的解讀,陸續撰寫了《新詩雜話》、《詩多義舉例》等關於詩歌文本的新批評論著。朱自清又轉而推動了他的同事俞平伯和浦江清。我們只要讀讀俞平伯這一時期連續發表的解詩之作《讀詞偶得》,就不難體會他在傳統的鑑賞和訓詁之外,顯著地加強了詩詞語言意味的分析,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俞平伯在朱自清的熱情鼓勵下,精心撰寫了〈詩的神祕〉一文,堪稱詩歌文本「新批評」之開創性的方法論文獻。俞平伯承認「詩(詞也在內),有一部分人看它永遠是很神祕的,類乎符咒」,但新的理論方法的自覺使他自信地宣稱:「我們要把詩從神祕之國裡奪出,放在自然的基石上,即使有神祕,卻是可以分析,可以明白指出的。」又謂詩的神祕「只是詩的複雜微妙幽沉各屬性的綜合,似乎一時不能了解,卻終究可以分析,敘述和說明的。「(俞平伯:〈詩的神祕〉,《雜拌兒之二》第1頁、第4頁、第5頁,開明書店,1933年。)
進入抗戰及四十年代,對於詩的文本的「新批評」又有進一步的拓展。此時除朱自清等資深學者外,又有不少年輕學者如林庚、吳世昌、金克木、李廣田、邢光祖、吳興華、程千帆、袁可嘉等陸續加入,並且也出現了專門服務於國文教學的文本批評刊物《國文月刊》、《國文雜誌》(葉聖陶主持)及《新生報》「語言與文學」副刊等,……矚目於詩歌文本的新批評一時蔚然成風,湧現出一批相當出色的成果,如浦江清的《詞的講解》、朱自清的〈古詩十九首釋〉、吳世昌的《論詞的讀法》、李廣田的《詩的藝術》、吳興華的《現代西方批評方法在中國詩歌研究中的運用》、程千帆和沈祖棻合著的《古典詩歌論叢》(該集出版於1954年,但集內的解詩文章多作於四十年代)等,都是詩歌文本新批評的傑出論著。其批評對象,則既包括新詩,也有古典詩詞,甚至涉及外國詩。比較而言,對古典詩詞的新批評最有成效。
在詩歌文本的新批評開展過程中,每個批評者的具體操作方法容或有別,但大的著眼點和方法論是非常一致的,其要旨在朱自清的〈古詩十九首釋〉(此文是朱自清1940年夏至1941年夏的休假期間為《國文月刊》的「詩文選讀」欄撰寫的)前言裡得到了扼要地揭示——
詩是精粹的語言。因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許多人覺得詩難懂,便是為此。但詩究竟是「語言」,並沒有真的神祕;語言,包括說的和寫的,是可以分析的;詩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徹的了解;散文如此,詩也如此。有時分析起來還是不懂,那是分析得還不夠細密,或者是知識不夠,材料不足;並不是分析這個方法不成。這些情形,不論文言文、白話文、文言詩、白話詩,都是一樣。不過在一般不大熟悉文言的青年人,文言文,特別是文言詩,也許更難懂些罷了。
我們設「詩文選讀」這一欄,便是要分析古典和現代文學的重要作品,幫助青年諸君的解,引起他們的興趣,更注意的是要養成他們分析的態度。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實欣賞;欣賞是在透徹的了解裡。一般的意見將欣賞和了解分成兩橛,實在是不妥的。沒有透徹的了解,就欣賞起來,那欣賞也許會驢唇不對馬嘴,至多也只是模糊影響。一般人以為詩只能綜合的欣賞,一分析詩就沒有了。其實詩是最錯綜的、最多義的,非得細密的分析工夫,不能捉住它的意旨。若是囫圇吞棗的讀去,所得著的怕只是聲調詞藻等一枝一節,整個兒的詩會從你的口頭眼下滑過去。(朱自清:〈古詩十九首釋〉,《朱自清全集》第7卷第191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年。)
如所周知,傳統的中國思想和學術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注重直覺印象之談和經驗綜合之論,而不擅長系統性、學理性的分析。這個共同性影響及於古典的詩歌批評,便是面對詩意比較含蓄以至「神祕」的詩歌文本,古人很樂於坦承「詩無達詁」,於是要麼滿足於「釋事忘義」的訓詁性注釋,要麼滿足於訴諸經驗直覺的印象性品評,而長期缺乏綿密深入的分析性批評。朱自清等人所開創的「詩的新批評」,則肯認詩歌作為精粹的語言藝術品並非神祕無解,其精微的意味和精妙的藝術仍可通過語言藝術的分析而得以彰顯和昌明。他們對新詩與舊詩詞文本的精闢分析,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詩是可以分析的語言藝術作品」。這與英美「新批評」對詩的文本批評之立場和方法若合符節,而又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典語文學傳統中的合理因素,如此「中西融合」委實具有開拓中國詩歌批評新時代的重大意義。
然而,很可能因為這種詩的新批評比較注重具體文本的解讀,乍一看似乎關涉度不夠宏大、理論性也不很鮮明,所以當今學界一直很少關注它的歷史和價值。此前只有資深的現代詩歌研究專家孫玉石先生敏銳地意識到此類批評的現代意義,他從1987年開始不斷探索、先後撰發了多篇專論,到2007年結集為《中國現代解詩學的理論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成為這一領域的開創性學術成果,也是迄今唯一的專題論著。按,孫玉石先生所說的「中國現代解詩學」其實就是陳越所謂詩歌文本的「新批評」。孫先生的開創性研究誠然功不可沒,但也有明顯的局限──只把「解詩學」視為針對新詩的解讀性批評,研究的視野一直限制在「中國新詩學」的範圍裡,而未顧及到現代人對古典詩詞的解讀同樣可以納入到中國現代詩學的視野、同樣屬於詩歌文本的「新批評」之列,甚至比新詩的文本批評更為出色。
正是在借鑑孫玉石先生的先行研究的基礎上,陳越的探索更進了一步也更深了一層。陳越自覺超越「中國新詩學」的限制,別具慧眼地從「中國現代詩學」的視野出發,將發生在現代中國的所有運用現代詩學觀念和方法來進行的詩歌文本批評──不論其對象是舊詩、新詩還是外國詩──都納入詩歌文本的「新批評」的考察範圍,著力揭示其現代的理論基礎、方法特徵和具體的批評成就,於是所見更廣、所論更深。當然,與此俱來的學術難度也更大了,為此,陳越付出了艱苦的勞動和辛勤的思考。讀博的幾年間,陳越埋頭窮搜相關文獻、補充相關的中外文學知識、思考相關的詩學理論批評問題,終於用數十萬字的論文,第一次完整地梳理了「詩的文本批評」在現代中國崛起的來龍去脈、深入發掘了此種新批評的理論基礎、批評方法和批評實踐,讓人對詩的新批評潮流的歷史和價值獲得了全面的認識,這無疑是中國現代詩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陳越窮搜文獻的勞績,可以本書第二章為例,該章對英美新批評在現代中國之傳播的梳理可謂集其大成,其中有許多條文獻都是陳越首發的。至於陳越對「詩的新批評」成就的分析之深入,則可以本書第四章為例,該章重點討論了「詩的新批評」在詞學領域的展開,乃以俞平伯、浦江清、吳世昌對詞的解讀為代表,深入發掘其作為詩的新批評的現代意義、具體分析其批評方法的現代性特徵,完全超出了一般古典文學學術史的研究視野、而又扎實地彌補了中國現代詩學研究的一個盲點,所以讀來令人耳目一新。……我相信凡是讀過此書的人,都會毫不遲疑地肯認「詩的新批評」確是中國現代詩學的重要成就之一,它通過把現代詩歌觀念落實到具體的批評實踐之中,為促進中國詩學的現代化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並由此留下了大批值得認真分析和學習的詩學遺產,而陳越此書作為該領域的第一本系統性的研究專著,其原創之功、搜求之勞和開掘之深,委實值得嘉許。
說起來,陳越在本科所學並非文學,只因熱愛文學,乃刻苦自修、考入南開大學攻讀文學碩士,後來又到清華隨我讀博。他的探討吳宓、梁實秋等新人文主義者的碩士論文,仔細追溯西方原典、校正流行比附之見,讓面試的老師們頗為讚許。也正因為他的英文很好,所以在博士論文選題時,最初曾想研討中西現代文學批評觀念的融合問題,後來覺得題目過大,容易失之浮泛,乃將視點集中落實到「詩的文本批評的中西融合」這個專門的詩學問題上,由此銳意探尋,遂有了不少重要的文獻發現和漸趨深入的理論思考。陳越的好學苦讀在清華中文系是出了名的。讀博生活本來就很清苦,陳越又是來自基層的一個窮學生,可他讀博期間卻節衣縮食,購買複印了大量文學詩學書籍,他的小小宿舍實在無法安頓,我只好把辦公室借給他,放了整整一屋子。如此勤學苦讀,給陳越的論文打下了厚實的基礎,答辯時一下子拿出了三十餘萬言的論文稿,其厚重度和完成度讓汪暉兄在答辯會上當面讚嘆說,「陳越的論文是本專業歷屆同學中唯一真正完成了的博士論文。」論學一向嚴格的方錫德兄則破例地在評議書裡讚揚陳越的論文,「是本學科近年來罕見的一篇優秀的博士學位論文,建議通過答辯後,申報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然而,謙虛樸實的陳越並沒有申報這個獎項,畢業後的幾年來他仍然孜孜矻矻地繼續修改和完善著論文。自然,此前的陳越在學術修養上也有明顯的不足,比如對中國古典解詩學傳統不很熟悉就是他的論文的一個薄弱環節。如今翻看這個即將出版的修改稿,在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進和補充。要說這個修改稿的問題,恰恰來自於陳越謙抑的個人性格和嚴格的學術自律:有些重要人物如葉公超本來可以專寫一節的,可是陳越卻因為有人論述在先,他便只註明別人的研究而不再詳論;有些重要文獻本來是陳越先發現的,可是別人後來率先發表了,他就删掉自己而轉注別人。在學術上如此過於嚴格的自律,反倒影響了本書論述敘事的完整性和個人觀點的充分表達。這是讓我很感可惜的。
陳越畢業已近四年,論文終於要出版了。欣悅之餘,乃略為介紹如上,即以此為序吧。
2015年6月10日於清華園之聊寄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