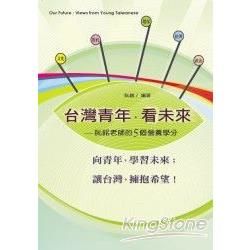向青年,學習未來;
讓台灣,擁抱希望!
當前朝的遺老遺少、懷抱舊思維的人,
仍霸佔著台灣的政治舞台,
被稱為「新世代」的年輕人,
如何看待台灣?
如何憧憬台灣的未來?
二○○六年《時代》雜誌
選出每一個活躍在Web2.0平台的「你」
作為改變世界的風雲人物。
活躍在Web2.0的台灣年輕人,
也將會是改變台灣未來的重要力量。
為了讓台灣人聽到新的聲音,
為了讓台灣邁向幸福的未來
阮銘老師與一群馳騁在Web2.0平台上的一代新人,
展開五場名為「台灣的未來」的精彩對談。
本書集結這五場對談的內容,
希望讓年輕人能取得發言位置,
進而爆發出無盡的生命力與創新力,
不僅能夠改變台灣,更改變「改變台灣的方式」。
對話主題:
第一場 我是誰?從身分認同到國家認同
第二場 台灣的未來掌握在青年們的手中
第三場 改造台灣未來藍圖-經濟、教育、環保議題
第四場 讓世界看見台灣
第五場 二○○八總統大選對台灣未來的意義與影響
編著者簡介
阮銘
一九三一年出生於中國上海,年輕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後遭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王震撤銷工作,開除黨籍。二○○二年取得台灣國籍,二○○四年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近十年來,關心台灣民主發展,長期為捍衛台灣民主自由仗義執言。
著有《民主台灣vs.共產中國》、《去恐懼,開創台灣歷史新時代!》、《兩個台灣的命運--認同TAIWAN vs.認同CHINA》、《從寧靜革命到寧靜建國》、《歷史的錯誤--台美中關係探源》等書。
對談者簡介(按姓氏筆劃排序)
李兆立
一九八一年在台北出生,目前就讀於東海大學政研所碩士班,並在台北工作,算半個台中人兼半個台北人。十五歲以前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忠貞信徒,十八歲以後叛逆至今;大學主修是公共行政,研究所轉戰國際關係,但真正有興趣的是政治哲學。有別於大多數人選擇郭台銘,最想效法的對象是汪平雲與陳博志。
呂家華
現任台灣青年公民論壇協會理事、台大社會系專任助理。這兩年因參與青年國是會議,進而接觸「審議民主」後,開始真正學習如何去愛這塊土地,並且認真思考整個台灣目前遇到的困境是什麼?真正的價值是什麼?期盼能將生命過程中的體驗及感動持續影響周遭所有的人,使大家都能跟這塊土地一起愈來愈好!
林彥志
一九八一年出生,巨蟹座,台中人,目前就讀於政治大學公行所。大學主修的是政治和經濟,順道選擇了法律當輔系,於是常在政治學的課程上當經濟學代理人,上經濟學時卻又成為政治學的守護神,偶爾穿插一點法律觀點。真正的嗜好則是文學與品茶,在四面遭書籍包圍的書桌上,享受一縷清香。
馬文鈺
台大政治系畢業,現正就讀於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大陸組,研究兩岸關係。大學時期曾擔任台大學生會副會長、台大建中北一女校友會會長,社會工作經驗為立委助理、縣長機要秘書以及台灣智庫專案助理。
高閔琳
畢業於台灣大學昆蟲學系。由於天生喜好汲取各種知識,所以從自然科學的專業領域轉而投入社會人文科學,目前就讀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期待能透過多元的視角與開闊的視野看待台灣社會,並透過堅定的信念,讓愛台灣、期待台灣更好的理想付諸實現。
陳怡文
一九八一年生。東吳大學哲學系畢業。二○○五年七月至二○○六年九月,於天主教善牧基金會擔任少女中途之家生輔員;二○○七年三月於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擔任執行秘書至今。
陳育青
一九七五年生。主修美術設計和電影,曾獲二○○七年K氏青年人文獎。
廖偉迪
東吳大學社會系雙主修社會工作學系,曾任社會系學會會長及系務、院務會議代表,目前為二○○八年青年國事會議諮詢會委員。二○○八年新年新希望為:「World Peace!!」並期望能結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讓台灣更好。
蔡依靜
族名Lamen。父親是花蓮馬太鞍人,母親是台南閩南人。從小在台南求學生活,只要假期就會回到遠在花蓮的部落,享受部落小孩的生活樂趣。也因為這樣的環境,所以超愛旅行和運動,目前回到花蓮當個部落工作者。
劉端鈺
大學及研究所主修法律,在理論研讀及實務經歷中,時時刻刻感受並體驗著台灣社會中的光明與黑暗。除了公法及基因科技法律專業外,更愛閱讀、思辯、塗鴉、書法、舞蹈、藝術以及所有美的人事物。身為年輕人,對於這塊土地上不公不義、光怪離奇的人事物深感痛心及憤怒,但相信可以在各個領域中同心協力去想像並實踐、關心並建言、監督並解決,為所寶貝的台灣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