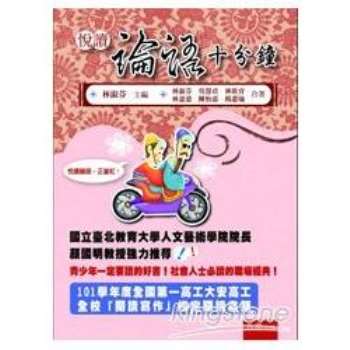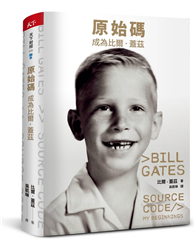拍攝《阿美嘻哈》的人類學家futuru,
在以紀錄片保存阿美族生活文化之外,
也以文字記錄他與都蘭的結緣故事,
以及阿美族人如何恣意地在傳統與現代的矛盾中,
協調出創造力與活力。
一個誤打誤撞闖入都蘭阿美族生活圈的客家年輕人,他有個阿美族的名字叫Futuru,字面上的意思是「睪丸」,引伸的意思是「真正的男人」。
這個真正的男人,和他的一群都蘭兄弟們,在都蘭感受變動中的「蘭調節奏」,經歷許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在年祭的海祭活動中下海,卻被水母電得遍體鱗傷;第一次硬撐著跳完舉花傘插番刀的kulakur舞後,腳抽筋;第一次拿魚叉刺魚,卻只叉到一隻有刺的小河豚……
雖然出糗不斷,卻在汗水與淚水中茁壯,在石堆滿佈中努力冒出新芽。
我選擇用最簡單的方式來書寫這個真實故事,希望能讓讀者像讀一本小說般地,透過輕鬆的閱讀,理解都蘭阿美族人生活的部分面向。對於我來說,人類學,不僅僅是一門探索人類社會與文化知識的學問,更是一種生活的方式。透過這些文字的描述,希望讀者能夠獲得一些關於阿美族社會與文化的知識之外,也隨著我的眼睛與感受,一同領略這個以石堆命名的阿美族聚落中馬嘎巴嗨(阿美語中的漂亮、美麗、亮麗之意)的人、事、物。
—— 蔡政良
本書特色
◎強烈的故事性,與幽默的筆法,讓都蘭阿美族人的年齡階層傳統,
就像發生在你我身邊的故事般親切。
◎看見都蘭在流行圖騰之外的活力與生命力。
◎一群男人之間,充滿汗水與淚水的故事。
作者簡介
蔡政良(Futuru)
1971年生,個人認同流動於新竹客家人與台東阿美人之間,生活方式如同在寫作一般,一連串的逗號、頓號、驚嘆號與問號勾連起他的文章。
喜歡旅行、電影、閱讀與各種戶外活動,興致來時也喜歡作菜。帶著點放蕩不羈的形象與行事風格,許多朋友皆稱其為瘋子。
曾為河左岸劇團成員與科學園區半導體公司訓練副理,現為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以及民族誌影片工作者。紀錄片作品包含《回來是土地肥沃的開始》(2001年)、《阿美嘻哈》(2005年)等,目前正在拍攝《從新幾內亞到台北》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