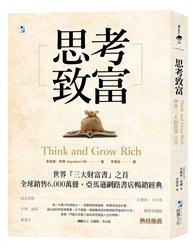我的這些歷史記錄,能讓謊言退卻嗎?
國共兩黨當前的百年慶,究竟是什麼樣的造史運動?
歷史真相又是如何?
少年時在蔣介石國民黨專政下,
我追求過自由,
後來得到的,
是毛澤東共產奴役制度的統治;
那是第一次「自由的追求與毀滅」。
毛澤東去世時,
我雖已四十五歲,
卻重做起少年時的自由之夢,
再次毀滅於鄧小平的「反自由化」大戰略。
——阮銘
中國、美國,到台灣,
他畢生追求自由;
在中國的大半生,經歷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統治,
年幼時遭遇父母親被國民黨殺害,
壯年時身陷文化大革命瘋狂般的鬥爭與下放勞改,
與胡耀邦共事時又目睹共產黨高層的權力惡鬥,
終於自由夢碎,
認清極權統治者只把人民當棋子的相同本質。
後半生他在美國與台灣呼吸自由的空氣,
驗證民主自由的價值,
但仍不免憂心奴役制度的無法根絕。
他的一生是個時代的縮影,
國民黨軍人子弟岀身,
又曾經是國共內戰中「勝利者」的一方,
親歷中國近代巨大的轉變,
這部回憶錄將是他最真實的人生記錄,
告誡世人自由、人權的可貴。
本書特色
1.一個身歷中國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共產黨權力鬥爭的自由主義者,最真實、最深切的回憶錄。
2.有別於國共兩黨觀點的國共鬥爭史。在國共兩黨即將合力迎接所謂百年慶的同時,這本回憶錄將帶給你不同的想法與感受,看見真相。
作者簡介:
阮銘
一位跨越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黨國統治時代,以及跨越大洋兩岸和海峽兩岸兩種社會的自由主義者,人生的重要歲月都投身在爭取自由民主,這個現代
文明的普世價值。
1931年出生於中國上海。父親是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砲兵科畢業,與何應欽同學,早年隨孫中山投身革命,於孫中山任非常大總統時期擔任總統府侍衛官,1922年「陳炯明兵變」時,曾護衛孫中山避居永豐艦,之後投身北伐與抗日游擊武裝,1940年底遭隸屬國民黨軍統特務系統的「忠義救國軍」秘密殺害。母親於1943年為尋找父親失蹤原因,遭誘至安徽廣德旅店,至今下落不明。
1945年與震旦附中一群關心時局的同學成立「耕耘社」,於該社刊物《耕耘》上發表批評時政的文章,也參加校外學生運動。隔年與「耕耘社」同學一起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上海市學生民主運動。
1948年,考入燕京大學,對於燕京大學校訓「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務)」相當認同,浸淫在燕京大學的自由學風之中。
1952年,因燕京大學在反美浪潮中遭撤銷,隨著就讀的工科被併入清華大學,擔任機械、水利兩系的學生黨總支書記,兼任團委副書記(後任書記)。前往清華大學之前,初次見到當時剛轉任青年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
1958年,反右鬥爭後,因應北京市委調學校知識份子幹部充實新聞戰線的
需求,調任《北京日報》社政法文教部副主任,1959年調任理論部主任,曾經下放到北京郊區朝陽公社的南磨坊第八生產隊與農民一起生活,一起體會饑餓的滋味。
1961年,調至中共意識形態戰線的前哨陣地中央宣傳部,於陶鑄任中宣部長時期任調查研究室主任,之後在中央文革小組對陶鑄的鬥爭中受波及,遭抄家六次,被安上「砲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接受軍事管制小組隔離審查。
1977年,應胡耀邦之邀,至中央黨校為《理論動態》雜誌效力;接著擔任新成立的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多次受胡耀邦之邀,參與中共中央主要會議提出改革意見。但終於因改革的言論不見容於胡喬木、鄧力群等,在王震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時被開除黨籍,撤銷工作。
1988年,經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向羅斯基金會推薦,前往哥倫比
亞大學任羅斯訪問學者。之後又在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做訪問研究。
1997年應聘來台,於淡江大學任教,與台灣人多所接觸之後,極為欣賞台灣人開放、勇敢、豪邁的海洋性格,也對台灣的民主制度頗為傾心,於2002年取得台灣國籍,2004~2006年,在陳水扁擔任總統時,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目前為台灣綜合研究院顧問。
著有《歷史轉折點上的胡耀邦》、《鄧小平帝國》、《中共人物論》、《兩岸統一百年大計》、《透視總書記》、《民主在台灣》。在玉山社有:《民主台灣vs.共產中國》、《去恐懼,開創台灣歷史新時代!》、《兩個台灣的命運——認同TAIWAN vs.認同CHINA》、《從寧靜革命到寧靜建國》、《歷史的錯誤——台美中關係探源》、《我看台灣與台灣人》、《鄧小平帝國30年》,編著《台灣青年.看未來》等書。其中《歷史的錯誤——台美中關係探源》一書被譯為日文,在日本由草思社出版。
章節試閱
正午黑影
一個深秋的正午,太陽在晴空中照著我和二姊從學校回家,正當跨進家門的一剎那,一個巨大的黑影轟然掠過。抬頭一望,是一架日本軍機,座艙裡的日軍飛行員清晰可見。我們急忙躲進門內,二姊抱住我,脫口說出一句:「多可怕的日子,生不如死啊!」她是個七歲的孩子,我們一起上學,一起玩,從未聽她說過這樣的話。
那天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日軍在金山衛登陸的日子,死亡正在逼近我的家。當晚二姊大口吐血,請醫師來,診斷是敗血症,需要立刻輸血。但那時大家都在逃難,已無法搶救。我守在二姊身旁,驚恐地看著她一次接一次吐血,結束了短暫的生命。
這是我最早的記憶,也是第一次看到死亡和經歷心靈的巨大痛苦。在此之前,我也有過快樂的童年吧?但腦中一片空白。我的記憶,從這正午的黑影開始。自己也覺得奇怪:難道痛苦的記憶,能使快樂的記憶消失無蹤?
第二天父親到家。那時父親在廣東工作,原本是回來接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去廣東的,沒想到二姊亡故,回廣東的路也被日軍切斷。父親考慮後,決定不回廣東,去上海投身抗日戰爭。父親說:日軍很快會過來,這家不能住下去了,去上海,在法租界安家,對母親和孩子們比較安全,他自己上戰場打仗。
我的父親阮毅然,原來就是軍人,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砲兵科畢業。他早年隨孫中山投身革命,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準備北伐時,父親是孫中山總統府的侍衛官。一九二二年六月,孫中山手下的粵軍首領陳炯明,以反對孫中山北伐為由,發動兵變,圍攻總統府。父親護衛孫中山離開總統府,避居白鵝潭的永豐艦,在短兵相接的作戰中,奪得陳炯明的馬鞭,我見過那時的一張照片。
孫中山去世後,父親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教官,因射擊優異,多次獲得當時蘇聯軍事顧問加侖將軍的獎勵。母親曾給我看過她保存的兩件獎品:一枚金質獎牌,上面刻有軍人射擊中標的浮雕;一塊歐米加牌懷錶。一九二六年夏,父親投入北伐戰爭,從廣東出發,一路同軍閥作戰,一九二七年抵達南京。
父親到南京後,看不慣當時國民革命軍內部爭權奪利,互相惡鬥的風氣,一度告假還鄉,與母親顧瑛石結婚。父親一八九二年生,半生戎馬生涯,那時已三十五歲。母親一九○一年生,比父親小九歲。父母兩人的原籍都是江蘇金山,父親是金山縣呂巷鎮,母親是金山縣洙涇鎮。結婚後父母回到南京,住在焦狀元巷。
我的大姊一九二八年生在南京,取名阮寧。那時父親的同學何應欽任訓練總監部部長,請父親到他的總監部任全國各中學視察,大概是管理全國中學軍事訓練之類事務。聽大姊說,何應欽在她出生時送了一份禮,是一個銀行存摺,等她長到二十歲,這個存摺累積的本息,可以支付出洋留學的學費。誰想到二十年後,瘋狂的通貨膨脹,不但讓這存摺成了廢紙,連發行這存摺的銀行和政府,也都一起從南京消失了。
父親在南京沒有待多久。母親告訴我,我生在上海昆明里一所弄堂房子裡。父親看不慣南京官場的風氣,以為到地方可以做些對百姓有益的事。他先後做過江蘇省江陰、川沙、淮陰等縣的縣長,和上海閘北區的警察局長。據母親說,父親每到一地,總是「與潮流不合」;他不願同流合污,做不久就「掛冠求去」。我四歲時,父親應保定軍校時的老同學歐陽惜白之邀,去了廣東;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離開上海回到家鄉。那時我已有兩個姊姊、兩個妹妹。
這次父親從廣東回來,二姊已去世;兩個妹妹還小,暫時留在鄉下託付給外祖父母照顧。父親帶著母親、大姊和我開始「逃難」;父親的目的地,是到上海把我們安置下,他自己去找軍隊抗日。那時金山到上海的公共交通,陸路和水路均已斷絕。父親選擇走鄉間小路,既可避開從金山衛登陸的日本兵,又能得到沿途鄉民的幫助。
傍晚,我們走到一個村莊陸家绔,在農家住下。第二天父親得悉,去上海的道路已滿佈日軍,無法通過,只得暫留鄉間。原來從「八一三」淞滬抗戰開始,防守金山衛的中國軍隊主力,已向北轉移到上海浦東,致使日軍十一月五日登陸後,得以長驅直入,迅速開往淞滬戰場。十一月八日中國軍隊從淞滬撤退時,遭南北兩路日軍夾擊,損失慘重,日軍於十一月十二日攻佔上海。
那些天我們住在陸家绔,每天清晨,大姊和我都與農家孩子一同到野地裡挖野菜。大姊挖的是薺菜,那是一種味道鮮美的野菜,但外形與一些野草相似,我難以辨識。我只會同幾個小男孩一起挖豬草,是只能給豬吃的野草,很容易找,一個早晨我就能挖到很多。
父親每天都同鄉間父老聚在一起議論局勢,晚間也和母親談論,我和大姊也似懂非懂地傾聽著。回想起來,父親的意思大約是,從淞滬戰場和金山衛日軍登陸的情形看,戰爭形勢已與過去不同。過去的目標是「蠶食」,從東北到華北,動員的主力是駐紮在中國的關東軍。現在的目標是「鯨吞」,要一舉吞併全中國。父親判斷從金山衛登陸的日本師團來自日本本土,受日本統帥部指揮,恐怕不只要打上海,還要打首都南京,逼中國投降。
父親半生都在軍隊,對國軍十分了解。他認為國軍的實力,短期內難以抵抗日軍攻勢,中國必須靠「全民抗戰」、「長期抗戰」,才能免於滅亡。他說,到了上海,他要去尋找到淪陷區組織「全民抗戰」、「長期抗戰」的機會。至今清晰地印在我記憶中的,就是父親加重語氣的「全民抗戰」、「長期抗戰」這兩點。
我們抵達上海時,日軍已經控制著英、法租界以外的地區。父親在法租界法國公園(現在稱「復興公園」)附近的呂班路(現在稱「重慶南路」)萬宜坊租到一處住房,安頓好家,他就離開我們去尋找抗戰之路了。
我家附近有一所「曉星小學」,母親陪我去申請入學。這所天主教學校的主事者,是穿著黑色長袍的「嬤嬤」(天主教神甫一級的女性神職人員),是一所女校,但一、二年級也收男生。我離開家鄉的學校時還是秋天,已經讀完一年級,開始讀二年級上學期。現在已經是春天,進入一個學年的下學期了。
嬤嬤問我:你想重讀一年級下學期呢?還是跳到二年級下學期?
我回答:二年級。
嬤嬤看了看我,沒說什麼就同意了。
這年(一九三八年)秋天,我要上三年級了,進了另一所「海星小學」,也是天主教小學,主持者和教師都是天主教徒,但沒有神職人員。學生中絕大多數也是天主教徒,我這一班二十多個同學,只有三個不是教徒,上課之前,都要集體朗誦一段歌頌「聖母瑪麗亞」的《聖經》。
我也有一本《聖經》,常隨同學一起上教堂,畫十字,聽神甫傳道,做禮拜;但沒有受洗,做禮拜時不「領聖體」(神甫把代表耶穌聖體的一片含葡萄酒的麵製薄片放入你口中)。
有人問過,我自己也想過,我上過曉星、海星、震旦大學附中,都是天主教學校,後來到北京上基督教學校(燕京大學),在震旦時還與一位法國神甫交了朋友,為什麼始終沒有信教?
我總會想起那最早的記憶,正午黑影和二姊之死。那似乎是命運對我幼小心靈的第一次襲擊,我失去了二姊,也失去了童年的幸福和記憶;卻同時在心中激起了一種對不可逃避的命運的反抗意志。
這種反抗意志開始是模糊的、暗淡的;隨著歲月的流逝和一次次命運的襲擊,這種反抗意志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更加清晰起來。然而,在我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朋友們身上,我看到真誠,看到善良,看到信仰和對命運的順從。我尊敬他們的宗教信仰,但保留我對命運的反抗。
父親之死
父親在上海,找到保定軍校老同學蔡劍夫,一同前往當時設在宜興張渚的江蘇省政府江南行署。行署委派父親出任江蘇省松江縣長。那時松江縣已被日軍攻佔,父親當的是「地下縣長」,也正好符合父親在敵佔區打開「全面抗戰」、「長期抗戰」局面的心願。
因為父親在敵佔區抗日,我們全家都改了姓名。我改名「李銘」,大姊改名「李鎮國」。我的兩個妹妹阮(李)澄和阮(李)錚,不久也隨外祖父母一起來到上海。同來的還有我的一位守寡的大姨母顧寶珪,和她的女兒阮慧良。大姨母是母親的姊姊,嫁給了父親的弟弟阮綿宗,她是個善良、勤勞的傳統女性,不幸在生下女兒後丈夫就去世了。
父親每隔半年左右,總要回上海一次,在家小住幾天。每次回家,都會帶一大包蘇州「采芝齋」的食品,像山楂糕、松子糖之類,分給孩子們吃,說是爸爸從蘇州帶來的。那是我們一年中最高興的日子,遠遠勝過過年。
後來母親告訴我,父親在鄉下打游擊,一次得了痢疾,連藥都買不到,秘密託人來上海買。這些好吃的東西,都是父親到上海後,在南京路那家「采芝齋」買來的。
母親還說,當時國民黨委任在敵佔區工作的官員,大多不下去組織民眾抗日,拿了抗日經費,住在上海租界裡當「寓公」。父親的「上級」,一個叫「平主任」的,父親每次穿過日軍封鎖線到上海,就為向他報告,請領軍費;有一回他還推說軍費發不出了。母親當時在中學當語文教員,所得薪水只敷家用;父親只得讓母親變賣結婚時的首飾,帶下鄉以應急需。
父親在敵佔區堅持抗日的頭兩年,雖然環境艱苦,但心境不錯,與當地民眾和青年戰士在一起,相處融洽,大家對「最後勝利」滿懷信心。那時父親不過四十多歲,大家卻都稱他「一心抗日的阮老」。父親每次回家,母親擔心他的安危,他總說,周圍戰友、同事、老百姓都對他關心,這是最大的安全。
然而有一回,父親剛離開家,當天晚上就有個法國巡捕帶著幾個中國人來敲門,說是要「抓拿阮毅然」。母親說:「我們家沒有這個人,你們弄錯了。」來人不理會,到處搜查,翻箱倒櫃,最後在二樓臥室五斗櫃的抽屜裡抄到一張藥方,上面寫著「阮先生」。
來人說:「我們就是抓這個『阮先生』!」
正在這時,大姨的女兒阮慧良站出來說:「『阮先生』是我,我在樂園中學附小教書,都叫我『阮先生』,這是我生病時醫生開的藥方!」
幾個中國人面面相覷,法國巡捕一揮手,都走了出去。
這場虛驚過後不久,一天下午,母親從中學教課回家,途中突然被幾名壯漢截住,叫她跟著走。母親發現他們是在把她帶往法租界的南部邊緣,朝「南市」方向走。當走到行人較多的一個街口,母親舉起雙臂高喊:「綁票!綁票!救人哪!」一名法國巡捕和人群過來時,這幾名「綁匪」放開母親,飛快消失了。
母親回家後分析,這次「綁票」很可能與上回「抄家」同一背景。他們上回大概是製造藉口欺騙法國巡捕房幫著來抓父親,這回法國巡捕房不再相信他們,才使出這一手,企圖把母親引出法租界控制起來,再設法找到父親。
他們是誰?
走出法租界,「南市」就是日本佔領區,是日本人要對父親下手了嗎?
母親覺得,萬宜坊不能再住下去了。日本人雖然沒有進法租界,但當時歐洲戰爭已經開始,日本與德、義勾結,希特勒正在進攻法國。日本人要下手,會繼續逼法租界當局「合作」的。
母親決定搬家。那時除了父親,家中有外祖父母、大姨、表姊、表姊夫和他們出生不久的第一個女兒;還有母親、姊姊和我、兩個妹妹,以及母親來上海後出生的小弟阮(李)鐮,共十二人。
母親說,她帶姊姊、我、小弟四人另覓住處。其他人應該不會有危險,暫時不動。母親在金神父路(現在稱瑞金二路)金谷租到新住處,帶我和姊、弟搬了過去。
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是一九四○年秋天。父親那次回來,是上級要他接任吳縣縣長。吳縣也是被日軍佔領的淪陷區,原來的吳縣縣長沈靖華,一直躲在上海當寓公,根本不到吳縣去,也沒有建立抗日武裝。父親在松江建立的抗日游擊武裝,這時已經初具規模,游擊活動擴展到吳縣境內的甪直、車坊一帶。上級可能是考慮到這種實際狀況,才要父親去接任吳縣縣長。
但父親認為,抗日需要各種力量的團結,才能孤立和打擊敵人,保護和發展自己。而吳縣周圍各種勢力錯綜複雜,互相牽制摩擦,加以大形勢的變化,前景恐難樂觀,他只能勉力而為。父親離家時,顯得心情沉重。
原來歐洲和中國戰場的「大形勢」,在一九四○年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六月二十二日,法國貝當政府向希特勒投降;九月,德、義、日三國在柏林簽訂《三國軍事同盟條約》。在中國,投降日本的汪精衛「國民政府」,於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成立,汪精衛和日本「特命全權大使」阿部信行簽訂《中日關係基本條約》,組織起一支「反共和平救國軍」投入淪陷區戰場,協助日軍掃蕩抗日武裝力量。汪精衛軍隊的旗幟,是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上面加一根黃色長條,上面寫上「反共和平救國」幾個字。
父親出發就任吳縣縣長時,恐怕心中已有疑慮,除了面對日本侵略軍和汪精衛「反共和平救國軍」的挑戰之外,難免還有自己營壘內部的背後殺手。父親的抗日武裝,隸屬於顧祝同的國軍第三戰區。國民黨在敵佔區還有一支武裝力量「忠義救國軍」,成立於一九三八年,當時指揮部在武漢,總指揮是戴笠,抗戰初期(一九三八~一九三九)也曾參與同日本侵略軍作戰;只有一部份投降日軍,後來變成汪精衛的「反共和平救國軍」。一九四○年春,「忠義救國軍」經過改組,指揮部由武漢轉到浙江孝豐,總指揮由阮清源(原名袁亞承)「代理」。阮清源還兼任淞滬行動總隊的總隊長。阮清源的「忠義救國軍」,名義上也受顧祝同的第三戰區「節制」,實際上是由軍統特務系統直接控制。
一九四○年冬,父親的抗日武裝在吳縣開始與汪精衛的「反共和平救國軍」作戰時,阮清源「忠義救國軍淞滬行動總隊」也進入了吳縣地區。
一九四一年初,吳縣有人來上海向母親報訊:「阮縣長」被「綁架」了。據說是去年(一九四○年)歲末一個寒冷的夜晚,一群蒙面人把阮縣長從住所綁走。母親追問具體情節時,來人表示一概不知。
誰「綁架」了父親?
日本人嗎?汪精衛嗎?如果是正面的敵人,為什麼要蒙面,要綁架?
父親生死不明,也不知落在誰手中?母親總要追究個水落石出。於是多方設法,在親友中,找到一位「品阿姊」,她嫁給一位文人丁丁,曾經編過一本《革命文學論》,當時算是進步青年,此時在汪精衛政府做事,願意幫忙。他查遍日本和汪精衛政府監獄,抓到的抗日份子中沒有父親。
此案一直到一九五一年,有位素不相識的鄭巴奮,從上海寫信告訴在新華社工作的姊姊阮寧:阮毅然在蘇州鄉下組織抗日力量時,被「忠義救國軍」秘密殺害,兇手軍統特務夏旦初已被逮捕,指使夏旦初殺人的元兇袁亞承(阮清源)逃往台灣。鄭巴奮請姊姊也去參加,因為特務夏旦初還曾殺害許多共產黨人員,上海要開公審大會。
姊姊因為工作任務重,走不開,又無路費,沒有去成。(當時實行供給制)父親究竟何時、何地、如何被殺害?屍骨何在?至今仍然是謎。
後來在上海工作的妹妹顧群(即阮錚,一九四九年參加西南工作團時改名),曾多方設法調查,找了許多當地人,都只能證實父親在「率領游擊武裝抗日時,被忠義救國軍阮清源(袁亞承)殺害」。也有人「聽說」,「忠義救國軍」殺害父親後,用船載到「太湖」,沉屍湖中。但只是傳聞,不知真假。
一九九七年我來台灣,意外遇到一位親戚阮鎮邦,他是我父親的弟弟阮續文之子。他告訴我阮清源還活著,而且他退休前還在阮清源手下工作。我拜託他向阮清源了解父親的事。我說,我不是要算賬、要報仇,只是想知道實情。幾天後阮鎮邦約我同他一起與一位老人見面,但不是阮清源本人。一見就知此人是來撒謊的,居然說:「阮毅然不是忠救軍殺的,是土共殺的!」我問他:「哪裡的土共,怎麼殺的?」他什麼也說不出。
父親之死,將永遠是不解之謎了嗎?
我想,「二二八」國民黨殺了那麼多台灣精英,殺人兇手彭孟緝,不是也同阮清源一樣無動於衷,拒絕說出真情嗎?殺人者的「良知」是不可期待的。
母親之死
父親遭「綁架」時,我已經九歲,上小學五年級。每天放學回家,做完功課,睡覺之前,母親總要選一篇古文同我一起讀。至今深深留在我記憶中的,是讀歐陽修的〈瀧岡阡表〉。母親說,這篇文章,是歐陽修在他父親去世六十年後寫的碑文;「瀧岡」是地名,在江西,是歐陽修父親陵墓的所在地,「阡表」是立於墳前的碑文,亦稱墓誌銘。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母親讀的這一段:
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這是碑文中歐陽修引用他母親的話。歐陽修四歲喪父,是從母親口中了解他父親的。
母親讀這篇文章時,在我幼稚的心中有一種沉重的感覺。母親似乎急切地要告訴我一些重要的東西,而又怕我不能理解。母親自己的心情,當時也處於矛盾之中。她似乎認為父親已經被害,似乎又不願相信,多次想親自去第三戰區司令部查個清楚,又怕回不來,丟下這些孩子和老人(外祖父母)怎麼辦?
這篇文章消磨了母親和我的三、四個夜晚。母親藉著向我傾訴她心中的父親,急切地希望我從她口中留下父親的形象。
母親說,「廉而好施與」,也是父親的為官之道。父親從軍,隨孫中山參加國民革命,投身抗日游擊武裝,都懷抱犧牲精神。他不能容忍官場的腐敗。譬如送禮,父親認為無論大小,不能送也不能接受,因為小缺口一開,就會變大,到不可收拾。父親當上海閘北區警察局長時,因為警民關係好,到中秋節,一些老百姓送來小盒月餅(一盒僅兩個)。父親讓退回。警察說:「這可不是賄賂,老百姓一番心意,退回去不好吧?」父親讓了步說:「那你們分給大家吃了吧,以後要更好替老百姓辦事。」父親自己一個也不拿,而是到永安公司買月餅給家人吃。
母親還說起姊姊出生時何應欽送的那個存摺。何應欽知道父親的怪脾氣,官場的禮不收,朋友的也不收;他對父親說:「我不是送給你阮毅然,我是給二十年後一個獨立公民為國家受高等教育。」
讀到「求其生」與「求其死」時,母親說,父親在戎馬生涯中,遇到的生死抉擇比歐陽修父親的司法工作更困難。父親常說,戰爭中消滅敵人不難,難的是在消滅敵人的同時保存自己的部隊和保護老百姓。戰爭難免付出犧牲的代價,但如何付出最小犧牲獲勝,就取決於指揮者的智慧和良知了。父親對「不惜一切犧牲爭取最後勝利」那類口號深不以為然,他說那不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嗎?
母親說,父親最感痛惜的,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失陷後,統帥部為阻擋日軍,竟下令於六月九日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百姓事先毫無所知。結果河南、江蘇、安徽三省五萬多平方公里的家園化為汪洋,淹死百姓數十萬人。日軍呢?避開洪水,另擇長江水路進軍,十月就佔領了武漢。父親認為戰爭中置百姓安危於不顧,與法西斯有何區別?老百姓為什麼要支持我們?
母親還說,父親去吳縣時,曾對「忠義救國軍」有所顧慮,那支武裝成份複雜,有幫派份子,有軍統特務,有散兵游勇,也有投身抗日的青年;一九四○年春整編後,強化了特務訓練,有法西斯化傾向,目標已從抗日轉到「清除異己」,常把不屬於他們控制的抗日武裝誣為「不忠份子」。但父親表示會去做團結工作,爭取一致抗日。父親認為以自己在國軍中的輩份和經歷,該不至於被列為「不忠份子」吧?
這幾個夜晚母親的話,成了我一生永不磨滅的記憶。平常和母親在一起,她從來不提她與父親之間的談話,此時卻如潮水般傾瀉而出。雖是由一篇古文引起,又讓我隱約感到似乎是母親在準備某種行動之前對我的囑託。
我後來知道,這段時間,母親一直在設法找到江南行署和第三戰區司令部的線索,她要親自前往,去弄清楚父親被「綁架」之事。
有一天,母親從學校回來比平時晚,顯得有點興奮。母親說,在路過一家蠟燭行(出售祭祀用香燭一類物品的商店)時,裡面出來一位生人向她打招呼,請她進去說幾句話。進去之後,知道這蠟燭行是國民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那位生人(母親說出姓名,我忘記了)說,他知道「阮夫人」,要告訴她阮毅然先生健在,「他是我黨忠實同志嘛!」還說母親可以去「那邊」看父親。
聽到父親活著的訊息,母親當然喜出望外,同時又有疑慮:是真的嗎?還是一個引誘母親跳進去的陷阱?
母親決定冒險前去。她又去了幾回蠟燭行,確定從上海去安徽廣德,到那裡會有人同母親接頭,帶她到父親那邊。
動身的時候到了。母親讓我和姊姊送她到我家附近的電車站,她一個人搭電車去火車站。快上車時,母親突然從衣服口袋掏出一串鑰匙,遞給我說:「差點忘了走時把鑰匙留下。」
我接過鑰匙,望著母親的眼神,似乎看不到她將見到父親的期待和喜悅,我看到的,不知是一種前途莫測的迷惘,還是走向絕望的悲苦……
電車來了,母親轉身上車,我強忍住幾乎流下的眼淚,在這一瞬間,結束了我的童年。
接著是漫長的等待。
母親從安徽廣德來過一信,在旅店寫的,告訴我們已經抵達,還找到一位過去的同學。她正在等候同她接頭的人。
又過了一段時間,接到母親那位同學的來信,說她得到母親在廣德旅店「自縊身亡」的消息,趕過去探望時,旅店說已經埋葬,還拒絕告知埋在何處?母親那位同學說她無法相信,母親見她時,還說快見到父親了,千里迢迢而來,怎能還沒有見到親人就自殺了呢?
當然不能。即使母親得到父親確鑿的死訊,也絕不會拋棄父親和她在上海的五個孩子。
母親死在父親被害的三年之後,表明自己營壘中的殺人者,往往比正面之敵更卑鄙、更殘忍。這三年中,他們對母親用盡「綁架」等卑劣手段未能得逞,終於以「父親健在」、「是我黨忠實同志」的謊言,誘騙母親墜入死亡的陷阱。
十年後,已是中央歌舞團舞蹈演員的妹妹阮澄到安徽演出,她找到母親住過的那家廣德旅館,察訪母親遇害之事。旅店的老店員記得曾有旅客在旅店死亡,不知自殺還是他殺,當時有軍人處置一切,不讓店方人員插手,也不知死者葬在哪裡。
妹妹僅從當地人士口中得悉,當時廣德是阮清源(袁亞承)的「忠義救國軍」出沒之地,這支特務武裝在這一地區殺了不少抗日人士。
母親之死,證實了與三年前父親的被殺害,出自同一隻手。
「一心抗日的阮老」,沒有死於日本侵略者之手,卻死於「我黨忠實同志」之手。抗戰八年,這樣的悲劇有多少?多少戰士、多少百姓是死於日本侵略者之手?又有多少戰士、多少百姓是死於「我黨忠實同志」之手?我們看不到一部真實的抗日戰爭史,殘殺抗日戰士的兇手逍遙法外,平白犧牲千萬無辜百姓的統帥在被歌頌,含冤而死的戰士和百姓,焉知魂歸何處?
我總在想,母親和我一起讀〈瀧岡阡表〉的那些夜晚,她究竟要告訴我什麼?在六十年後也寫一篇〈瀧岡阡表〉嗎?
父親死於一九四○年,終年四十八歲(一八九二~一九四○)。
母親死於一九四三年,終年四十二歲(一九○一~一九四三)。
距今已超過六十年,我找不到父母的墳墓,恐怕根本就沒有墳墓,到哪裡去立墓碑呢?
父母的命運告訴我,我生長在一個比歐陽修時代更黑暗的時代,遭遇的是外部侵略和內部「我黨忠實同志」雙重的奴役與殺戮。我能夠在這黑暗中生存下去嗎?
正午黑影
一個深秋的正午,太陽在晴空中照著我和二姊從學校回家,正當跨進家門的一剎那,一個巨大的黑影轟然掠過。抬頭一望,是一架日本軍機,座艙裡的日軍飛行員清晰可見。我們急忙躲進門內,二姊抱住我,脫口說出一句:「多可怕的日子,生不如死啊!」她是個七歲的孩子,我們一起上學,一起玩,從未聽她說過這樣的話。
那天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日軍在金山衛登陸的日子,死亡正在逼近我的家。當晚二姊大口吐血,請醫師來,診斷是敗血症,需要立刻輸血。但那時大家都在逃難,已無法搶救。我守在二姊身旁,驚恐地看著她一次接一次吐...
推薦序
人要多堅強,才能調理一次又一次的幻滅創傷?目前台灣最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的首推阮銘教授;而他又是對中共幻滅而導致創傷最嚴重的人。閱讀他頭兩集的自傳《尋找自由》,內心沈重有如鉛塊。他了解自由有如空氣,平時沒感覺,等沒有空氣才覺察空氣的珍貴。阮教授豐富又感人的自傳,應可敲醒很多台灣知識份子的腦袋。
蘋果日報總主筆 卜大中
人要多堅強,才能調理一次又一次的幻滅創傷?目前台灣最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的首推阮銘教授;而他又是對中共幻滅而導致創傷最嚴重的人。閱讀他頭兩集的自傳《尋找自由》,內心沈重有如鉛塊。他了解自由有如空氣,平時沒感覺,等沒有空氣才覺察空氣的珍貴。阮教授豐富又感人的自傳,應可敲醒很多台灣知識份子的腦袋。
蘋果日報總主筆 卜大中
作者序
前言
多年前,有人約我寫回憶錄。我說不,因為我這一生,只是俗話說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撞過了,再不去想它,我沒有過去的回憶。對未來,那不是我所能左右,也不去想,我沒有未來的夢。我好像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把石塊推上去,滾下來,再推上去,日復一日,做著同樣「荒謬」的事,有什麼可寫的呢?
今年(二○○九年)十月,有人重提寫回憶錄的事了。這回的理由是:台灣和中國,開始了一場稱作「迎接百年慶(一九一一~二○一一),詮釋大時代」的「造史」運動。陸續登場的「兩岸一甲子」、「古寧頭一甲子」、「大江大海1949」,「新加坡連(戰)胡(錦濤)會」,可以看出他們不但在偽造兩岸百年史,還在顛覆從反法西斯勝利到共產奴役制度瓦解的二十世紀世界史。
朋友問:你一生跨越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黨國統治時代,跨越大洋兩岸和海峽兩岸兩種社會,又經歷反法西斯戰爭和共產奴役制度瓦解的進程,難道不想留下一點真實的記錄,來揭穿歷史的偽造者嗎?
我想,國共兩黨偽造歷史,作為鞏固權力的手段,並不是新鮮事。但過去雙方,各造各的偽史,各騙各的大眾。這回的不同,是雙方合作「造史」,共同欺騙兩邊的大眾。
這一波聯合「造史」,從中共「建國一甲子」(一九四九~二○○九)開始。一部影片「建國大業」,明知是騙,多少名牌演員搶著去演,多少大牌政客爭著去看。蔣介石的孫子,國民黨副主席蔣(章)孝嚴,趕去看了兩遍,稱讚中共「客觀、進步」。可不是?過去扮演他爺爺的演員總是兇神惡煞,今天換上個面團團、慈眉笑眼的張國立,不就為騙你這句話嗎?
同時,龍應台出了本《大江大海1949》,封面題簽赫然是「一本書改變一個時代」。我不禁好奇,她要怎樣改變一個已經過去的時代呢?買來一看,原來她要「改變」的,是反法西斯勝利和共產主義瓦解那個「大時代」人們腦中的歷史觀與價值觀。書中描繪的,不只一九四九年的兩岸圖景,而是涵蓋二十世紀反法西斯戰爭到柏林圍牆倒塌的歷史畫卷。她的畫卷是巧妙地用一個個精選的個案剪接起來,為了傳達出一個訊號,就是那句誇張的質問:
——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
她剪接的戰爭,從亞洲到歐洲,從上海到南太平洋,從列寧格勒到長春;時間跨度涵蓋日本侵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共內戰。她選擇一系列的故事:圍困列寧格勒的德軍的家書,圍困長春的共軍的回憶,南太平洋戰俘營中被俘的反法西斯戰士的漫畫,接受日本軍官命令刺殺反法西斯戰俘的台灣兵的訪談,國共內戰時逃到澎湖的流亡師生被槍殺……等等,都是為了表明她那似乎是坐在雲端裡的說教:
——戰爭沒有「勝利者」,沒有「原因」,也沒有「罪犯」,對「戰爭罪犯」的審判是荒謬的。(「勝利者就沒有戰犯嗎?」)生在這個「大時代」裡,你只能忍受被「大時代鐵輪輾碎」的命運。
而槍殺流亡師生的「失敗者」卻是有「原因」的。書中寫了五千個山東流亡學生,逃避國共內戰渡海來台就學,由七位老師帶領到了澎湖,被「失敗者」(國民黨)強迫當兵。一個學生站出來,只講了半句話:「報告司令官我們有話要說……」,司令官李振清一個眼色,衛兵舉起刺刀刺去,學生的鮮血噴湧而出,倒斃地上。承諾這五千個孩子的父母帶他們來上學的七個老師,到處奔波、陳情,結果全被當作「匪諜」槍殺。對這樣的恐怖殺戮,龍應台寫道:
——關鍵的「原因」之一就是,共產黨的間諜系統深深滲透國軍最高、最機密的作戰決策,蔣介石痛定思痛之後,決定最後一個堡壘台灣的治理,防諜是第一優先。
有意思的是,這本「向失敗者致敬」、「以身為失敗者為榮」的書,卻獲得了「勝利者」的青睞。「兩岸一甲子」大會上,中國來的共產黨代表、「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原創者鄭必堅,在演說中特意引用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鄭必堅說:
——一九四九年台海分隔,給兩岸留下大江大海般深深歷史遺憾,如今在歷史新起點上,共同迎來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新階段。
台灣的媚共媒體自然不會放過機會,立刻發表社論〈柏林(圍)牆倒塌與台灣海峽開通〉:
——不須讚嘆柏林(圍)牆倒塌,台灣海峽開通是更重大歷史事件。共產主義瓦解,不是始自戈巴契夫新思維,而是始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不是始自柏林(圍)牆倒塌,而是始自蔣經國開通台灣海峽。中共改革開放是共產專政修正轉型的指標樣版,海峽兩岸互動為人類文明和平發展寫下新頁。共產專政轉型與戰爭陰影消除,柏林(圍)牆未給世人答案,是由台海兩岸作答,經二十年來互動激盪,如今在和平發展主旋律下,愈來愈理智,愈來愈昇華,世人應可期待一個典範式答案,將在不日繳券時呈現。
(編按:台灣的慣用語法是「柏林圍牆」。)
為什麼毛澤東的「兩個凡是」理論家鄭必堅,欣賞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呢?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只有顛覆反法西斯勝利和共產奴役制度瓦解的歷史,才能開闢中國新奴役制度「崛起」的「歷史新起點」;只有顛覆天安門屠殺和柏林圍牆倒塌的歷史,共產中國新奴役制度才能跨越台灣海峽,消滅台灣人民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創建的自由民主制度。
這場「造史」運動,今天才開始。依胡錦濤、馬英九的規劃,至少要連續兩年,「造」到二○一一「百年慶」。在中國,叫「辛亥革命」百年慶;在台灣,卻叫「中華民國」百年慶!你不覺得滑稽嗎?百年前,台灣在日本統治下,「辛亥革命」既未革到台灣,「中華民國」也不在台灣,哪來的「百年慶」?可見「百年慶」是假,藉此偽造台灣百年史,為共產中國企圖跨海吞併民主台灣「繳」出「一個典範式答案」是真。
朋友說:難道台灣無法阻止歷史的偽造者嗎?
我說很難。揭穿歷史的偽造不難,難在人們不願接受真相而願意受騙。巴特勒主教(Bishop Butler)說過:「事物和行為原來是什麼就是什麼,其後果將是什麼也就是什麼,我們為何竟想要受騙呢?」你知道想要受騙的人,是不願接受真相的。你若告訴他真相,他會視你為敵。在中國文革那個時候,說出真相,相信真相,都要死;要活的人,只有騙人或甘願受騙。
——但現在不是這樣的時候了,朋友說。
——所以更難。被迫騙人或受騙,形勢變了,還會說出真相或相信真相。自願騙人或受騙,視說出真相為敵的,你對他有什麼辦法?
——然而總還有不願騙人和受騙,願意了解歷史真相的人吧?即使現在沒有,下一代或者更遠的未來,會有人想探究這段已被重重謊言湮沒的歷史;他若能找到一點被謊言湮沒時代的真實記錄,該會帶給他如獲至寶的喜悅吧?
——對未來我不能確定,我不做未來的夢。
然而朋友很熱心,說要給我錄音,做口述歷史。我想大概是看我老了,不願讓我荒謬的一生,不留一點痕跡地化為煙塵吧?
回顧此生,一大半在中國(一九三一~一九八八),我曾在一篇短文裡概括為兩度「自由的追求與毀滅」:少年時在蔣介石法西斯奴役制度下,我追求過自由,後來得到的,是毛澤東共產奴役制度的統治;那是第一次「自由的追求與毀滅」。毛澤東去世時,我雖已四十五歲,卻重做起少年時的自由之夢,再次毀滅於鄧小平的「反自由化」大戰略。然後是一九八八年走出中國,見證了柏林圍牆倒塌和全球第三波自由民主化的高潮與退潮。在美國和台灣的這最後二十多年,又看到無論古老的自由國家,或是新生的自由國家,今天都還未能避免奴役制度國家的挑戰。我的經歷不過如此:
一九三七~一九八八 自由的追求與毀滅(中國)
一九八八~二○一○ 自由的見證與挑戰(美國、台灣)
但留下這點歷史的記錄,能讓謊言退卻嗎?我想起哈維爾(V. Havel)的話:「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他相信真話終將戰勝謊言,且在捷克得到歷史的驗證。然而需要等到更多的人支持說出真話,相信真話,不想受騙的那一天。
二○○九年十二月於台北紅樹林
前言
多年前,有人約我寫回憶錄。我說不,因為我這一生,只是俗話說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撞過了,再不去想它,我沒有過去的回憶。對未來,那不是我所能左右,也不去想,我沒有未來的夢。我好像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把石塊推上去,滾下來,再推上去,日復一日,做著同樣「荒謬」的事,有什麼可寫的呢?
今年(二○○九年)十月,有人重提寫回憶錄的事了。這回的理由是:台灣和中國,開始了一場稱作「迎接百年慶(一九一一~二○一一),詮釋大時代」的「造史」運動。陸續登場的「兩岸一甲子」、「古寧頭一甲子」、「大江大海...
目錄
(下冊)
PART 3 毛帝國的終結(1966~1976)
文革之初(上)
文革之初(下)
三國演義(上)
三國演義(中)
三國演義(下)
新星殞落(上)
新星殞落(下)
全面奪權
砲打司令
軍事管制
賀蘭山下
旅途驛站
陶瓷菩薩
十月政變
PART 4 開放的新地獄(1976~1988)
富強胡同
理論漩渦
歷史轉折
分道揚鑣
訪美歸來
包圍戰略(上)
包圍戰略(下)
特區調查
黨校易幟
異化事件
自由之死
別了中國
(下冊)
PART 3 毛帝國的終結(1966~1976)
文革之初(上)
文革之初(下)
三國演義(上)
三國演義(中)
三國演義(下)
新星殞落(上)
新星殞落(下)
全面奪權
砲打司令
軍事管制
賀蘭山下
旅途驛站
陶瓷菩薩
十月政變
PART 4 開放的新地獄(1976~1988)
富強胡同
理論漩渦
歷史轉折
分道揚鑣
訪美歸來
包圍戰略(上)
包圍戰略(下)
特區調查
黨校易幟
異化事件
自由之死
別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