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本重要的新書中,傑索普以一個新穎而激進的觀點來詮釋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未來可能的發展。他所著重的是,自一九五○年代以來,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社經政策不斷變遷的形式、功能、層級與效力。
戰後在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中已發展成熟的凱因斯式福利國家,長久以來都被認為正處在某種危機當中。技術變遷、全球化、經濟政治危機產生了緊張,且新的社會政治運動也具有不穩定因子。傑索普檢視了關於大西洋式福特主義之興起、鞏固及危機的這些因素,並且問一個問題:目前正在成形中的資本主義國家新類型,是否提供了上述危機與不穩定的解決之道。他認為,在新的國家類型鞏固之前,仍有數個難題有待克服;特別是對於新國家類型的新自由主義形式,他保持著批判態度,並思考其他的替代選項。
本書橫跨數個學科,其寫作對象以社會學者、政治學者、制度經濟學者、地理學者及社會政策研究者為主。
作者簡介
Bob Jessop
英國蘭開斯特大學(Lancaster University)社會學系教授
譯者簡介
梁書寧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經濟學系雙修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譯有「國際關係的基礎」(合譯)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思索資本主義國家的未來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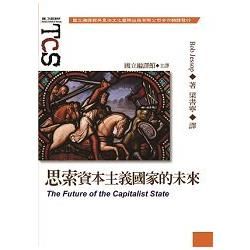 |
思索資本主義國家的未來 作者:Jessop / 譯者:梁書寧 出版社: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2-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30 |
二手中文書 |
$ 405 |
財經企管 |
$ 427 |
中文書 |
$ 428 |
經濟學 |
$ 428 |
社會 |
$ 428 |
Others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內容簡介
目錄
縮寫對照
緒論
第一章 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類型
第二章 凱因斯式福利國家
第三章 熊彼得式競爭型國家
第四章 社會再生產與工作福利國家
第五章 國家層級重整的政治經濟分析
第六章 從混合經濟到後設治理
第七章 邁向熊彼得式工作福利後國家體制
參考書目
索引
序
譯者導讀
現代國家與政府制度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的影響力不言而喻。但我們不應將國家視為一種外在於經濟體或公民社會的一個自主政治主體;相反地,國家應當是緊密鑲嵌在更廣大的社會形構。緣此,我們不但必須研究國家,更要「將國家放到學術研究的適當位置」(putting states in its place)?。
然而,國家(state)概念及定義是如此多元分歧且含混不定,以致於戰後美國社會科學界否定並遺棄國家概念,轉而研究政府、政治系統與政治行為(Mitchell, 1991: 77; Easton, 1981: 321)。由於多元主義(pluralism)與政治系統理論(political system theory)當道,國家角色被化約為眾多利益團體角逐影響力的場域,或被視為黑盒子(black box)。直到一九八○年代出現新國家中心論(neo-statism),學界重新認知到國家的重要性,而採取國家中心論的研究途徑,並將國家視為自變項。上述不重視國家的態勢才被扭轉過來,但往往被批評矯枉過正,過份強調國家角色,此種將國家視為自變項的方法,可能使國家在學術研究上脫離於廣泛社會整體之外,本書即強烈批評這類的研究途徑。
反觀歐洲,探究國家的傳統未曾稍歇。戰後更隨著凱因斯主義的盛行,國家角色不斷擴大等現象的刺激,各方重燃國家研究的興趣。其中,馬克思主義可謂源遠流長的學術傳統。馬克思與恩格斯、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西方馬克思主義等,皆對國家的批判分析有重大貢獻。然而,這樣一個豐富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卻也意味馬克思主義陣營裡對國家本質沒有一致的看法?。
一、國家理論與國家自主性
國家理論關心國家自主性、國家角色、國家與社會關係、政治與經濟關係(如經濟決定論、化約論)等議題,不同取徑圍繞這些議題相互爭辯。當然,這些問題顯是相連的,國家自主性的問題不可能與國家社會關係分離,也不能不釐清對於政治與經濟關係的看法。然而,許多文獻從此角度切入檢討,我也就不免俗地從自主性角度切入。
如果以國家自主性為分類標準,則各類國家理論大致可以放在一道以「絕對自主性」及「完全無自主性、無自身意志」為兩端的光譜上來觀察。上述一九八○年代興起的新國家中心論?便是站在絕對自主性的一端;該途徑有幾個關於國家的主張:(1)國家機關有自身意志與利益、有自我決定力量、有自身運作邏輯與生命;(2)可以將國家視為因果關係的自變項;(3)國家與社會之間互不相屬(mutually exclusive)、且它們的界線清晰可辨;也因此主張:(4)我們可以將國家與社會分開研究。但這個取徑常被批評只片面強調國家的決定與自主力量,並低估國家面臨的限制。此外,在統合主義或政策網絡這類難以純然歸類為國家或社會的案例中,更是難以提供令人滿意的解釋(Jessop, 2001a: 4-6; 1990b: 50-52)。
至於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有些主張國家無自主性、無自身意志,有些則主張相對自主性。前者通常稱為工具論(instrumentalism),這個途徑通常將國家視為一種可被階級操縱與奪取的工具,馬克思與列寧的宣傳性質作品中也曾出現,更晚近的代表人物為米利班(Miliband)。米利班認為由於國家被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階級支配,因此國家是資產階級支配社會其他階級的工具,且負責促進資本階級利益(Hay, 2006: 71-72)。由於米利班將研究焦點置於控制國家的菁英與人之間的關係,並將國家角色化約為控制國家者的行為,因而是著重行動者(agent)及意志的取徑(Hay, 2006: 72-73),因此儘管批判多元主義論點卻難以超越多元主義架構(Gold et al., 1975: 34);此外,既然以經驗主義及個案方式做研究,得出的結論當然能以其他例子來否證(Barrow, 1993: 49)。
主張國家有相對自主性者被稱為結構論(structuralist)?,最具代表性者便是普蘭查斯(Poulantzas)。普蘭查斯早期的國家理論著作認為行動者為客觀結構的承載者(所以在結構框架中,行動者能發揮的空間不大),國家便是這類結構,其形式與功能很大程度決定於客觀社會生產關係與資本主義社會功能需求,而非由身處國家職位的人或資本階級決定(何況資本階級或特殊資本之間是否有意識地團結,根本是個問題);他的分析起點在於社會的階級結構(Golden et al., 1975: 36),以此論證國家為資本主義國家。例如在資本家並未直接掌握政府職位的情形下,國家仍然促進生產,因為國家在結構上根本地不利於非資本階級,從來不是中立的工具(Barrow, 1993: 69)。此外,他認為在階級對立的社會裡國家有維持社會凝聚,進而維持正當性,從而須調解階級矛盾並表現中立;另外,國家為了有利於一般資本,須採取行動對抗特殊資本,因此,國家便需要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自主性為相對的?(Block, 1977: 34; Golden et al., 1975: 38)。
這些是較為常見的理論立場,然而,作者傑索普的看法為何?大體而言,傑索普認為國家是否具有自主性是有待經驗探究的「結果」或「待解釋事物」(explicandum),而不是一種理論主張(Jessop, 1982: 227; Marsh, 2002: 162);而這涉及我們如何看待國家,上述的國家取徑可以再簡單分類為「實體」(entity)觀點(無論是工具或主體)與「社會關係」觀點。前者顯然過於簡化,明顯粉飾國家機關內的諸多事實,並簡化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或者是兩者過度區隔),前述的新國家中心論與工具論都犯了這類毛病;至於「國家管理人行使權力」的觀點,在作者看來,同樣也是圖一時方便的說法?(本書第一章第參節第一小節)。如果我們以「社會關係」觀點界定國家,而不做任何本質主義式的界定(Kelly, 1999),則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在理論上便更為彈性開放、也能符合變遷不居的現實。這是普蘭查斯晚期採取的觀點,更重要的是,這也是本書作者傑索普採用的觀點。
將國家視為一種社會關係,這意味國家權力反映出各股社會力量之間的對比(balance of social forces);對普蘭查斯而言,國家之所以是資本主義國家及一般資本長期利益的護衛者,是因為它反映過去鬥爭的結果,並且也限制各股意欲在國家平台上追求利益的社會力量的能力,此謂「結構性選擇」(structural selectivity) (Marsh, 2002: 161)。然而,儘管他嘗試跳脫經濟決定論,但普蘭查斯仍然保留有「經濟關係最終有決定性」的基調,而「最終」究竟是何時、會不會到來,卻是無法驗證的;此外,普蘭查斯仍特別偏重階級關係、結構層面與物質層面等(Marsh, 2002: 161)。
總之,傳統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仍然多半受到經濟決定論的影響,若非服務於階級利益、否則便是服務於資本利益。
二、傑索普的突破與其他理論淵源
儘管普蘭查斯未能完全跳脫上述諸多批判、而其結構論也被稱為「思慮縝密」的工具論翻版,但他晚期將國家視為「社會關係」的作法已為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開了一扇窗;傑索普承繼此觀點,但試圖針對上述批評加以改進。
傑索普採取「策略–關係」途徑,發展出「策略性選擇」(strategic selectivity)的概念,此概念意指「各股意圖藉由影響國家能力來追求其利益的政治力量的能力,它們受到國家差別性的影響」(本書第一章第參節第一小節)。國家形式或結構鑲嵌著社會力量間策略鬥爭的結果,是一個帶有選擇性的平台,較有利於某些策略而非其他策略,然而有別於結構性選擇的是,傑索普引進能動性(agency,此字或有人譯為「施為」)的概念,亦即行動者並非單純的結構承載者,在採取行動時可能考慮結構的策略脈絡,並規劃策略以克服不利行動者的限制,如此結構與能動性的關係變得較具辯證性(Marsh, 2002: 162)。儘管結構限制了行動者,但不決定最終結果,行動者有其自身理性計算而會改變結構脈絡(無論行動者有無意圖或改變有多細微)(Hay, 2006: 75-76; McAnulla, 2002: 281),總之,這樣的取徑開啟了策略反思以及策略學習的空間(Jessop, 2005: 48)。此外,此取徑也承認階級之外的其他不平等形式。如此便拒絕了經濟決定論或是任何單向的決定論,而較為支持多重複雜的決定論解釋,在理論上使國家與資本利益或階級利益間的必然關係鬆脫,儘管國家可能是資本主義國家、也可能服務於資本利益,但這樣的關係在理論層面為非決定性的、偶發性的(Kelly, 1999; Marsh, 2002: 162; Hay, 2006: 76),實際上,國家當然可能損害資本的利益。這需要輔以經驗層面之具體複雜的分析。至此可知,傑索普的途徑實際上為研究架構,不在自主性的問題上宣稱某種「確定」(guaranteed)的結果,因為這些皆取決於社會力量的對比。
回到國家自主性,就社會關係的觀點而言,國家的自主性與權力來自於特定政治結構與策略(但它們與國家之間互動、相互形塑),我們可將此種擺脫本質主義式解釋理解為抽象層次的說法。就具體層次而言,現代西方國家有沒有自主性?傑索普認為有,現代西方國家有一個重要特徵在於政治與經濟的制度分立(例如法律保護財產權並限縮政府介入的權力),分立創造出政治、經濟各自的獨立領域;在此,傑索普借用了盧曼(Luhmann)的自創生(autopoietic)理論,在此理論中,政治、經濟、法律、科學等都是其中一種自我組織系統,各有其運作準則、組織原則、運作自主性,這些系統完全只關注維持自身持續再生產的條件,在具體層次上便確立了國家或政治的自主性(Smith, 2000: 204; Kelly, 1999);然而,這些系統之間在物質層面是互賴的,如此一來,各系統的運作自主性便多少都受到互賴的影響(Jessop, 2001b: 217)。互賴的性質遲早都必定整合到各系統的運作中,各系統隨著時間而變得結構耦合並共同演化。這也就意味經濟、政治等系統的動力與發展方向,皆會受到物質互賴性質的形塑,這樣的情形便潛藏著矛盾,以及不同邏輯衝突的空間。同樣地,從自創生理論觀點來看,政治結果便不保證一定服務於資本家的利益,與他否定經濟決定論的立場不謀而合。
在理論層次否定經濟決定論、或否定國家與資本或階級利益的必然關係,它們之間是否有偶然關係或是「傾向」性質的關係?傑索普認為否定經濟力量的最終決定角色未必要否定經濟的重要性,但傑索普改以生態優勢概念來處理,經濟與非經濟層面之間的關係就不是經濟決定論式的單向支配關係了;毋寧是它們之間會相互影響,但這樣的影響力顯然有大小之別;而這樣的關係會隨著時間而變、也是偶發的(本書第一章第貳節第二小節)。解決了經濟決定論問題,我們可以再追究市場與經濟何以傾向於具有生態優勢且影響力較大?傑索普認為資本主義具有某些特質使其傾向於具有生態優勢,進而支配社會(Jessop, 2001b: 219-220):例如市場是一種彈性的學習機制,而且資本主義發展出時空延伸與時空壓縮的能力,使其更易自我擴張等。此外,在馬克思主義觀點,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是否為自我調節的體系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傑索普在此引入調節學派取徑(regulation approach)的概念,亦即經濟的社會鑲嵌性及經濟層面以外的調節與規制,對經濟體制再生產而言,是有其必要的。就這樣的概念而言,經濟以外層面會發展出各種組織、制度來進行時空修補,以延後移置資本主義的矛盾與兩難困境,這些都有助於經濟的再生產(Jessop, 2001b: 216)。因此,國家理論與調節學派之間可以輕易結合,亦即國家在經濟調節中扮演著核心角色(Kelly, 1999)。
最後,在批判實存論的基礎上,傑索普援用批判論述分析,除了實存的物質基礎外,也承認論述與建構的中介作用;那麼這對於國家理論的啟發為何?傑索普認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界線並非如新國家中心論假定的如此理所當然,而是經常變動,且有想像及論述的建構成分(Jessop, 2001a: 12;參見本書第一章第參節第一小節),當前國家機關重整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由於重視論述的地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可跳脫唯物論的批評。
至此已相當扼要地描述作者的國家理論觀點,下文則略加勾勒本書的概要。
三、全球化時代的國家
處於全球化時代裡,談論國家角色的文獻在市面上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超全球主義論者宣稱民族國家終將終結,未來將出現全球公民社會與市場至上的局面;懷疑論者則宣稱全球化被誇大,反而認為現在全球的貿易來往密切程度還比一次大戰之前倒退,因此國家並未受到影響。此兩種最先出現而立場極端的論證已招致不少批評。此外,轉型論認為全球化是個過程而不是最終狀態,某些人則認為是全球化的「論述∕理念」扮演重要角色、所有的「打造競爭力、開放政策」其實是在回應全球化論述。事實上,作者在本書也處理到全球化時代的國家議題。
本書最主要的關注對象為戰後實行凱因斯福利主義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作者稱之為凱因斯式福利國民國家(Keynesian Welfare National State)〕,並討論這些國家歷經一九七○年代以來接踵而來的危機,以及隨後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挑戰後,產生怎樣的衝擊轉變、各國如何因應。作者分別從經濟政策、社會政策與福利、層級重整(rescaling)以及協調與治理模式的角度來說明這些轉變。
在作者的觀點裡,國家負有維持社會凝聚力的功能、也是最具有政治正當性的層級;這種功能與角色是否在全球化時代中削減或弱化了?全球化時代是否不需要這些國家功能?答案是否定的。作者認為儘管國民國家受到全球化影響,但國家並非萎縮消逝,而是重構。全球化影響到的是與「凱因斯式福利國家」相關的功能,而非所有的功能,特別是政治功能,例如,我們到現在還未曾見到有哪一個國際組織可以取代國民國家而具有決策正當性;此外,國家在新的趨勢中獲得新角色與任務及權力(例如決定何種權力要上交、下放、外移,層級間接合,爭取國際組織中的議題等),如此,作者主張其實國家重構的過程是國家性質與角色的轉變、而非消亡。但這樣的陳述也不表示國家沒有受到影響;我們最好是描述為國家的某些面向受到影響,特別是與凱因斯式國民國家相關的面向──然而它只是國家的其中一種類型而已,而不是全部(參見本書第五章第捌節)。整本書說明了這些轉變後,作者下結論,目前「熊彼得式工作福利後國家體制」正在取代「凱因斯式福利國民國家」。
這是我首次獨自翻譯整本書並為這本書撰寫導讀,過程十分艱鉅,因為這本書跨越領域甚廣(作者在書中說明本書是「打破學科領域的」)。翻譯完後,原先以為就此可以鬆了一口氣,心想只剩下校稿一事。但是,出版社希望寫一篇四頁類似「書鼻子:十分鐘掌握全書」的文章,由於初稿字數頗多,後來總編鼓勵我擴充成具學術規格的「譯者導讀」,再加上台大社研所博士班學長萬毓澤督促並指引我寫作方向,於是我尋找並閱讀相關文章,終於達成目標。我心血來潮,把寫好的導讀譯成英文寄給本書作者看,請作者評論,傑索普教授十分熱心地幫我修改部分用詞,又寄給兩篇他未發表過的文章要我補充導讀某些地方。我便依照他的意見修改後再寄給他,後來他又修改甚多,目前所見完稿便是依照他修改過的文章、以及萬毓澤學長的意見來修改我原先寫好的「譯者導讀」。
倘若這篇導讀有半分勾勒出本書作者在國家理論的位置,其實要歸功於萬毓澤學長與本書作者傑索普教授細心且熱心地教導、以及出版社的鼓勵;反之,倘若這篇導讀未能傳達出作者的學術地位,那要歸於我的資質愚魯。
譯者 梁書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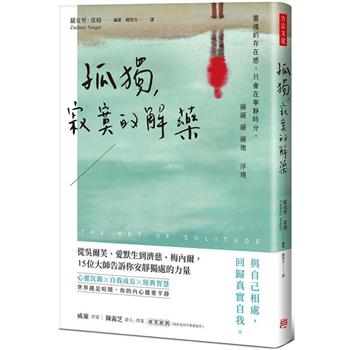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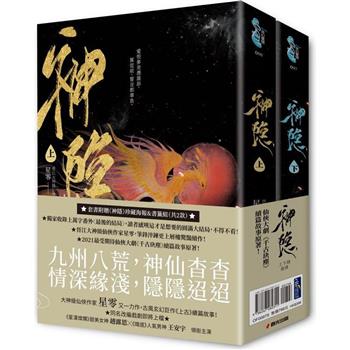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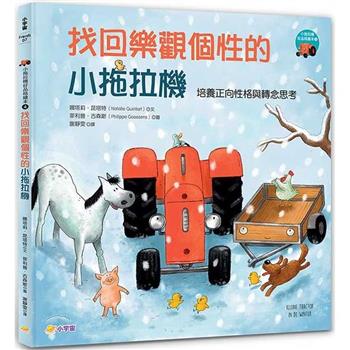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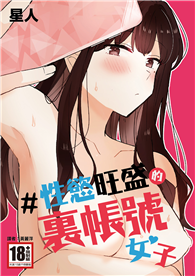

![圖解 適齡教養 ADHD、亞斯伯格、自閉症[暢銷修訂版] 圖解 適齡教養 ADHD、亞斯伯格、自閉症[暢銷修訂版]](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6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