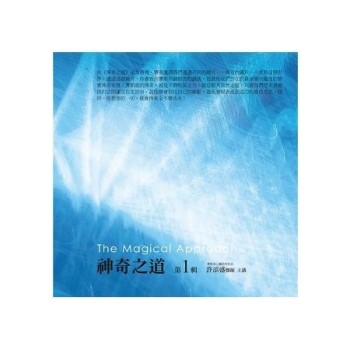自序-分享藝術的大美
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件藝術創作,而藝術家是比你我更深刻追索生命而痴迷一世的人,只因他們願意把青春、愛戀、哀傷、痛苦、孤獨、夢想與生死全部交給藝術,在作品上銘刻每個當下的生命印記。
立願要為台灣藝術家作傳是我不悔的承諾,寫出藝術家的創作生命,對我一直是個神祕的吸引力。這本書著重藝術家創作生命的探求,我希望能將知性的論述以感性的形式書寫。全書以藝術家面臨創作瓶頸時內心的掙扎與追尋的過程為經,以各個時期不同階段的作品為緯,祈能鋪陳出藝術家風格的誕生與蛻變的心境轉換。
我喜歡以生命學的角度看待藝術家,生命是個令人欣喜的奇蹟,人生也是一場生命的冒險,每位藝術家大都經歷過慘綠的歲月,也都曾在創作的路口茫茫然,然而生命中的種種磨鍊,都將化為參悟藝術的契機,他們是自己生命的領航者,也是自己生命的證道者,我只是嘗試去了解他們的道,並把路上的風風雨雨,娓娓道來而已。
品味藝術家的生命風景,也許時而令人眩暈,時而令人沈思或令人低吟,每位藝術家都是以青春之泉,引火玩命地奔赴永無終點的藝術祭壇,像是獻祭美神,毫無恐懼,他們的生命情操令人動容。
這本書所集結的藝術家包括第一位打入「馬格蘭攝影通訊社」,以影像隱藏文化滲透力與批判力,深富人道主義的台灣報導攝影家張乾琦;以英文書寫台灣第一個觀光標誌TAIWAN,解放書法,寫出當代經驗的徐永進;由慾望山水的情慾世界到欲仙欲死的仙境,以繪畫勘驗生死的于彭;以水墨、陶藝為人文關懷,別人做過的他不做,別人不敢的他敢,全方位開跑,時時備戰的袁金塔;既土又拙又有草根味,濃墨重彩的國家文藝獎得主鄭善禧;匯通中西文化,形塑神祕混沌的宇宙之愛的苦行僧趙春翔;用藝術照見生命行腳佛陀聖地,虔誠修道的奚淞;獨擅精密寫實捕捉南島之風,留下風土見證的黃銘昌;出沒夜店寫真,記錄百態人生的計程車司機周孟德;在城堡?打造藝術王國,以畫撥除迷亂生命的黃銘哲;行走非洲、大洋洲,以原始主義觀點血戰畢卡索的吳炫三;失聰卻以甘蔗板做版畫又以〈約翰走路〉焊鐵雕塑走入西方雕塑史的陳庭詩,以及開創阿美族雕刻,尋找原住民文化的當代意義,活出祖靈榮光的拉黑子等十三位藝術家。
就像張乾琦說的:「要玩,就要玩真的。」藝術是無止盡,全方位的競賽,與自己拼搏,也與歷史廝磨,每一出筆都是靈魂的錘鍊,迸放出藝術家的生命靈光。不玩真的,如何護持藝術的尊嚴?甘願苦行,選擇落籍藝術國度裡的藝術家,真如聖堂的修士或寺院修道的苦行僧,不為取悅他人,不為風潮寵幸,只是盡一個修道者的角色,競競業業地做自己,完成此生不杇的靈魂志業。
我喜歡了解藝術家的創作歷程,探索創作的奧祕,採集獨特的藝術故事,並加以想像,再繁殖成更豐沃的想像,讓思維在抒情感性與理性架構之間擺盪,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擔任學術編審的十二年,我最大的滿足是一年年地培養自己藝術鑑賞的能力,而離職後六年,我最大的幸福是一步步地建構自己的藝術寫作觀,一次次地向自己證明可以在書寫上有新的體會,新的發現,也把似曾相識的自己再次召喚出來,讓內在的能量,毫無掛罣地流動,讓今世的靈魂再次學習。
近兩年我接觸到新時代思潮,尤其是賽斯(Seth)思想,感謝簡湘庭老師,許添盛醫師的引導,使我對生命有一種新的認識,新的開啟,也明白我們的靈魂與宇宙是一個愛的無盡連結,相信我能創造自己的實相,我就是一個自由豐盛的光體。
這十三篇文章先後發表於《源》雜誌「藝術人生專欄」,也是我嘗試以身心靈的視角書寫藝術家的創作生命史。我以最欣喜的心情向各位推介,從我這第十五本新作裡,你可以知道現代藝術與你的生活有何關係,也可以大方地走入藝術家的創作世界,更可以品嘗藝術家不同階段藝術生命的轉折起伏,彷彿我是不在場,而藝術家正神靈活現地與你的生命共振。
願你與書中的十三位藝術家攜手遨遊在廣闊的天地裡,領略藝術是樁非量產的生命工程,從而相信生命是個無盡藏的寶藏,你也能勇於開創出個人全新的生命能量,做你自己。
我也期盼你能樂於親近現代藝術,其實現代藝術並不那麼難以被了解與欣賞,而一張作品也不是只有一種解讀的方法,你可以允許自己提出不同的觀感,因為多重意義本身就是一種藝術。當藝術家把他看事物的方法藏在畫中,讓我們在看了他的作品後,激起想像力,並對於我們自己及周圍各種各樣的事物與環境,產生新的觀看,新的思維。所以面對複雜善變的現代藝術,你永遠不要忘記時時保有一顆敏銳的心去感受它,用開放的胸襟去體認現代藝術所表現的自由與多樣,甚至與它互動,你將會發現現代藝術的奧祕,你也會開啟更豐富的生命視野,分享藝術的大美,也享用生命存在的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