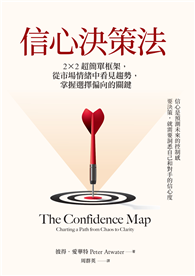美國文壇傳奇女作家奧茲2008年的最新短篇小說集,內容幻想五位美國作家生命中的最後一段時間,包括:愛倫坡、愛蜜莉‧狄更森、馬克吐溫、亨利‧詹姆斯、海明威。奧茲用豐富的想像力和有力的筆調,重新編織出這些文壇巨人的故事。僅管全是作者個人的奇想,但確比真實事件更深入挖掘這些著名作者的內心世界。運用每位作家特有的文字風格,歐茲創造出一個黑暗、生動、引人爭議的心理密語之作,讓讀者從一個全新而驚異的角度重新認識這些文壇名家。《狂野的夜!》是喬伊斯.卡洛.奧茲最具原創性,最能在讀者腦中縈繞不去的想像力之作!
<愛蜜麗.狄更森豪華複製人>:一對生活優渥、膝下無子的夫婦,一直希望生活中多個人陪伴。於是,在太太的慫恿下,夫婦兩人到了城裡的「真人機器人店」,打算買一個適合的機器人。再三考慮之後,他們選擇了一個安靜、不愛出門、小女孩似的女詩人──愛蜜莉‧迪更森。愛蜜莉機器人住進夫婦家之後,常常躲在屋子裡,不出一聲,慢慢地,她開始幫忙做家事,陪女主人喝下午茶,或像幽魂似地走來走去。有一天,女主人發現,愛蜜莉竟然偷偷在小紙片上寫詩……
<大師於聖巴特羅謬醫院>:七十歲的亨利‧詹姆斯拄著拐杖,來到聖巴索羅謬醫院,加入照顧大戰傷兵的志願者行列。他,這麼一位當時的文壇大師,在暴躁護士的催促下,走進最慘烈的六號病房──那裡擠滿了缺腿斷手的士兵,哀聲不斷,混雜著糞便與膿血的惡臭撲鼻而來。亨利的工作,是用言語為這些瀕死的年輕人帶來心理的安慰……尤其是其中一個,年輕孤獨令人垂憐的傷患,引出了老人近乎病態的愛戀……
<克萊門斯爺爺和天使魚>:馬克吐溫爺爺有個祕密的俱樂部,唯有善良可愛純潔的小女孩可以加入,她們的年齡介於十歲到十六歲之間,她們的識別徽章是馬克吐溫爺爺送的那個美麗的天使魚別針。其中最受爺爺愛戴的天使魚,是爺爺在簽書會的時候認識的,她讓爺爺想起不幸夭折的女兒,爺爺給了她祕密的名片、祕密的別針、然後兩人開始當起祕密的筆友……直到天使魚十六歲生日的那一天……
<燈塔>:日記開始於愛倫坡死後的那一天。他獨自一人,帶著條忠心獵犬,來到智利的一座荒島上擔任燈塔看守員──這是一位蕭博士為他做的安排。喪妻的愛倫坡打算在島上渡過孤獨的餘年,他享受著每天的閱讀與沉思,每天守著燈塔,不與任何人接觸……然而有一天,他發現蕭博士的文件,明白自己只是他的實驗品,要測試一個人在孤獨中會變成何等模樣。在一次脾氣暴發中愛倫坡親手打死了忠心的狗,由於食物缺乏他開始吃生食,他逐漸退化,最後甚至進入了兩棲類的世界……
<老爸在克川,一九六一年>:海明威拿著一把長獵槍對準自己的下巴,這次他一定不能失誤,一定要在屋裡那個女人──他第四個太太──阻止之前,扣下扳機。太多次了,每次都是警笛響起,救護車把他送進醫院,女人在旁邊哭喊,救救我們!酒精、寫不出文字的早晨、盛名的作家、女人的叨唸、醫院、電擊、鎖進櫃子裡的槍……這次他真的受夠了。
作者簡介:
喬伊斯‧卡洛‧奧茲 Joyce Carol Oates
論產量、論跨文類之廣、論勇於嘗試,美國小說家喬伊斯.卡洛.奧茲大概都稱得上是世界文壇之冠。至今她已出版了四十餘本長篇小說,更遑論短篇小說與詩歌的結集、文學論述與她主編的書刊文集加起來總共已突破百本。她曾獲美國國家書卷獎,二○○三年獲得「合眾國傑出文學貢獻獎」,並在二○○七年獲頒「芝加哥論壇報終生成就獎」,更被認為是可能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她的作品獲獎無數,包括《我們曾是馬文尼家》、《金髮》(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瀑布》(獲法國「費米納文學獎」)以及《掘墓者的女兒》。
譯者簡介:
李淑珺
台大外文系畢業,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英國劍橋大學,蘇格蘭聖安德魯大學進修,曾任新聞翻譯,於實踐大學教授翻譯課程,現為自由譯者,專職翻譯書籍,譯作包含心理學、文學、建築、藝術、歷史等範疇。
譯作累積達三十餘種,包括《巧奪天工》、《滅頂與生還》、《牛頓書信》、《波特貝羅女巫》、《神奇城堡》、《非零年代》、《躁鬱奇才》、《生命的哲思》、《解剖自殺心靈》等。
章節試閱
愛蜜麗•狄更森豪華複製人
好孤獨!他們怯怯地隔著餐桌對望,櫻桃木桌面上的燭火閃爍不定,如隱約憶起的夢。一個人像是剛剛才想到似的,說:「我們應該買一個豪華複製人,」而另一個立刻回答,「豪華複製人太貴了,而且你也聽過它撐不了一年。」
「才不會!除非──」
「我上禮拜才查過,比例是百分之三十。」
所以丈夫上網去查了。太太留意到這件事,覺得高興。
因為她心底一直在渴望,多一點生命力!多一點活力!
九年的婚姻。還是十九年?
到了某個時刻,你會突然醒悟:這就是人生給你的。比這更多,你也得不到了。而且這一切,你的人生至此得到的一切,還會被從你手中奪走。只要假以時日。
「一個文化人!可以提升我們的人。」
柯林先生是稅務律師,專長領域是公司法/跨州商務。柯林太太是柯林先生的妻子,在市郊的哥德綠坡社區素有「慷慨」、「活躍」、「熱心公益」的名聲。他們一起開車到二十哩外,如龐然大物的「新自由購物中心」,那裡有一間「豪華複製人」的專賣店。這間專賣店其實主要是提供目錄訂購,不會比網路方便太多,但是柯林夫婦很興奮可以看到以實體展示的豪華複製人樣品。
太太認出了佛洛依德,丈夫認出了全壘打王貝比魯斯、老羅斯福總統、梵谷。這些人像不能說是「栩栩如生」,因為他們都不超過一百五十公分高,五官也按比例縮小簡化,眼神順從而呆滯,原因是聯邦法律嚴格規定任何人造的複製人都不能「按照實際尺寸」,也不能包含「有機」的身體部分,即使有熱切的捐贈者想提供。展示的豪華複製人都處於睡眠模式,還沒被啟動,但是丈夫與太太卻在他們面前看得入神。太太帶著一絲戰慄低聲說:「佛洛依德!偉大的天才,但是有這樣一個人在家裡盯著你看,不會讓人覺得渾身不自在嗎……」丈夫則低聲說:「梵谷!──想想看,就在我們哥德綠坡社區的家裡!不過梵谷有『躁鬱症』,對吧,而且他不是自殺……」
在燈光明亮的店裡,到處是一對對夫妻在急切而低聲地商量。你可以看豪華複製人啟動時的影片,也可以翻閱厚重的目錄。銷售員隨侍在側,熱心提供協助。在供應十二歲以下兒童人物的「豪華複製寶貝」部門裡,討論尤其熱烈。這麼多偉大的運動員、偉大的軍事領袖、偉大的發明家、偉大的作曲家、音樂家、表演藝術家、世界領袖、畫家、作家和詩人,要怎麼選擇?還好,肖像權的限制讓廠商無法製造許多二十世紀知名人物的豪華複製人,大幅減少了可能的選擇(默片時代之後的電視明星和演藝圈人物寥寥可數)。太太告訴一個銷售員,「我想,我決定要一個詩人!你們有……」但是席薇亞•普拉絲的肖像權還不屬於公共財產,羅柏•佛洛斯特和迪倫•托馬斯也是。華德•惠特曼整個四月都有打折促銷,但是太太非常猶豫:「惠特曼!哇,想想看!但他不是……」(這位太太雖然絕對不是衛道人士,甚至不像她在哥德綠坡社區的鄰居,是有傳統中產階級道德觀的女人,但還是說不出同性戀這幾個字。)
丈夫在詢問畢卡索,但畢卡索還沒有上市。「那羅特克呢?」太太笑著對銷售員說:「不好意思,我先生自認是藝術行家。我相信『豪華複製人』公司應該根本沒有人聽過羅特克。」銷售員在電腦上查詢時,丈夫固執地說:「我們可以買小時候的羅特克。他們有『加速模式』,讓我們可以目睹一個開創性的藝術家的養成……」太太說:「可是這個羅特克不是很憂鬱嗎?他後來不是自殺了?」而丈夫不耐煩地說:「那席薇亞.普拉絲呢?她也自殺了啊。」太太說:「可是,我相信,她如果跟我們在一起,住在我們家,一定不會自殺。我們會給她全新的、良好的影響。」
銷售員回報沒有羅特克。「那你們有哈波嗎?『二十世紀美國畫家愛德華.哈波』?」但哈波的肖像權還受到保護。太太突然說:「愛蜜麗•狄更森!我要愛蜜麗•狄更森!」銷售員問名字怎麼拼,然後迅速地打進電腦裡。丈夫很吃驚看到太太這麼興奮,最近這幾年來,柯林太太已經鮮少這樣像個少女,這樣不設防地,在公共場合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紅著臉說:「我心底一直覺得自己是個詩人。小時候,我緬因州的露米絲奶奶給了我一本她的『詩集』。我們剛認識的時候,我給你看過我最早的時候寫的詩,其中一些……真可悲,現實生活讓我們越來越遠離……」丈夫安慰她:「那就愛蜜麗•狄更森吧!至少她會很安靜。詩也不會像六尺的畫布那麼佔空間,也不會有味道。而且據我所知,愛蜜麗•狄更森也沒有自殺吧。」太太喊道:「喔,愛蜜麗沒有自殺!而且事實上她經常在照顧生病的親人。她是家裡的天使,總是一身純白無瑕。她也可以照顧我們,萬一……」太太話只說到一半,不安地咯咯笑了兩聲。
銷售員唸出電腦螢幕上的字:「愛蜜麗.狄更森,一八三○至一八八六年,備受景仰的新英格蘭女詩人。柯林先生,柯林太太,你們運氣真好,這個『愛蜜麗』是限量版,就快絕版了,但到四月前還可以打八折買到。愛蜜麗.狄更森豪華複製人設定為從三十歲到五十五歲,這位詩人過世的年紀,所以顧客可以擁有她二十年,而且可以隨你們的意思加速,甚至可以倒轉,但是當然沒辦法倒到三十歲之前。限量供應到……」太太很快地說:「我們要這個!要她!麻煩你了。」太太與丈夫緊握著彼此的手。在那一刻,他們之間突然傳過一股包含著暖意、溫情,和孩子氣期盼的顫抖。彷彿出乎意料地,在即將跨進新生活的門檻前,他們又成了年輕的愛侶。
即使打折,「愛蜜麗.狄更森豪華複製人」的價格還是很可觀。但是柯林夫婦生活優渥,又沒有孩子,連寵物都沒有。「比起養一個孩子的花費,包括大學學費等,『愛蜜麗』的花費只是九牛一毛……」柯林太太興奮不已,根本連看也沒看,就在文字印得密密麻麻的好幾頁合約上簽了名。柯林先生的工作就是細讀這類文件,因此多花了一點時間。「愛蜜麗.狄更森豪華複製人」將在三十天內送達,保證期限半年。
這個銷售員用很真誠的態度提醒道:「柯林先生,柯林太太,相信你們都了解,你們買的豪華複製人跟原來的本人,並不是一模一樣。」
「當然!」柯林夫婦笑起來,表示他們沒這麼傻。
這位銷售員繼續說:「但是有些顧客,雖然已經聽過詳盡的解釋,卻還是很堅持期望看到真正的本人,並在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時要求退錢。」
柯林夫婦笑道:「我們不會的。我們沒那麼傻。」
「嚴格說來,豪華複製人事實上是由一個電腦程序驅動,製造得唯妙唯肖的人體模型。這個電腦程式是原始本人的精華篩選版本,就像是藉由豪華複製人公司的天才創意,抽取出他本人的精髓,或者──如果你相信這種想法的話──也可以說是靈魂,然後重新灌注在一個全新的環境裡。我想,你們應該看過報導,知道我們已經獲得令人興奮的突破,可以大幅延長複製人原本的壽命。例如針對英年早逝的本人,例如莫札特。我們可以給莫札特豪華複製人比原本長很多的壽命,讓他可以創造出更多,更多的作品。你們訂購的愛蜜麗.狄更森豪華複製人是模擬歷史上的『愛蜜麗.狄更森』,但是當然不像原來的本人那麼複雜。每個豪華複製人都各不相同,有時候差異相當可觀,而且也無法預料。但請千萬不要預期你們的豪華複製人會像是『真』的人,因為你們已經看過合約,一定知道他們並沒有配備消化系統,或是性器官,或血液,或是『一顆溫暖跳動的心』──不過不要失望!根據他們的程式設定,他們會對新環境有多少類似原始本人的反應,雖然是以比較簡化的方式。當然,不是所有豪華複製人都會適應得很好,也不是所有家庭都很適合他們。你們也知道,美國政府禁止豪華複製人出現在私人家戶領域之外,否則我們就會有拳王傑克•鄧普塞與傑克•鄧普塞對打的拳擊賽,或兩隊全都是全壘打王貝比魯斯的棒球賽了。男運動員是最暢銷的商品,但他們其實不適合一般家庭,因為根據法律規定,主人不可以讓他們到戶外運動。可是他們就跟大麥町、惠特比犬或獵犬一樣,都需要每天運動,而我不得不承認,這確實引起了一些問題。但你們選的詩人實在太理想了,因為『愛蜜麗•狄更森』似乎從來不出門!恭喜你們做了一個明智的選擇。」
柯林夫婦在興奮昏眩的狀態中,並沒有完全聽清楚這個銷售員說的一切,但此刻他們跟他握了手,謝謝他,準備離開。他們決定了這麼重大的事,而且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在開回哥德綠坡社區的車上,太太竟快樂得突然哭了起來。雙手緊抓著方向盤的丈夫,兩眼直直望向前方,只希望不去想我們做了什麼?我們做了什麼?
為了迎接貴客到來,太太買了《愛蜜麗•狄更森詩作全集》,好幾本傳記,還有一本巨大的攝影集,《安賀斯特的狄更森家族》。但是她大多數時候都坐立不安,無法安靜地坐下來看書,她尤其難以看懂狄更森雜亂糾結,謎語一般的小詩。她於是埋頭於準備豪華複製人說明書上規定的「恆溫恆溼,適當的環境」,以預防豪華複製人在過度的溼氣/乾燥下,產生「機械退化」。她還在古董店裡買到許多類似這個詩人臥室裡的、當時風格的家具家飾:一張一八五○年代,桃花心木製,前後有高起床板的「雪橇」床,窄到像是孩子睡的,加上一床象牙色的編織被子,和一個花色相同的鵝毛枕頭;用看起來磨得發亮的結實楓木做的四抽衣櫃;一張小寫字檯,和其他相稱的桌子,太太並在桌上放了蠟燭。太太也找到兩張有編織椅墊的直背椅,和薄紗般的白色棉布窗簾,掛在房間的三個窗戶上,還有圖案細緻的米色壁紙,跟一盞大約是一八六○年生產的白色玻璃煤油燈。她不可能奢望複製愛蜜麗臥室牆上那些裱框的肖像,那些想必是她的祖先,但她找到一些不知名的十九世紀紳士的畫像,同樣地陰沉、若有所思,如鬼魂一般。在當中,她還掛上了她許多年前過世的露米絲奶奶的畫像。當房間終於準備完成,而丈夫也進來欣賞驚嘆過之後,太太終於在那張小得不實用的寫字檯前坐下來,面對著一扇流瀉著春日陽光的窗戶,拿起一支筆,然後等著靈感降臨,準備寫作。
「我嚐到一種酒……」
但是沒別的了,現在還沒有。
第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愛蜜麗是這麼小。
當「愛蜜麗•狄更森豪華複製人」被運到柯林家,拿出箱子,直立起來後,這個據稱三十歲的女人看起來更像是營養不良的十歲或十一歲女孩,身高甚至不到太太的肩膀。雖然柯林夫婦已經看過連貝比魯斯也被縮小了,但他們還是沒有準備好看到他們的詩人伴侶這樣矮了一大截。豪華複製人公司所用的模特兒似乎是這個詩人唯一留下來的,她十六歲時拍的一張銀版攝影相片。她的眼睛大而深色,而且怪異地沒有睫毛,她的皮膚則是象牙般蒼白,如紙張光滑。她的眉毛比你想像的粗,更濃,線條更分明,像男孩子的眉毛。她的嘴也出乎意料地寬而豐滿,在那窄小的臉上彷彿透著一絲不屑。她深色的頭髮在頭的中央一絲不苟地中分,然後密實地往後梳,緊緊梳成一個髮髻,像一頂帽子,蓋住了她小小的耳朵的大部分。愛蜜麗•狄更森豪華複製人穿著深色的長袖棉質洋裝,裙長及膝,加上細得難以置信的腰肢,看起來更像是個萎縮的娃娃修女的屍體,而非一個三十歲的女詩人。非常緊張的丈夫搞不清楚該怎麼操作遙控器,就像他碰到這類設備時常有的情形。上面有好幾個功能選項,而他已經開始不耐煩地按著數字。「『睡眠模式』。這玩意到底該怎麼『啟動』?」
但丈夫必定是碰巧按到正確的按鍵,因為愛蜜麗•狄更森豪華複製人發出喀啦一聲和低沉的嗡嗡聲,一秒鐘後,那對沒睫毛的眼睛就活了起來,無神卻警醒,迅速地四下張望,然後停在站立在這個人像面前約一公尺半左右的柯林夫婦身上。現在那窄小胸腔裡的肺開始呼吸了,或者是詭異地模擬著呼吸的樣子。那豐厚的嘴唇移動,露出一個像是微笑的,轉瞬即逝的苦笑,但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丈夫喃喃地吐出一句尷尬的招呼:「狄更森小姐──愛蜜麗──哈囉!我們是……」丈夫介紹了自己和柯林太太,而在此同時,愛蜜麗•狄更森則是眨眼,睜大眼睛,除了頭稍微歪了一下,一雙小手絞在一起以外,便文風不動。「愛蜜麗,歡迎你遠道而來,到我們位於紐約市哥德綠坡的家!不曉得你覺得……」丈夫猶豫地說,但他已經盡可能地表示出最大的誠意,就像在工作上他時常被要求對年輕的同事表示歡迎,讓他們覺得自在,即使他自己顯然都不自在。太太靦腆地說:「親愛的愛蜜麗,我……我希望你叫我麥蒂琳,或……麥蒂就好。我是你在哥德綠坡這裡的朋友,而且我很愛……」太太突然漲紅了臉,因為她說不出「詩」,害怕自己被誤認為是做作愚蠢的郊區家庭主婦;但是說出「愛」這個字,又沒把話說完,也同樣讓人尷尬不自在。愛蜜麗.狄更森豪華複製人垂下仍快速閃動的眼睛。她仍然直挺挺地動也不動,似乎在等候指示。丈夫感到一陣懊悔,失望。在豪華複製人的店裡,他為何要縱容太太一時興起的怪念頭!他根本不想讓一個神經質的女詩人進他的家門,他本來想要的是活力充沛的男藝術家。太太滿懷希望地對愛蜜麗.狄更森豪華複製人微笑。看到這孩子般大小的愛蜜麗,穿著扣釦子的小鞋子,雙手扭著一條白色蕾絲手帕,太太心底不禁升起一股憐愛。
她纖細的脖子上繞著一圈絲絨緞帶,在她喉頭處交叉,並用一個浮雕別針固定住。愛蜜麗這麼膽怯,也是理所當然的:她一定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柯林夫婦是什麼人,自己是醒著還是在做夢,又或者在她這樣奇異的變化狀態下,清醒跟夢境之間有沒有區別。在裝著她的箱子裡,跟著一起送來的還有一個應該是裝著她衣物的行李箱、一個旅行袋,還有一個用紅色緞布蓋起來的,應該是縫紉盒的東西。
太太說:「親愛的愛蜜麗,我很樂意幫你整理東西,但是我想你現在可能比較想獨處,是吧?哈洛跟我會在樓下,你隨時想下來的話……」太太的口氣遲疑但溫暖。柯林太太對狄更森豪華複製人同時感到害怕,又強烈地受到吸引,像是見到一個失散多年的妹妹。那一瞬間,愛蜜麗的眼睛對她抬起了一下。那突然而銳利的眼神彷彿認定了她(是姊妹?)。那對小手繼續絞著蕾絲手帕,顯然詩人希望男主人和女主人消失。
柯林夫婦轉身要離開時,第一次聽到狄更森豪華複製人細小如耳語的聲音,小到幾乎聽不見:「是 謝謝 先生太太 我 非常 感謝。」
在樓梯上,太太緊抓著丈夫的手臂,用力到他可以感覺到她指甲的壓痕。她喘不過氣來地低語:「你想想看,愛蜜麗.狄更森來跟我們住了。這本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那真的是她。」丈夫覺得震撼而不安,不耐煩地說:「別傻了,麥蒂琳。那不是『她』,那是個假人,『她』是個很精巧的電腦程式,她是個『東西』,而我們是她的主人,不是她的朋友。」太太突然厭惡地推開丈夫:「不,你錯了!你也看到她的眼睛了。」
那天晚上,柯林夫婦等著住在家裡的客人加入,一開始是在晚餐時,接著是在客廳裡,太太還在壁爐裡生了火,而平常這時候都在看電視的丈夫也坐在客廳裡看書,或者說試著閱讀一本名為《神奇宇宙》的新書;但好幾個小時過去,令他們失望地,狄更森豪華複製人並沒有出現。他們有幾次聽到頭頂響起微弱的腳步聲,地板嘎吱作響,鬧鬼般的聲音。但如此而已。
在之後氣氛緊張的幾天裡,詩人都一直隱居在房間裡,雖然太太極力勸她隨意在屋裡「四處走動」。她說:「愛蜜麗,現在這就是你家了。我們都是你的……」但她猶豫著說不出「家人」這個字,因為家人似乎意味著親密,熟稔。到週末前,他們開始看到愛蜜麗出現在房間以外的地方,像森林裡行蹤神祕飄忽的動物,驚鴻一瞥後就消失無蹤。「你看到她了嗎?剛才那是她嗎?」當一個幽靈般的身影無聲地飄過門口,或轉過角落,然後立刻消失時,太太便會這樣對丈夫低語。丈夫冷酷地說:「不是『她』,是『那個東西』。」於是丈夫盡可能頻繁地躲到公司的辦公室去。
愛蜜麗仍舊像修女似的,每天穿著那件深色的長洋裝,但在洋裝上面,在腰間緊緊著綁上了一件白色的圍裙。雖然她似乎對太太的懇求邀請──「愛蜜麗,親愛的?等等──」──置若罔聞,但是太太開始發現廚房在她不在時整理乾淨了,地板掃過擦亮了,甚至花瓶裡還插上了幾枝帶著黃色花苞的金鐘花!──證明愛蜜麗其實不是那麼足不出戶,她能在沒有人發現時,去後院剪下金鐘花的花枝。因為愛蜜麗喜歡忙個不停:打掃家裡,烘烤麵包(她最擅長的是摻了糖蜜的黑麵包)和派餅(大黃餡餅、碎肉餡餅、南瓜派),幫忙太太做飯(太太曾在紐約一間很正式的烹飪學校上過課,但是學過的東西大都忘光了)。太太很愛聽她的詩人朋友自顧自地輕聲哼歌,而當她坐在灑滿陽光的窗戶旁繡花,或編織、刺繡時,歌聲最是輕快活潑。愛蜜麗也常會暫停手邊的工作,在一張紙片上寫一些字,然後快速地塞進圍裙口袋裡。如果太太就在旁邊,而且看到了,也一定會假裝沒看到。她已經開始寫詩了!在我們家裡!
…...(略)
克萊門斯爺爺和天使魚
小女孩?你不來跟我打招呼嗎?
他收集她們:他的「寵物」。十歲到十六歲的女孩子。不能比十歲小一天,或比十五歲大一天。這是私人俱樂部的年代,而他是水族館俱樂部的薩謬爾•克萊門斯上將,是裡面唯一的成人。私人專屬水族館俱樂部的新會員被稱為「天使魚」。啊!成為克萊門斯上將私人俱樂部的天使魚,是多大的特權!太平凡的女孩就不必申請了。他不要呆頭呆腦瘦巴巴的笨女孩。不要焦躁陰沉的女孩。不要吃吃傻笑的女孩。不要胖女孩。不要笨手笨腳的女孩。不要愛逞強的女孩。不要悶悶不樂的女孩。不要大呼小叫的女孩,一定要是聲音像鵝毛一樣輕柔,笑起來天真自然,又興奮激動,彷彿爺爺的手指正像彈奏木琴一樣,在她窄小的肋骨間搔癢。必須是喜歡讀書也喜歡別人讀書給她聽的女孩。最喜歡的書是《乞丐與王子》、《湯姆歷險記》、《哈克歷險記》的女孩。喜歡玩遊戲的女孩:紅心大戰、比手畫腳、中國象棋。
很高興有機會學撞球的女孩──而且是「由大師調教」。很興奮能在中央公園或郊外乘坐敞篷馬車的女孩;很高興能到戶外「踏青」,在冬天坐著雪橇穿過積雪小徑的女孩。能帶到廣場飯店、華爾道夫飯店,或聖瑞吉絲飯店喝下午茶,而表現得像是在場最完美,最泰然自若的小淑女的女孩。頭腦非常機靈、敏銳、聰明,但不會太過聰明的女孩;經得起玩笑,甚至會開玩笑,但不會變得苛刻或嘲諷的女孩;從來不會因厭惡而給人白眼,或因驚慌而眼神亂飄的女孩;絕對,絕對不會諷刺挖苦人的女孩。「精神奕奕」、「活力充沛」,但不固執己見的女孩。會為自己著想,但不任性倔強的女孩。漂亮──而且經常非常漂亮──但絕不虛榮的女孩。甜美天真信任別人的女孩。年輕可愛,人生對她而言是完美的喜悅,還不曾帶來任何傷害、苦澀、或太多淚水的女孩。
這些女孩是他最親愛的「寵物」─「珍寶」-「天使魚」。因為在所有熱帶魚當中,沒有別種魚比天使魚更優雅,色彩更精緻,更有神奇的魔力。這些女孩會把克萊門斯爺爺當成她們的領袖一樣敬愛,她們的母親會因為這位名作家對自己女兒的興趣而備感驕傲,也毫無疑問地會同樣敬愛克萊門斯先生;而她們的父親不會加以干涉,或事實上不在身邊(或已經過世)。這些女孩穿著學校制服、頭髮綁著馬尾,為特殊場合穿一身裝飾繁複的白,到處是蕾絲邊的白,頭髮上綁著白色緞帶蝴蝶結,好搭配克萊門斯爺爺傳奇的一身白衣。她們跟克萊門斯爺爺合照的照片,掛在他房子裡很特別的撞球間牆上。她們驕傲地佩戴著克萊門斯爺爺在她們進入天使魚俱樂部時,贈予的琺瑯鑲金天使魚別針。
她們是懂得感激的女孩。很快就寫謝函,署名「愛你的」的女孩。道別時會擁抱,但從不會黏著不放的女孩。親吻時快速輕巧,像快速俯衝的蜂鳥一啄一樣的女孩。將會對上將爺爺充滿溫柔回憶的女孩,會說,喔,克萊門斯先生是我這一生最深刻的愛,因為他對我的愛是完全純潔無瑕的,沒有一點肉慾。如果真的有天堂,那克萊門斯先生一定就在那裡。
不會紅顏早逝的女孩。
不會哭的女孩。
「小女孩?你不來跟我打招呼嗎?」
時間是一九○六年的四月。他七十歲。他情緒高昂,正在蓮花俱樂部一場爆滿的「與馬克吐溫共度一晚」的座談會後幫觀眾簽書。在貼滿富麗堂皇嵌板的樓上圖書室裡,他讓這些口袋滿滿的觀眾哄堂大笑,因為這些紳士和豐腴的女士們是來接受馬克吐溫的娛樂,而不是啟發的。那麼,好吧,他會娛樂他們。而此刻他坐在一張雕刻得有如王座的桃花心木座椅上,在有華麗圓頂的門廳裡的一張書桌前,幫重新出版的《老憨出洋記》(The Innocents Abroad)簽名。數百個書迷迫不及待想跟作者握手,得到他潦草而幾乎難以辨識的簽名,來好好珍藏。而在手上拿著一本書或許多本書等著他簽名的崇拜者當中,有一個大約十三歲,看來很害羞的女孩,身邊跟著她的媽媽,也可能是奶奶,那種身材豐碩的女性之一。
這些女人對克萊門斯先生的仰慕讓他好生疲憊,因為你一定得殷勤有禮,不能在她們話說到一半時打岔,也不能對著她們撲了粉的臉打呵欠。因為她們是買書的消費大眾,你當然得心存感激。但他運用他滿頭白髮七十歲老人家可以行為反覆無常的權力,示意那個女孩上前到隊伍的最前端,沒錯,當然還有她的媽媽或是奶奶,然後在她們的書上題贈,用他著名的簽名方式署名。
「親愛的,你叫什麼名字?」
「麥蒂琳……」
「麥蒂琳這名字很好聽。那親愛的,你姓什麼呢?」
「艾佛力。」
「啊,『麥蒂琳.艾佛力』。你知道嗎,我就知道是你:麥蒂琳.艾佛力,沒人比她更美麗。」為了掩飾心底的情緒,克來門斯先生用炫耀誇張的字體,在這女孩的《老憨出洋記》的版權頁上潦草寫下這句打油詩,然後簽上像是一圈圈銳利鐵絲網的,馬克吐溫的簽名。在近距離下,這女孩比他原本想的更漂亮。她有著心形的臉蛋,骨架細緻,皮膚光滑,因興奮而泛紅;多像他自己的女兒年輕時的樣子。尤其是蘇西,他最愛的,已經過世的女兒──喔,他親愛的蘇西是什麼時候過世的?──那麼多年前了,他對於自己居然活得比她久感到震驚又困惑。老年人活得比年輕人久實在反常。
而且是這樣自吹自擂滿頭白髮的老頭子!麥蒂琳的深棕色頭髮梳成規矩的女學生辮子,披在肩膀後,瀏海蓋住額頭,幾乎碰到她的眉毛。她穿著酒紅色背心裙,襯衫則有白色的蕾絲和反折袖口。她的白色長襪有四分音符的圖案,小腳上穿著亮閃閃的黑色漆皮皮鞋。她緊抿著甜美的小嘴,努力不讓自己笑出來。她眨著漂亮的大眼睛,他猜測她有些許近視。他對她湧上一股如此強烈的情感,以致他只能用顫抖的手指緊握著一個書迷送他的黑檀木鑲金鋼筆,緊緊盯著她。
這是夢嗎?這一定是夢。他是七十歲,而不是十七歲了。他愛過的每一個女孩,都已經腐朽消失。除了你以外,一切都不存在。而你不過只是個念頭。
克來門斯先生令人氣憤地完全不理會在大廳裡等著跟他握手,跟他要簽名的其他成人書迷,仍繼續跟這女孩和她母親(這容光煥發的豐腴婦人事實上是女孩的母親)嬉鬧地聊天,並很快地得知她們住在公園大道和二十八街交叉口,離這裡不遠;還有艾佛力先生在「毛皮業」;以及麥蒂琳念河岸女子學院,並且在學鋼琴及長笛,希望有一天能成為「詩人」;還有她事實上比她的外表大一點,十五歲,可是是年輕的十五歲,因為她喜歡溜冰,玩雪橇,還有小貓咪;而且她最喜歡的馬克吐溫作品是《乞丐與王子》。
克萊門斯先生慈祥地說:「親愛的,你應該帶你的那本過來的,我就可以幫你簽名了。」克萊門斯先生不情願地讓麥蒂琳和艾佛力太太離開,因為他還有很多話想跟眼睛閃閃發亮的麥蒂琳說,也希望她還有別的話要跟他說;但他已經狡猾地在她的《老憨出洋記》書裡塞進了一張他的名片,上面印著薩謬爾•藍霍爾.克萊門斯(Samuel Langhorne Clemens)和他在第五大道的地址,並潦草地寫下露骨的請求:
孤單!誠徵祕密筆友!
腰桿筆直的克拉拉過來了。她是克萊門斯先生未婚的女兒,經常在這種場合陪伴他,而且經常必須帶著掩飾不住的不耐煩在一旁等候,看著這虛榮的老頭子像個醉鬼般,暈頭轉向地留戀在眾人的吹捧中。簽書,握手,接受讚美。簽書,握手,接受讚美。克萊門斯先生穿著量身定做的白色斜紋布西裝,一頭蓬鬆如雲的雪白頭髮,留著堅硬向下彎而顏色較暗的白鬍子,仍舊跟平常一樣散發出和善而尊貴的氣息,但是眼尖的克拉拉看得出他已經筋疲力竭:扮演密蘇里來的丑角「馬克吐溫」,讓他日漸疲乏。
他最愛的女兒蘇西多年前過世後,他始終不曾恢復過來;他纏綿病榻多年的妻子麗薇三年前過世後,他始終不曾恢復過來;他因為不當的投資導致損失一小筆財富,以及在《老憨出洋記》和《苦行記》(Roughing It)後已經數十年都沒有大熱賣的暢銷書,因而自尊受到打擊之後,也始終沒有恢復過來。雖然他在大眾面前還是態度親切,開心地瞇起眼睛,從不讓人失望地風靡全場,但他在私底下卻是尖酸刻薄。忿忿不平,幼稚又難以相處。他的健康日漸惡化:他的「老煙槍」心臟、五十年來被廉價難聞的雪茄毒害的肺。在父親過去散發著藍綠色光芒的眼中,克拉拉看到一個迷失的人的寂寥悲涼。
今天晚上的表演中,他好幾次忘記自己在說什麼,那濃重的拖拖拉拉的密蘇里口音延續成尷尬的沉默,而他的左眼皮也不斷顫動,像色瞇瞇地眨眼時那樣下垂。在這冗長的簽書時間當中,他還好幾次掉了他誇張炫耀的鋼筆,必須由蓮花俱樂部的一個小嘍囉撿起來還給他。克拉拉一想到他的呼吸裡威士忌的酸臭味,就覺得厭惡:他一定是把他的銀扁瓶偷塞進了外套口袋裡,隨身帶著,以便可以躲到洗手間去偷喝一口。她就像自己親眼看到一樣,完全肯定這點。此刻,她強迫自己露出像個女兒該有的微笑,彎身靠近坐在雕花桃花心木寶座上召見臣民的父親,在他耳邊低聲說:「爸爸,你跟那個女孩說什麼?」
她無法忍受這件事,克萊門斯先生的弱點。克萊門斯先生眾多弱點當中最難聽的一個。
克萊門斯先生不予理會地驅走她。他是在公眾場合裡高高在上的自己,不在乎任何批評。大家都喜歡他,「馬克吐溫」是如此有趣,他只要扭動斑白的眉毛,動動大而圓、微血管顯露而紅通通的鼻子上的鬍子,背脊直挺挺的克拉拉根本就不是對手,也不敢惹惱他,否則他的好脾氣轉眼間就會變得刻薄,讓她承受不住。因此在將近一小時裡,克萊門斯先生就一直在蓮花俱樂部的大廳裡,熱情地跟書迷握手,如同飢餓的狗舔著粥一般,接受最令人作嘔的讚美,為所有想要的人,簽下他著名潦草的「馬克吐溫」簽名。而這簽名也隨著歲月的流逝和時間越來越晚,變得更加誇張和難以辨識。
機器,宣傳機器!既然薩謬爾.藍霍恩•克萊門斯是一具機器,馬克吐溫就是機器創造出來的機器。這是最甜美的諷刺,但是:誰是那個諷刺家?誰是那個跟人類嬉戲,又嘲笑人類的人?在他的筆記本上,他胡亂戳刺的潦草筆跡當中,紙頁上撒落了許多雪茄煙灰。
但是,他半夜醒來,拿起筆,匆匆點燃一根雪茄,在潮溼混亂的糾結床單中,試著捕捉一個夢的殘餘記憶和餘味。色彩最精緻美麗的天使魚,淡淡水藍色點綴著絲絲金黃,細緻的魚鰭,大大的眼睛,天真無邪地游進我細密的網裡,啊!做夢的人心跳得如此強烈,亢奮得再也睡不著,宣示著,我還活著──是嗎?──還活著──沒錯!他臥室的空氣隨著煙霧而變藍,像百慕達海岸外的加勒比海海底。
在第二天早上的郵件中,從一個顯然是女學生筆跡的方形奶油色小信封裡,它到來了!克萊門斯先生偷偷地,在他的女妖女兒和管家都看不到的地方,懷著最甜美的心情撕開了信封。
親愛的克萊門斯先生,
我可以當你的祕密筆友嗎?我也很孤單。
但是克萊門斯先生,我今天是全紐約市最快樂的小女孩。非常非常感謝你幫我珍藏的《老憨出洋記》簽名。我會把簽名拿給學校裡所有人看,因為我真的好驕傲。也謝謝你從我臉上看出來我有多想跟你講話。我希望你能當我的祕密筆友,而沒有人會知道我是每個白天的每一刻,甚至每天晚上,在我最祕密的夢裡,都想著克萊門斯先生的那個小女孩。
你的新朋友,麥蒂琳.艾佛力
一九○六年四月十七日
公園大道一○八八號
……(略)
愛蜜麗•狄更森豪華複製人好孤獨!他們怯怯地隔著餐桌對望,櫻桃木桌面上的燭火閃爍不定,如隱約憶起的夢。一個人像是剛剛才想到似的,說:「我們應該買一個豪華複製人,」而另一個立刻回答,「豪華複製人太貴了,而且你也聽過它撐不了一年。」「才不會!除非──」「我上禮拜才查過,比例是百分之三十。」所以丈夫上網去查了。太太留意到這件事,覺得高興。因為她心底一直在渴望,多一點生命力!多一點活力!九年的婚姻。還是十九年?到了某個時刻,你會突然醒悟:這就是人生給你的。比這更多,你也得不到了。而且這一切,你的人生至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