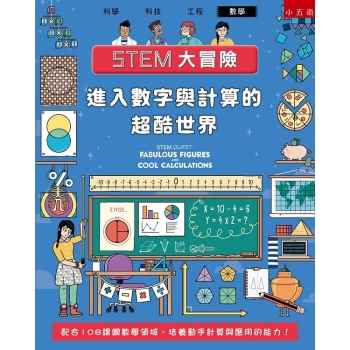精平裝銷售超過三十萬冊
紐約時報、邦諾書店、獨立書商協會、出版者週刊、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今日美國報、北加州獨立書商協會暢銷排行榜。
Amazon.com 2007年度銷售Best100
獲選紐約時報精選好書,書評家 Janet Maslin 個人十大選書。
獲選時人雜誌年度十大好書。
榮獲2007年鵝毛筆大獎(Quill Award)「偵探、推理、懸疑類」,擊敗麥可?康納利。
榮獲2007 史全德雜誌評論家獎(Strand Critic Award)「最佳小說」大獎。
提名英國犯罪作家協會鄧肯.羅利匕首獎(Duncan Lawrie Dagger)。
提名安東尼獎年度最佳長篇小說(Best Novel)。
提名麥卡維提獎年度最佳長篇小說(Best Novel)。
提名致命快感雜誌之巴瑞獎年度最佳長篇小說(Best Novel)。
提名 Mystery Ink 之警察獎(Gumshoe Award)。
提名 Spinetingler 大獎。
售出英國、德國、法國、荷蘭、義大利、日本、台灣等十四國版權。
當真相如此遙不可及,
失去妳們,人生該如何繼續下去?
就算要再傷一千遍的心,我還是希望有個答案
三十年前,貝塞尼家15歲的珊妮和12歲的妹妹海瑟,在城裡的購物中心消失無蹤。警方竭盡所能調查仍毫無頭緒,也始終未尋獲屍體。這樁離奇的失蹤案,讓一個家庭從此分崩離析,也讓所有當事者從此活在歉咎與哀痛中。
而今,在一場公路車禍裡肇事逃逸、徬徨失措的女子,卻自稱是貝塞尼家失蹤多年的妹妹海瑟。沒有絲毫證據可以支持她的說法,但她卻對往事歷歷如繪,甚至知道一般人不可能得知的細節。
為何回家的路要經過三十年?為什麼事隔這麼久她才打破沉默?而這些年來她又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最重要的,當初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當所有塵封的傷痛、謊言和祕密,因為女子的出現而再度開啟,這場延宕了多年的折磨,是否終能劃下句點?
蘿拉.李普曼是一位以犯罪推理類型見長、得獎不斷的小說家,在這本書中,她在一開場就利用一個身分神祕的女子帶出昔日的離奇失蹤案,之後拋出一個接一個的謎團,以及角色互相衝突的人物情節,讓讀者一開卷閱讀就無法停止。然而,就在讀者誤以為是在閱讀一部精采的推理小說時,別有企圖的作者已經悄悄地帶領我們走向各種歧路,去追索人生的種種荒謬、巧合、宿命、信任、背叛、脆弱與懊悔等複雜難解的習題,其中寫實的心理描述,讓故事有了豐富的情感層次和高度,因此當書中的謎團終於撥雲見日,驚嘆於作者佈局高妙之餘,心中的沉重卻也久久不散。
作者簡介
蘿拉.李普曼
生於1959年,曾在《巴爾的摩太陽報》擔任記者達十二年之久,後轉而嘗試小說的創作。1997年出道至今,發表了十部「黛絲探案」系列,三部獨立作品,不但獲得愛倫坡、安東尼、夏姆斯、阿嘉莎等推理大獎,此外在羅曼史、主流文學圈均獲得肯定,包括浪漫時代女性偵探成就獎、馬里蘭作家獎、首屆巴爾的摩市文學獎等殊榮。目前定居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
《貝塞尼家的姊妹》是她第三部獨立作品,甫上市即攻佔全美暢銷排行榜,包括紐約時報、邦諾書店、獨立書商協會、出版者週刊和華盛頓郵報等,並獲得2007年鵝毛筆獎「偵探、懸疑、驚悚類」大獎,以及2007史全德評審獎「年度最佳小說」大獎。
譯者簡介
李靜宜
政大外交系畢業,外交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美國史丹福大學訪問學者。
曾任職外交部與出版社。
譯有《追風箏的孩子》、《燦爛千陽》、《奇想之年》、《直覺》、《理察費曼》、《古典音樂一○一》、《完美的間諜》等書。


 2011/11/03
2011/11/03 2010/01/21
2010/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