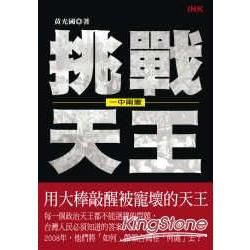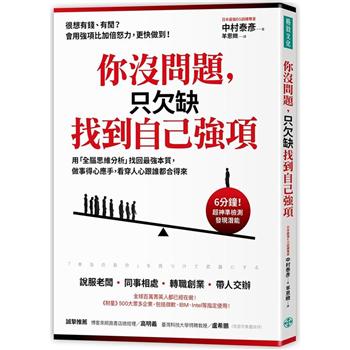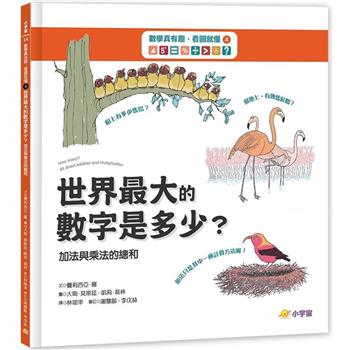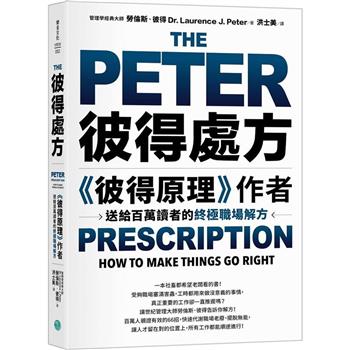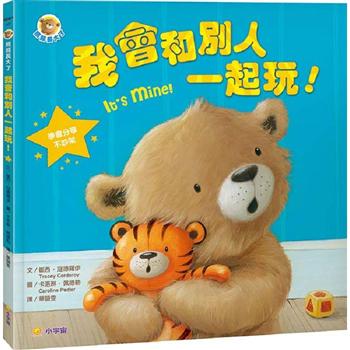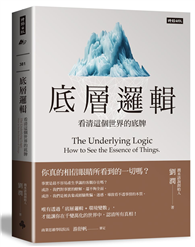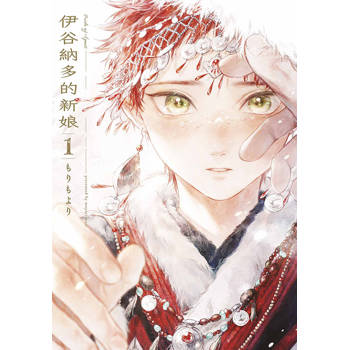第一章 我的終極關懷
二○○七年元月十日,我在民主行動聯盟許多朋友的陪同下,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宣布將參加國民黨內總統候選人初選,許多人都大為吃驚,認為這項宣布完全不符合我的行事風格。誠然,「從政」這件事確實是和我的生涯規劃背道而馳;然而,瞭解我政治理念的人即不難看出:我這樣做,實在是不得已也。更清楚地說,我參選的主要目的,是要藉由國民黨內初選的辯論,迫使國民黨二○○八年的總統候選人,對台灣的未來提出一套清晰而且明確的願景,讓台灣人民對國家的未來能夠看到希望。
過去幾年中,我和民盟的許多朋友因為對台灣政治運動的高度參與,經過反覆的辯論,對當前台灣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已經發展出一套完整的論述。我們認為:以「一中兩憲」的主張作為基礎,不僅可以建構台灣海峽兩岸間穩定的和平關係,而且可以解決台灣內部由憲政體制和意識型態對立所衍生出來的諸多問題,更可以讓台灣在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中得以定位。
我們希望:藉由參與國民黨內總統候選人初選,能夠以這套論述和國民黨的其他候選人互相辯論。如果有人能夠提出比「一中兩憲」更好的論述,我們願意甘拜下風,並全力幫他輔選。反過來說,如果其他候選人提不出更好的論述,「一中兩憲」就應當成為國民黨內的共識,大家同心協力,一起打贏二○○八年的這場選戰。換句話說,在國民黨內總統候選人初選,我們將以「一中兩憲」的相關論述挑戰其他的候選人;在未來二○○八年的總統大選中,我們也希望用同樣的論述來挑戰民進黨的「天王」。
從哈柏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來看,一個採行批判理論的學者,必須保持清冷的批判意識,先對自己潛意識中的意識型態進行自我批判,然後才能夠對社會中主流的意識型態進行社會批判。因此,在這本書中,我將從我的家世背景,分析我深層潛意識中的「反帝情結」。然後說明:「從政」這條路為什麼背離我自己的生涯規劃;但在眾多主客觀因素的因緣際會之下,我又不得不走上這條路,希望能夠落實「一中兩憲」的政治理念,徹底解決十餘年來困擾台灣政壇的「台獨民粹主義」現象。
*
第一節 末代皇帝的台灣御醫
二○○七年元月二日,《中國時報》第五版以全版的篇幅,刊登出一篇對我的專訪,題為〈末代皇帝生命交給台灣御醫〉,詳細敘說滿清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在東北滿洲國稱帝時期,竟然十分信任一位台灣籍的御醫,就是家父黃子正。甚至在二次大戰結束,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寧可捨棄第四位妃子,也要帶他的私人醫師一起逃亡!這篇專訪刊出之後,許多朋友跟我見面時,最感興趣的話題就是:前清時期,皇帝御醫是朝廷命官,地位崇隆。到了滿洲國時代,為什麼末代皇帝溥儀會找一個台灣人當他的御醫?
●我的父親黃子正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答案癥結在於:溥儀內心對日本人的恐懼。我在瞭解這個問題之後,整個世界觀起了相當大的變化,對於我日後政治理念的形成也有極大的影響。為了說明這段因緣,我又撰寫了一篇長文〈末代皇帝的恐懼與台灣御醫〉,分兩次刊登在元月廿二、廿三日的(聯合‧副刊)之上。
要把這個歷史故事說清楚,必須先暸解三位關鍵人物,第一位是溥儀的私人醫師,家父黃子正,第二位是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第三位則是關東軍派在他身邊的聯絡官吉岡安直。先談家父。根據我家族譜的記載,我的祖先世居於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美人山麓,一個稱為「興堡」之處(目前為廈門市集美區洪塘鎮),傳了十二世,到清朝乾隆年間(1761),始祖黃志松渡海來台,傳到第四代,我的曾祖父黃耀性在台北市迪化街蓋了一棟閩南式的建築。清朝末年,來自福建的貨船可以沿淡水河航行至台北的艋舺(萬華)和大稻埕(延平區)一帶,我的曾祖父便在閩、台兩地往返經商為業。這棟祖厝位於台北市迪化街台北大橋附近,佔地百餘坪,前面是商店,縱深卻長達十餘間店面,台語俗稱「竹篙厝」。據說當年從福建來台的商船,可以沿淡水河航行到大稻埕,卸下來的貨,儲存在屋後倉庫,商品則在屋前店面待價而沽。
目前迪化街一帶已經發展成為著名的南北年貨市場,大多房舍都曾經數度翻修,我們這棟祖厝傳到家父一代,卻因為家道中落,再加上所有權的持分人愈傳愈多,子孫經濟稍微寬裕之後,即搬離祖厝,無人肯出錢翻修。到了二○○四年,這棟祖厝已經變成無人居住的廢墟,內部仍然保有前清時期的格局。結果,竟然意外成為台北市政府古蹟保存的對象。我的祖父改業學習西醫,日據時代實行公醫制度,祖父黃煙篆曾是當時的公醫。父親黃子正和堂叔黃樹奎兩人都是當年「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的畢業生。據一位堪輿先生說,我的曾祖父所葬的風水叫做「飛鳥過枝」,所以注定子孫會漂洋過海,遠至異鄉。事實上,可能是受了先人從事商貿的影響,我的家族到家父一代,我的叔伯輩以及堂叔、堂伯,都紛紛離開家鄉,到中國大陸和南洋一帶尋求發展。家父和堂叔黃樹奎兩人自台北醫專畢業後,相偕到上海開業行醫,不久之後,家父又到長春(當時稱為「新京」),開設「大同醫院」。
●國務總理鄭孝胥
鄭孝胥是福建人,和溥儀的老師陳寶琛是同鄉。在前清時期中過舉,當過清朝駐日本神戶的領事,也做過一任廣西邊務督辦,國學基底扎實,詩書文章都相當不錯。民國成立之後,鬻書筆潤為生,很受陳寶琛賞識,而一再向溥儀推薦。民國十二年夏天,鄭孝胥第一次和溥儀見面,即暢談他「大清中興」的構想,溥儀大為傾倒,立刻請他留下當「懋勤殿行走」。嗣後,鄭孝胥為建立滿洲國出了許多力。一九三二年滿洲國建立之後,他也順理成章成為第一任「國務總理」。
當時閩、台之間交流十分頻繁,滿洲國成立後,鄭孝胥因為自身是福建人的地緣關係,提拔了不少台灣人到滿洲國政府任職,其「外交部總長」即為新竹人謝介石。滿洲國建立之初,溥儀體弱多病,亟需找一位醫生照顧他的健康。當時日本關東軍不准他用中國醫師,他自己又不信任日本人,雙方折衝之下,鄭孝胥就找「既不是中國人,又不是日本人」的台灣人謝介石,請他替「皇上」找一位御醫。家父雖然是西醫出身,同時兼習中醫,在種種因素因緣際會之下,謝介石即介紹家父,成為溥儀的私人醫生。
●「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
●當時所謂的「滿洲國」,其實是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政權,內閣各部總長是中國人,次長則是日本人,日常政務幾乎全由次長決定,甚至連宮內府亦不例外。「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便是關東軍派在溥儀身邊的聯絡官。吉岡是日本鹿兒島人,溥儀的弟弟溥傑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讀書時,吉岡還在該校擔任戰史教官,兩人結為好友,關東軍知道了這層關係,再加上吉岡本人的積極活動,一九三五年,關東軍終於任命他為高級參謀,派他「掛」在「滿洲帝室」達十年之久。
那時候,宮內府設有「憲兵室」,住有一班日本憲兵,監視宮內的一切活動。根據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的說法,關東軍好像一個「強力高壓電源」,他自己本人就像一個「精確靈敏的電動機」,吉岡安直就是「傳導性能良好的電線」,他這個皇帝「不能過問政事,不能隨便外出走走,不能找個『大臣』談談」。當關東軍那邊沒有電流通過來的時候,他在「宮內」根本無事可幹,日常生活用八個字就可以概括:「打罵、算卦、吃藥、害怕」。
*
第二節 末代皇帝的恐懼
●鄭孝胥和「凌升事件」
年,溥儀「登極」後,對日本人已經開始心懷戒懼。翌年四月,他在日本人安排之下,到日本訪問,回到長春不到一個月,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告訴他:「鄭孝胥總理倦勤思退」,溥儀大吃一驚。後來多方打聽,才知道鄭孝胥不久前在他主辦的「王道書院」裡,向學員發了一次牢騷:「滿洲國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就該讓他自己走走,不該總是處處不放手。」日本人知道了,立刻把他一腳踢開,在日本憲兵隊的監視下,只能留在家裡做詩、寫字。不久他的兒子「國務院祕書官」鄭垂暴斃;三年之後,鄭孝胥本人也在長春暴卒,據說都是出自日本人的暗殺。
一九三六年,滿洲國的「建國元勳」之一,興安省省長凌升在省長聯席會上發牢騷,說他在興安省無權無職,一切都是日本人說了算。開完這個會,凌升回到本省,立刻被抓走,並以「反滿抗日」罪名,跟幾個親戚一起被處斬首。
●「帝位繼承法」
「凌升事件」使溥儀感到極度不安,讓他感到更恐懼的,則是日本人搞的「帝位繼承法」。一九三五年冬,溥傑從日本回到長春,當了禁衛軍中尉。本來溥儀想幫他安排一門親事,吉岡立刻向溥儀表示:為了增進「日滿親善」,關東軍希望他和日本女子結婚,本庄繁大將要親自替他作媒,希望他這位「御弟」能作為「親善」表率。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溥傑與嵯峨勝侯爵的女兒嵯峨浩在東京結婚。過了不到一個月,關東軍便授意國務院通過一項「帝位繼承法」,明文規定:皇帝死後由子繼之,如無子則由孫繼之,如無子無孫則由弟繼之,如無弟則由弟之子繼之。
溥儀一看就明白:這個「帝位繼承法」最緊要的只有「弟之子繼之」這句話,關東軍要的只是一個有日本血統的皇帝,必要時候,隨時可以拿他們兄弟開刀。由於時刻擔心自己生命的安危,溥儀宮內生活的第二件事就是「算卦」,吃素念經,求神拜佛,占卜打卦。譬如,溥傑的日本妻子懷了孕,溥儀就「提心吊膽地為自己的前途算過卦」,直到得知她生的是女兒,「才鬆了一口氣」。
●「慮病症」和疑心病
因為日夜擔心自己的安危,溥儀得了嚴重的「慮病症」,不僅嗜藥成癖,而且還收藏各種藥品,中藥有藥庫,西藥有藥房。他的侍從主要的工作之一,便是替他管藥房、藥庫;每天和他的私人醫師為他打補針,總要忙上幾小時。一九九六年,我藉著到吉林大學講學之便,順道參觀溥儀在長春的舊「皇宮」,這所建築據說是由道尹衙門改裝而成,並沒有一般皇宮的氣派。皇帝居住的「緝熙樓」,一端是皇帝寢室,另一端是皇后寢室,中間則是個藥房,也就是家父替皇帝看病的地方。在世界各國的皇宮中,這種「寢宮」的格局,大概也是絕無僅有的。
除了「害怕、算卦、吃藥」之外,溥儀的日常生活還有一項「打罵」。由於疑心病極重,成天擔心有人會害他,「脾氣日趨暴躁,動輒打人罵人」。打罵的對象除了侍從之外,也包括他的「妻子、弟弟和妹夫」。「打人的花樣很多,都是叫別人替我執行」。那時大家最怕溥儀說的一句話,就是「叫他下去!」意思就是到樓下去挨打。打傷了再趕快「把醫生叫來搶救」。因此,家父的醫護工作,不僅要照顧皇帝的健康,還包括後宮及宮內侍從的醫療診治。根據家母的說法,家父的御醫工作十分繁重,每天早上去,下午回來,有時候甚至晚上還得再進宮一次,忙到深夜兩、三點鐘才回到家。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挑戰天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政治 |
$ 270 |
政治評論 |
$ 270 |
台灣政治 |
$ 270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挑戰天王
用大棒敲醒被寵壞的天王!挑撥統獨問題、緊抓清廉光環,就可以穩坐天王寶座?就能領導國家?會不會太簡單了!?
每一個政治天王都不能迴避的問題,台灣人民必須知道的答案:2008年,他們將「如何」帶領台灣往「何處」去?
21世紀台灣的政治天王如雨後春筍般一個個冒出頭來,但關於台灣前途的論述在哪裡?從心理學到教改,從《民粹亡台論》到民主夜市,黃光國的關懷觸角越伸越廣,因為參與才知有所不及,因有所不及而更加投入。台灣的政治天王如雨後春筍,但關於台灣前途的論述在哪裡?從兩岸關係、意識型態、憲政改革到全球定位,黃光國跳出來挑戰台灣的政治天王們,逼使他們正對台灣人民提出治國理念,告訴人民,他們將台灣帶往哪裡去?
作者簡介:
黃光國
台北市人,1945年生。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現任國立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致力於結合東、西文化,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發展本土社會心理學。著有《中國人的權力遊戲》、《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王者之道》、《知識與行動: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詮釋》、《民粹亡台論》、《教改錯在哪裡?》、《社會科學的理路》以及中英文學術論文一百餘篇;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優良研究獎十餘次,教育部國家講座兩次,目前為國科會特約研究員、台大終身特聘教授、台大講座、傑出人才講座及國家講座教授。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我的終極關懷
二○○七年元月十日,我在民主行動聯盟許多朋友的陪同下,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宣布將參加國民黨內總統候選人初選,許多人都大為吃驚,認為這項宣布完全不符合我的行事風格。誠然,「從政」這件事確實是和我的生涯規劃背道而馳;然而,瞭解我政治理念的人即不難看出:我這樣做,實在是不得已也。更清楚地說,我參選的主要目的,是要藉由國民黨內初選的辯論,迫使國民黨二○○八年的總統候選人,對台灣的未來提出一套清晰而且明確的願景,讓台灣人民對國家的未來能夠看到希望。
過去幾年中,我和民盟的許多朋友因為對...
二○○七年元月十日,我在民主行動聯盟許多朋友的陪同下,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宣布將參加國民黨內總統候選人初選,許多人都大為吃驚,認為這項宣布完全不符合我的行事風格。誠然,「從政」這件事確實是和我的生涯規劃背道而馳;然而,瞭解我政治理念的人即不難看出:我這樣做,實在是不得已也。更清楚地說,我參選的主要目的,是要藉由國民黨內初選的辯論,迫使國民黨二○○八年的總統候選人,對台灣的未來提出一套清晰而且明確的願景,讓台灣人民對國家的未來能夠看到希望。
過去幾年中,我和民盟的許多朋友因為對...
»看全部
作者序
挑戰天王》自序
二○○七年二月十二日,名政論家南方朔在《中國時報》上發表了一篇專論〈國民黨還有希望嗎?〉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民進黨基本上是以「四百年來最後一戰」的台獨意識型態,在對待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他們深知:只要贏了這一戰,不但所有的貪瀆非法醜聞可一揭而過」,而且「藍營即會潰散。一個真正萬年執政黨即可誕生」。正是基於這樣的意識,他們才會用盡一切手段,讓阿扁的「大問題」變成「沒問題」,也才會有系統地在教科書,以及中鋼、中油、中華郵政,和慈湖陵寢等具有符號指標意義的問題上製造話題。「藉著操作符號...
二○○七年二月十二日,名政論家南方朔在《中國時報》上發表了一篇專論〈國民黨還有希望嗎?〉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民進黨基本上是以「四百年來最後一戰」的台獨意識型態,在對待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他們深知:只要贏了這一戰,不但所有的貪瀆非法醜聞可一揭而過」,而且「藍營即會潰散。一個真正萬年執政黨即可誕生」。正是基於這樣的意識,他們才會用盡一切手段,讓阿扁的「大問題」變成「沒問題」,也才會有系統地在教科書,以及中鋼、中油、中華郵政,和慈湖陵寢等具有符號指標意義的問題上製造話題。「藉著操作符號...
»看全部
目錄
第一章 我的終極關懷
末代皇帝的台灣御醫
末代皇帝的恐懼
認同危機與塑造自我
第二章 我的學術生涯
中華文化傳統的研究
科學哲學的提倡
心理學本土化運動
第三章 民粹亡台論
民粹主義
李登輝的崛起
李登輝的民粹主義
第四章 民粹式教改
知識虛無主義
「重建教育宣言」
李遠哲的「責任倫理」
《教改錯在哪裡?》
第五章 反6108億軍購
凱子軍購
美國人的看門狗
反軍購行動
軍備競賽
第六章 反修憲法理
台獨的目標
單...
末代皇帝的台灣御醫
末代皇帝的恐懼
認同危機與塑造自我
第二章 我的學術生涯
中華文化傳統的研究
科學哲學的提倡
心理學本土化運動
第三章 民粹亡台論
民粹主義
李登輝的崛起
李登輝的民粹主義
第四章 民粹式教改
知識虛無主義
「重建教育宣言」
李遠哲的「責任倫理」
《教改錯在哪裡?》
第五章 反6108億軍購
凱子軍購
美國人的看門狗
反軍購行動
軍備競賽
第六章 反修憲法理
台獨的目標
單...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黃光國
- 出版社: INK印刻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7-06-07 ISBN/ISSN:986687322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0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