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背為特殊設計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年輕小說家邱妙津自死於巴黎,得年二十六歲,聞者莫不唏噓。其先後出版的作品如《鱷魚手記》、《蒙馬特遺書》等至今仍傳誦不絕,獨特的文體、寫女同志的熱烈情慾、真誠率直的筆法,對年輕一代的創作者啟發甚多。
忽忽又已過了十二個年頭,人間干支走過一輪,如今讀者們終於能看見在她1989?1995年日記中宛如她《蒙馬特遺書》未收錄的小說細節與生命內裡,與直面生活的思索。
我們不只再一次見到其中驚人的生命能量與早慧才氣,也看到她在時間中忍熬傷痛與沉澱靈魂的證據;更看到她其他作品中環環相扣又相互推翻的,對於愛與死亡的辯證的源頭。其中也包含她學習與進行創作構想的軌跡。
作者簡介
邱妙津
台灣彰化人,一九六九年生,一九九一年畢業於台大心理系,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前往法國,留學巴黎第八大學心理系臨床組,一九九五年六月日在巴黎自殺身亡,得年僅廿六歲。
邱妙津多方面的才華在大學時代就開始充分顯現,曾以〈囚徒〉獲得中央日報短篇小說文學獎,並以〈寂寞的群眾〉獲得聯合文學中篇小說新人獎。除了寫作,邱妙津還擔任義務性的心理輔導工作、雜誌社的記者,同時拍攝了一部長度三十分鐘的十六釐米影片《鬼的狂歡》。
一九九五年六月邱妙津驟然辭世掀起了台灣文壇一陣驚愕,隨即造成一時風潮。同年十月她的首部長篇小說《鱷魚手記》獲得時報文學獎推薦獎,書中的「拉子」、「鱷魚」等詞也成為台灣女同志習襲用的自我稱號。最後一部作品《蒙馬特遺書》更由導演魏瑛娟搬進劇場,這都證明邱妙津作品的影響之日久不衰。
主要著作有《鬼的狂歡》、《寂寞的群眾》、《鱷魚手記》、《蒙馬特遺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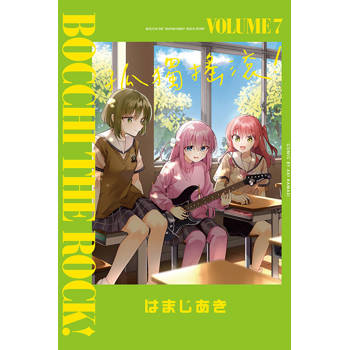




【我之於人生確實是強悍的,我一點都不軟弱。且是愈來愈強悍的。在這個世界上,我所懼怕的人,我所懼怕的事,我所懼怕的情境、人生現象是愈來愈少了。 人生中可以得到的,我全部都可以得到,現在我明白只要我想要的一切我都可以得到。人生何其美。但得不到也永久得不到,那樣的荒涼是更需要強悍的。】 這是邱妙津自殺前三日的日記,也是她留給這世界最後的隻字片語。才宣示著強悍,交出蒙馬特遺書的完稿後,卻在巴黎自殺,得年僅二十六歲。 邱妙津是早慧且很年輕便嶄露頭角的作家,自殺前她便以\"寂寞的群眾\"、\"鱷魚手記\"等書成名文壇,但我之前並沒有讀過她任何的作品。我先在博客來看到這本書的試閱\,一讀上癮,便買了回家。買回家之後,一直放在我的床頭,有時間、有心情的時候就讀一點。 照理說,日記是一個人最私密的書寫,文字理應是晦澀的,但看她的文字,對我來說去卻相當的流暢。我想她的思維和我有某種程度的契合吧?! 她的日記充滿了對自己感情的自剖、對文學的熱愛,對寫作的堅持、對生命的熱情及質疑。不管是年少時談過刻骨銘心戀情的,或是曾動過獻身文學、藝術念頭的熱血青年,都能在她的文字裡找到相同的癡狂。 【爬上去,再利用寫作爬上去,埋頭苦寫,不相信你無法瞭解世界。生命的挫折正好有助於埋頭苦寫,不管世界。(1992/06/26) 】 讀完她的日記,最大的感動,是她對於以文學為終身職志這件事情,始終抱持著嚴肅的態度,嚴格地規範自己讀寫並行,另一方面督促自己達成預設的目標。當時她才二十一歲,還是台大心理系的學生。 【自己一定要寫作,如果不寫作或太久沒寫作人生就完全沒有意義,我生活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要寫作。(1994/01/16)】 讀完她的日記,最大的遺憾,當然是她最後選擇以自殺結束自己對愛情、對文學、對生命辯證。愛她的人少了一個朋友,中文文壇少了一個奇葩。我邊看著她日記中濃烈的情感,常想,被她以這樣強烈的感情愛著的人,未嘗不是痛苦啊!? 【死亡和瘋狂都沒什麼好害怕的,它們只是內心的幻象,我可以用更大的愛克服它們的,儘管我要再受多大的痛苦與折磨,我還是要述說愛是不滅的。(1995/04/14) 】 讀完了她的日記,最大的疑惑,還是為何她要選擇以自殺的方式,向這個她懷著遠大理想的世界告別。從日記的最後,以及我去書店稍微翻了一下蒙馬特遺書的內容,我猜想,答案應該就在蒙馬特遺書的字裡行間。好像是王爾德吧,說過,愛情只會有三種結局:愛我的人我不愛、我愛的人不愛我、相愛的人終須分離。凡是愛,總是有遺憾,如同蘇軾在水調歌頭裡寫到,「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這世界太寂寞也太冷寞,什麼樣的文章都有,就是沒有談論關於如何活著的東西,文學不就是訴說關於「如何活著」的事。(寫幾本書,有一個人可以愛)。就是這樣,人生只維繫在這個東西之上,其他的很難使人活下去。(1992/05/31) 】 在她身亡後十二年,這些日記問世。印刻出版設的文案上寫道:「如果沒有付印,原稿上這些鉛筆書寫的字跡,也許\再過幾年就會消逝了吧。像一個漸褪的夢,教人無法判清倒底發生過什麼,又是因為什麼而錯愕驚醒。」我在讀完後,沒有錯愕驚訝,只有點淡淡的惋惜,有時卻莫名地可以理解,她為何選擇這樣的方式離開人世。 就像櫻花凋零在最盛開的時分,她以自我了斷做為她對摯愛的文學及愛情的回應,像一顆彗星劃過天際,短暫而又燦爛。某種程度來說,我倒是有點羨慕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