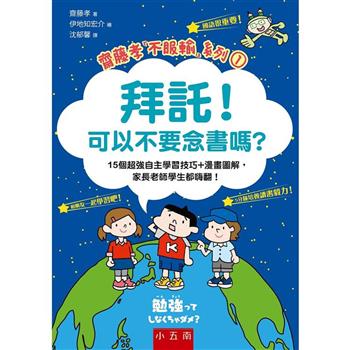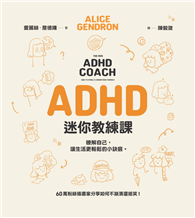名人推薦:
名家談朱天文
◎丁亞民:約是日本語吧,有句話是「女心」,這兩字望著真好,天文的人是那樣深那樣曲折婉轉,真是那女心無限了。
◎王德威:因著對官能世界的誘惑有著由衷好奇,對時間及回憶的虛惘有著切身焦慮;朱天文最好的作品掌握了道德與頹廢間的二律悖反關係,使她的世紀末視野,超越了顧影自憐的局限。
◎胡蘭成:那些好句子都是天文的人。
◎袁瓊瓊:天文的柔情大概託在散文裡;小說就一直地簡潔俐落,沒有忸怩之態,不帶廢辭廢筆,有種泱泱大氣。
◎黃錦樹:朱天文不僅從胡蘭成那裡習得神姬之舞而已。而是學了一整套的世界觀、認識論,它提供了一個整體的觀照,包含了文明/文化起源觀、歷史觀、美學觀等等...她的「後四十回」寫作修行毋寧是緘默的,她的關切不在那些易逝的、流變的「現象」,而是一些更為「本質」的事物。
◎詹宏志:一逕描寫熱鬧的、炫目的、芳香的事物,卻透露了腐爛前、衰敗前的有機分解,這位技藝圓熟、見解融達的朱天文是來到她寫作生涯的高處了。
◎舞鶴:在生活中,朱天文「讀物閱人」,物不離人,書寫來自她對「現實存有」的熱情;「物的情迷」正是她小說的特色,這種情迷頗似所謂「物之哀」,它也使作品中常出現的類「博物誌」書寫具有文學的美。
媒體推薦:
朱天文用《巫言》雕出心中的龍 /2008.01金石堂《出版情報》.文 蘇惠昭
還是從胡蘭成說起。
農曆年前好長一段時日,朱天文伏匿在家中校稿,夜以繼日,由最早的《傳說》開始,依時間序是《淡江記》《炎夏之都》《世紀末的華麗》《有思,乃在大海南》《黃金盟誓之書》《最好的時光》,以及她創作七年多,方才完成的二十萬字小說《巫言》,八本書跨越三十多年,如果以25歲作為分界點,25歲之前的作品如今讀起來,「哈!濫情到像神經病。」朱天文感覺到臉微微發熱,狠狠刮了自己一頓「如果不是為了存檔,留下紀錄,我寧可拿去銷毀。」
朱天文25歲那年,胡蘭成去世,而她開始下山。是的,下山。因為一段仙緣,朱天文姊妹親受胡蘭成調教,「吟哦詩禮中國,想像日月江山」。胡蘭成扮演智慧老人,賜給青春正盛的朱天文姊妹視野和高度,並且呼一口仙氣,把一生學問的總結灌進「三三集刊」一群才情洋溢的少男少女腦袋裡,「就像畫龍點睛吧!他點了睛,但我們卻還不知那龍長什麼樣子。」
張愛玲與胡蘭成,張愛玲的文學如今受到神樣的供奉,而胡蘭成至今還仍歸不了檔。
那麼對創作者來說,朱天文問自己,那樣輕而易舉就空降在顛峰,這究竟是幸還是不幸?她不敢給答案,只知道25歲以後自己就開始下山,一直一直的往山下走,求知識,累經驗,「花了快三十年只為了去畫出那條龍」。
朱天文以文字畫龍。
《世紀末的華麗》是朱天文畫龍的第一筆,「勾勒都會意志下疲憊眾生的存在狀態和精神狀態」文學評論家黃錦樹語;《荒人手記》如同「某類現代知識分子的懺悔錄」,這一短篇一長篇,黃錦樹都將之讀成「朱天文對『蘭師』的致敬致祭之文」,對朱天文來說,這也都是「畫龍」的過程,她越來越清楚看見龍的樣子,但要精確描述那龍,就必須「格物」,致知於人世間每一件細瑣俗凡的人情、物件、故事,不可思議的是,這又是她在與主流社會幾乎隔絕的狀態下靠著大量閱讀、日行餵貓溜狗和偶爾的出門或旅行完成,「我越來越是一個觀察者,包括觀察自己」,這也是朱天文七年多來寫作《巫言》的背景。
站在社會邊緣的邊緣觀看一切也明白一切,這樣的人即巫,而巫人的書桌即是巫界,朱天文伏首巫界以文字召喚意象,意欲寫出「巫事」與「巫途」,有時候沒日沒夜的於紙上施法,有時候又飄然他去,是以荒疏許多時日。
巫人寫紅酒族:「她們節衣縮食,練得一口紅酒經。其實她們喝紅酒的歷史老早在酒商炒作之前,為了酒裡的單寧酸說是健身、瀝脂而喝起來的,當時她們更喝別的酒。又其實喝酒是餘事,酒杯,才是主題。她們嚴格區分白蘭地酒杯、葡萄酒杯、香檳杯之間的差異」。巫人寫馬市長:「……故而存活下來的首長物種中,仔細考察,馬市長的眼睛是關上的。初步研判,因為帥,他不能打開眼睛。一打開,就會放電。為免電著群眾,以及自群眾迴向回來的電擊倒自己,馬市長將眼睛偽裝成淡漠無神的三白眼即、豬眼,形成了絕緣體、防護罩。」
更多時後巫人是在「我」的小宇宙裡穿行和考掘。
終於完成那一刻,「寫完了」朱天文用平常的語氣對朱天心說。朱天心驚問:「妳是不是該戲劇性一點?」
50歲,交出《巫言》,朱天文下得山來,在平闊無風的大地上,雕了一尾自己的龍,點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