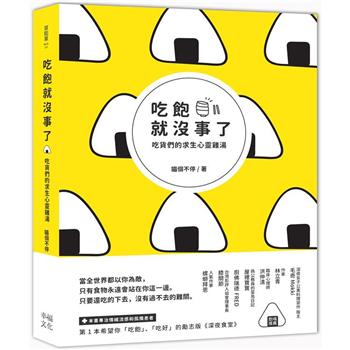楔子
『你要記得,你們不能分開,但是絕對不能在一起,這是命運,要勇敢接受,知道嗎?』
這是奶奶的遺言,只說給我聽的。
『奶奶跟你說了什麼?』
『……沒什麼。』
沒什麼…
這是命運,我要勇敢接受。
【第一回】
叮咚~地一聲,室外的冷風在自動門開啟的一瞬間咻地刮了進來,讓便利商店裏稀落的人都縮了縮脖子。
葉冬海走進便利商店拿了瓶熱咖啡,抬起手腕望了下時間。
十二點五十八分。
再二分鐘…
葉冬海想著,走到櫃檯結帳。中年男子不太熟練的按著收銀機,想是最近一到深夜就出現的那個菜刀大盜,讓老闆不敢在晚上用年輕工讀生。
「您辛苦了。」老闆朝葉冬海笑笑,不知道什麼時候包了二顆茶葉蛋一起塞給他。
葉冬海沒有推拒,朝老闆笑笑,然後走出便利商店。
又是叮咚地一聲,站在寒風裏,背後的自動門隔絕了一室溫暖。葉冬海把夾克拉鍊拉到最高。
再抬起手腕看了下。
一點零一分。
「ok!下班了~」葉冬海愉快的拎著咖啡和老闆的愛心茶葉蛋回到車上,脫下手套剝起蛋殼打算好好享用。
突然喀的一聲。
葉冬海愣了一下,他的手錶好像卡了一下,翻過手腕看看。
一點零六分。
葉冬海奇怪的放下手,眼前好像有什麼晃過,抬頭望向前方馬路,一輛機車正好從他眼前駛過,在前方遇到紅燈停了下來。
似乎是個年輕男孩。戴著全罩式安全帽看不到臉,個子不高,後座坐了個年輕女孩。
女孩有著長髮,長長地披散著快到腰部,隨風吹來飄呀飄的,看來很有教養的把二隻手放在膝上,雙腳優雅地併攏著側坐,這麼冷的天氣居然只穿了件絲質連身無袖洋裝,身子輕盈地像在隨風擺動。
葉冬海從警校畢業以來五年,因為單身所以執夜勤的比例比隊上大部份都結了婚的同事要來得多。他想起同事之間流傳的笑話。有執夜勤的同事,在攔下幾輛沿山路飛車的年輕男女,其中一個男孩咬著煙嘻笑著,酒味甚濃,後座那個酒紅色頭髮的女孩裝著一臉無辜的問『你看得見我嗎?』,一群年輕人哄笑了起來,一個女同事冷靜地一把將那個女孩從機車上扯下來,微笑著,「這個沒人看見的就留在山裏,其它的全帶回去。」。後來好一陣騷動才把人全帶回去。
葉冬海望著那個年輕人,還蠻有耐性的在沒車的十字路口上等綠燈亮了才起動。
「好吧,看在你那麼守交通規則的份上。」葉冬海嘆了口氣地放下還沒塞進嘴裏的茶葉蛋,開車跟上那個年輕人。
他並不想嚇到那個年輕人,於是緩緩的跟著,在下一個紅燈時攔下他。
年輕人有些訝異,脫下安全帽,有張稚氣的娃娃臉,黑白分明的眼睛看起來很純真。
「我、我騎太快了嗎?」年輕人有些慌張。
「駕照。」葉冬海走近,只望著手上的PDA。他沒有抬頭,可是他知道那個女孩在看他。
那年輕人乖乖的掏出駕照,葉冬海望了一下。
陸以洋,二十四歲。本人看起來比實際年紀小很多,像是只有十七、八歲的大男孩。
葉冬海把駕照還給他,回到車上拿出酒測儀。
陸以洋有些慌張,「我、我沒有喝酒。」
「沒有你怕什麼。」葉冬海把酒測器拿給他。「吹氣。」
陸以洋只好用力的吹著氣,然後還沒看清楚數值,葉冬海一把拿了回去。
「我只喝了一口,真的……」陸以洋有些心虛。
葉冬海望了他一眼把酒測儀收起來,「熄火下車。」
「欸欸?不是開單就好了嗎?」陸以洋睜大了眼睛一臉驚恐。
「深夜喝酒騎車有多危險你知道嗎?」葉冬海用著嚴厲的口吻。
「我、我知道…可是我真的只喝一口…」陸以洋覺得有些委屈。
「喝一口也是喝了,下車我載你,你的車明天再騎回去。」葉冬海命令著。
陸以洋只好乖乖的下車把車停好鎖好大鎖,葉冬海示意他坐在前座。他只好上車。
那女孩靜靜的看著,然後下車慢慢地、慢慢地滑到車邊,站在警車門邊,望著葉冬海。
葉冬海這才注意到,有個東西纏在她腳上,仔細一看原來是個嬰兒。
葉冬海猶豫了下,才走過去打開後車門,女孩緩緩滑上了車。他才回座去發車起動。
「有女朋友嗎?」葉冬海望了那陸以洋一眼。
陸以洋搖搖頭,把外套拉開些,「呼…車子裏暖好多,謝謝您。」
很純淨的微笑,葉冬海把後視鏡調了下,「不客氣。」
沿路無語,過了五分鐘,陸以洋注意到葉冬海不時地望著後視鏡,然後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低下頭半晌,陸以洋小聲的開口,「警察先生…」
「嗯?」葉冬海應了聲。
「其實…我酒測有過吧……」陸以洋有些猶豫的開口。
葉冬海望了他一眼,「對。」
陸以洋吞了口口水,「那…你剛剛開後車門……是不是因為有…有…要上車…」
葉冬海再望了下後視鏡,女孩乖乖的坐著。「你常常被跟嗎?」
陸以洋靜了一下,突然抱頭慘叫了起來,「哇哇哇~~果然又是!!我也不想呀!可是不曉得為什麼每個都要跟著我!!」
葉冬海被他的慘叫嚇了一跳,差點要踩下剎車,他又好氣又好笑的摸摸他的頭,「你冷靜一點。」
「對…對不起…」陸以洋低著頭,緩緩的偷偷朝後頭瞄了一眼,卻什麼也沒看到,一害怕又趕忙轉回來。
「你看不到嗎?」葉冬海開口。
「有、有時候看得到…有時候看不到,可是常常東西都被丟的亂七八糟…筆記本、報告也被塗得一團亂…晚上洗臉的時候偶爾抬頭在鏡子裏會看到…或者打開衣櫃的時候…」陸以洋一臉快哭出來的樣子。
葉冬海望了他一眼,不曉得該笑還是該同情他,「那種的都沒惡意,只是想開玩笑而已。」
「可是好可怕耶…」陸以洋睜大了眼睛一臉驚恐,像是隨時要哭出來。
葉冬海再調了下後視鏡,那個寶寶在後座爬來爬去,他很怕他想留在車上就糟了。
「你一定也常常被男人纏吧…遇過跟蹤狂嗎?」葉冬海開口。
「你、你好厲害!怎麼知道的。」陸以洋眨眨眼睛,崇拜的望著葉冬海。
葉冬海覺得有些目眩,這男孩太危險了,他那種純淨的氣質有任何東西纏上,他都不會覺得奇怪…
「那個…後、後面那個…是什麼樣的…」陸以洋見葉冬海一直很鎮定的樣子,小心的開口問。
「是位小姐,有很長的頭髮。」葉冬海隨口回著。
陸以洋愣了一下,「是個很漂亮的小姐,髮長到腰,下巴有顆痣嗎?」
葉冬海擰著眉,那女孩果然慢慢抬眼望了下陸以洋。
「不要加形容詞。」葉冬海開口。
「什麼形容詞?」陸以洋一頭霧水。
「舉凡會讓女孩子注意到的都不要加,你想被纏多久?」葉冬海沒好氣的回答。
「對、對不起。」陸以洋縮了縮頸子馬上道歉。「我想…我想她是我學長的女朋友…也算學姐…」
「你認識?」葉冬海望了他一眼。
「不算認識…有見過一、二次而已,也沒說過話…我離她最近的距離也只有早上陪學長去參加她的喪禮而已…為什麼要跟著我…」陸以洋扁著嘴,很委屈的模樣。
「因為她不知道該去哪裏,你很醒目,所以就跟著你。」葉冬海回答。
「醒目…我嗎?」陸以洋指著自己,表情有些茫然。「這麼一說…除了被…跟以外,我從小就常常被奇怪的男人跟蹤……收到奇怪的信,接到噁心的電話…我又不是女孩子,為什麼會這樣呢?」
葉冬海聳聳肩,「有人生來的氣質就是會惹上某些東西。」
陸以洋很煩惱的揪起眉心,然後半天才微微側著頭朝後面喊話,「那個…妳趕快回去好嗎…我知道學長對妳不好…可是妳…那樣了…他也很難過呀…你還是早點超生比較好…」
葉冬海差點爆笑出來,伸手揉揉他的頭,「你別傻了,這樣就會走的話就不用跟著你了,不要同情她。」
陸以洋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對了、你要載我去哪裏…」
「警局,她進不去,應該自己待一陣子就會離開了。」葉冬海回答著。
「是嗎…那她會怎麼樣…?」陸以洋有些擔心的問。
葉冬海望了他一眼,「在路邊晃到有人渡她走為止,不是叫你別同情她?」
「喔…可是…她好…」可憐這二個字還沒說出口,被葉冬海瞪了一眼不敢說出來。
「難怪你會被跟,不要做無謂的同情,同情她對你並沒有好處,讓她一直跟著你對她也沒好處。」葉冬海嚴厲的開口。
「嗯…」陸以洋低下頭,看來有些難過。
「還、還沒請問你的名字…」陸以洋偷望了葉冬海一眼。
「葉冬海,冬天的冬,海洋的海。」簡單的介紹自己。
「你…都看得到嗎?」陸以洋好奇的問。
「嗯。」應了聲,葉冬海沒有多說。
停了半晌,陸以洋才鼓起勇氣開口,「那、那你不能幫幫她嗎……」越說越小聲。
葉冬海偏頭瞪了他一眼,「我為什麼要幫她。」
陸以洋思考了很久,大概是沒想出理由,沮喪的低下頭。
葉冬海嘆了口氣,「你住哪?」
「本來住新莊…」陸以洋沒力的開口,同情心大概取代了他的恐懼。
「本來?」葉冬海掃了他一眼。
「嗯…一起住的室友好像去地下錢莊借了錢就跑,討債公司每天上門鬧,房東氣的把我也趕出去了…本來想說去中壢的朋友家暫住…可是學長又叫我陪他參加喪禮,結束後又喝個不停,就搞的好晚了……哈哈…」陸以洋傻傻的笑著。
葉冬海翻翻白眼,他沒見過那麼笨的小鬼。
放棄的回轉車道,一路上沒有再說話,葉冬海把警車直接開回家。「下車。」
「呃…是…」陸以洋忙下了車。見葉冬海繞到他這一頭打開後車門,連忙退了好幾步。
陸以洋望著葉冬海扶著車門一陣子,突然不耐地開口。「你也給我下來。」
陸以洋再退了二步,『也』的意思就是不只一個……
葉冬海瞪了陸以洋一眼,「你想退到哪裏去,過來。」
陸以洋乖乖的跟著葉冬海走進一棟外觀相當華麗的大樓,起碼不太像一個交通警察會住的地方。
跟管理員打了招呼,走進了電梯,在密閉的空間裏,陸以洋覺得特別的恐懼,不由自主的貼近葉冬海。
葉冬海笑著,「要不要我叫他們搭下一班呀?」
陸以洋用力的點點頭,看見葉冬海的笑容才發現他在開玩笑,臉上一熱退開了小半步。
電梯上了二十三樓,似乎是頂樓,葉冬海取出磁卡開門。
陸以洋茫然地望著那扇縷空雕花的青銅色大門,要不是葉冬海穿著制服,他開始懷疑起眼前這個人是不是真的是一個交通警察。
一進門就感到暖氣襲了過來,陸以洋脫下外套,跟著葉冬海穿過寬大的玄關,看見一個明亮莊嚴的客廳,整室柔和的白色光線,原木長椅上頭雪白的軟墊一塵不染,大理石地板光可鑑人,正前方的木雕神壇佔了這個廣大客廳的四分之一。陸以洋張著嘴看著,最令人注目的還是神壇上那座半人高的白玉觀音像,飄忽的衣帶似乎隨時都要飛起,水瓶裏的柳枝似乎真有水滴下來,臉上莊嚴慈愛的神情讓人想就地跪下來。
「唷,真難得,是人耶。」
陸以洋愣了一下,循聲望見長椅上躺著個人,看起來大約二十五、六歲,頭髮稍長,穿著件無袖背心,右肩頭到手臂上觸目驚心的龍鳳刺青簡直像個流氓,那人看起來很隨便的把腳抬在大理石桌上,懶洋洋的開口。
「別理他。」葉冬海對著陸以洋開口,然後走到神壇前燒起香來。
那個男人朝陸以洋後面望了一下,陸以洋以為那男人在看他,有禮貌的點點頭,那男人卻突然間跳了起來,伸手從被他躺得亂七八糟的軟墊下拉出一件皺巴巴的黃色長杉,雙手一轉就套在自己身上,陸以洋仔細一看居然是件道袍。
「哪來妖孽!敢踏進我觀音殿中!還不速…」
陸以洋目瞪口呆的看著那男人不曉得從哪裏抽出把木劍,話沒講完被點完香的葉冬海從後面一腳踹了下去。
「欸!會痛耶!」那男人撫著腰回頭瞪著葉冬海。
「閃遠點,要發瘋到樓下發去。」葉冬海沒理他,把香交給陸以洋。「去拜觀音大士。」
「喔、喔…」陸以洋趕緊走過去誠心的拜了拜,然後依葉冬海的指示把香插好。
那個女孩進了門就盯著神壇沒有動。
「妳還不走,想一直待到什麼時候?」葉冬海望著那個女孩。
那女孩才慢慢側頭望葉冬海,本來沒有表情的臉上此時看來有些迷惑。
葉冬海望著神壇,「妳沒看見嗎?」
陸以洋也愣愣的望著神壇,他似乎看見了白玉觀音像上發著白光,像是直通著天上。
女孩也慢慢的往前移動,拖著她的寶寶。
葉冬海搖搖頭,「孩子抱好,妳做媽了不曉得嗎?連孩子也不會抱。」
女孩茫然的望著葉冬海,再慢慢的低頭,然後緩緩的彎下身去笨拙的抱起未成型的寶寶。然後一步步走白玉觀音像,最後消失。
「你什麼時候那麼好心我怎麼不曉得?」那男人索性橫躺在地上,單手撐著頭看著葉冬海。
「不用你多事。他會在這裏住幾天。」葉冬海用著冷淡的口氣,伸手拉過陸以洋卻像是在徵求那個男人的同意。
陸以洋見那男人盯著他,覺得有點緊張,仔細一看,那男人有張相當俊秀的臉,但此刻那張漂亮的臉看來並沒有很高興,他抬頭想開口,「我想我…」
話沒說完被葉冬海瞪了一眼忙閉上嘴,想想現在是半夜二點多了,車也沒騎過來,從這裏走出去也沒地方可以去,說那種客套話只是多餘而已…。
「叫什麼名字。」那男人突然開口。
「我姓陸,陸地的陸,以為的以,海洋的洋。」陸以洋趕忙開口。
「幾歲?」聽了他的名字,那男人擰了下眉心,又開口問。
「二十三了…」陸以洋回答。
「屬羊…」那男人扳起手指不曉得在算什麼,看模樣還真像是個道士,也不像神經有問題的樣子,陸以洋滿心的疑惑。
放下手那男人像是在瞪他,陸以洋有點不知所措的望著葉冬海。
葉冬海對他笑笑,像是叫他不用擔心。
「八天以內給我滾出去。」那男人突然站起身,不曉得是在生氣還是怎麼了,突然跳起身走進神壇左邊走廊。不久就聽見砰地一聲甩門聲。
「對、對不起,我明天會快去找房子的,給你添麻煩了。」陸以洋抱歉的對著葉冬海,自己好像給他添了麻煩。
「他就那死樣子,別理他,我明天會幫你留意有沒有合適的房子。」葉冬海拍拍他的頭。
直覺自己似乎是被當成了小孩,陸以洋紅了紅臉,「我明天也會自己去看看的,讓你費心了。」
「還在唸書吧?」葉冬海望著他一副學生樣。
「嗯,研一。」陸以洋點點頭,想了想又開口,「你為什麼要這麼幫我呢?」
「就撿到了,不然怎麼辦?」葉冬海扯著他走向神壇右邊走廊。
撿到……我、我是流浪狗嗎…
陸以洋一臉茫然的走進去才曉得,原來神壇後面是通的,左右共有四間房。
葉冬海打開最靠近客廳的房間,「先睡這裏吧,裏面就有浴室,早上六點吃早餐、十二點中餐、六點晚餐、十一點宵夜,早餐會有人叫你,一定要起來吃,這是我們家規,其它的不吃隨便,過了時間就自己出去解決,廚房不會有東西給你吃知道嗎?」
「呃…嗯,知道了。」陸以洋忙點頭。
「早點休息吧,我還得回警局,有事打電話給我。」葉冬海抄了張紙條給他就轉身離開。
陸以洋關上房門,望著太過舒適華麗的擺設,一時間之不曉得該往哪裏坐,不過待在這個房子裏的感覺又溫暖又舒服,他這一生中,第一次毫不猶豫的打開任何在往都會有東西跑出來嚇他的門。
也是頭一次睡在床上的感覺能如此安穩。他想著,明天一定要再好好的謝謝葉冬海。
如果能一直這樣下去的話,就算做流浪狗也無所謂,陸以洋舒服的讚嘆著。
【第二回】
『阿洋,阿洋不要再睡了,要遲到了,阿婆煮了芋頭稀飯唷,快起來吃。』
啊啊~~芋頭稀飯~~我要吃我要吃~~
睜開眼睛看到的是和外婆相仿地佈滿了風霜的臉,一張帶笑的溫柔臉龐。
陸以洋一時之間反應不過來,怔怔地望著那位婦人。
「抱歉呀,你門沒鎖我就進來了,喜歡芋頭稀飯的話我明天煮好嗎?」
婦人微笑著,手上抱著他昨夜扔在椅子上的衣服,陸以洋不自覺地點點頭。「好…」
「快六點了唷,刷牙洗臉好吃早餐了,衣服我拿去洗。」婦人笑著對他點點頭,離開時幫他帶上房門。
陸以洋怔了半晌才回過神。
那…那是誰呀…這、這裏是哪裏…
抱著頭思考了半天,才想起來昨夜被一個好心的警察大哥當成流浪狗撿了回家。
啊、六點要吃早餐…
陸以洋跳了起來,衝進浴室,隨意地梳洗。
從洗臉盆抬起臉,望著鏡子的時候,陸以洋怔了下。
鏡子裏除了自己什麼也沒有。
他伸手摸摸鏡子,「…這才是正常的吧…」
沒有突然出現在鏡裏的鬼東西,也沒有那種恐懼的感覺,這才是正常的。
陸以洋不由自主地開心起來,把亂七八糟的頭髮梳好,愉快地準備去吃早餐。
一開房門就聞到線香的味道,有點像沉香,但又沒有沉香那麼濃的味道,是很古樸的香氣。陸以洋走到客廳,看見昨夜那個不太歡迎他的年輕人正盤腿坐在觀音前,身前焚著香,閤著雙眼像是在打坐。
陸以洋不敢吵他,主人坐在那裏他也不好意思亂走,只好靜靜的站在一邊。仔細端望著那個青年,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明明昨夜看起來是個暴躁又隨興的人,現在安靜打坐地樣子看起來,就像面前的觀音像一般地…莊嚴肅穆?
陸以洋覺得自己的形容詞用得不太好,正皺起眉來想著有沒有好點的形容詞,那青年突然睜開眼狠瞪了他一眼。
我、我有說出口嗎……
陸以洋嚇了一大跳,小退了二步,確定自己應該沒有開口。「…早、早安…」
青年又瞪了他一眼,像是不甘不願地冷冷地回答。「早。」
陸以洋鬆了口氣,起碼對方有算是善意的回應…
看著青年起身,把燒完的香爐拿起,放在神桌上。
陸以洋鼓起勇氣,在青年完成所有的動作回身的時候,才開口詢問。「對不起,我還沒有問您的名字…。」
青年望著他半天,才開口,「我姓夏,夏春秋。」
啊、沒有冬天…
陸以洋胡亂地想著,朝著夏春秋點點頭,「不好意思突然來打擾您,我會盡快找到房子離開的。
「請你盡快。」夏春秋丟下這句話,轉身走向客廳另一頭的走道。
陸以洋有點喪氣,他很少遇到有人對他擺出那麼明顯的厭惡。
果然不速之客是很惹人嫌的…
他站在原地替自己哀悼了會兒,聽見開門的聲音,葉冬海從玄關走了進來,看見陸以洋站在那裏發呆,朝他展開微笑,「你杵在那裏幹嘛?不是告訴你六點吃早餐嗎?」
「嗯,我、我正在想飯廳在哪裏…」陸以洋不好意思地笑了下。
葉冬海走過來,把外套往長椅上扔,順手摸摸他的頭,「飯廳在另一頭的走道,你沒看見春秋嗎?」
陸以洋縮縮頸子,葉冬海的手有點冷,外面的氣溫應該很低,不過他並不討厭這種被當成小孩的感覺,這讓他想起他好久沒回去的老家。
「剛剛有看到,我和他道了早安。」陸以洋露出可愛的微笑。
「春秋個性有點任性,要是有哪裏不禮貌的話你別介意。」望著他的笑臉,葉冬海忍住伸手去捏他的臉的衝動。
「別這麼說,他看起來人很好。」陸以洋想著會有那麼…莊嚴肅穆?…的神情,那一定是個好人。
陸以洋自己隨意的下了定論,然後和看起來很愉快的葉冬海一起走進飯廳。
◇
一頓極為愉快的早餐,陸以洋滿足地抱著吃撐的肚子。
除了他討厭吃香菇,在葉冬海笑著悄悄把盤子推過去,示意他把香菇放上去的時候,夏春秋很剛好地打翻了牛奶,讓煮得一手好菜的素香婆婆看見,用關愛的眼神望著他把香菇硬吞下去以外……
其它都算得上非常美好,餐桌上雖然沒有出現芋頭粥,但是鮮魚粥加上七、八種自製的醬菜、軟嫩鬆滑的菜埔蛋,現炒的香味十足又熱騰騰的肉鬆,還有撒上大把細蔥和柴魚醬油,溫熱柔軟得像是布丁的傳統豆腐,陸以洋想著想著,口水又要滴下來…
不過他倒是很驚訝,他以為這麼供佛的家裏應該是吃素的,看來並不是的樣子…
陸以洋一邊回想著他美好的早餐,一邊打開實驗室的門。
他一向是第一個來開門的人,雖然他很討厭打開門後看見一片漆黑的感覺。
他總會想著那一片漆黑裏有多少一般人看不見的東西在蠢動著。
握著門把,一如往常地深吸了口氣,旋開門把。
陸以洋衝了進去,在一片黑暗中,快速的摸著左邊牆上的電燈開關。背後傳來啪地一聲,他覺得自己的心臟也重重地跳了下。
陸以洋緩緩地回頭。黑暗中,一個人影慢慢的從寬大的實驗桌上爬了起來。
陸以洋的手摸上牆壁,想要開燈,卻半天摸不到開關。
只見高大的人影越昇越高,像是在伸懶腰一樣的舉起來雙手。
咦?
陸以洋愣了下,鬼需要伸懶腰嗎?
「是小陸嗎?這麼早…哈啊~~~」
熟悉的聲音和懶洋洋的哈欠聲,伴著一陣酒味而來,卻讓陸以洋一下子安心了起來。
一安心下來,隨手一摸就摸著了本來就該在那裏的電燈開關。
「…學長,為什麼老愛睡我們家的實驗室…」
「你們家比較乾淨嘛…。」易仲瑋聳聳肩,轉了轉僵硬的身軀,從實驗桌上跳下來。
…那是因為我有在打掃好嗎…
陸以洋扁扁嘴,望著那一團被易仲瑋拿來當棉被的,好像是他前一天才剛洗好的窗簾…
嘆了口氣,認命的去把窗簾折好,只是才抓起來就聞到撲鼻的酒味。
得再洗一次了…
邊把窗簾折起,邊看著從桌上跳下來,換坐到椅子上的易仲瑋。
陸以洋把剛剛在超商買的咖啡和準備當下午點心的飯團塞給他。
「啊啊~~小陸真貼心,還知道幫我帶早餐。」
易仲瑋笑著,卻只拿了咖啡。陸以洋想他大概也沒有食慾。
「學長,你先洗把臉吧,不然等一下顧學長來了發現你睡在我們實驗室會生氣唷。」陸以洋把實驗室的窗簾全拉開,再把窗子打開,冷冽的風灌進室內,讓酒氣散了去。
易仲瑋把咖啡擱在桌上,拉著椅子坐到了窗邊,把手枕在頭下趴在窗檯上,像是沒睡飽一樣,就這麼趴著單手點了隻煙。
「…學長,我們家禁煙…」
易仲瑋笑著,把夾著煙的手,伸到窗外整條手臂掛在窗檯上。
陸以洋邊收拾易仲瑋造成的一團亂,邊想著到底要不要問。「…學長…」
「嗯?」
「…那個…學姐她…是不是懷孕了?」
易仲瑋望了他一眼,「小顧說的?」
陸以洋勉強地笑了下,總不能說是他『看』到了…
易仲瑋倒也沒追究,吸了口煙再朝窗外吐去。「嗯,她懷孕了。連我在內,都是在她出事那天送到醫院去才知道,之後她爸一直覺得她死是我讓她懷孕的錯,要我在靈堂跪了好幾天跟她道歉,我爸媽大概連冥婚的打算都做好了。」
陸以洋一直覺得,自從學姐出事以來,易仲瑋的態度就很怪,說他不難過也不是,說他很難過也覺得哪裏不對…
易仲瑋是他大學時的直屬學長,人很有趣而且玩起來很瘋,在系上算是很活躍的人物,因為一張像偶像明星的俊秀臉容,大學四年換了八個女朋友,每一個都變成他的『好朋友』,沒有一個女孩說他壞話,這也是讓人稱奇的事蹟,最後一個女朋友能交到研究所都沒被換成好朋友,大家都以為學姐是他的真命天女了,卻沒想到會因意外過世。
陸以洋覺得,易仲瑋其實早就把學姐歸類為『好朋友』,只是學姐沒有提分手吧…。易仲瑋是那種從來不主動提分手的人,所有人都覺得易仲瑋對女生很好,是很寵女孩子的那種人,陸以洋想自己大概是唯一一個對易仲瑋說他對學姐不好的人。
他當時這麼說之後,易仲瑋看起來卻很高興,笑著說我們大概是同類吧。然後摸摸他的頭就走了。陸以洋那時一頭霧水,他以為他會惹易仲瑋生氣。
就像大家都說易仲瑋是很好熟,很好瞭解的人一樣,陸以洋覺得其實易仲瑋把自己藏的很好,沒人能瞭解他在想什麼。
現在想想,易仲瑋大概根本沒有真的愛過他的女朋友們吧。
「不過呀…孩子不是我的。」易仲瑋突然冒出了一句。
「嗄?」陸以洋愣了下。
「孩子的父親是她家教學生的哥哥,他看我跪著道歉了好幾天,昨天終於忍不住衝到靈堂來說孩子是他的,不曉得是有罪惡感還是不甘心我認了他的孩子當爸。」易仲瑋吐出一個漂亮的煙圈。
「…那、那你為什麼一開始不說?」陸以洋看著他的態度,應該是開頭就知道那孩子不是他的。
「說出來多丟臉呀,女朋友劈腿耶。」
陸以洋撇撇嘴角,易仲瑋從來就不怕丟臉。
「學長對女孩子好是最大的優點也是最大的缺點吧。」陸以洋望著易仲瑋露出不置可否的笑臉,邊打開櫃子。
「啊啊~還是小陸最瞭解我了。」易仲瑋笑著說。
「…我才不瞭解學長哩…」陸以洋回頭想把放在櫃子裏的培養土拿出來。
回頭後看見的不是他的培養土,而是一雙睜得太大的眼睛,大到看得清眼球上下的眼白有著紅色的血絲。
那是一顆頭,鮮血從頭上流下滑過了那對圓睜的眼睛再滑落沒有血色的臉頰。
一滴、二滴,滴在洗手檯上。
而那顆頭正慢慢地慢慢地朝前移動。直到滾了下來,重重地摔在洗手檯上。
恐懼的感覺又回到了全身,陸以洋全身冰冷,易仲瑋好像在說些什麼,聲音卻很遙遠。
他望著那顆在洗手檯上滾來滾去的頭,視線移到牆上,灰白的牆上浮出一個身體,頸上冒著鮮血,搖搖晃晃地摸索著像是在找她的頭。
「哇啊~~~~~」陸以洋忍不住地叫了出來,退了好幾步撞到實驗桌上。
「小陸?怎麼了?」易仲瑋熄了煙起身走了過來。
陸以洋驚恐地望著那個無頭女伸手摸索著到處走動。他伸手指著那顆在洗手檯上的頭,掀了掀唇想開口卻不知道該說什麼。
易仲瑋順著他的視線望著洗手檯,回頭用詢問的神色望著他。
半天,陸以洋才勉強出聲。「……………蟑…蟑……蟑…螂…」
易仲瑋愣了下,也沒嘲笑他,伸手摸摸他的頭。「不要怕,學長幫你打。」
說著走近洗手檯找了半天,順便連櫃子也翻了翻,最後把他的培養土拿出來,回頭望著陸以洋,「大概跑掉了,你要拿培養土對嗎?」
陸以洋望著那個無頭女摸索回洗手檯邊,眼看要碰到易仲瑋了,陸以洋提起勇氣把包包提起來,邊搖頭邊衝過去把櫃子關起來,拉住易仲瑋就跑。「學長我們去吃飯吧!」
「啥?你不是要做實驗?」一頭霧水的易仲瑋只來得及放下培養土跟抓起自己的外套,就被陸以洋扯了出去。
直到跑出大樓外,陸以洋坐在樓梯口喘著氣,易仲瑋常常運動倒是不覺得喘,彎腰望著陸以洋,「不曉得你這麼怕,我去買點蟑螂藥好嗎?蠻有效的,過幾天再幫你拿去丟就好了。」
易仲瑋對他說話的語氣總是很溫柔,陸以洋想起他在大三的時候說過,『學弟要好好照顧,學妹是用來寵的。』
可是從來也沒見他這麼照顧學弟,倒是真的很寵學妹。
「…學長,其實你把我當學妹吧…?」陸以洋沒頭沒腦的冒出一句。
易仲瑋笑了起來,居然也沒有產生疑問的,矮身下來平視著他,「是呀,因為小陸比學妹更可愛哪。」
陸以洋扁起嘴,起身拍拍褲子上的灰塵。倒不是不高興,只是有點鬱悶自己這張娃娃臉,如果自己長得像易仲瑋那樣高大俊挺就好了,倒不求有他那張偶像明星般的英俊臉容,只要有張更男人點的臉,就不會老被歸類成老弱婦孺了…
不奢望惹學姐妹們尖叫,至少不想被當成玩具或姐妹…
易仲瑋的笑臉常常帶點無所謂的感覺,自己擺出那種笑容卻像是小朋友賭氣…上天真是一點也不公平…
望著陸以洋鬱悶的臉,易仲瑋像是知道他在想什麼似的,也沒有再笑他,只是站起來拍拍他的肩。
「謝謝你剛剛的咖啡,學長請你吃飯好了。」易仲瑋笑著。
「那我要吃知多家。」陸以洋倒是一點也不客氣。
「…小陸你比學妹還狠…」易仲瑋苦笑了下,倒也沒拒絕。
跟易仲瑋走在同學們都引以為傲的林蔭大道上,陸以洋想著,如果能告訴易仲瑋,學姐和孩子安心的離開了的話,也許他會好過一點。
但是他說不出口,也不知道該怎麼說,他可以料想得到,易仲瑋不會把他當神經病,只會摸摸他的頭說謝謝他的安慰而已。
嘆了口氣,陸以洋決定,還是什麼都不要說來的好。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示見之眼(1):深夜一點零六分的偶遇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90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示見之眼(1):深夜一點零六分的偶遇
深夜一點零六分,陸以洋無故被交警葉冬海攔下。
「經常被男性糾纏」這樣的命運還算小case,但比吸塵器還強力的吸引鬼魂體質才讓人欲哭無淚。
就像現在,他只是去參加學姊的葬禮,為什麼學姐就跟他回來了!?
從實驗室的無頭女鬼到電梯裡那雙帶著惡意的眼睛。
從眾多學長的關懷到被好心的交警撿回家住。
陸以洋的「新生活」,仍然從旺到不行的男人運和撞鬼運開始……
章節試閱
楔子
『你要記得,你們不能分開,但是絕對不能在一起,這是命運,要勇敢接受,知道嗎?』
這是奶奶的遺言,只說給我聽的。
『奶奶跟你說了什麼?』
『……沒什麼。』
沒什麼…
這是命運,我要勇敢接受。
【第一回】
叮咚~地一聲,室外的冷風在自動門開啟的一瞬間咻地刮了進來,讓便利商店裏稀落的人都縮了縮脖子。
葉冬海走進便利商店拿了瓶熱咖啡,抬起手腕望了下時間。
十二點五十八分。
再二分鐘…
葉冬海想著,走到櫃檯結帳。中年男子不太熟練的按著收銀機,想是最近一到深夜就出現的那個菜刀大盜,讓老闆不敢在晚上用年輕工讀生...
『你要記得,你們不能分開,但是絕對不能在一起,這是命運,要勇敢接受,知道嗎?』
這是奶奶的遺言,只說給我聽的。
『奶奶跟你說了什麼?』
『……沒什麼。』
沒什麼…
這是命運,我要勇敢接受。
【第一回】
叮咚~地一聲,室外的冷風在自動門開啟的一瞬間咻地刮了進來,讓便利商店裏稀落的人都縮了縮脖子。
葉冬海走進便利商店拿了瓶熱咖啡,抬起手腕望了下時間。
十二點五十八分。
再二分鐘…
葉冬海想著,走到櫃檯結帳。中年男子不太熟練的按著收銀機,想是最近一到深夜就出現的那個菜刀大盜,讓老闆不敢在晚上用年輕工讀生...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拾舞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05-15 ISBN/ISSN:986690467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