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房子
星光從天空消失的那個晚上,我十二歲,那對雙胞胎十三歲。
那是十月,萬聖節的好幾個星期之前,羅頓家有一場大人才可以參加的宴會,於是我們三個小鬼就被趕到地下室去。羅頓家的大宅,我們都叫它大房子。
關到地下室,根本算不上處罰。對黛安和傑森來說,那不是處罰,因為他們本來就喜歡一天到晚窩在地下室。對我來說,當然也不是。他們的爸爸老早就宣布過,在他們家裡,什麼地方是大人的,什麼地方是小孩子的,界線劃分得很清楚。不過,我們這裡有一套最高檔的電玩平台,有電影碟片,甚至還有一座撞球台……而且,大人管不到。除了楚羅太太,不會有大人到這裡來。她是這家常用的宴會服務員。大概每隔一個鐘頭,她就會跑到樓下來開小差,逃避送小菜,順便跟我們講一些宴會裡的最新八卦。(惠普公司的一個傢伙當眾出醜,對方是郵報專欄作家的太太。有一個參議員在書房裡喝得爛醉。)樓上的音響系統播放著驚天動地的舞曲,像大怪獸的心跳聲,穿透地下室的天花板。傑森說,我們什麼都不缺,就是缺少清靜,缺少天空的景觀。
清靜和天空的景觀。以傑森的脾氣,他兩樣都要。
黛安和傑森兩個人出生的時間只隔了幾分鐘,但很明顯看得出來,他們是異卵兄妹,而不是那種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同卵雙胞胎。除了他們的媽媽,沒有人會叫他們雙胞胎。傑森曾經說,一個兩極的精子分裂,分別侵入兩個屬性完全相反的卵子,而他們就是這種過程的產物。黛安和傑森差不多,智商也是高得驚人,不過,她比較不像傑森那麼愛搬弄術語。她形容他們兩個人是:「從同一個細胞牢房裡逃出來的兩個不同的囚犯。」
他們兩個人都同樣令我敬畏。
傑森十三歲的時候,不但聰明得嚇人,體格也很強壯。雖然不是肌肉特別發達那一型的,卻是體力充沛,是田徑場上的常勝軍。那個時候,他的身高已經將近六英尺,瘦瘦長長的,長相有點呆,還好他那歪著嘴的純真笑容,使得他看起來比較不那麼呆。當年,他有著一頭像鐵絲一樣硬梆梆的金髮。
黛安比他矮了五吋,只有在跟她哥哥比的時候,才算得上胖,膚色也比較深。她的臉晶瑩剔透,眼睛四周長了一圈雀斑,看起來像是戴上了套頭外衣的兜帽,臉的上半部籠罩在陰影中。她曾經開自己的玩笑說:我的浣熊面具。我最喜歡黛安的地方,就是她的微笑。以我當時的年紀,她這些小地方顯然已經開始令我著迷,雖然還不太明白是什麼道理。她很少微笑,但笑起來很燦爛。有人說她的牙齒太凸了,她自己也這麼認為,可是我不覺得。所以,她養成了一種習慣,大笑的時候都會把嘴巴摀起來。我喜歡逗得她開懷大笑,但內心偷偷渴望的,是她那燦爛的微笑。
上個禮拜,傑森的爸爸送給他一副很昂貴的雙眼天文望遠鏡。整個下午,他興奮得一秒鐘也靜不下來,抓著望遠鏡玩個不停。電視機上面有一幅裱著框的旅遊風景海報,他對準那張海報,假裝自己從華盛頓的郊區可以偷看得到墨西哥的坎昆島。後來,他終於站起來說:「我們應該去看天空。」
「不要,外面好冷。」黛安毫不遲疑地回答。
「可是天氣很好。這個禮拜,一直到今天晚上天氣才放晴。而且,外面只不過有點涼。」
「今天早上草坪都結冰了。」
「那是霜。」他反駁。
「已經半夜了。」
「現在是禮拜五晚上。」
「我們不准離開地下室。」
「我們只是不准去吵到他們的宴會。沒有人說我們不能出去。如果妳是怕被逮到,放心,不會有人看到的。」
「我才不是怕被逮到。」
「那妳在怕什麼?」
「怕在外面把腳凍成冰塊,還要聽你囉嗦個沒完。」
傑森轉過來看我。「怎麼樣,泰勒?你想看看天空嗎?」
這對雙胞胎意見不合的時候,老是要抓我當裁判,令我很不自在。不管我怎麼回答,都裡外不是人。如果我和傑森一個鼻孔出氣,好像冷落了黛安;可是,如果我老是和黛安站在同一邊,看起來好像……呃,滿明顯的。於是我說:「我不知道,小傑,外面好像滿冷的……」
幫我解套的是黛安。她一隻手搭到我肩上說:「沒關係,出去透透氣也好,強過在這裡聽他抱怨個沒完。」
於是我們在地下室的玄關抓了件外套,從後門溜出去。
我們幫大房子取這個綽號其實是有點誇張的,它沒有那麼大。不過,在這個中高階層的社區裡,它還是比一般的住宅要來得大一點,占地也比較廣。屋後是一大片修剪得很整齊的草地,如波浪般起伏。再過去,草地被一片野生的松樹林擋住了。樹林像邊界一樣,另一頭緊鄰著一條有點髒髒的小溪。傑森在房子和樹林中間選了一個觀測星星的地點。
十月以來,天氣一直很舒適宜人,直到昨天,一道冷鋒入侵,才趕走了暖烘烘的秋老虎。黛安裝模作樣,抱著肋骨發抖,其實只是為了要給傑森一點顏色看。夜晚的風有點涼颼颼的,但還不至於冷得受不了。天空如水晶般清朗透澈。草坪相當乾爽,儘管明天一早可能又會結霜。天空萬里無雲,看不到月亮。大房子燈火輝煌,看起來就像一艘密西西比河上的蒸氣輪船。窗口透出金黃的燈光,像虎視眈眈的眼睛,掃視著外頭的草坪。不過,根據過去的經驗,在這樣的夜裡,如果你站在樹蔭下,就會像是被吸入黑洞一樣,徹底消失,從屋子裡絕對不可能看得見。
傑森仰臥在草地上,舉起望遠鏡對準天空。
我翹著腿坐在黛安旁邊,看她從外套口袋裡掏出一根煙,可能是從她媽媽那裡偷來的。(卡蘿•羅頓是一位心臟科醫生,雖然號稱已經戒煙,可是梳妝台、書桌、廚房抽屜裡還是藏著好幾包煙。這是我媽告訴我的。)她把煙叼到嘴上,用一個半透明的紅色打火機點燃,火光在四周的黑暗中顯得明亮無比。她吐出了一縷煙,煙霧盤旋而上,消失在黑暗中。
她發現我在看她。「想不想來一口?」
傑森說:「他才十二歲,麻煩已經夠多了,他可不想再得肺癌。」
我說:「當然想。」這正是展現英雄氣概的大好機會。
黛安很開心地把煙遞給我。我試著吸了一口,好不容易才憋住沒有嗆出來。
她把煙拿回去。「小心別上癮了。」
傑森問我:「泰勒,你懂星星嗎?」
我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沒有煙的乾淨空氣。「當然懂。」
「我不是指你從那些廉價科幻小說裡看到鬼東西。你有沒有辦法叫得出隨便一顆星名字?」
我臉紅了。希望這裡夠暗,不會被他看見。「大角星,」我說:「半人馬座,天狼星,北極星……」
傑森問:「哪一顆是星艦迷航記裡,克林貢人的母星?」
「少惡劣了。」黛安說。
這兩個雙胞胎都具有超乎年齡的聰明。我並不笨,但還夠不上他們那個天才的族群。這一點,我們都心知肚明。他們上的是資優兒童學校,我則是跟別人擠公車上公立學校。我們之間有許多明顯的差異,這是其中之一。他們住在大房子裡,我和媽媽則住在大房子庭院東側最邊邊的小屋子裡。他們的父母追求事業上的飛黃騰達,而我媽媽在他們家裡幫忙打掃。我們知道那種差異,但很奇怪地我們就是有辦法不把它當一回事。
傑森說:「那好,你能不能指給我看,北極星在哪裡?」
北極星,北方之星。我曾經在書裡面讀過南北戰爭和黑奴的故事。有一首歌描述逃亡的黑奴:
當太陽開始回歸,鵪鶉發出第一聲啼叫
追隨那酒瓢
老人正等待著你,他會帶你奔向自由
只要你追隨那酒瓢
「當太陽開始回歸」是指冬至過後。鵪鶉會到南方過冬。酒瓢就是北斗七星。瓢柄的尾巴指著北極星,指向北方,那是自由的方向。我找到了北斗七星,滿懷希望地朝著它揮揮手。
「你看,我就說嘛。」黛安對傑森說。似乎他們也不怕我知道,他們曾經因為我的事情有過爭辯,而我證明了黛安是對的。
傑森也沒話說。「還不錯嘛。那你知道什麼是彗星嗎?」
「知道。」
「想看看嗎?」
我點點頭,在他旁邊躺下來。抽了黛安那口煙,嘴巴裡還是有一股苦苦辣辣的味道,心裡有點後悔。傑森教我怎麼把手肘撐在地上,然後讓我舉起望遠鏡貼住眼睛,調整焦距。星星漸漸變成一團模糊的橢圓形,然後變成無數細密的光點,比肉眼看到的多得多。我來回擺動望遠鏡,終於找到了傑森指給我看的那個光點,或者,自以為找到了。那個彗星看起來就像一個瘤結,在冷酷黝黑的天空中散發出幽幽的磷光。
「彗星……」傑森開始說。
「我知道,彗星就像一個沾滿灰塵的雪球一樣,朝太陽飛過去。」
「你要那樣說也行。」他的口氣有點不屑。「你知道彗星是從哪裡來的嗎,泰勒?它們是從太陽系外圍來的。太陽系外圍環繞著一個冰冷的雲團,像一團圓球狀的光暈,範圍從冥王星的軌道開始,向外擴張,最外圍可達到與太陽系最鄰近的恆星之間五分之一的距離。彗星就是從那裡誕生的。那遙遠的太空深處,冷到你根本不可能想像。」
我點點頭,心裡有點不太舒服。我已經讀過不少科幻小說,已經足以體會夜空那無以形容的浩瀚遼闊。那種浩瀚遼闊,有時候也是我喜歡想像的。只不過,在夜裡某些不恰當的時刻,屋子裡靜悄悄的時候,想到那些,會有一點壓迫感。
「黛安?」傑森問:「妳想不想看看?」
「有必要嗎?」
「當然沒必要。高興的話,妳可以坐在那邊燻妳的肺,胡說八道。」
「少跩了。」她把煙按熄在草裡面,伸出手來。我把望遠鏡遞給她。
「拜託拿那個小心一點。」小傑很寶貝他的望遠鏡。上面還聞得到塑膠膜和保利龍包裝的味道。
她調整焦距,朝天上看。她安靜了一下子,然後說:「用這個東西看星星,你知道我看到什麼嗎?」
「什麼?」
「還是一樣的星星。」
「用點想像力吧。」他聽起來真的被惹毛了。
「如果可以用想像力,我幹嘛還要望遠鏡?」
「我的意思是,你有沒有想過,你看的是什麼。」
「哦!」她說。停了一下,又說:「唉呀!傑森,我看見……」
「看見什麼?」
「我想想看……,對了,那是上帝!祂留著長長的白鬍子!祂手上舉著一個牌子!上面寫的是……傑森遜斃了!」
「很好笑。不會用望遠鏡的話,那就還我。」
他伸出手,她卻不理他。她坐直起來,望遠鏡對準大房子的窗戶。
宴會從今天傍晚之前就開始了。我媽之前跟我說過,羅頓家的宴會是「企業大亨花一堆錢鬼扯淡的大會」。不過,我媽加油添醋的本領爐火純青,所以她說的話你一定要打點折扣。傑森跟我說過,大多數的客人都是航太圈子裡嶄露頭角的人物或政界的幕僚參謀。他們不是華盛頓當地社交圈子裡的老面孔,而是從西部來的、有軍火工業背景的新貴。艾德華•羅頓是傑森和黛安的爸爸,每隔三、四個月他就會辦一次這類的宴會。
黛安眼睛貼在望遠鏡兩個橢圓形的接目窗後面,一邊說:「老把戲了,一樓,喝酒跳舞,現在,舞沒什麼人跳了,酒愈喝愈兇。廚房好像要收工了,我看那些服務生已經準備要回家了。書房的窗簾拉上了。艾德華和幾個客人在圖書室裡,好噁!有個人在抽雪茄。」
傑森說:「少在那邊裝噁心了,騙不了人的,萬寶路女郎。」
她繼續逐一瀏覽每一扇看得見裡面的窗戶,傑森跑過來我旁邊。他喃喃叨唸著:「讓她欣賞宇宙,她卻寧願偷看人家宴會在幹什麼。」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就像往常一樣,傑森說的很多話,聽起來總是充滿智慧,聰明伶俐。那樣的話不是我說得出來的。
黛安說:「我的房間,沒看到人,謝天謝地。傑森的房間,也沒有人,只不過,床墊底下藏了一本閣樓雜誌……」
「這副望遠鏡很棒,不過沒有棒到那種地步。」
「卡蘿和艾德華的房間,也是空的。那間客房……」
「怎麼樣?」
黛安忽然沒聲音了。她坐著一動也不動,眼睛還是貼著望遠鏡。
「黛安?」我問。
她還是不說話。過了一下子,她開始發抖,轉身把望遠鏡丟……應該說,摔回去給傑森。傑森叫罵著,似乎沒有意識到,黛安看到了什麼令她很煩躁的東西。我正要問她怎麼樣了……
這個時候,星星消失了。
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事。
那些親眼目睹這件事發生的人,通常都這麼說。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事。真的不是。我以一個目擊者的身分告訴大家:黛安和傑森在鬥嘴的時候,我一直在看天空。那只不過是一道怪異刺眼的強光,剎那間閃了一下,星星的殘影,在眼睛裡留下綠色冷磷光的視覺殘留。我眨了眨眼睛。傑森問:「那是什麼?閃電嗎?」黛安一句話也沒說。
「傑森。」我叫他,眼睛還是眨個不停。
「幹嘛?黛安,我對天發誓,要是妳砸破了上面的鏡片……」
「閉嘴!」黛安說。
我說:「別吵了!你們看,星星怎麼搞的?」
他們倆都抬起頭往天上看。
我們三個人當中,只有黛安願意相信星星真的「熄滅」了,像蠟燭一樣被風吹熄了。那是不可能的,傑森很堅持:那些星星的光芒,穿越了很長的距離才照射到地球。五十光年,一百光年,或一億光年,距離長短,要看是從哪顆星來的。所以,那些星星當然不可能同時停止發光。這種消失的順序,以人類的肉眼來看是同時的,簡直像是人工設計的,太精密了,不可能這樣。不管怎麼樣,我要強調的是,太陽也是一顆星,而且它還在發光,至少在地球的另一邊,不是嗎?
當然是。傑森說,如果不是,還不到明天早上我們就凍死了。
所以,根據邏輯,那些星星還在發光,只不過我們看不見。它們並沒有消失,只是被遮住了,像日蝕一樣。沒錯,天空忽然變成一片黑檀木一樣地漆黑,不過,那只是一個神祕現象,不是世界末日。
然而,傑森推論的另一個角度,還殘留在我的想像中。萬一太陽真的消失了,會怎麼樣?我腦海中浮現出一幅畫面:在永無止境的黑暗中,大雪飄落,然後,搞不好,空氣會被一種異樣的雪凍結住,於是,人類所有的文明就被埋葬在我們所呼吸的空氣下面。所以,假設星星只是像「日蝕」一樣被遮蔽了,那就還好,噢,絕對更好。可是,被什麼遮蔽了?
「嗯,顯然是很大的東西,某種速度很快的東西。泰勒,你是親眼看到的,究竟星星是瞬間同時消失的,還是好像有什麼東西飛過天空?」
我告訴他,看起來好像是星星突然閃了一下,然後瞬間就同時滅掉了。
「去他媽的星星。」黛安忽然說。我嚇了一跳,「去他媽的」這種話不是她平常會說出口的。不過,年齡邁入二位數的我和小傑就常常掛在嘴上。今年夏天,很多事情都改變了。
傑森聽出她聲音裡的不安。他說:「我不覺得有什麼好怕的。」雖然他自己顯然也很不安。
黛安皺著眉頭。她說:「我好冷。」
於是我們決定回大房子裡,看看CNN或CNBC有沒有報導這個消息。當我們走過草坪,天空看起來令人畏懼,極度黝黑,輕飄飄卻又無比沉重,比我從前看過的任何天空都更黑暗。
「我們必須告訴艾德華。」傑森說。
「你去告訴他。」黛安說。
黛安和傑森不叫爸爸媽媽,卻直接叫他們的名字,是因為卡蘿以為這樣的家教走在時代前端。然而,實際的情況卻複雜得多。卡蘿寵孩子,卻沒有花很多時間照顧這對雙胞胎的生活起居。而艾德華則是一板一眼地培養他的繼承人,那個繼承人,當然就是傑森。傑森崇拜他爸爸。黛安怕他爸爸。
羅頓家宴會快結束的時候,大家都喝得醉醺醺地,我沒有笨到會讓自己出現在大人的地盤上。於是,我和黛安躲在門後面,那裡不會被炮火波及。傑森在隔壁的一個房間裡找到了他爸爸。我們聽不清楚他們在裡面講些什麼,但我們絕對不會聽錯艾德華的口氣,那種憤怒的、不耐煩的、急躁的口氣。傑森回到地下室的時候,滿臉通紅,幾乎快要哭出來了。我跟他們說再見,朝後門走過去。
走到玄關的時候,黛安追上我。她抓著我的手腕,彷彿把我們兩個人扣在一起。她說:「泰勒,它會出來的,對不對?我是說太陽,明天早上。我知道問這個很蠢,可是,太陽會出來,對不對?」
她的聲音聽起來非常消沉。我開始跟她說一些不痛不癢的話,像是「如果沒出來,我們都活不了」之類的。可是,她的焦慮卻也激起了我的疑惑。我們看到的究竟是什麼?那代表什麼意義?顯然傑森的爸爸不相信他說的,今晚的天空發生了什麼重大變故,所以,也許我們只是在杞人憂天,自己嚇自己。可是,萬一世界末日真的來臨了,而只有我們知道這件事,怎麼辦?
「我們不會有事的。」我說。
幾縷細柔的髮絲遮住了她的臉,她的眼睛在髮絲的細縫間凝視著我。「你真的相信嗎?」
我勉強擠出笑容。「百分之九十。」
「不過,你今天不會睡覺,你會熬到明天早上,對不對?」
「大概,也許吧。」我心裡明白,自己不會想睡覺。
她比了一個打電話的手勢。「晚一點打電話給你好不好?」
「當然好。」
「我大概也不會睡。不過,萬一我睡著了,明天太陽一出來,你可以打電話給我嗎?這樣的要求好像有點蠢。」
我說我一定會。
「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她這樣請求我,讓我受寵若驚,暗自興奮。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時間迴旋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30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84 |
西洋科幻小說 |
$ 284 |
歷年誠品選書 |
$ 306 |
小說/文學 |
$ 317 |
中文書 |
$ 317 |
科幻小說 |
$ 324 |
翻譯科幻小說 |
$ 324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時間迴旋
在一個十月的夜裡,群星忽然綻放光芒,然後同時熄滅。那一年泰勒十二歲,與他最好的朋友雙胞胎黛安、傑森一起目睹了這一幕,他們的人生與整個世界的命運從此改變。一張不知名的黑網遮蓋了地球,黑網之外,整個宇宙的時間正以驚人的速度前進,地球上的一瞬間,對太陽卻是千百萬年。熟悉的世界一夕改變,全球陷入恐慌,股市崩盤、社會動盪,有的人自殺,有的人發瘋,有的人則裝作一切正常。
在末日的陰影下,泰勒與雙胞胎漸漸長大,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傑森成為頂尖科學家,用先進科技展開探索;黛安歸向宗教,在神學中尋找心靈慰藉;泰勒選擇成為濟世救人的醫生,卻不知道這在世界毀滅時還有什麼意義。地球之外的時間仍然不停流逝,太陽即將走到生命盡頭,那一天也將是人類的末日……一個讓你感同身受的動人故事,在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後一天的絕望中,該如何找回心靈的勇氣?
本書作者威爾森是加拿大科幻名家,說故事功力備受好評,紐約時報讚美他:「完全了解類型長處,自信地揮灑自如,絕不忽略人文關懷的角度。」他的作品內涵豐富,充滿人性,超越一般類型小說,華盛頓郵報因此讚譽:「長久以來,我們期盼硬科幻小說和文學小說的聯姻,能夠繁衍出充滿想像又敘事優雅,結合兩者優點的後代。這個願望終於因為『時間迴旋』而成真。」超人氣出版讀書部落格「頑固老書蟲」更盛讚:「強力推薦給所有喜歡有深度、有文學性、內涵的小說讀者,管他什麼類型。」
作者簡介:
作者:威爾森(Robert Charles Wilson)生於加州,成長於加拿大,威爾森是最受歡迎的小說家之一。他長期耕耘類型小說,初期在雜誌上發表短篇作品,兩次入圍世界奇幻獎;1994年的長篇《神秘地帶》以平行世界為主題,獲得菲利普迪克
章節試閱
大房子星光從天空消失的那個晚上,我十二歲,那對雙胞胎十三歲。那是十月,萬聖節的好幾個星期之前,羅頓家有一場大人才可以參加的宴會,於是我們三個小鬼就被趕到地下室去。羅頓家的大宅,我們都叫它大房子。關到地下室,根本算不上處罰。對黛安和傑森來說,那不是處罰,因為他們本來就喜歡一天到晚窩在地下室。對我來說,當然也不是。他們的爸爸老早就宣布過,在他們家裡,什麼地方是大人的,什麼地方是小孩子的,界線劃分得很清楚。不過,我們這裡有一套最高檔的電玩平台,有電影碟片,甚至還有一座撞球台……而且,大人管不到。除了楚...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威爾森
- 出版社: 貓頭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8-02 ISBN/ISSN:9789867001665
-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592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科幻小說
圖書評論 - 評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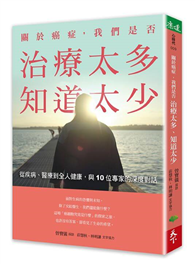





本書的分享心得很不容易下筆,因為只要一不小心曝了一點雷(也就是透露出故事劇情),都會減損讀者的閱\讀樂趣,畢竟本書是本世紀以來不可多得的科幻小說,用句好像廣告賣藥的詞彙:「沒看會後悔!」 在閱\讀本書以前,我實在不太願意涉獵科幻小說,寫了七百多篇書評中,除了少數幾本與穿越時空有關的作品外,我幾乎沒有寫過科幻小說的讀書心得分享,主因是沒有興趣,沒興趣的原因應該是被昔日倪匡那些科幻小說所框限住了,然而就在本書闔上的那一瞬間,我又重拾對科幻小說的信心了。 本書迷人之處不單單在於科幻的想像力之外,她還有極為溫馨的人性,這本小說讓我驚艷的是,從來沒有科幻小說曾嘗試「真正地」處理人性,在科幻小說中,往往想要清楚描繪科技就很辛苦了,作者通常會忽略其中的人的面貌。 本書的科幻想像力卻橫跨了演化、生物、星際、環境甚至宗教,所架構的世界不會向奇幻作品中的荒誕不羈,本書的故事舞台和現在你我所身處的世界沒有兩樣,除了SPIN(時間迴旋)和人心以外;本書有股傳統科幻小說所沒有的人性觀和人文觀;除了讓人嘆為觀止的想像力之外,還牽扯出人性的恐懼、愛、焦慮、絕望和信念,並且讓整個故事由幾個主要角色的成長互動為故事主軸,而不是傳統那種百分百科幻純度的情節。很多小說能天馬行空的編造世界末日的理由,但很少的故事描寫平凡的人面對末日的轉變。 故事以主角泰勒第一人稱,並且以過去和現在兩條線進行故事的鋪陳。 在一個十月的夜裡,群星忽然綻放光芒,然後同時熄滅。那一年泰勒十二歲,與他最好的朋友雙胞胎傑森、黛安兄妹一起目睹了這一幕,他們的人生與整個世界的命運從此改變。地球上空出現了不明高等智慧體,以「時間迴旋」將地球包覆住。被包覆其中的地球,時間流逝將是未被包覆知宇宙的一億分之一(也就是說,地球一年,宇宙已經過了一億年,這個假設挑戰了既有科幻想像中時空觀,但卻有所本,本於聖經的「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 在末日的陰影下,泰勒與雙胞胎好友、雙胞胎的父母,幾個主要角色所面對的方式都大不相同,泰勒用務實但卻有點麻木的態度、傑森積極探索時間迴旋的真相、黛安歸向宗教在神學中尋找心靈慰藉、傑森與黛安的父親則熱中追逐權力、母親選擇以酒精度日.....在閱\讀過程中,我自己不免也數度問起自己:如果面對相同的世界巨變與末日隱憂,會用什麼人生觀點去面對自我? 本書和一般科幻小說最大的不同在於,所有的科幻小說所設定的假設,不是很難合理化和自圓其說,就是會讓讀者卡在科學的專業胡同裡頭,畢竟不是所有讀者都有足夠的專業科學知識去完整解讀科幻場景,但本書卻不會有這種困惱,原因並不是因為本書的科幻篇幅太過薄弱,而是本書所營造的想像空間和人性刻劃,其精采度足以讓人忽略到科幻小說中那些難懂的科學專業知識,也就是說,即便讀者無法看懂本書所架構的科學理論,也不會減少一丁點閱\讀上的津津有味。 本書最迷人之處在於「演化」,演化讓本書的故事有了各種天馬行空之想像空間,我必須賣個關子,不想書寫太多本書的演化的情節。 閱\讀本書之後我忽然想起了幾個問題: 萬一預期中的世界末日遲遲不降臨,那又將要如何把失去的一切找回來呢? 地球滅亡前的最後一夜,我想跟哪些人在一起? 究竟要從科學的角度去理解,還是要從宗教的角度去體會?當一個人面臨生死關頭的時候,比較希望在哪裡得到永生?在人間天堂,還是荒涼的實驗室? 或許\可以引用本書的一段話:「瓜地馬拉人無視於世界末日即將來臨,還是努力種咖啡。瓜地馬拉人不見得相信末日將至。即使相信,不種咖啡又如何?坐在地上哭嗎?那不用等末日降臨,先就餓死了。」 務實面對一切說不定是最好的面對末日的心靈圭臬吧! 最後用一句馬克吐溫的話來覆蓋\《時間迴旋》的閱\讀回合:「上天堂,是因為那裡天氣好。下地獄,是為了找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