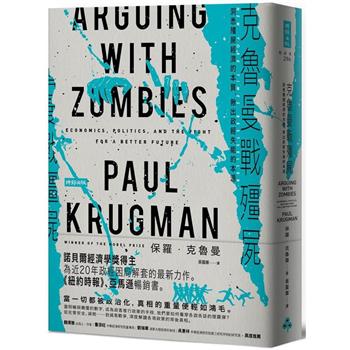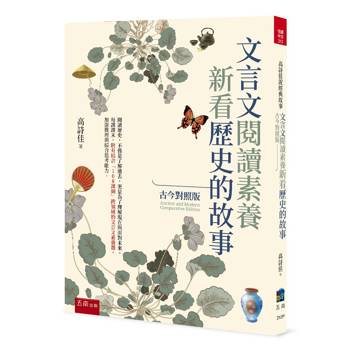* 上市前網路口碑延燒,上市後熱銷好評不斷!
* 使人耽醉其中的東方奇幻小說,描繪出獨樹一幟的妖怪宇宙!
* 一本推人入坑、奪人睡眠的最佳夜讀好書!
* 絕美書衣台灣版,特別新增作者序。
人生自是有情癡,只要有情,妖和人便也沒什麼分別,
但很多時候,人不如妖,妖卻比人還像人……
「出了寨就不要回頭,閉著眼走,出了林子才可以睜眼。」
龍涯從沒想過,號稱京城第一名捕的他,也會有落荒而逃的一天。當他閉著眼睛,邁步向那小路奔去時,腦中不斷響起沙蔓的叮嚀,心中不停追問自己:「她為什麼如此……?」
幾日前,為了追捕江洋大盜風麒麟,龍涯與四名捕快在貴州苗嶺地界迷失方向,最後踏進一座只有女人的苗人山寨,本以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來到了充滿女人香的溫柔鄉和安樂窩,誰知一夕之間,全都變了調……
人與人之間總有負心之人,妖和妖之間,又何嘗不是如此?有些人義無反顧愛著另一個人,有些人則是一往情深愛著一隻妖,然而,有些妖也願意為了一個人而放棄千年道行,只願化身為人與之相守。還有一些妖,為了守護彼此,甘願犧牲性命,就算是半人半妖也沒什麼不同,他們有的快樂、有的悲傷、有的遺憾,也有憤恨和心碎的,但相同的是,他們都有情。
《魚館幽話》在作者淡淡的筆調中,將人帶進一個渾然天成的奇妙世界,令人醉心其中,品嘗著人與妖的百味、況味,以及耐人尋味,就像飲著故事中傾城魚館的美酒一樣,總是滲出五味雜陳的餘韻……讓人難以忘懷……一杯酒,一個故事,不管你是人、是妖還是神,都請你一同光臨傾城魚館,和大家一塊煮酒烹茶聽故事。
名人推薦
暢銷小說家 蝴蝶 特別推薦!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魚館幽話 之一 相思藤的圖書 |
 |
魚館幽話(之一):相思藤 作者:瞌睡魚游走 出版社:悅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9-1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52 |
文學作品 |
$ 253 |
華文奇幻/科幻小說 |
$ 253 |
科幻/奇幻小說 |
$ 253 |
東方玄幻/歷史 |
$ 255 |
小說/文學 |
$ 281 |
中文書 |
$ 282 |
奇幻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魚館幽話 之一 相思藤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瞌睡魚游走
八○後的典型射手女,生於巴渝之地,自幼偏愛舞文弄墨,性格開朗偕內斂,生性崇尚自由、無拘束。畢業於重慶大學,現為一名室內設計師。工作之餘,喜歡寫寫小說,說說故事。由於莫名偏愛北宋年代,故而所寫的故事通常是以此為背景。
代表作品有玄幻志怪系列小說《魚館幽話》、武俠長篇小說《傾城》,以及懸異魔幻系列小說《昌州拾異錄》。
瞌睡魚游走
八○後的典型射手女,生於巴渝之地,自幼偏愛舞文弄墨,性格開朗偕內斂,生性崇尚自由、無拘束。畢業於重慶大學,現為一名室內設計師。工作之餘,喜歡寫寫小說,說說故事。由於莫名偏愛北宋年代,故而所寫的故事通常是以此為背景。
代表作品有玄幻志怪系列小說《魚館幽話》、武俠長篇小說《傾城》,以及懸異魔幻系列小說《昌州拾異錄》。
序
序
白雲生鏡裡,明月落階前
前些時候與一位十多年沒見過的老同學聚會,她得知《魚館幽話》成書的事,頗為意外地問我:「你明明喜歡舞文弄墨,當年怎麼不念文科,跑去念建築、設計呢?」
我愣了三十秒,然後回答她:「因為建築和設計可以最直接地改造世界。只是後來發現,原來文字也可以,不只是改造,甚至可以打造書中的大千世界,所以就把筆也撿起來了。」
「那麼你以後都走文學路子,老本行丟了不可惜嗎?」
「為什麼一定要放棄一樣呢?」
「都說一心不可二用,既然不棄本行,那你寫的書對你而言又是什麼呢?」
我想了想,指了指外面庭院裡的一處盆池。盆池鑿於地下,與地齊平,有蓮葉田田,有游魚逶迤,水平如鏡,倒映出一片藍天白雲的浮影,宛如青青苔痕間,偷來的一片天。
鑿破蒼苔地,偷他一片天。
白雲生鏡裡,明月落階前。
這是杜牧名為〈盆池〉的詩。身在繁華都市,朝九晚五的人們,每天都不可避免地跟隨著城市的快節奏高速運轉,哪怕再鍾愛的東西,久而久之也不免心生困怠。這就需要自我調節,時不時地抽離,才能避免原本喜歡的專業,墮落為純粹的工作。於是我在閒暇之餘為自己鑿下一隻盆池,這就是《魚館幽話》。
一切始於十年前的一次心血來潮,我用「瞌睡魚游走」的帳號在天涯蓮蓬鬼話裡開始連載《魚館幽話》。帳號很隨意,連載也很隨意,不曾有過人設和構架,就這麼「佛系」地開始了。最初只是信馬由韁地隨便寫寫,打發時間,就好像最初兩話的〈相思藤〉和〈雙生花〉。不想漸漸地,看的人多了,回覆留言也多了。書上的魚館是聚集各路神仙妖怪的忘憂之地,而《魚館幽話》的帖子就好像現實之中的一處酒館,也是各路朋友相聚的所在,一起聊聊時事和生活,發發牢騷和感慨 ,於是就有了〈忘情草〉和〈紫苔〉。
筆下的世界光怪陸離,故事就好像不經意間撒下的種子,有了自己的意識,等到了第五話〈鼉淚〉,我突然覺得,不應該像之前一樣隨意無序了,既然開了這個盆池,就該好好地打理養護,讓它真正成為一個不同於真實世界的完整體系,於是這個時候,一系列的問題第一次出現在腦海之中:
神祕的魚姬,她從何而來?
魚館四人組的相聚是偶然,還是必然?
那些各自獨立的故事,它們彼此有關係嗎?
……
這個時候,恰好因為本職工作的需要,接觸到了古代家具的相關資料,其中宋代黃伯思的《燕几圖》給了我不少啟發。「燕几圖」即是現代七巧板的原形,不同形狀的案几各自獨立,但又能相互拼合,變幻多樣,就好像《魚館幽話》裡的這些人和故事,它們可以是各自獨立的,也可以相互相關,互為因果。但它們結合在一起,則又對應著不同的大事件。於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魚館幽話》有了自己的脈絡,草蛇灰線,在不經意的角落,藏著故事的主線,聚集成一個完整的世界。
幾年後它很幸運地成為鉛字,也成為了這十年來,對我而言很重要的一件事。通過它,我終於擁有了屬於自己,能生白雲,落明月,偷來一片天的那只盆池,它開鑿於繁忙的快節奏生活中,卻又擁有超越現實的浪漫與瑰麗。
得之幸甚。
謹以此書獻給父親楊德友先生、母親陶平女士、外婆雷瑤先女士。
白雲生鏡裡,明月落階前
前些時候與一位十多年沒見過的老同學聚會,她得知《魚館幽話》成書的事,頗為意外地問我:「你明明喜歡舞文弄墨,當年怎麼不念文科,跑去念建築、設計呢?」
我愣了三十秒,然後回答她:「因為建築和設計可以最直接地改造世界。只是後來發現,原來文字也可以,不只是改造,甚至可以打造書中的大千世界,所以就把筆也撿起來了。」
「那麼你以後都走文學路子,老本行丟了不可惜嗎?」
「為什麼一定要放棄一樣呢?」
「都說一心不可二用,既然不棄本行,那你寫的書對你而言又是什麼呢?」
我想了想,指了指外面庭院裡的一處盆池。盆池鑿於地下,與地齊平,有蓮葉田田,有游魚逶迤,水平如鏡,倒映出一片藍天白雲的浮影,宛如青青苔痕間,偷來的一片天。
鑿破蒼苔地,偷他一片天。
白雲生鏡裡,明月落階前。
這是杜牧名為〈盆池〉的詩。身在繁華都市,朝九晚五的人們,每天都不可避免地跟隨著城市的快節奏高速運轉,哪怕再鍾愛的東西,久而久之也不免心生困怠。這就需要自我調節,時不時地抽離,才能避免原本喜歡的專業,墮落為純粹的工作。於是我在閒暇之餘為自己鑿下一隻盆池,這就是《魚館幽話》。
一切始於十年前的一次心血來潮,我用「瞌睡魚游走」的帳號在天涯蓮蓬鬼話裡開始連載《魚館幽話》。帳號很隨意,連載也很隨意,不曾有過人設和構架,就這麼「佛系」地開始了。最初只是信馬由韁地隨便寫寫,打發時間,就好像最初兩話的〈相思藤〉和〈雙生花〉。不想漸漸地,看的人多了,回覆留言也多了。書上的魚館是聚集各路神仙妖怪的忘憂之地,而《魚館幽話》的帖子就好像現實之中的一處酒館,也是各路朋友相聚的所在,一起聊聊時事和生活,發發牢騷和感慨 ,於是就有了〈忘情草〉和〈紫苔〉。
筆下的世界光怪陸離,故事就好像不經意間撒下的種子,有了自己的意識,等到了第五話〈鼉淚〉,我突然覺得,不應該像之前一樣隨意無序了,既然開了這個盆池,就該好好地打理養護,讓它真正成為一個不同於真實世界的完整體系,於是這個時候,一系列的問題第一次出現在腦海之中:
神祕的魚姬,她從何而來?
魚館四人組的相聚是偶然,還是必然?
那些各自獨立的故事,它們彼此有關係嗎?
……
這個時候,恰好因為本職工作的需要,接觸到了古代家具的相關資料,其中宋代黃伯思的《燕几圖》給了我不少啟發。「燕几圖」即是現代七巧板的原形,不同形狀的案几各自獨立,但又能相互拼合,變幻多樣,就好像《魚館幽話》裡的這些人和故事,它們可以是各自獨立的,也可以相互相關,互為因果。但它們結合在一起,則又對應著不同的大事件。於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魚館幽話》有了自己的脈絡,草蛇灰線,在不經意的角落,藏著故事的主線,聚集成一個完整的世界。
幾年後它很幸運地成為鉛字,也成為了這十年來,對我而言很重要的一件事。通過它,我終於擁有了屬於自己,能生白雲,落明月,偷來一片天的那只盆池,它開鑿於繁忙的快節奏生活中,卻又擁有超越現實的浪漫與瑰麗。
得之幸甚。
謹以此書獻給父親楊德友先生、母親陶平女士、外婆雷瑤先女士。
二○一八年五月七日,於重慶巴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