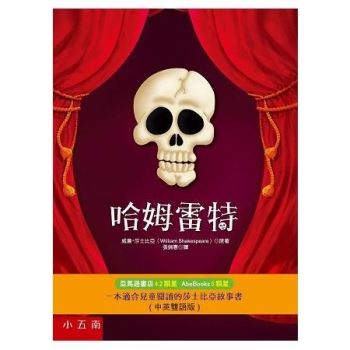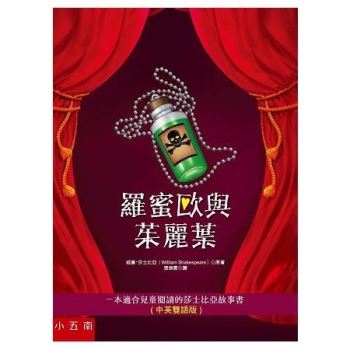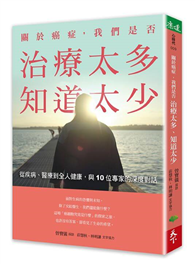第一章
作為聖凱提卡王的國王軍總司令,弗克爾斯自認見過不少世面──嗜血的狂戰士啦,散發著寒氣的鬼屍骷髏啦,但若要說到他這輩子遇到最荒唐的情景,無疑就是現在了。
剛才他正在和他的舅媽──法斯廷王國的王后瑪格麗特聊天,這時一個面容緊張的侍者走了進來。
「御醫們對王子殿下的匯診結果已經出來了,」侍者吞吞吐吐地說,「我猜他們是有點太老了,以至於神志不清……」
瑪格麗特皺了下眉,有些不滿侍從的評論——下人總得有規矩不是。
「御醫是怎麼說的?」她柔聲問,一頭子夜般漆黑的長髮以最時髦的髮式挽在腦後,即使已經不再年輕,可良好的保養仍讓她看上去像剛結婚那時一般。法斯廷的女人永遠懂得怎麼永保青春。
「這個……」侍衛明顯猶豫了一下,看了一眼弗克爾斯。
瑪格麗特優雅地做了個手勢,示意外甥並不需要離開,他們之間沒有秘密。「說吧,弗克爾斯不是外人。」
「實際上,御醫說……殿下他……懷孕了……」
弗克爾斯剛喝到口中的紅茶整個噴了出來,然後連忙道歉,覺得自己一定發生很嚴重的幻聽。
「懷——」瑪格麗特的女高音發生了奇怪的變調,「你在胡說八道些什麼!還是那些老古董們記錯了愚人節的時間……」接著她突然靜止下來,像被施了定身魔法般呆若木雞,石化在那裡。
「剛才他說什麼?」弗克爾斯無意識地問,確定自己是幻聽了。
「沒有!」王后大聲說,「沒事沒事,我猜是御醫開玩笑呢!他們總是為老不尊……」纖細的手指絞著手絹,「你請自便,我想我得去看看傑林特,兒子生病時最需要母親在身邊!」她乾笑兩聲點頭告退,房間裡只留下一絲素心蘭的香水味。
弗克爾斯故作鎮定地喝了口茶,那麼他沒聽錯,剛才那個待者確實是說……傑林特……懷孕了?
傑林特躺在沙發上,蹺著腿,侍女小心地把葡萄剝去皮,把肉放到他嘴裡。作為法斯廷的王儲,他是位相當富有吸引力的男子,雖然以貴族的標準他看上去著實有些放蕩和不體面——他的黑髮並沒有正經地束好,而是隨便地散在肩膀上,之下的臉孔倒是彰顯著貴族世代對美女的壟斷,如果不是那副吊兒郎當、不正經的德性,想必會更加好看一點。這會兒他正枕在一個衣著暴露的侍女大腿上吃著水果,態度悠閒。
「傑林特!」王后歇斯底里的聲音劃破了貴族寧靜的私生活,纖細的身影因為憤怒而顯得格外有張力地出現在門口,看到眼前景象她有一種把手中扇子用力丟過去的衝動,但看在有旁人在的份兒上,還是強行忍了下來。
「傑林特!讓她們都出去,我有話跟你說!」她咬牙切齒地說。她的兒子漫不經心地瞟了她一眼,用讓人恨不得掐死他的懶洋洋語調說:「哎呀,母親大人,您以前進父王的臥室都不敲門嗎?難道父王在和別的女人調情時喜歡您在場?」
瑪格麗特氣得渾身發抖,天哪,為什麼她會養出這麼個女兒!
好吧,現在不得不承認,十八年前作為側妃的瑪格麗特生出了這麼個寶貝,為了在後宮中得到更高的地位,她買通接生婆,謊稱生出來的是個男孩兒,為了使謊言更加完美,她甚至買通了一些法師,讓女兒看上去是個男孩兒。
這個決定後來被證明是正確的,瑪格麗特順利地做上了王后的寶座,她的女兒也因為是長子而冊封為王儲。瑪格麗特正在找機會提倡修改憲法,讓法斯廷王國成為一個承認女王的國度──這一切最好可以等傑林特即位之後來做,因為規矩永遠是權力者定的。
她的努力眼看成功在即,可是這時候卻偏偏出了這樣的大漏子——她的女兒懷孕了!
侍女無聲地退了出去,瑪格麗特一屁股坐到沙發上,傑林特一臉不情願地坐起來;那副不耐煩的勁頭讓王后有衝動直接給他一個爆栗!
「說吧,什麼事讓您十萬火急地趕來,母親大人。父王又要納新妃子了?」傑林特說,拿起一顆葡萄丟進嘴裡。
「傑林特!」瑪格麗特咬牙切齒地說,「孩子是誰的!」
「哦,」王子殿下慢條斯理地把葡萄皮丟掉,「好像是個傭兵。」
瑪格麗特幾乎要暈過去了!她用力喘了好幾口氣才緩過勁兒來,「傭……傭兵?妳……妳居然跟一個該死的傭兵……妳難道沒有一點法斯廷公主基本的矜持!居然和一個低賤的人——」
「得啦!」傑林特不耐煩地擺擺手,「我是一個生理和心理都發展正常的年輕人,難道妳想讓我一輩子躲在臥室裡自慰?找點樂子而已,大驚小怪的幹嘛啊。」
瑪格麗特很想暈過去,可是她顯然沒有自己預計的那麼柔弱,所以她的神志還很清醒。可她的兒子繼續一顆接一顆地丟下重磅炸彈,「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弗卡羅下面跑腿那小子,長得倒是標緻。」她繼續咬著葡萄,「就是那個戰羽的弗卡羅。」她向母親解釋。作為王儲,她得負責處理法斯廷所有的對外關係,而迪庫爾的弗卡羅無疑是最麻煩的一個。
「啊……見鬼,一個跑腿的!你至少也得找那個團長啊……」她說。傑林特做出陣亡的樣子,呻吟道,「妳殺了我吧,和他上床像抱著把沒帶鞘的利刃睡覺!」
「那個該死的傭兵叫什麼!」王后咬牙切齒地說,「我們不能讓他活著,他也許會拆穿妳的身份!」
「我怎麼會知道那種事情呢,親愛的母親?」傑林特慢條斯理地擺弄著她的甜點,「知道他們為什麼去當傭兵嗎?因為他們的命不值錢。傭兵的產地從邊海到喀卡山脈,從黑暗森林到底綠比斯,只為了一個字,錢!弗卡羅那個笨蛋居然以為可以從傭兵身上找到忠心,」她不屑地冷哼,「他還不如去和一個法斯廷的妓女結婚!」
她把葡萄皮用力擲到桌上,提起弗卡羅這名字就讓她心情很不好,那男人的狂妄和獨裁總讓她有一種把手套丟到他臉上的衝動,不過鑒於她打不過他,所以從沒有付諸實踐過。
「那這個孩子怎麼辦?」她的母親說,「難道墮胎……光明之神在上,這是多麼不能容忍的褻瀆啊!」她做了個祈禱的手勢,「願神原諒我們,這也是迫不得已!我得向菲格洛亞要些墮胎藥,她好像很懂這個!」
「很多人懂,只是不說出來。」傑林特說,「艾美拉城的女人離不開它們,這是幸福生活的關鍵。」
「妳得有常識,傑林特!」瑪格利特絕望地叫道,「妳是個女孩子!聽著,別總跟那些狐朋友狗友混在一起了!他們除了享樂什麼也不會幹……」
「不,我是未來的國王。」傑林特危險地瞇起眼睛,她不喜歡母親說到這個。那雙冰冷黑色眼睛裡一瞬間流露出的殺氣讓瑪格麗特打了個寒顫,她不自在地移開眼睛。傑林特聳聳肩,恢復了漫不經心的樣子,「貴族分享國王的權力,我可不想還沒登基就讓他們以為我是個無趣的人。」
「而且我不得不說,迪庫爾的避孕藥仍停留在三十年前的階段!大約和那個國家的男人總是毫無情趣有關。」王子裝模作樣地歎了口氣,不想再繼續這個無趣的話題,「好啦,母親大人,我要準備去出席晚宴了,妳去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把這孩子搞定,去找個法師,弄個轉移術什麼的,我可不希望謀殺案在我肚子裡發生。」
瑪格麗特張大眼睛,「妳是說……妳……要生下來?」
「不是生下來,」傑林特回過頭,耐心地說,「是轉移出去,讓那些法師在培養罩裡養他,動作快點,我三天後要起程去迪庫爾,僵屍待的鬼地方!」
她不耐煩地扯開襯衫的鈕釦,招呼侍女來幫她換衣服。瑪格麗特靜默地看著兒子矯健俐落的身影,看上去像個十足的男性,也許即使……她再讓她穿上長裙,把挽起長髮、輕施脂粉的權利還給她,她也再難以像一個女孩兒了。
她絕望地揉揉眉心,但她想,這孩子至少不用她擔心了,她保護得了自己;她是從小被作為王子教育長大的,深知所有政治的權謀把戲,雖然也把那些貴族的吃喝玩樂弄了個樣樣精通,而且現在頗有成為艾美拉、甚至整個法斯廷領頭羊的趨勢。
女性的矜持?不,她只知道自己享有國王的權力——至少將要享有,而不承認有凡世間的義務可以束縛她,如果有,那也只將是屬於國王的責任。
法斯廷雖然相對土地較少,軍隊也較弱,但卻毫無疑問是最有錢的一個國家,王都艾美拉城不光是大陸的商業中心,也是藝術中心。這裡是弗克爾斯母親出生的國度——她是聯姻來到聖凱提卡蘭的。
作為長子,弗克爾斯在另一個國家造就了一副軍人的嚴謹性格,雖然不久前發生的一件事讓他確定他毫不缺法斯廷男人對愛情的瘋狂和浪漫,但當來到法斯廷時,他仍常常會覺得不適應。
宮廷晚宴上,弗克爾斯漫不經心地啜著一杯紅酒,法斯廷的「玫瑰色晨曦」大陸聞名,這個國家的人一向對享樂獨有心得。
他這會兒可沒什麼心情管這些,對於一個國家,即使年輕國王陛下的身上有諸如「坐著巨龍朝太陽的方向飛去」,或是「被梅莎柔斯神所眷寵的勇者,開始了新的冒險」等等美好又凝聚民心的傳聞,但國王失蹤對一個國家都不是件好玩的事。
如果不是多虧了那些神乎其神的民間傳說,恐怕聖凱提卡蘭早已天下大亂,諸侯紛起了。
凱洛斯……注意到自己的手有些抖,他不著聲色地把酒杯放到桌上。每當念起這個名字時,他還是忍不住心中痙攣般的疼痛,弗克爾斯不知道再過一段會不會好起來,現在他只能盡力避免想起。
他疲憊地歎了口氣。他很累,不只聖凱提卡蘭內政的混亂,也因為這些天他一閉上眼睛那個人的影子就會浮現,讓他無法安眠,隨之而來的記憶會帶起太多的愛戀與痛苦。可是那個影子始終孤獨如昔,沒有任何感情可以牽絆,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溫暖……
「我親愛的表哥,」一個誇張的聲音傳過來,「您真是出落得一年比一年英俊,這次來恐怕要帶走不少艾美拉少女的芳心呢!」
「哦?那我豈不是搶了你的東西,傑林特?」弗克爾斯反射性地寒喧回去,對面站著的正是法斯廷的王子傑林特,黑髮用緞帶束在後面,只在前面垂下一綹,俊秀的面孔正笑吟吟地看著他。
弗克爾斯對這位王子表弟的印象並不深,除了他那總是最新潮的打扮。但得到有錢人的支持總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大老遠趕來,希望得到他們的援助,這點,是有法斯廷王室血統的弗克爾斯的責任。
「這次準備待到什麼時候?」傑林特親暱地搭著他的肩膀,「最近艾美拉有不少好地方,帶你去找找樂子?」
「最近都忙翻了。」弗克爾斯歎了口氣,突然想到中午那個侍者關於「王子懷孕了」的稟報,這讓他結結實實打了一個寒顫,小心瞟了眼身邊的傑林特,對方依然是那副公子哥兒般漫不經心的德性,纖細高挑的身形,一點也看不出……呃,懷孕的樣子來。
「哦,是為了你們那位傳說中的國王被光明之神回收的事?」傑林特說,拿起一杯酒,「我都還無幸見他一面,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機會?」他說。
弗克爾斯覺得心臟猛地一緊,「天知道,那是梅莎柔斯神的事情。」他聽到自己回答。
不會了……他不會回來了……因為他本來就不屬於這裡,他寧願在孤獨的地方一個人死去,也絕不會……他下意識地按著桌沿,抑制住身體的顫抖。
他避免去想那些,可是真的不想就等於什麼事都沒發生了嗎?他知道那不可能……可是,即使是偶爾一閃念的瞬間,也足夠讓他感到難以呼吸,那疼痛竟如此巨大!
傑林特不著聲色地瞟他一眼──確認聖凱提卡蘭那位大名鼎鼎的年輕國王是否健在是個大情報,關於那些神蹟、勇者之類的,不管有沒有,對他只代表一件事:政治籌碼。
「弗克爾斯,你看上去操勞得很,」他作擔心狀說,「你們的陛下真是不懂體諒,要不要和我到迪庫爾散散心?」
「迪庫爾?」弗克爾斯問,迅速警覺了起來,法斯廷的王子到迪庫爾幹什麼?
「三天后……老實說吧,我一點也不想去那裡!」他的表弟小聲說,用一種慘不忍睹的誇張表情看著他,「那真是個一本正經、管理嚴厲的國家,那裡的妓院像是給清教徒開的,妓女裹得緊得像被多看一點就會嫁不出去了一樣!」
——法斯廷和迪庫爾不合不只是在政治上,兩方的民風差距也很大。傑林特到迪庫爾究竟想幹嘛?弗克爾斯想,聯合?不,不可能……也絕不允許這種可能!
「那還真是可怕,」他不動聲色地說,「國王陛下派去的公差?」
傑林特歎了口氣,「身為王子,總是得像個雜役一樣負責他老爸所有嫌麻煩又不重要的工作。照我說嘛,傭兵的忠誠就像妓女的貞操,恐怕他們自己都找不著。」
弗克爾斯打量著他,雖然對方看上去一副不務正業的樣子,他可一點也不覺得這位王子是盞省油的燈。
他在向他暗示什麼?
「也許我該陪我的表弟一起去散散心?」他舉起酒杯,「我和弗卡羅團長還有些舊賬沒有算呢。」他說。他是在說上次那傢伙逃出戰俘營的事,腦袋裡卻不期然浮現出閱兵儀式上那個人嘲弄的嘴臉,他毫不懷疑,是他策劃了所有刺殺凱洛斯的行動。
而最後,他成功了……不,不是他,他攥緊拳頭,指甲陷到肉裡,是我!真正害死他的,是我!
「那可太好了,」傑林特露出燦爛的笑容,和他碰杯,「我正想找個有趣點兒的旅伴呢。」他說,啜飲紅酒的唇邊露出一個狡猾的笑意。
和弗克爾斯猜測的一樣,傑林特也看得出大約是弗卡羅策劃了刺殺凱洛斯的事件,可是誰也沒料到的是一隻巨大銀龍的橫空出現。傑林特以為凱洛斯的勇者身份是一種純政治的籌碼,可是早在遠古滅亡的巨獸的出現打破了一切計畫——神的意志是不可預料的,超脫於一切政客的算計之外。
那位國王是否真是……梅莎柔斯神的使者?他到底死了沒有,是否還會回來?就那個人大得可怕的聲望,他的生死足可影響整個大陸的局勢!
不管他是否活著,他在民眾心裡早已成為一個「代表神的意志」的符號,而和「光明」聯合,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必要的。
兩個各有打算的人相視而笑。傑林特放下紅酒,今天他得早點回去,希望母親已經讓那班法師準備好,把這個孩子轉移出來;這兩天他得把離開前的所有事宜安排好。他歎了口氣,王子真是不人當的。
第二章
馬車突然停了下來。
「怎麼了?」傑林特揚聲問,拉開車簾,車夫正盯著路中央的什麼東西發呆,聽到王子的聲音,用顫抖驚懼的語調說,「先,先生,前面有怪東西……」
弗克爾斯探出頭去,他們正在抄近路趕往迪庫爾,這會兒已經快到達邊境了。
傑林特跳下馬車,弗克爾斯也緊跟著走了過去,前者皺著眉停下腳步。眼前是一具屍體,實際上不走近點看根本難以看出它曾經有個人形——雙腿和左臂已經被撕下,腹腔和胸膛以及裡面的內臟被掏空,肋骨像腐獸的牙一樣大張著,面孔則只剩一團紫黑色的腐敗肉渣。
車夫一副想要乾嘔的表情,傑林特毫不介意地在屍體旁蹲下身查看。「是牙齒咬的。」他說。
「喪屍。」弗克爾斯說,從屍身上可以看到鈍牙的咬痕——不屬於野獸的尖利,是人類的牙印。
傑林特煩躁地站起來,「他媽的,什麼時候開始鬧這個的?怎麼從沒人跟我報告過!」他說。弗克爾斯思忖著他這發音正宗的髒話是從哪裡學到的,可接著,傑林特俐落地轉身走向馬車,「我得去看看。」他說。
「我們不能再往前走了,先生!」車夫恐懼地看著這個不要命的人,「前面在鬧喪屍!我前幾天聽說還不大信,所以才冒險帶你們走這條路,但我們現在去那裡會被撕成碎片的——」
「白天他們不會出來的。」傑林特安慰,「我們可以趕在太陽落山前離開。喪屍聚集的話,只要召幾個白袍來就能擺平了,我只想看看它們的規模。」
車夫依然用力搖頭,眼中的懼怕像深不見底的黑洞,傑林特歎了口氣,「恐懼比光明更容易深入人心,太久的和平真是信仰的大敵。」他攤攤手,「好吧,老兄,我買下你的馬。一匹還是兩匹?」他轉頭看弗克爾斯。
「我和你一起去,你的母親大人要是知道我把你弄丟了,非殺了我不可。」弗克爾斯說,解下其中一匹馬,「如果是幽靈那麼毫無問題,但你有沒有想過死靈法術?」
「可能性之一。畢竟不久前剛有一個愚蠢的王國被巨大的力量所誘,進行了這項倒行逆施的法術。」另一個人嚴肅地點頭,翻身上馬,「帶你真是帶對了,『光明王的子民』,這年頭只有聖凱提卡蘭的人才能真正洗清和死靈法術的關係,我可不想法斯廷被扯進這種不名譽的事件裡去。」
弗克爾斯僵了一下,露出一副不知道是想哭還是想笑的表情。傑林特奇怪地看了他一眼,繼續說道:「雖然人們總說只有失敗是一種罪過,因為歷史是由勝利者編寫的。但我還是覺得不合常理的事總會有另一件奇蹟解決,像死靈術被神蹟打敗。」
「神蹟?」弗克爾斯露出一個嘲諷的笑容。誰又知道,那個傳說中金髮俊美的勇者,具有無限神力的光明之神轉世,軀殼裡靈魂陰冷的成色?他想起那個男人嘴角譏誚的弧度,肆無忌憚的大笑,那種毫不動搖的傲慢眼神總讓他打從心裡發寒,現在想來,對那個總是被大陸驅逐的人來說,被奉為這樣一個身份是件多麼絕妙的諷刺。
雖然即使那傢伙以如此絕決的方式離開了,他留下的盛名和那宛如天神般俊美正直的壁畫,依然在全力支撐著這個國家,可事實不容置疑。
「如果是死靈魔法,」他淡淡地說,「我只希望我們逃跑時能動作快點。」
膽大妄為的王子笑起來,驅動馬匹,毫不猶豫地地向另一個方向跑去。「雖然這馬比宮裡的遜了點兒,我想還是能跑過兩條腿的喪屍。」
弗克爾斯看了他幾秒,策馬前進。看來法斯廷的貴族遠沒有人們以為的那樣為奢華所腐蝕,曾經開創疆土的戰士血統仍然在後代的血管裡奔流。
當他們來到鎮子時已經是傍晚了,道路比想像中難走。
村莊裡是無人的死寂,巨大的夕陽掛在天邊,把一切裝點成曖昧的金紅色,本該炊煙四起的居住地靜得連落下一顆橡子都聽得十分清楚,消失了蟲聲和人聲,村裡流動著一種不屬於人界的邪惡氛圍。
兩人牽著馬慢慢向前走去,村莊乍看之下沒有什麼異樣,除了靜謐得過分;而且離最後留下的人跡顯然已經有一段時日,空氣裡彌漫著一股屍體腐敗的味道,像厄運女神散播在空中不祥的冷笑。
「我們去哪裡?」弗克爾斯問,傑林特駕輕就熟地向一個方向走去。
「刑場,」另一個人說,「刑場總是放在東南方,是整個村莊最黑暗的地方。什麼法術都避不開那裡,我得去看看。」
刑場是一片有些簡陋、可面積還頗為不小的空地。「就是這裡。」傑林特說,兩人停下腳步,眼前的地界一絲聲息也沒有,空地中央豎著簡陋的木製絞架,上面結著難看的樹痂,在夕陽下,像某個邪惡怪物的屍體般瘦骨嶙峋,不懷好意。
傑林特走過去,挑起他秀氣的眉頭,「麻煩是從這裡來的嗎?」他說。細細察看,木架上黑不溜秋的東西像乾涸的血跡,它用這種恐怖的外殼囂張地齜牙咧嘴,滿面威脅,讓傑林特有種踹它一腳的衝動。
想必這裡就是亡界力量聚集之所了,弗克爾斯想。可這真是幽靈作祟嗎?那片寸草不生的空地飄浮不散的、濃烈的黑暗氣息讓他很不舒服……
腳底被什麼絆了一下,他讓開腳步,卻發現下面有什麼白色的東西露出了一個角——雖然沾滿灰塵,但看得出那不是石頭,它泛著一層邪惡的灰白色,像被黑暗入侵過度的骨頭。弗克爾斯用腳撥開周圍覆蓋的浮塵,然後倒抽一口冷氣——邪惡的白色骨質竟長長地向外延伸開去,顯然具有相當的規模!
他迅速蹲下身,撥開更多的浮土,一個直徑三米的骨製魔法陣慢慢浮現在眼前,弗克爾斯口瞪口呆地看著眼前驟然浮現的邪惡陣形,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他再一次意識到了從進村子以來就感受到的那股寒意,那是一種游走於死亡邊緣的森冷之氣,他曾經在另一個人身上嗅到過這種氣味。可笑的是,每次靠近那個人,這種氣息總讓他興奮不已,難以自制。
傑林特注意到了這邊的情況,「這是什麼?」他問,走過來,聲音有些緊張。「魔法陣,顯然有法師搞鬼……」
弗克爾斯突然站起來,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快走!」他叫道。邪惡的味道從四面八方濃烈地湧來,夕陽只剩下一條細細的邊,曖昧地窺探。
弗克爾斯大叫道:「是死靈魔法!」
前方的稻草下伸出一隻手,那是隻泛著灰白色的浮腫手指,它試圖抓住傑林特的腳踝;劍士在感到褲角觸動的瞬間迅速逃開,身邊整個草堆動了起來,一具穿著農夫服裝,渾身腐爛但是還被邪惡之法操縱著的喪屍爬了出來。
弗克爾斯抬起頭,鄉村的小路上三三兩兩的人影正在慢慢聚集,那全是會吞吃任何活物的屍體。「快點!」他大叫,喪屍只是先遣軍,不知道後面還會有什麼麻煩,死靈法術是大陸最黑暗的東西!
馬匹躁動著,不安地打著鼻息,弗克爾斯俐落地跳上去,抓緊韁繩,控制住不安的馬匹;傑林特一劍砍掉喪屍的頭,但後者並沒有停止攻擊,雙手狂亂地試圖抓住一些溫熱的血肉,王子的劍再次揮出,砍掉他的腿!
「快走,傑林特!」弗克爾斯說。同伴的臉頰因為怒氣而有些紅潮,他跳上馬,眼神冰冷;自己的國民被弄成這樣誰都不會開心的,接著他看到路邊溝壑上的草動了一下。弗克爾斯見他不動,拉住他的韁繩,「快點……」
「弗克爾斯,那是什麼!」他叫道。弗克爾斯看到那從草從裡爬出來的東西。
他們最先看到的是它的爪子,看上去還是人類的手,有著人類的肉色和粗糙的皮膚,可是深嵌在他指甲上的,卻是一指長的漆黑色尖刺,它緩緩地爬上來,兩人同時湧起一股想吐的感覺。
這是個怪物。它已經不是人類,曾屬於人類的皮膚像是一層正在蛻動的腐爛皮肉,頭上另一個有著突出嘴部的臉孔正在冒出來,把它的頭撐得很大,以至於屬於人類的灰白皮肉被撐成奇怪的緊繃形狀,一些地方已經爛開,難看地向外翻著。
兩人可以從那曾屬於人類眼眶中,看到裡面將要破殼而出的血紅色巨大瞳孔!
它繼續向上爬,伸出另一雙腳,弗克爾斯注意到它從胯間又長出一雙腿,正用六隻腳向前爬行著。
「它……變異了……」傑林特結結巴巴地說,「這是死靈魔法的力量?」
弗克爾斯終於反應過來,他叫了一聲,「快走!」用力向傑林特的馬踢了一腳,那同樣嚇呆的動物驚嘶一聲,向前跑去。
傑林特迅速挽緊韁繩,控制住受驚的馬匹,他擁有相當精湛的騎術,最重要的是他能臨危不亂——他的動作十分穩定有效,雖然他的咒罵更加精彩。
法斯廷境內竟然出現了死靈法術,這可出大麻煩了!
兩人一路砍開擋路的屍體,死靈術的喪屍可以對抗陽光,也擁有更大的力量。弗克爾斯用力砍掉一隻大張著血口,試圖攻擊自己的喪屍的腦袋,腐臭的腦漿四濺,裡面爬滿骯髒的蛆蟲。
他看到一張張死白的面孔,浮腫的身體……黑暗的法術,弗克爾斯咬緊牙,以及修習這種法術的邪惡的人……
他們策馬狂奔,一邊揮劍砍開饑餓的攻擊者,劍士覺得有些想吐,村莊裡的邪惡氣息讓他窒息!遠遠已經看得見官道,因為仍被喪屍追趕,他們並沒有放慢速度。
四蹄的動物每向前一點,便能讓更加安心,怪物似乎剛剛變異,還不大懂得如何捕獵,弗克爾斯看見那曾是人類的軀體內部蠕動的波紋——是無數個喪屍因為黑暗魔法的力量黏融結合而成的,裡面的東西很快就將撐破人類的皮肉,變成某種他所不瞭解的純粹邪惡的存在!
「見鬼!」前方傳來傑林特一聲咒罵,弗克爾斯一驚,王子殿下已經高難度地停住了馬匹,劍尖指在一個人鼻尖前一寸的地方。
是個人類在橫穿官道!傑林特氣急敗壞地想。把他嚇得心臟都快停了,是的,這是個人類,他穿著法師用的旅行斗篷,看上去相當陳舊,可那之上的一頭金髮卻燦爛奢華得像用金子融出來的,他的面孔英俊得找不到一絲瑕疵,像宗教畫裡的騎士,打從生下來就受神祗的眷寵。
可他的眼睛卻是陰冷淡漠的,流動著黑暗的氣息,這種對比讓他懷有某種令人移不開眼睛的奇異氣質。
看到傑林特的劍尖,年輕的法師不著聲色地皺了一下眉。
確認了眼前人的無害,王子收回劍,「抱歉,」他嘀咕,「體諒被一群喪屍追著的人的驚慌吧!梅莎柔斯神在上,我很多年沒這麼刺激過了。」
「喪屍。」法師低聲說,像在打算著什麼。
弗克爾斯目瞪口呆地看著這個人,懷疑自己幻視了──因為想得太多的關係。
他大氣也不敢出,看著那張熟悉的臉,以及那雙藍眸中冰冷淡漠的神情,他穿著法師的斗篷,他從沒見過他這樣的裝束,他的金髮束在腦後,因為趕路有些凌亂,可那確實是他在腦中無數次描摹,為之瘋狂思念的人!
他還活著?這怎麼可能……
藍眼睛淡漠地掃過他,金髮法師挑挑眉,眼神顫都沒顫一下,然後轉過身,向和他們相反的方向走去。
他的步邁緩慢,但是優雅平穩。
他不可能還活著,因為我太思念他,所以把另一個法師的看成他了?弗克爾斯的腦袋一片混亂,情緒尖叫著卻找不到重點,只能目瞪口呆地看著那個人。
傑林特叫道:「凱洛斯!想起來了,你是弗卡羅下面的那個副官吧!」
怪不得總覺得面熟,這樣英俊過頭的男人理論上他是不會忘的,可是還不到半年——確切地說是四個月,一個人的氣質竟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使得他一時沒有反應過來。
「嘿,別過去了,那個村莊現在很危險!」他大叫著提醒,沒看到這名字讓金髮男人露出厭惡的表情。
看到對方腳步停也不停,傑林特索性跳下馬,急速向前走了幾步,一把拽住凱洛斯的手臂,後者迅速把他的手甩開,傑林特可以看到他眼中的不耐煩。
「那裡在鬧喪屍,你是去找死。」他耐著性子放輕聲音,「你跟弗卡羅鬧彆扭了?」
——他可不捨得看著弗卡羅的寶貝寵物、這麼個金髮美人兒跑去送到喪屍腐臭的肚子裡。
弗卡羅的名字讓正準備離開的男人眼睛閃了一下,緊緊盯著他。看上去猜對了,傑林特想,他和凱洛斯談不上太熟,但這個人對黑髮的傭兵團長不知所謂的迷戀他很清楚。
「前面的村莊有大量喪屍,凱洛斯,你去的話會死的,實際上這裡也很不安全,我們最好離開。」他說。
「你說弗卡羅?他很聰明地失蹤了,」金髮男人喃喃說,「你知道他在哪裡?」
傑林特突然打了個寒顫,凱洛斯的聲音輕柔得可怕——真正有力量的人從不需要用大喊大叫來表現權力,那薄薄的聲線下透著某種讓他不自在的冷酷強勢。他想知道弗卡羅的所在理所當然,可是不知為何,傑林特覺得可能不是件好事兒。
年輕王子揮掉這不知所謂的念頭,沒錯,弗卡羅離開時沒有告訴凱洛斯自己現在正在進行的那個計畫,所以這個年輕人在生氣,一定是這樣。
「我可以帶你去找他,他正忙於工作,已經獨處了好一陣子了,但他也許會想見你,他總說你是唯一不會背叛他的人——」他說,露出一個慣有的輕佻笑容,決定為自己的團長做做「好事」。
對面那雙漂亮得不像話的藍色眼睛閃動了一下,然後點點頭。
「好。」費邇卡說,感到自己的雙手因為渴望而有些顫抖,他不著聲地把它們收到法師袍的袖子裡。
「費邇卡……」弗克爾斯喃喃說,叫出那個不可相信的名字,「你,你怎麼……」
這時法師也看到了他——也許早就看到,只是不想理會。這會兒,他向將要同行的旅伴微點了下頭,移開眼神。
弗克爾斯覺得有什麼梗在那裡!前一瞬間他想過無數種可能,這個曾被他束縛、恨自己入骨、幾乎命喪黃泉的男人,再見到他會有什麼反應,也許會殺了他,或者用無數種方法讓他生不如此,可是,他只衝他點了一下頭。
像最素不相識的陌生人一樣,微點一下頭,疏遠而且毫不經心。
他咬緊牙關,他無數次悔恨於自己對他那個高傲靈魂的自私束縛,可這一刻他再次湧起一種強烈的、渴望把這個傲慢又自以為是的男人鎖在身邊,固定他視線的衝動!
雖然,即使那樣也毫無辦法,他露出一個苦澀的笑意,他連這個靈魂的指尖都觸碰不到。
費邇卡向傑林特淡淡道:「在此之前我必須處理一點事情,我的旅伴在等著救命。」
「那堆東西是你弄出來的?」弗克爾斯說,提高聲音,指著那被活死人佔領的村莊,似乎這種指責可以讓他提起勇氣。
法師看到他眼中的懼怕與厭惡,嘲諷地挑挑眉,如願看到那個人更加憤怒的神色。他知道他恨自己,也許有那麼一點愛,但大多數是恨,但這並不重要,他低低地說:「也許吧。」
那個人怎麼想,和他一點關係也沒有。
他不理會弗克爾斯複雜的表情,他現在的爛攤子已經收拾不完了,那隻愚蠢的黯精靈居然為了賺旅費而把死靈法器留在這個村莊,以幫他們震懾幽靈,真不知道他那顆漂亮的腦袋裡為什麼會裝了如此之多的垃圾,費邇卡不屑地想,那種法器離開他的手中,除了會帶來巨大的麻煩外,帶不來任何其他的東西——哦,或許還有一點小錢。
現在,自己這個不幸必須與之同甘共苦的旅伴,就得出手擺平他留下的所有問題——那個笨蛋居然生病了,他第一次聽說會發燒的精靈,這個種族不是和自然最契合嗎,為什麼居然會因為露宿而感冒?
「因為該感冒的那個是你!」精靈惡狠狠地說,「你最好去幫我把黑暗之盒拿回來,不然恐怕會發生一件非常噁心的事——我們兩個將共赴黃泉!」
——因為這種族詭異的體質,根本找不到適用的草藥。
費邇卡只能來這裡。他厭惡這種和另一個人命運聯繫在一起的情況,而能快速解除這一切問題的,就是弗卡羅。費邇卡想,只要找到聖獸,讓雙方都厭煩透頂的同伴生涯就可以順利結束了!
「我說……我們最好快點離開。」傑林特緊張地說,纖長的手指緊握在劍柄上,身體繃緊,天空完全暗了下去,月亮還未升起,餘暉無法溫暖黑漆漆的樹叢,他可以聽到裡面傳來窸窸蘇蘇的聲音,彷彿無數人在移動。倒是弗克爾斯鎮定了下來,他只是死死盯著金髮的法師,有這個人在他們會很安全。
叢林中爬出一隻腫脹蒼白的屍體,傑林特驚訝地發現一向討厭魔法的凱洛斯的表情如此平靜,他的笑容變得淺淡溫和,像看到什麼心愛的對象。
他轉身向村莊的方向走去。那腳步堅定得讓傑林特一時忘記了拉住他,他不知道四個月能讓一個人變多少,但那是屬於法師的步伐,因為長久泡在大圖書館裡而輕柔無聲的步子,會捏著藥材或手勢而習慣於收在長袍裡的手指,那完全是一個法師的形象!
凱洛斯停下腳步。
他的身影靜謐而放鬆。
「好啦,孩子們,該回家了。」他柔聲說。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重返人間之灰袍法師(上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95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重返人間之灰袍法師(上冊)
當以為已經死了的法師出現在他的眼前時,弗克爾斯還以為自己在作夢。
但那冰冷高傲睥睨一切的眼神讓他知道,費邇卡仍活著,只是對權勢……乃至於世間除知識以外的所有東西不屑一顧而已。
他知道死靈法師心中只有力量沒有善念,也知道繼續追逐這個沒有感情的法師不可能會有結果。但他無法讓自己放棄,正如同費邇卡永不會放棄追逐知識的狂熱一般。
他知道這個騎士願意為他死,而他也相當樂意利用這一點。
人類的慾望總是這麼簡單,整個王國……或是整個世界,等他得到了上古神祇的知識,這些東西垂手可得!但他卻沒有想到,弗克爾斯選擇的竟然是──性!?
太可笑了,他一邊覺得不可思議,一邊卻被決定要先收訂金的騎士壓倒…… 可惡,他這輩子最無法忍受的一件事,就是沉淪啊……
章節試閱
第一章
作為聖凱提卡王的國王軍總司令,弗克爾斯自認見過不少世面──嗜血的狂戰士啦,散發著寒氣的鬼屍骷髏啦,但若要說到他這輩子遇到最荒唐的情景,無疑就是現在了。
剛才他正在和他的舅媽──法斯廷王國的王后瑪格麗特聊天,這時一個面容緊張的侍者走了進來。
「御醫們對王子殿下的匯診結果已經出來了,」侍者吞吞吐吐地說,「我猜他們是有點太老了,以至於神志不清……」
瑪格麗特皺了下眉,有些不滿侍從的評論——下人總得有規矩不是。
「御醫是怎麼說的?」她柔聲問,一頭子夜般漆黑的長髮以最時髦的髮式挽在腦後,即使已經不再年...
作為聖凱提卡王的國王軍總司令,弗克爾斯自認見過不少世面──嗜血的狂戰士啦,散發著寒氣的鬼屍骷髏啦,但若要說到他這輩子遇到最荒唐的情景,無疑就是現在了。
剛才他正在和他的舅媽──法斯廷王國的王后瑪格麗特聊天,這時一個面容緊張的侍者走了進來。
「御醫們對王子殿下的匯診結果已經出來了,」侍者吞吞吐吐地說,「我猜他們是有點太老了,以至於神志不清……」
瑪格麗特皺了下眉,有些不滿侍從的評論——下人總得有規矩不是。
「御醫是怎麼說的?」她柔聲問,一頭子夜般漆黑的長髮以最時髦的髮式挽在腦後,即使已經不再年...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狐狸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06-06 ISBN/ISSN:986706805X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