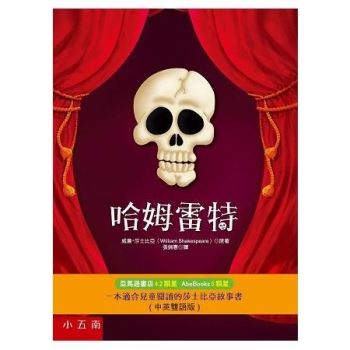白狐
東方傳說狐可以修練成精,這種精明的動物在中國文化中有著亦正亦邪的雙重形象。山海經中《南山經》提到「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海外東經》中也有類似的紀錄),大概是最早關於九尾狐的文字。此時九尾狐還只是一種能食人、叫聲獨特的奇獸。到漢代石刻畫像及磚畫中,開始出現九尾狐與白兔、蟾蜍、三足烏之屬列於西王母座旁以示祥瑞。從此九尾狐象徵子孫繁息,食人之傳漸隱,為瑞之說日漸廣傳。
《說文解字》中,解狐為「祆獸也,鬼所乘之」。唐宋時期,人設廟參拜狐仙。唐朝張鷟《朝野僉載》說﹕「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村。」而到了明清,狐的形象就更加豐富了。《封神演義》有著名的妲己,《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中,狐仙、狐妖的故事更是形形色色、情感豐富。「妖媚」、「仙怪」、「神秘」、「狡猾」……等,可以說是中國人提到狐時最明顯的成見。
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國大陸某個默默無名的小地方,曾經有棟不大的小木屋。曾經木屋裡面住了一個單身男子,和他飼養的寵物白狐。
曾經曾經,在秋風中,那男子摸著白狐的頭說「我來生做牛做馬……」而被白狐焦急的跳躍打斷。
「怎麼?不要我做牛做馬回報?」男子笑著問。
白狐聞言站定,猛力甩甩耳,搧出整片嘩啦聲。雖然一般人看去都會認為那是動物耳朵癢造成的自然舉動,但男子看了卻笑意更深。
「這傢伙,是寧願我生生世世照顧你?」
而這次,白狐用力點了頭,一次又一次。
於是時空轉換,很久很久以後某個冬天的傍晚,白狐出現在水泥叢林裡。車水馬龍的現代都市中,有對夫妻將沒精打采的「白狐狸狗」送進獸醫診所。而執業獸醫辛艾仁很快就知道了這不但非狗是狐,還是隻會說人語、能化身成人的四百歲白狐。
妖狐開口自我介紹叫「白靈」之後,辛艾仁像正常人一樣被超出這常識太多的生物嚇到。若不是白狐變成比他高比他壯的男人抓住他,他可能會打電話報警──雖然警察照理不負責這類問題,叫和尚道士來還比較有效,可是人慌起來是沒理性的。
「拜託,別這樣。不要怕我嘛!」白狐後來無奈的放開獸醫,搖身一變變成比較不具威脅性的少年模樣。「我講個故事給你聽,聽完你再決定要不要把我送走,好嗎?」
辛艾仁沒有說好也沒說不好,他只是默默看著眼前白衣少年落寞的表情,壓下驚慌等妖狐開口。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很遠很遠的地方的故事……」
於是白狐講了一個很長很長的故事,關於牠最早的主人和牠主人的好朋友。牠最早的主人是一個醫生,對萬物一視同仁,在明末清初的亂世中懸壺濟世,卻因此捲入戰火之中。故事中的人生充滿無奈,無奈引起追尋,而一追就是一輩子。
「……他就這樣死了,而我發誓要找到他。」妖狐最後看著頂上的日光燈,悠悠的說。「無論百年、千年,不管他變成男人、女人、好人、壞人,他永遠是我的主人。」
「找到過嗎?」
「找到過啊!好幾次了。」少年扳著指頭算。「一次是女人、一次是老考不上的秀才、還有一次是蹩腳捕頭……每次都要我救他,還有、唔,很多次啦!為了他我快把全中國都跑遍了。」
「那你怎麼會來到台北?」
「民初得到消息說一甲子後他此世會生在夷州首府,所以我就跟國民黨撤退的軍隊一起過來。」白靈聳聳肩,有些感傷的回答。「帶我過來那個老士官長對我很好,可是前兩天他也走了,他兒子媳婦怕我怕得要命,我只好另覓居處……」
「難道我就不怕你?」獸醫問。
「你不怕我。」妖狐變成的少年看向獸醫咧嘴笑笑。「我感覺得出來,你已經不怕我了,不然你不會把故事聽完,一開始我放手你就會逃得老遠。」
「說的也是。」辛艾仁也笑起來。「不過就是隻狐狸嘛!有什麼好怕的呢?」
「所以我可以住下?」
「住就住吧!」獸醫說。「你應該不會傷害病患、也沒傳染病吧?那就讓你住到找到主人為止。」
「真的?」
「當然是真的。」辛艾仁雙手一攤。「反正我剛好有幾包免費狗食快過期了……」
「喂……」
於是故事就這麼連接了起來。
從現在,到很久很久以前……
年獸的故事 臘月三十除夕
相傳中國古時候有一種叫「年」的怪獸,長的青面獠牙、尖角利爪,凶惡無比。年長年深居山中,每到除夕才下山吞食牲畜傷害人命。因此,每到除夕這天,家家戶戶人們都離家躲避年獸的傷害,把這個稱為「過年」。
某年除夕,人們正扶老攜幼上山避難,從村外來了個乞討的老人。人們有的封窗鎖門,有的收拾行裝,到處一片匆忙恐慌景象,沒有人關心這乞討的老人,只有村東頭一位老婦包了餃子請老人吃,勸他快上山躲避年獸。為了報答老婦的好心,老人告訴她年最怕紅色、火光和炸響,要她穿紅衣,在門上張貼紅紙、點上紅燭,在院內燃燒竹子發出炸響。
半夜時分,年獸闖進村。發現村中燈火通明,牠的雙眼被刺眼的紅色逼得睜不開,又聽到有人家傳來響亮的爆竹聲,於是渾身戰慄的逃走了。從此人們知道了趕走年的方法,每年除夕家家貼紅對聯、燃放爆竹;戶戶燭火通明、守更待歲。初一一大早,還要走親串友道喜問好,恭賀對方渡過了年獸的肆虐。後來這風俗越傳越廣,成了中國民間最隆重的傳統節日。
窗外下著毛毛細雨,冬天的冷意從窗縫滲進沒開暖氣的屋內。雖是正午,都市樓群看出去的天空卻暗得讓人失去時間感。巷弄間偶爾傳來零碎鞭炮響,沖天炮的嗶嗶聲刺激著鼓膜,雖說不遠不近、不多不少,這些音效卻總是斷斷續續提醒人它們的存在。現代化都市裡一年之中極少日子有如此陣仗,不知該說幸或不幸,農曆新年就是其中最張狂的一個。
心愛動物醫院二樓,不太大的臥室中,獸醫辛艾仁正在收拾換洗衣物。對獨自居住在都市中工作就學的人來說,過年回家團聚除了表達對傳統的敬意,當然也有更多放鬆的功能。單身男子行李簡便,收拾隨身用品打包回父母家本不是什麼難事,難只難在旁邊有隻動物搗亂。
除去獨居的屋主之外,房間裡還有隻白狐繞著走來走去的獸醫,擺明著在妨礙收拾。白靈看到辛艾仁要拿什麼就叼什麼去別處,不然就是一腳踢遠去。在從狐狸嘴巴裡搶回兩雙襪子、一條皮帶和去房門外撿回一把梳子之後,辛艾仁終於受不了了。
「白靈!」他罵。「你到底在做什麼?」
原本跟前跟後的白狐停下來,在人類面前坐定,兩隻大眼睛眨呀眨的,滿面無辜。
「不幫忙就算了,搗什麼亂啊?」辛艾仁繼續罵。「要玩那邊有狗玩具,不要煩我!再煩把你丟出去!」
「不要走。」白狐說。
「為什麼不要走?不是早就說了要回老媽家過年嗎?你哪根筋不對了?」
「可是我留在這裡很無聊啊!」
「跟你說過幾百次了?」辛艾仁嘆一口氣。「老媽家有條大狗,我不能帶你回去。」
「那你就不要回去嘛!」
「做不到。再怎麼樣過年一定要回去的。」獸醫用堅定的語氣宣布完,接著馬上安撫的說:「你乖,吃的都準備好了,我三天就回來。你覺得無聊就去找找你的主人轉世嘛?如果他是這裡人、或著出生剛出院的話,搞不好會回家過年?」
白靈看著屋主,牠在上個春末以「找尋主人轉世」為由住進心愛動物醫院,這將是在這邊度過的第一個新年。無論理由為何,都可以明顯看出牠白毛覆蓋的尖臉上寫著對留下來過年的不滿。
「我自己會很寂寞……」
「寂寞就去找人啊!」
「唉唷!過年有什麼好慶祝的?不過是一場誤會!」白靈換一下姿勢,眨巴著眼睛。「你要是知道為什麼當初要過年,就不會想過了。」
「為什麼?除舊佈新家人團聚啊!」辛艾仁不悅的回嘴。「還是你說那個放鞭炮趕年獸那個?誰不知道?」
「沒錯,可是背後的原因絕對跟你聽過的不一樣。你不覺得原本的傳說很不合理嗎?」
辛艾仁雙手抱胸,懷疑的看著狐狸。一枚沖天炮在窗邊爆開,勾起那個家喻戶曉的傳說。年獸吃人,人放鞭炮貼紅紙嚇年獸,哪還需要什麼背後的原因?合理的傳說?傳說要能合理,還叫傳說嗎?
「哪裡不一樣?哪不合理?」
「很不一樣。」白狐坐直。「聽好了,這可不是隨處可以聽到的故事。」
※ ※ ※ ※
很久很久以前,在傳說和歷史還無法分辨的年代,某座山的山腳下有個小村莊。那是個很普通的村莊,村民以耕種、狩獵,以及飼養牲畜維生;夏天有驕陽、冬天有白雪,分明的四季讓此處生活不如南方那般輕鬆愜意,但每個人都很努力的工作,所以都過著安和富足的日子。
時值晚秋,正午,深山獸徑上走著一位青年,他的名字叫做戣,姓則是和全村百分之九十的人一樣姓狄。戣是村裡少數獵人中的佼佼者,以獵取山上的走獸為生。
今年夏天靠村邊的山腰上起過一場不大不小的火,雖然造成損害不大,但野獸都走光了,所以到了秋獵時戣往年常走的區域獵物都不多。為了養活自己和新婚一年不到、懷有身孕的妻子,年輕獵人只好帶齊傢伙往更深的山上走,希望能找到野獸新的群居地。
小路沿著山壁拐了個彎,剛好露出密林中少見的天空,戣看看太陽,決定在轉角的空地休息一會兒。他靠山壁坐下,解開腰間裝水的皮囊和乾糧袋。雖說是在休息,戣心裡可是一點也不輕鬆:已經晚秋了,再過不到一個月就要降大雪,到時候飛禽走獸都躲在洞穴裡過冬,就什麼也打不到。自己一個人的時候,餓著肚子一咬牙就過去了,可是總不能餓著妻子和即將出世的孩子啊!
說到妻子,戣心裡就有些奇怪的感覺。戣的父親也是個獵人,在他還不懂事前就死在山上,沒幾年又死了母親,全靠族裡一個多病的叔叔養大;可是戣才能獨力上山沒多久,叔叔也死了。這樣一個窮苦的孤兒,還有人願意嫁給他已是萬幸,更何況妻子勤奮又溫柔,隔年初夏即將為他生下頭胎,照理說戣不應該再會有什麼怨言,但他就是覺得心裡空空的,像是少了些什麼。
管他心裡空不空啊!戣告訴自己倉庫和廚房灶上空不空才重要。所以年輕獵人站起身來,撢撢衣褲上的塵土,準備動身。可是他伸懶腰時不經意一瞥,突然發現不遠處,小路反方向的山壁上有蹊蹺。
看來好像是落石堆吧?可是戣直覺不是,地形也讓他懷疑那裡有個山洞,所以走上前去查看。果然,那是一個洞穴的入口,只是被許多大塊岩石遮住不易發現而已。戣才小心地把一塊石頭搬開,就聞到裡面微弱的生物氣息。
獵人點燃了火摺子,緊握長矛走進洞中。這是一個鐘乳洞,頂上不時會滴下冰冷的水滴,地上積著水窪。而洞底一個高起的石台上,睡著山洞的主人。那是一團棕色和白色的毛皮,球成一團發出沉穩的呼吸,似乎是隻提早開始冬眠的老熊。
戣屏住呼吸,小心地避開水窪向前走去,他知道如果想要獨力打倒這頭熊,就必須在牠清醒前動手。於是他慢慢接近熟睡的獵物,兩步、一步……終於到了攻擊範圍內,戣深吸一口氣,舉矛就刺。可是萬萬沒想到,那團毛皮卻發出人類一般的慘叫。戣在一瞬間愣住了,然後突然被某種怪力舉了起來,但舉起他的東西卻又在他還來得及反應之前慘叫一聲將他丟開。
戣掉在地上時火摺子熄了,山洞中一片漆黑,戣緊握著獵刀聽著對手和自己的喘息聲,等待著那隻野獸隨時向他撲來。可是他只聽到喘息中傳出一個聲音,是斷斷續續,卻很清楚的一句話──
「走……你給我走……」
戣的緊張轉為愧疚和擔心──他竟然誤認為野獸刺傷了一個山中的隱者!他摸索著站起來,在身上尋找打火石和火摺子。
「對不起!真的很對不起!您傷得重嗎?」戣一邊點火一邊說:「請……請讓我看看……」
「不!不要!你快出去!我不要看到你!」
結果火一點燃卻引來另一陣慘叫。戣不解地走上前,想要查看那個用毛皮把自己整個蒙起來的人的傷勢。
「不要!走開!」毛皮下的人只是慘叫著蒙住頭。「走開!把你身上那恐怖的顏色拿走!」
戣先是一愣,再是就著火光檢查身上的穿著:都是很普通的褐色粗衣啊!除了……對了!
「你說的顏色,是這條紅領巾嗎?」戣問。
毛皮下的身體動了動,好像在點頭。於是戣取下紅領巾塞進襟內報告收好了,那毛皮的主人才緩緩地探出頭來。
這次戣真的呆住了,掀開毛皮現身的不是他想像中的長鬚隱者,而是一個全裸的年輕妖怪。剛才看到一團中的白色原來不是用來蓋的毛皮,是牠的長髮和身上的飾毛。這個妖怪有一種和人類男性女性都完全不同的纖細美貌,半瞇著金色的眸顯示出慵懶和憤怒,雪白的長髮中伸出一對金色長角,白裡透紅的肌膚上襯著粉紅的唇和青藍色的紋路,修長的手臂末端是長了長爪的五指,而充滿力感的腰間則突騖地插著戣的長矛,豔紅的血正汩汩流出。
「看夠了嗎?」妖怪沒好氣的說。「可以滾了嗎?我想睡覺。」
戣從驚愕中醒來,心中湧起的不是恐懼而是憐惜,一方面又愧疚自己誤傷了妖怪。憐惜?愧疚?戣自己想了也訝異,他面對的是一個怪物,卻沒有一丁點恐懼。可能是因為這個妖怪會說人話,被他所傷只想趕他走,而且還一副很想睡覺的樣子。
「讓我看看你的傷。」戣走向前。
「不關你的事,這是小……」妖怪可能是想瞥一眼腰傷,裝做沒啥大不了,卻看到自己鮮紅的血而慘叫一聲轉過頭去。
「你怕紅色,要怎麼幫自己治傷呢?」戣走到石台前跪下。
「我不用你管,我睡一覺就好了。」妖怪氣得露出獠牙。
不,或許是因為即使是妖怪,血的顏色也和人類一樣溫暖吧?
戣絲毫不管妖怪的抗議,他是個堅毅執著的人,向來決定要做的事沒人能夠阻止。而不知道是因為腰傷、困倦、戣的真心或是撕爛戣之後會見到的鮮血改變了妖怪的心意,戣的指尖碰到妖怪雪白的肌膚時,只聽到妖怪一聲悶哼,沒有做出下一步的阻止反應。
「傷得很深,我去採一些藥草來再幫你治傷。」戣檢查完傷勢,站起身。
「不用……」妖怪趴著,似乎已經快睡著了。「我要睡覺……」
戣自顧自地離開山洞去採藥草。當他找了麻藥和止血藥回來,發現妖怪已經自己拔掉了矛,再度裹著毛皮沉沉睡去。年輕獵人嘆氣搖搖頭,無法相信這個妖怪竟然這麼相信人,於是他嚼碎藥草,撕下衣襟替妖怪包紮了起來。
回到村中天已經黑了,戣的妻子梅著急地舉著火把在門口等候。戣很興奮地告訴妻子:今天,他在深山裡遇到了一個妖怪。
妻子的驚訝是當然的,但戣努力地跟她解釋,這個怕紅色的妖怪有多美麗、多溫和、多麼的信任人。
之後戣天天都上山去探望那妖怪,替牠換藥,如果打得到獵物也分給妖怪一份。不過妖怪總是在睡覺,幾乎不理會戣的存在,也不吃戣帶來的食物,只有偶爾被戣吵得煩了,才跟他說一兩句話。慢慢戣知道了妖怪叫做年,怕所有紅色的東西,一覺要睡四季,只有在隆冬時會醒來一天在大雪中找東西吃,吃一餐再睡覺。他們的交談模式大約是這樣的:
「喂,年,你上次說你睡一覺起來一天找東西吃,那要是找不到呢?」
「繼續睡下一覺……」
「再睡四季嗎?喂!年,不要睡!」
「………」年又睡著了。
戣在年的洞穴附近找到了新的野鹿群,幾乎天天可以帶著獵獲物下山。可是他開始覺得,每天年有沒有跟他說話,比他下山時有沒有背著獵物還重要。那種心裡空空的感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每天年愛睏鬧出的新笑話,或是一些年隨口新講的習性和瑣事。年的山洞變成戣的第二個家,他每天剛破曉就上山,無論是否獵到獵物,正午以後就窩在年的山洞裡直到傍晚,對著熟睡或半清醒的年說一大堆有的沒有的事。本性沉默的從來不知道,原來自己有這麼多話可以說。
漸漸戣發現,年在他心中的份量越來越重、越來越重……
一個月不到,年的傷好了,初冬的第一場雪也降下。戣知道自己不應該再冒險上山找年,他開始告訴年他的住處,希望年一覺醒來可以來見他。戣的努力過程是如此:
第一天:
「年,你睡醒來我家玩吧?我準備吃的給你,你就不用出去找了。」
「好……」
「我想介紹給你我的妻子,還有……喂,別睡……」
年睡著了。
第二天:
「年,我跟你講,喂,年……」
年死也不起床。
第三、第四天下大雪,上不了山。
第五天:
「年,我跟你講,我家在山腳的那個村子裡,你知道怎麼走嗎?」
「大概知道……」
「就是沿著旁邊那條小路往山下走……」
「知道了……」可是這句是夢話。
第六天:
「年,我家是村西那棟新蓋的獨門獨院小屋,知道嗎?」
「知道……」
「那你講一次給我聽。」
「……」年又睡死了。
第七天:
「年,喂,我明天就不能再來了,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家在哪?」
年顯然意識不清醒。
「好吧,我放棄,地圖畫在這裡……」
所以最後戣拿木炭把地圖和自己家的外貌畫在山洞的洞壁上。
終於,隆冬的十二月來臨了,大雪封山。在連續幾次上山半途因為路況不明折回後,戣只好待在家裡,刮製獵得的獸皮,偶爾到鄰居家聊天喝茶,也偶爾巡視設在村莊四周的小陷阱。「日子過得好無聊」──戣在心中由衷地感嘆。以往他最喜歡的就是冬天,可以和一年農忙之後的村人在火爐邊閒聊扯淡,享用一年工作的成果,冬天就是休息的季節。可是今年冬天他卻覺得有比以往強烈的、那種心裡空空的感覺,遠比遇見年之前強烈好幾倍。年……戣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等年來。
戣看得出來梅對年的期待遠不如自己強烈,畢竟她還是會怕一個長角和尖牙利爪的妖怪。對於這點戣也有一點擔心,他害怕年的出現會嚇到村人,不過想見年的思念遠強烈過所有的憂慮。
想見年……戣知道自己瘋狂地想見年……
不知道年……想見他嗎?
一場暴風雪後的清晨,天還未破曉,敲門聲就在戣家的木門上響起。怕是村中出了什麼急事,戣不情願地從炕上爬起,裹著棉襖去應門。
「誰啊?大清早的……」
「我。」
「我我我,我是誰啊?」戣一千個不情願地拉開木門,想要看清楚門外到底是哪個傢伙,一大早擾人清夢還不報上姓名。
「咦?你是……?」
門外披著熊皮襖的,是像雪原一般晶瑩美麗,五官深邃的纖細青年。他有烏黑的髮、淡紅的唇,剔透的肌膚下隱現微微玫瑰色,夜空般深沉的瞳閃爍出妖魅的金光。這個青年完全無懼於天寒地凍的氣溫,在戣的門口微笑著,任由吐出的蒸氣在雙頰上結成冰晶。
「不認得我了嗎?我是年啊!」他說。
戣沒有反應,只是盯著這個青年,他被眼前的容貌所震懾。他見過最嬌美的女人、最俊朗的男人,但遠不及眼前的萬分之一。戣無法拿這人來與自己妻子比較,因為他一點也不像女人。那就像山巔的雪豹一般,優雅、敏捷、自在而犀利,這張臉的確是他在山洞裡誤傷的怪物,可是,看起來卻是不折不扣的人形……
「你還沒睡醒嗎?醒醒啊!我都醒了!」
年在戣眼前晃著手,努力想要確定戣是否還醒著。
戣一把抓住年晃動的手,望入那星空般的眼眸,他知道,那正是數月前在山洞中一瞬間奪去他靈魂的金光……
「夫君?」
梅的聲音打破門口凝結的時空,她見到丈夫應門之後久久沒動靜,疑心起身查看,卻看到自己的丈夫握著年輕男子的手,兩人僵立在門前。
那樣的戣,是梅從來沒有見過的。她認識的戣,一直是溫和平淡的堅毅男人,她從來沒有見過丈夫像這樣激動到只能呆立在原處。而且是她多心嗎?為何戣聽到她呼喚回頭的一瞬間,露出尷尬的驚慌神色?
「啊!梅,向妳介紹,這就是我常提起的年。」
梅很訝異年並不是戣當初形容的青面獠牙,可惜年的人形並沒有加深梅對牠的好感。但是梅還是像對其他人一樣,和年寒暄,找了套戣的衣服給年穿,然後一起吃早飯。
「你知道嗎?你很特別。」在餐桌上,年對戣說。
「哪裡特別?我不就這樣?」戣笑著挾菜到年碗裡。
「你看我的眼神,和我遇到的其他人類都不一樣。」
戣頓了頓,不知道年這是褒還是貶。
「那,你不喜歡我這樣嗎?」
「不會啊!我很喜歡。」年有種特技,嘴裡塞滿食物還能笑得很美。「其他人類看到我全都嚇得半死,只有你,竟然還會想要幫我治傷。」
「啊……那是因為……」戣有點窘,畢竟,那是自己的錯。
突然,旁邊的土製暖爐中傳來巨大爆裂聲,年嚇得整個彈起來,像受驚的雪兔一般奪門往屋外衝去。戣追上去,跑了好久才追上終於冷靜下來的年,他正瑟瑟地在站風中顫抖。
「那……那是什麼聲音啊?」年不怕冷,讓他顫抖的是剛才的巨響。「人類的家裡,隨時都會發出爆裂聲嗎?我不回去了。」
「不是不是,那是竹子啦!是木柴不夠,我劈來燒的竹子。」戣雖然知道年不怕冷,但看他發抖還是忍不住將年擁入懷中。「只是竹子燒久了,裂開發出的爆炸聲。不用怕,我叫梅把暖爐搬走就是了,嗯?」
體型和戣相去無幾的年在戣懷中悶聲笑了起來,笑得戣手足無措。
「戣,你真的很特別。竟然會關心我這怪物怕什麼啊!」
「管他什麼怪物,你現在看起來是人啊!」
「但之前可不是人形啊!」年推開戣,甩甩頭。「你真的是很特別。」
「一直說特別特別的,到底是哪裡……」
「那不重要了。」年拖著戣往回家的路走。「反正我喜歡你,這樣就好了。」
一路上戣給年拖著,反覆想著年剛才的話。喜歡,好不熟悉的兩個字啊……
於是兩人回到戣的家中吃完剩下的早飯,吃完以後戣就帶著年到村中蹓躂。這種小村莊的人們都好客,尤其是年的外貌如此引人,每個人都想在年身旁多待一下、再多看年一眼。不再整天想睡的年出乎意料的博學又健談,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對於自然的脈動又瞭若指掌,聽到戣不禁暗自納悶:這個永遠在睡覺的傢伙怎麼會知道這麼多?
就這樣,戣帶著年在村人熱情的招待中玩到了晚餐時間,漸暗的天色讓年打起了呵欠。很明顯,唯一一天的時光過去了,年應該要回去再開始那漫長的睡眠。戣帶年回家跟梅告別,年卻遠遠就停下來,怎麼也不肯接近他們家。
「這次又怎麼了?」
「怪聲音,好吵的怪聲音。」年捂著耳朵說。
戣回到家中一看,原來是妻子在剁餡包餃子,刀碰砧板的鈍聲叩叩作響。他只好無可奈何地告訴妻子:不要剁了,年怕吵。
「我睡覺的時候,你還是會來找我吧?」年向梅道歉帶來的麻煩後,又再轉向戣。
「雪融了之後就去。」戣咧出一個自己都不知道的微笑。
「啊……那我又不能好好睡覺了……」年打出個誇張的呵欠,連手都遮不住。
「你不希望我吵你嗎?」
「不會啦!我喜歡戣啊!」年笑著說。「如果你不來找我,我會在作夢的時候來找你。」
戣看著年的笑容,不禁又愣了。而年早習慣了他看著自己發呆,所以揮手向梅告別。
「那麼,梅,下次睡醒時再見囉!」
「啊!我送你出去。」戣從發呆裡醒過來。
「好啊!」年再次露出那魅惑人的微笑。
看著一人一怪話別,梅知道這裡有些許不對勁:戣對年的感情和對村中好友、對妻子的感情都不同。她突然發現,一個冬天讓戣朝思暮想、魂不守舍的,就是眼前的雪白身影!
沒關係,梅告訴自己,只要過了今天,這個怪物就會回到山裡繼續沉睡。只要過了今天,丈夫就會恢復正常,回到自己身邊……
事情並不如梅所設想的那樣美好,年的離去只是惡夢的開端。戣比往常更心不在焉了,總是直直望著窗外的雪景發呆,也比從前任何一個冬天都強烈祈求著春天的到來。
而立春以後情況只有越來越糟,戣不樣往年般趁著春天萬物休養生息、不適合打獵的季節去別人田中幫忙春耕,卻一個勁地往山上跑,藉口是打獵。梅知道戣從不在春天打獵,他上山,是去見年的!
梅忍無可忍了,再過三個月孩子就要出生,她不能忍受家中沒有男人工作,更不能忍受將出生的孩子沒有父親。所以梅偷偷跟蹤戣上了山,打量著好的話,可以勸年找新的山洞,離開戣身邊;不成的話,找出年的山洞,改天趁戣不在時,將年薰昏了再另做打算。
梅帶了把短刀防身,悄悄跟著在丈夫的身後。饒是為了想見年過了頭,原是敏感至極的戣竟一路沒有察覺到她的存在。這樣半途遇到猛獸攻擊怎麼應付得來?越是這樣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梅的心就越往下沉,加緊腳步跟好信步在春風中的獵人。
梅看到戣點燃火把進了那個洞穴,一方面出自好奇,一方面要確定是否真的是這裡,她在戣進去一段時間後躡足摸進洞中。說來也不可思議,竟然連這樣她都沒被發現?
搖曳的火光中,梅看到自己的丈夫坐在一隻熟睡的、全身雪白的怪物身旁,極其溫柔地撫摸怪物的銀白色頭髮,然後彎下身吻那怪物。梅驚訝的看著眼前景象,戣從來不曾在她面前展現過這張臉,就算在黑燈瞎火的夜裡枕邊也沒有。那表情是如此深情、溫暖,並充滿了寵溺,看到讓她全身流過電殛般的嫉妒和恨意。
於是梅再也無法克制自己衝上前拉開兩人的衝動,筆直向兩人走去。她刻意踩響地上的水潭宣告自己存在,戣驚嚇了,手足無措地從年身邊站起。
「你……和這怪物是這種關係嗎?」梅走向年躺臥的高台。
「不……不是!我只是……」年輕獵人心虛的回應。
「只是什麼?」梅用足以將怒火凍結的喉音逼問,拔刀丟下刀鞘逼向兩人。
「梅,妳冷靜一點,聽我解釋。」
梅不發一語,揮刀向睡夢中的年砍去,被戣即時擋了下來。
「梅!妳冷靜下來!」
「我為什麼要冷靜?」梅的髮髻在掙扎中散了,她披散著亂髮恨恨地說道。「這怪物搶走了我的丈夫,搶走了我孩子的父親,我還該冷靜嗎?」
「不是!妳聽我說,這不是年的錯!」
「我不要聽!」
戣和梅在山洞中扭打,努力想奪過妻子手中的刀。可是沒想到女人拗起來力氣大得嚇人。爭執中刀刃劃過戣的肩頭,他分了心,絆到一塊斷落的石塊,腳下一滑,不偏不倚就讓一根特別尖利的石筍穿腹而過。
戣俯臥在那根石筍上,努力想要起身,將這龐大的異物從自己腹中拔出。梅只能呆呆站在那裡,看著戣徒勞無功在痛苦中掙扎。戣的雙手揮舞著,一下子就伸手抓住她的衣襬,抬頭用呆滯的眼光向她求救。梅害怕到了極點,拚命想把衣襬從戣的手裡扯出,但垂死的戣用畢生所有的力氣緊握住那塊布片,好像是抓住這塊衣襬,就能抓住最後一線生機一般。
扭動著嘴唇,戣張口想說些什麼,卻只吐出一個大血泡。梅不顧一切地用刀割斷那塊衣襬,她現在只想逃,逃離這個恐怖的洞穴。
梅衝下山,強忍著作嘔的感覺,腦中一團混亂。怎麼辦?說戣失蹤嗎?要怎麼跟村人解釋戣的失蹤?要是年醒來懷疑戣的死因,要怎麼解釋戣死在洞裡、手中握著她的衣襬?如果要殺掉年滅口,她做得到嗎?而且她害死了戣!天啊!梅想到就不知所措,她害死了自己的丈夫啊!
看著村落接近,漸漸恨意回到梅的胸口,一切都是那隻妖獸的錯啊!要是牠不接近她的丈夫,一切不都沒事了嗎?黑色濃雲纏繞梅的心,她沒有勇氣再回到自己害死戣的山洞裡殺年,也不能再讓年回到村中揭露所有的疑點……一個萬全的毒計,在這弱女子的心中逐漸成型||反正只要讓年現出原形,沒有人會相信一個妖怪的。
於是她深吸一口氣,喊出那惡毒的控訴:
「不好了!戣給山上妖怪吃了啊!」
梅拔高的嗓音在村中迅速傳開,引來所有三姑六婆和她們的丈夫。怎麼可能呢?人們議論紛紛,戣是村裡最好的獵人啊!
「是妖怪!是那個冬天來作客的白衣人啊!他是妖怪變成的!戣被那食人妖怪騙了啊!」
梅嘔著害喜和恐懼的酸水,悲苦地解釋自己如何擔心丈夫而找上山,最後發現妖怪正血淋淋啃噬著戣的屍首。
「好險啊!妖怪追了上來,差一點就逃不掉了……」梅說。
鄰人溫暖的扶持下,可憐的妻子展示身上被破裂的衣襬,告訴大家還好她戴著紅頭巾,不然鐵定逃不了。怪物的所在?她荒不擇路逃跑時早迷失了方向,能下得山已是幸運,不然她也想帶人上山圍剿。不過,那妖怪在隆冬中會醒來,會再來村裡找東西吃。這次,要不做點預防措施,大概全村都逃不掉了吧……
經過長長的沉睡,年在山洞裡醒來,始料未及,第一眼見到的竟然是戣腐壞的屍身。嗅著因腐敗而變化的戣的氣味,妖獸發出哀傷的嚎叫迴盪在石洞中。戣怎麼會死了呢?他還以為沒人吵他,是戣終於要讓他好好睡覺了呢!年有生以來第一次深惡痛覺自己長時間的睡眠習慣,他不懂怎麼會這樣。難道戣在這裡出了什麼意外嗎?村裡的人知道嗎?梅知道嗎?
年化為人形,跳起來往村子的方向狂奔。他要回去村子裡告訴村人、告訴梅……
年遠遠接近村落就覺得村裡好吵,為什麼人人都在剁餡做餃子?而且還家家戶戶都燒竹子發出爆裂聲?那不重要,年急著要回村裡報告戣的死訊。但一近村口,穿著讓年發昏的紅衣的小孩就尖叫著跑回,引來成群的大人。每人不是穿著紅衣就是帶著什麼紅色的東西,全村的人都敲鑼打鼓,像是驅趕什麼一樣朝他這邊湧來。
什麼?年聽不懂梅在說什麼,也不懂村人皺著眉頭的意思,他們說他殺了戣?怎麼可能有這種事?他想要說話,但被震耳欲聾的爆竹和鑼鼓聲蓋了下去;他大叫,人們只當他在瘋狂地怒吼。整整十二個月,友善好客的村民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如烈火般燃燒過來的惡意、讓他作嘔的大紅色和幾乎要震破他耳膜的吵鬧聲。
年越來越驚慌,也越來越憤怒,這個讓他不解的恐怖環境將他團團包圍,大口啃噬著他的理智,猛力將他推向瘋狂的懸崖邊緣。戣……戣呢?
戣死了!
這三個字化為最尖厲高亢的嘶吼,年一瞬間變回了原形,長角、尖齒、利爪,這個雪白的怪物撕裂身上穿著的人類衣著,像要從滿天寒星那討回公道般,對無盡蒼穹發出令人顫慄的心碎哭號。年用利爪在人群包圍中殺出一條血路,在村民慘叫中飛也似的逃向覆滿白雪的山上。他聽到背後傳來人群的歡呼聲,慶祝趕走了披著人皮的食人怪物;他也聽到歡呼聲中有哀叫,那是被他利爪所傷的「無辜」受害者。但他管不著了,他要逃回他的山洞繼續沉沉睡去。
反正這次,不會再有人打擾他了……
據說後來,被年大鬧的村落害怕年再回來,所以在每年冬天的這個時候都要穿紅衣、在門上貼紅紙、剁餡包餃子,並且敲鑼打鼓燃放爆竹,他們稱這個叫「過年」,並且把年睡一覺醒來的時間叫做「一年」。
漸漸這個習俗傳開了,各地的人都怕年來,因此都在冬天的這個時候做這些活動,防止「年」來騷擾他們。而當孩子們問起這個習俗時,老祖母就會告訴孫兒──
從前,有一隻凶狠殘暴的食人怪物,叫作年……
※ ※ ※ ※
窗外鞭炮響一串緊過一串,不知不覺天已經黑透。只被窗外霓虹燈點亮的暗室內,辛艾仁起身、按開臥室的電燈開關,然後走去外面客廳。
「你去哪?」白靈問。
「……你以為現在幾點?」辛艾仁恨恨的拿起電話。「我現在回去幾點才到?」
「耶?所以你是說?」狐狸興奮的跳起來。
「喂?爸?」青年自顧自的講起電話來。「對不起,今天有急診病患,我現在才要出門。會很晚才到……」
隨著辛艾仁和家人的對話進行,白狐的頭越垂越低,尖尖的耳朵也塌了下來。等到青年收線掛上電話回房間,只見身後床上坐著全身白衣的美少年,兩顆金色大眼睛水汪汪的只差沒掉下淚來。
「還是要走?」白狐變成的少年問。
「沒錯。」獸醫扯起少年屁股底下的毛衣,塞進背包裡。
「為什麼?都這麼晚了你還要走……」白靈說。「聽完年獸的故事,你不覺得過年應該是增進異種族感情交流的好時機嗎?」
「不覺得。聽起來倒比較像大家都應該在家過年以避免外遇發生……」辛艾仁意有所指的斜瞄白靈。「特別是跟不是人的對象。」
「鐵石心腸……」
無視於白靈的哭音,辛艾仁把最後幾樣東西用提袋裝好,期間理也不理喃喃唸著的妖狐。直到他收拾完,站直身,才再轉頭回床的方向。被揉皺的被單上,少年可憐兮兮的看著人類,滿臉小狗要被拋棄的表情。
「你以為講個故事拖時間我就不會走了?」辛艾仁冷冷的問。
「不是嗎?」白靈哀哀的說。「就跟你說過年沒什麼好慶祝的了……」
獸醫從鼻子裡哼出一口氣,右肩把旅行背包扛好,左手提起提袋。然後,他還是冷冷的開口:
「變回原來的樣子,不然休想我帶你去。」
「欸?」
「約法三章:在老媽家期間不准變成人的樣子,不准說話,不准跟狗打架,也不准沒報備就跑出門。」獸醫皺著眉頭警告。「你敢讓我家人察覺丁點不對,就沒有下次了。」
「意思是說我可以去?」白狐變回原形,一蹦跳起來。「我可以去嗎?我可以去嗎?」
「笨狗,我敢不帶你去嗎?回來大概房子都被你拆了吧?」辛艾仁舉舉手上的提袋,旁邊凸出一塊狗碗的形狀,不知道什麼時候被塞進去的。「還虧你說自己四百歲,難道是老眼昏花沒注意到?」
「我是狐狸!」白靈抗議。「而且我才四百歲!很年輕!」
「行為舉止明明就像狗,而且是條笨狗。」獸醫邊說邊大跨步走出房間。「走不走?再不走要天亮了。」
「愛人!等我!」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合理的傳說(上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合理的傳說(上冊)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單身男子和白狐做了這樣的約定:
「這傢伙,是寧願我生生世世照顧你?」
於是今世成為獸醫的辛艾仁,莫名其妙就收留了一隻自稱有四百歲,並且很會說故事的狐狸精白靈。
「你不覺得原本的傳說很不合理嗎?」
人類會過年只是緣於一場誤會?初三老鼠嫁女兒的真相究竟是?夸父追日是一個悲慘的愛情故事?火神祝融與水神共工戰爭的原因究竟是……
您或許在小時候就聽過這些熟悉的中國神話,但您確定您真的知道這些故事背後所發生的事嗎?
章節試閱
白狐
東方傳說狐可以修練成精,這種精明的動物在中國文化中有著亦正亦邪的雙重形象。山海經中《南山經》提到「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海外東經》中也有類似的紀錄),大概是最早關於九尾狐的文字。此時九尾狐還只是一種能食人、叫聲獨特的奇獸。到漢代石刻畫像及磚畫中,開始出現九尾狐與白兔、蟾蜍、三足烏之屬列於西王母座旁以示祥瑞。從此九尾狐象徵子孫繁息,食人之傳漸隱,為瑞之說日漸廣傳。
《說文解字》中,解狐為「祆獸也,鬼所乘之」。唐宋時期,人設廟參拜狐仙。唐朝張鷟《朝野...
東方傳說狐可以修練成精,這種精明的動物在中國文化中有著亦正亦邪的雙重形象。山海經中《南山經》提到「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海外東經》中也有類似的紀錄),大概是最早關於九尾狐的文字。此時九尾狐還只是一種能食人、叫聲獨特的奇獸。到漢代石刻畫像及磚畫中,開始出現九尾狐與白兔、蟾蜍、三足烏之屬列於西王母座旁以示祥瑞。從此九尾狐象徵子孫繁息,食人之傳漸隱,為瑞之說日漸廣傳。
《說文解字》中,解狐為「祆獸也,鬼所乘之」。唐宋時期,人設廟參拜狐仙。唐朝張鷟《朝野...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田終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08-22 ISBN/ISSN:986706860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