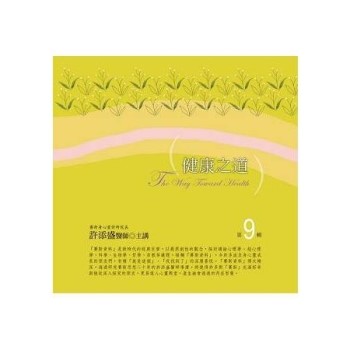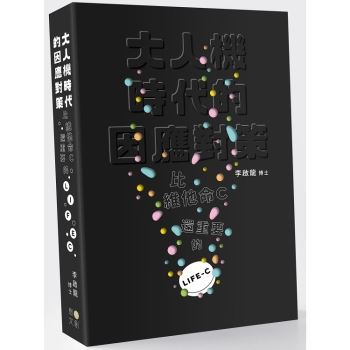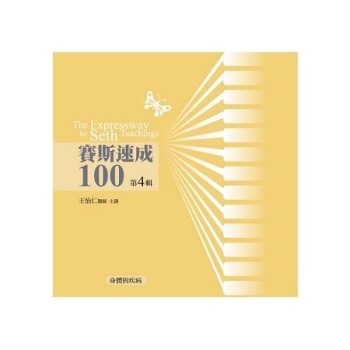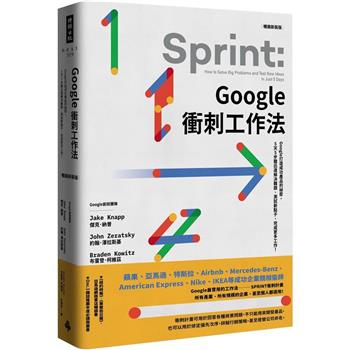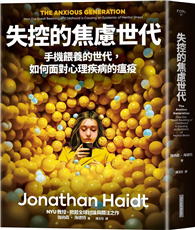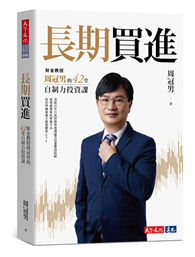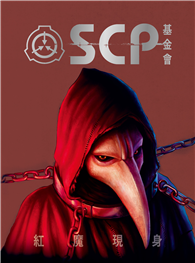簡介
「基督」是基督徒信仰的對象,「神學」是反思與表達信仰的過程與結果。本書書名提出了兩個問題:「哪位基督?」以及「何種神學?」雖說沒有人會否認基督教信仰的對象是耶穌基督,但對耶穌基督的理解卻大不相同;進而神學的方法與走向也就大異其趣。
本書承認讀經的神學性、以此作為主軸來處理神學詮釋學的進路;論述結構上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著重當代神學釋經學的介紹;第二部分則為作者對當代神學反思之成果。第一部分介紹了巴特(Karl Barth)、布特曼(Rudolf Bultmann)、弗萊(Hans Frei)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等四位當代神學家的思想、當代神學詮釋學的內涵,強調一種「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學詮釋學。進而,第二部分先探討神學、哲學、釋經學的關係,且批判種種忽視「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學、或「以哲學凌駕啟示之上」的立場;其中包括「歷史批判法」、「社會科學法」、「讀者中心論」等等的內容。作者不僅消極地批判,更對教會的神學走向提出積極可為的建議。
「歐力仁博士可以說是當今台灣最優秀的神學家之一,他非常關注神學詮釋學的議題。在此書中,歐博士與幾位當代最重要的神學詮釋學家展開清新且批判性的對話。我發現力仁博士的諸多堅持十分正確。所以,我認為這本書值得你我花時間去閱讀,有助於我們比較全面地了解詮釋學的議題。
──周學信 中華福音神學院教會歷史與神學教授
「歐博士的新作為我們開了眼界,他能夠深入到神學家的文本來析辨其論旨,堅定地站在作者的立場上為文立論,著實為這已被後現代思潮主宰的時代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洞見。歐博士既有學者素養,又帶牧者關懷,行文中捍衛真道之情、堅定信徒之心流露…。此時此刻,我們需要此等紮根之作幫助我們重省何謂基督中心的聖經詮釋。」
──橄欖華宣出版公司主編 鄧元尉 博士
【編輯導讀】
「基督」是基督徒信仰的對象,「神學」是反思與表達信仰的過程與結果。本書書名提出了兩個問題:「哪位基督?」以及「何種神學?」雖說沒有人會否認基督教信仰的對象是耶穌基督,但對耶穌基督的理解卻大不相同;進而神學的方法與走向也就大異其趣。
「神學詮釋學」(theological hermeneutics;或「神學釋經學」)是一種理解和詮釋信仰內容(聖經)的方法。這種方法不同於「歷史批判法」(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和「社會科學方法」(social-scientific approaches),它不把詮釋的焦點放在鑽研聖經歷史、作者意圖或讀者身分,或是盡力重構以色列╱猶太社會體系之上,而是教義性地來理解聖經。進一步來說:神學詮釋學的目的不在於從聖經原作者、讀者的考證中去尋找「歷史的耶穌」,而是指出基督徒在「福音傳揚」(Kerygma)中「信仰的基督」在聖經的地位與合法性。神學詮釋的起點絕非將讀經活動視為一種對流傳文獻的考古,而是與三一真神的會遇、對話;這個起點必須在神的無限作為、絕對自由、與全然慈愛之中才能理解。由此觀之,聖經乃是來自耶穌基督所彰顯的恩典,讀經則是靈性渴求者與豐盛的生命和真理的福音會遇的行動。
本書為歐力仁教授六篇論文集結而成,雖為不同時期發表之期刊論文,卻可看出一貫而嚴密的論述主題。就主旨而言,他承認讀經的神學性、以此作為主軸來處理神學詮釋學的進路。就論述結構來說,可以分為兩部分:本書的前四章與最後兩章。
第一部分著重當代神學釋經學的介紹;作者介紹了四位主要人物的思想:巴特(Karl Barth)、布特曼(Rudolf Bultmann)、弗萊(Hans Frei)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他們的神學釋經學及其中「基督」在聖經中的地位。第二部分則為作者對當代神學反思之成果:第五章探究了哲學、神學和釋經學三者之間的辯證關係,進而批判了不當的神學-哲學觀點;第六章則探討「歷史批判法」和「社會科學法」這兩種不容忽略的當代聖經詮釋理論,也探討了「讀者中心論」的讀經、釋經方法;進而,對這些方法不當地去除信仰基督的神聖性進行批判。然而,這部分不僅是消極性的批判,作者亦指出積極可為的道路。
因此,可以說第一部分對「信仰的基督」的強調,是第二部分批判的基礎,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對比:第一部分介紹的神學家從不同角度強調:「信仰的基督」是聖經的焦點,亦是詮釋聖經和神學思考的主軸;第二部分則以「信仰的基督」的神學態度指出「以哲學凌駕啟示」和探究「歷史的耶穌」之基本立場的不當之處,並提出自己積極性的建議。
因此,這不僅是一本當代神學的介紹性書籍,同時也是一位神學工作者反省神學詮釋學議題的洞見與成果;作者不僅與各種神學思想對話,亦為將來的神學工作指出一條明路。值得認真反省信仰的讀者細細品味。
(責任編輯郭大維)
作者簡介:
歐力仁,台南神學院神學研究所碩士、英國聖安德烈大學神學/宗教研究所博士。專長系統神學、基督教教義史、基督教思想史、哲學神學、神學詮釋學、神學知識論等。著有《信仰的類比:巴特神學與詮釋學中的修正與顛覆》(文字事務出版社)、《你的神祇,我的上帝?──宗教的神學省思與信仰的實踐》(天道)等。現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榮譽副研究員。
章節試閱
試閱文字
第五章 雅典、耶路撒冷與伯利恆
──哲學、神學與釋經學關係之再思
前言
雅典、耶路撒冷與伯利恆分別象徵愛智慧的哲學、表達信仰的神學以及以基督為中心的釋經學。翻開二千多年的基督教歷史,因為重視哲學、神學與釋經學之間應有的互動關係而提出看法或解決方案者之中不乏重量級的神學家。縱然所提的方案之間有些差異,他們仍一致認為如果運用得當,哲學可以為神學提供紮實的方法論。顯然地,就神學發展的歷史來看,哲學和神學是關係最密切,互動最頻繁的人文訓練之學科。通常神學家與哲學家是最佳的對話伙伴。這種情況絕對不是偶然發生的。主要是因為神學與哲學之間存有為數相當可觀的共通點,它們成了兩者的接觸點。例如,兩者除關注人的問題以外,也研究肉眼和經驗不可及的題材。諸如,「萬物終極的基礎」、「認識的方法」、「價值觀」、「倫理」和「生命」……等。
不過,雖然哲學對神學有不容否定的貢獻;兩者關係之密切,同質性之大也是不爭的事實,它們終究是兩門不同的學問;各自背負著不同的使命,也有不容取代的地位。因此,它們之間的關係可能是友好互助的,也有可能是敵對競爭的。德國神學家艾柏林(Gerhard Ebeling)的一席話頗能說明兩者之間這種聚合力和張力並存的複雜關係:
自神學肇始以來,哲學就是神學史的一個一體化的因素。神學與哲學的這種伙伴關係……從最內在的滲透一直延伸到最外在的敵對關係:從一種冒充神學的哲學一直到一種從與神學對立出發來理解自身的哲學;從一種顯得化解入哲學的神學一直到一種力圖擺脫與哲學有任何接觸的神學。在這中間,以無數種組合和層次存在……彼此之間的交往關係中。
也就是說,它們兩者之間的互動模式,從水乳交融到水火不容均有。神學人最大的任務之一就是用心去拿捏神學與哲學之間的分際;釐清責任歸屬,使哲學不致於反客為主,越俎代庖。這便是本文的目的。為達到此一目標,本文首先探討四種神學發展史當中最常見的神哲關係模式。
筆者將在每一種模式中均列舉一至二位代表性的人物為例,加以剖析、批判,進而具體建議有心學習神學的讀者選擇本文列舉的第四種模式(以哲學做為檢驗神學內容的工具)。避免重蹈第三種模式(以哲學做為神學的內容)的覆轍。本文最後,筆者將以「過程神學」(運用過程哲學理論)和「讀者反應╱後現代釋經學」(以後現代哲學做主軸) 做為檢討的對象,藉以指出第三種關係模式之不當,並以此回應凱勒和讀者反應釋經學的擁護者。
神學歷史中幾個主要的神哲關係模式
一、敵對關係──神學與哲學毫不相干
採取此種態度的神學家,認為哲學對基督教而言全然無用。因為兩者致力的方式,及思考的過程南轅北轍,欲達到的目標更是風馬牛不相及。因此,他們認為基督徒對哲學最好是敬而遠之,兩者井水不犯河水。教父們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特土良(c.160-230 A.D.),針對異教徒的影響及教會內所盛行的「異教哲學」風氣,他對當時的基督徒提出三個語意相同且頗具修辭學價值的問題,敦促他們務必三思。
雅典到底和耶路撒冷有什麼關係?
學院(Academy)和教會之間有何共通點?
異端教徒和基督徒之間有何關聯呢?
相較之下,曾經浸淫經院神學之中的宗教改革先驅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對哲學的態度則幾近侮辱。他毫不諱言地說:「讓哲學留在上帝指定的範圍內,且讓我們把她當作一名丑角吧;但卻不能把她和神學混在一起……。」他甚至指名道姓地對喜好賣弄哲學的經院學派加以無情的批判。路德說:
經院學家喜好以自己的臆度去探測上帝的話。他們的探測完全是虛空,或是些由人的理智所得來的空想,波拿文士拉便是個充滿這種空想的人,他使我幾乎成了聾子。我曾想要從他的書中明白上帝和我的靈魂如何可以重新和好起來,但我沒有得到一點消息。這派人講了很多話,……。但實際上,都是些無稽縹緲之誤。
敵視哲學的基督徒往往因哲學論證過程繁瑣,目標模糊,且和信仰生活沒有直接而明顯的關聯而對它產生厭惡感。同時,他們也敏銳地察覺到,哲學論證過程所暴露的缺點不僅無法說明基督教的真理,甚至可能會誤導信仰的追求者(將哲學方法上的缺失歸咎於信仰內容本身的謬誤,而拒絕接受之),實在得不償失。但是為此完全排斥哲學,對其視而不見亦非明智之舉,且不無矯枉過正之嫌。其實,「哲學」一詞所指的不只是某種思想內容而已,也包括如何傳達那些內容的方法。因此,只要運用得當,哲學內容有助於神學內涵的闡述;哲學方法也可為基督教信仰辯護。神學歷史中不乏藉哲學來表達深奧難懂得神學或為基督教真理辯護之佼佼者奧古斯丁(Augustine)和多瑪斯(Thomas Aquinas)就是最佳的例子。
二、輔佐關係──哲學輔助闡述、強化神學內涵
雖然奧古斯丁始終強調信仰及啟示的優先性,但也指出(柏拉圖)哲學可以幫助基督徒更了解自己所信的教義。事實上,啟示的權威和哲學是他的信仰生活的兩大支柱。也就是說,一方面他相信基督是真理,另一方面藉由柏拉圖的哲學來理解、解釋該真理。承如包達理所言:「〔奧古斯丁〕相信基督,但他到柏拉圖派那裡去找,並確信能夠找到適於解釋其信仰的哲學。」例如,奧古斯丁的創造觀顯然是源自柏拉圖的宇宙論和觀念論。柏拉圖認為世界有如被一條想像的分割線隔開般的分成兩邊。一邊是看不見的觀念界(ideal world),另一邊是看的見的感官界(sensible world)。前者比後者更真實;在感官界所看到的一切只不過是觀念界裡真實事物的影像而已。
循著柏拉圖的思路,奧古斯丁認為人所生活的世界只是上帝的意念的副本而已。此外,他也認同柏拉圖的看法,視惡為善的缺乏(人的意念所造成的),而不是獨立的實體,因為上帝所創造的一切皆為善。奧古斯丁認為:
如果一物喪失了所有的「善」,便不在存在。……,若說一物喪失了所有的善,進而至於更善,則還有什麼比這論點更荒謬呢?因此,任何事物喪失了所有的善,便不再存在。如果存在,自有其善的成分。因此,凡存在的事物,都是善的;至於我所追究其來源的惡,並不是實體;因為如是實體,即是善……。我清楚認識到你所創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且沒有一個實體不是你所創造的。
這種創造觀雖然可以突顯上帝的超越性,卻大有可議。按奧古斯丁的看法:若世界只是一個「副本」,亦即「原版的缺乏」,那麼這世界便是惡的。然而,聖經卻明確地告訴我們,這世界是上帝「看為好的」。另一個眾所週知的例子是阿奎那。他延用了大量的亞里斯多德哲學來解釋自己的神學,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證明上帝存在的「五路論證」。在這五種證明上帝存在的方法中,上帝被形容為「最初的原動者」、「第一因」、「必然性存有」、「絕對的價值」和「神性的設計者」。這些都是從亞里斯多德的形上學中「第一原動不動者」的觀念借用或衍生出來的。
除此之外,主張基督真實臨在於聖餐之中亦是受亞里斯多德形上學中「偶然」與「本質」這兩個相對概念的影響。在此必須強調的是奧古斯丁和阿奎那對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並非照單全收,而是指擷取他們認為與聖經不相衝突並能夠適切的解釋基督教信仰的部分。以奧古斯丁為例,某些對於不合乎上述二個原則的柏拉圖學院則加以譴責。但是這種作法並非毫無危險性。誠如奧古斯丁所言,人受原罪的影響及轄制,導致喪失「離惡行善的自由」,無法作正確的選擇。那麼。奧古斯丁視為「與聖經不相衝突」得哲學成分可能違背聖經的教訓,只是他無法辨認出而已。
三、混合關係──哲學作為神學的內容
神學家中除了如前面所舉的例子篩選,並有條件地運用哲學來說明神學以外,尤有甚者大膽地用哲學內容取代傳統以聖經為基礎的基督教信仰。與前者所不同得是,在這一種神學與哲學的互動模式中,哲學所扮演的不是消極、被動的配角,取材的原則端賴神學的需要而定。相反地,哲學已越俎代刨,成為宰制神學的主角。換句話說,哲學不是用來解釋、突顯基督教的真理,而是用來修改或刪減所謂「不符合哲學標準的神學內容」。只要是被哲學家判定為不合理的部分,都必須在哲學的手術台上切除或修補。這種作法固然使得經過大幅修改後的「教義」或「信仰」看起來更合理,更容易讓人接受,但是往往必須以賠上正統信仰為代價。
例如,布特曼(Rudolf Bultmann)的存在神學(existential theology)完全採納與他同在馬爾堡大學(Marbury University)的同事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哲學;以存在主義的角度及方法來看待、處理基督教教義。比方說,從海德格把人的存在(existence)區別為真實的(authentic,德文eigentlich)和虛假的(inauthentic,德文uneigentlich)兩種對立的型態。布特曼用它們來說明「罪」和「拯救」的意義。
按照海德格的說法,虛假的存在是指不願意以一己之力作抉擇、行動的人,因為他們不想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所以極盡所能地辯稱自己的思想與行動均受生理基因、心理結構、社會文化、宗教信仰或其他因素的左右,自己毫無自由可言。相反地,真實的存在就是選擇自己認為可以實現自我潛力的生活方式,並有勇氣承認、必須為本身的所作所為負責。總之,虛假的存在以遵守所謂的「公眾意見」為藉口來逃避其「日常生活中的責任」。真實的存在卻為了保存自主性而願意承擔自己的過失。根據海德格的觀察,選擇了這種真實的存在就是選擇了不可避免的道德上的罪(有犯錯的可能)和責任(承擔過錯)。
布特曼相信,真實的與虛假的存在之別正可以作為人的罪與拯救之最佳詮釋。他指出罪人(虛假的存在)就是因自私與自恃而對他人的苦難坐視不管,進而拒絕順服上帝或乾脆否認祂的存在之輩。反觀,得救的人(真實的存在)就是被上帝的話感召而毅然決然地放棄自私與自恃,並且轉向上帝的人。上帝的話是激勵人勇敢地走出虛幻的安全堡壘,邁向尋找上帝的大道之催化劑。這就是所謂的「信仰」。布特曼說:
信靠上帝的話意味著摒棄人為的安全保障,並且勝過因企圖去尋求安全保障而帶來的絕望。……。信仰就是……願意靠一已之力從超越的、看不見的上帝那兒找到避難所【的行動】。換句話說,信仰就是一種即使看不見任何安全保證時【也願意相信】的安全感;也就是如路得所說的,是一種隨時準備要踏入不可知的未來的意願。
總而言之,追求人類的可見的安全屏障就是活在虛假之中,亦即罪;放棄一己之私,擁抱上帝和恩典之信仰行動便是人應過的生活,亦即得救。
雖然布特曼的神學亦提及「信仰」、「上帝的話」、「罪與拯救」……等等和傳統神學一樣的觀念,但兩者之間卻有天壤之別。雖然他也強調「上帝是人唯一的信仰對象」,但是對上帝的信靠必須藉著人的主動性與努力才能達到。如此一來,在拯救行動中上帝的主動性已然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布特曼所謂「人的信仰」或「人的努力」。那麼,他所說的「得救」其實不是「上帝的拯救」,而是「人的自救」。這顯然違背聖經的教訓。關於此,白高倫的評論頗為中肯:
他【布特曼】以自己先入為主的人生哲學來歪曲基督教的信仰,卻自以為思想新穎,趕上時代,並以為經他改變了的基督教信息也正配合現代科學與哲學的要求。……,這並非否認布式對聖經教訓的分析下了苦工,只是說,布特曼這樣徘徊在理想主義與存在主義解釋新約的牢籠裏,對聖經明明指出的解釋反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與聖經教訓背道而馳」似乎是以哲學作為神學的內容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一開始或許能取得一些非基督徒的同情與贊同,但是卻賠上了自己的信仰。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存在神學只是其中之一罷了。過程神學(Process Theology)是另一個顯著的例子。筆者將在稍後以它為剖析、檢視的對象,證明過程神學的謬誤及不可行。
四、批判關係──哲學作為檢驗神學的工具
這種立場的代表人物是巴特。他認為神學是一項科學,因為它與其他科學一樣有探討的對象,有自己的一套尋求知識的途徑,也有嚴謹的治學態度。既然神學是一門科學,那麼就必須要求觀念與論述的精確性和理性。對巴特而言,哲學所用的分析方法正好可以、也只能滿足神學在這方面的需求。巴特說:「哲學、倫理學、政治學和其他想得到(的學問)在它們的領域裡,也許有它們的價值和正當性。但畢竟它們是有罪和失落之人所擁有的哲學、倫理學、政治學。不論多麼的深切與真實,都不能用它來評斷奉上帝的名所傳達給有罪和失喪之人的話,也就是教會的講道(本身)。」
也就是說,哲學不能取代神學的內容(聖經的教導);只可以用它來分析(1)神學用詞的意義是否易於掌握而不曖昧;(2)神學的理念與目的是否明確而不含糊;(3)論述是否合理順暢而不牽強;(4)所要傳達的整體訊息是否清晰而不晦暗。除此之外,哲學對信仰和神學毫無益處。
因此巴特一方面認為神學不可能完全否定、逃避哲學,另一方面亦不贊成用「護教」的名義借某種哲學來建構神學體系,來為神學代言以應付外界的挑戰。更不容許拿哲學作為神學的內容,以取代那些「不符合現代思潮的神話或謬誤」。因為前者不切實際,後兩者明顯悖離上帝的話。值得注意的是,對巴特而言,即使是如奧古斯丁或阿奎那般地謹慎使用哲學來協助表達神學訊息,以便在基督教和外界搭起一座溝通橋樑(意即護教學),也不見容於巴特,在他的眼裡,那等於向敵人舉起白旗,讓對方予取予求。他堅持:「 福音不是諸多真理之一而已。它是評斷其他真理的判準。福音不是門戶而是樞紐。(因此)為福音是否能得勝──也就是指護教學──而焦慮是毫無意義的,因為福音早就勝過世界了。福音使整個有形的世界消失於無形又將他建立起來。」
在一封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寫給布特曼的信中,巴特調侃式地說:
你希望我和神學建立的那一種關係不適合我。而且,基本上,你說我忽視哲學著作(的重要性)我也不辯駁。……不過事實上,沒有任何一種哲學可以像海德格的哲學影響你一樣地影響我。所以我不得不用你的標準來衡量我的思想,認真的思考。不瞞您說,我已經對那種費盡心思,不斷地想調整自己(神學焦距)去適應當代哲學潮流的神學眼鏡感到十分厭惡。
一九五二年聖誕節前一天,巴特再次向布特曼提及他三十四年前的堅持:
我絕不是哲學的敵人,但是我對於哲學知識論或方法論具有絕對性的說法無法苟同。偶而我會愉快地運用到存在主義的範疇──有時必須回顧柏拉圖或其他人的(看法)──但我就是沒有辦法鼓起道德的勇氣去接受那個哲學方法。你到底想怎樣?顯然地,存在主義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頻繁地控制我了。
隱藏在這種思維的背後是巴特的憂慮。他擔心自啟蒙時代(Enlightenment)以降大部分的神學家為文化與神學之間的整合所付出的努力會斷送神學的獨立自主性。縱然巴特深知神學不能漠視文化的地位,因為「文化的問題就是作人的問題」,但是他絕不容許任何的社會、文化因素或意識型態來決定神學的命運。唯有在神學的自主性能獲得保障的情形下才能與哲學產生互動;如此一來才不會因不小心「引狼入室」而忙於收拾殘局。
試閱文字
第五章 雅典、耶路撒冷與伯利恆
──哲學、神學與釋經學關係之再思
前言
雅典、耶路撒冷與伯利恆分別象徵愛智慧的哲學、表達信仰的神學以及以基督為中心的釋經學。翻開二千多年的基督教歷史,因為重視哲學、神學與釋經學之間應有的互動關係而提出看法或解決方案者之中不乏重量級的神學家。縱然所提的方案之間有些差異,他們仍一致認為如果運用得當,哲學可以為神學提供紮實的方法論。顯然地,就神學發展的歷史來看,哲學和神學是關係最密切,互動最頻繁的人文訓練之學科。通常神學家與哲學家是最佳的對話伙伴。這種情況絕對...
作者序
推薦序 周學信 牧師
聖經與神學的關係是什麼?經文的神學意義又是什麼?幾世紀以來,聖經學術研究和神學研究總是劃清界線。然而,近年來我們看到神學研究與聖經研究有了復合的跡象。
神學詮釋的起點絕不是「將閱讀聖經視為探究已死作者的書面言論」,而是與三一神的會遇:即神聖而永恆的神、藉著聖靈的力量、透過那位與我們相遇並且活生生活在我們當中的基督,與我們對話。而這神聖的會遇必須在神的無限作為裡、在神超越時空中所擁有的絕對與完全的自由下來理解。此一「自由」是神親自向墮落的受造物,和因遭受罪的咒詛而痛苦呻吟的世界,所說的慈言愛語。這樣說來,對讀經的基本理解應該是源自於耶穌基督所彰顯的恩典,而那恩典正是為了實現神慈愛的外在行動(opera ad extra)而賜下的。閱讀聖經並非是那自己關起門來,埋首窮究的經文考古學家的活動,而是靈性飢渴的受造物,與豐盛的生命和真理福音會遇的行動。
無論我們承認與否,閱讀聖經都是神學性的, 這就是歐博士處理神學詮釋學的進路,亦是本著作的軸心。因為讀經本是源自對這基本信仰的了解所驅,不管你肯定或拒絕這本神聖的代言者對原始作者(三位一體的上帝)的觀點。「聖經的神學解釋」這詞便是多餘的。
歐力仁博士可以說是當今台灣最優秀的神學家之一,他非常關注神學詮釋學的議題。在此書中,歐博士與幾位當代最重要的神學詮釋學家展開清新且批判性的對話,例如,巴特、潘霍華、布特曼和弗萊。這是一部力挽神學詮釋學之重要性的論文集。這些論文代表著他多年深思神學詮釋學議題的成果。歐博士在此將他努力的果實收成,並與我們分享。我發現力仁博士的諸多堅持十分正確。所以,我認為這本書值得你我花時間去閱讀,有助於我們比較全面地了解詮釋學的議題。
我要表達我對歐博士的欣賞,他接受神學訓練也講授神學,更關注聖經的神學詮釋。這股清新的空氣提醒了我們:在現代不斷地將專業細分之際,所有的神學家都是解經家、釋經者;對他們而言,將神學與釋經區分開來乃是不可思議的。當我閱讀到歐博士對這幾位神學家的評論時,我好幾次受到感動。它使我更加地欣賞這幾位神學家的作品,好幾次想到他們的神學洞見時,我的心歡喜雀躍。
我在此鄭重向讀者推薦歐博士這本可讀性非常高且有益的著作,它必定能作為我們持續探討「如何以信心接受聖經?」這個問題的絕佳參考。
周學信
中華福音神學院教會歷史與神學教授
推薦序 鄧元尉 博士
歐力仁博士的新作《哪位基督?何種神學?──當代神學釋經學中的基督與哲學》由橄欖華宣出版發行集團旗下之聖經資源中心出版,囑我為文作序,在讀過全書原稿後,我要誠摯地向讀者推薦此書,不單因為它是由本公司出版,更緣於它對台灣神學界與教會界的助益。
巴特、布特曼、潘霍華等德國神學家之名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但其實我們並不常看到台灣本土的神學工作者出版關於德國神學的專著,抑或綜有談論,卻不脫一些老生常談及背景介紹,又或綜有深入討論,卻常過於遷就本土處境議題或論者個人的學思關切,而未能忠實呈現神學家的原本面貌。歐博士的新作則為我們開了眼界,他能夠深入到神學家的文本來析辨其論旨,堅定地站在作者的立場上為文立論,著實為這已被後現代思潮主宰的時代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洞見。歐博士既有學者素養,又帶牧者關懷,行文中捍衛真道之情、堅定信徒之心流露。尤其他敢於針對所爭論議題作出明確判斷,面對反對意見亦毫不迴避,析論清晰流暢,立論徵引有據,使得讀者就算不盡同意其立場與論述,卻也不能輕易棄而不顧。
本書的主題是「神學詮釋學」,從某種角度來說,是一種與時代思潮既對話又抗衡的神學詮釋學,不只書中所論之神學家是如此,本書自身亦復如是。透過在這樣的對話與抗衡中來界定基督與哲學的關係,本書刻畫了何謂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學詮釋學。這不能被化約為一種釋經理論或一套解經法則,毋寧說這是一種關乎基督與聖經的信仰宣言,它雖然表面上並未直接向種種新興的詮釋學觀點迎戰,卻涉及基督徒反思自身詮釋學立場時的真實根基之所在。此時此刻,我們需要此等紮根之作幫助我們重省何謂基督中心的聖經詮釋,誠願恩主賜福本書之讀者。
鄧元尉
橄欖華宣出版發行集團主編
推薦序 周學信 牧師
聖經與神學的關係是什麼?經文的神學意義又是什麼?幾世紀以來,聖經學術研究和神學研究總是劃清界線。然而,近年來我們看到神學研究與聖經研究有了復合的跡象。
神學詮釋的起點絕不是「將閱讀聖經視為探究已死作者的書面言論」,而是與三一神的會遇:即神聖而永恆的神、藉著聖靈的力量、透過那位與我們相遇並且活生生活在我們當中的基督,與我們對話。而這神聖的會遇必須在神的無限作為裡、在神超越時空中所擁有的絕對與完全的自由下來理解。此一「自由」是神親自向墮落的受造物,和因遭受...
目錄
第一章 基督作為真理的循環──巴特的神學與釋經學方法論
第二章 神按著基督的形像造人──巴特對創世記一章26-27節和二章18節的詮釋
第三章 福音宣揚的基督──布特曼的「解神話」詮釋學以及「敘事神學」的回應
第四章 創造與救贖的基督──潘霍華對創世記一至三章的基督中心詮釋
第五章 雅典、耶路撒冷與伯利恆──哲學、神學與釋經學關係之再思
第六章 尋找耶穌的蹤跡──歷史批判法和社會科學法在新約福音書詮釋上的應用及其批判
第一章 基督作為真理的循環──巴特的神學與釋經學方法論
第二章 神按著基督的形像造人──巴特對創世記一章26-27節和二章18節的詮釋
第三章 福音宣揚的基督──布特曼的「解神話」詮釋學以及「敘事神學」的回應
第四章 創造與救贖的基督──潘霍華對創世記一至三章的基督中心詮釋
第五章 雅典、耶路撒冷與伯利恆──哲學、神學與釋經學關係之再思
第六章 尋找耶穌的蹤跡──歷史批判法和社會科學法在新約福音書詮釋上的應用及其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