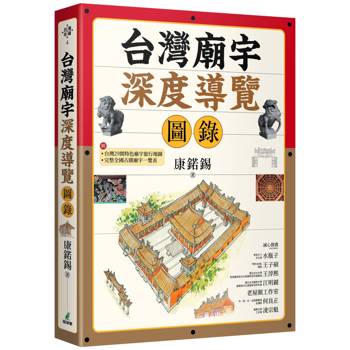第一章
加州那座有著蒼鬱松林,有著碧海銀浪的『濱海牧場』,不失一個絕好的被放鴿子地點。那裡還有野紫丁香跟壞脾氣的海獅,可以分散你被你夢想中的女人丟在紅毯前的傷痛,分散個那麼幾分鐘。另外,再附上一大堆的酒精,就可以辦到更長的時間。我跟我弟弟寇特提早到潛水酒吧,那裡同時也是鎮上唯一的酒吧,裡面的酒保要是聽見你點 Mojito或是 Caipirinha,是會渾身抖一下的。我預付了二十元的美金給那名酒保,要他確保稍後抵達的客人飲料會持續的供應。蓄了落腮鬍的酒保立刻丟了數灌的啤酒進冰箱。這會是個漫長但愉快的夜晚。牧場內這座已有百年歷史的冠拉拉飯店,有著白色的迴廊,跟西部繫馬樁。閉上眼睛,你可以想像西部牛仔把馬繫在繫馬樁後,推開活頁門扉,看到的是野餐桌,看到的是滿滿的觀光客,看到的是他們在狼吞虎嚥地喝著用家庭號大碗盛的義大利蔬菜濃湯。至於酒吧的這一部份是以松木裝潢,還掛了山豬頭做裝飾。寇特幫我買了罐啤酒後,問我怎麼樣。我沒有開罐。望著他剛生的白髮,望著他瘦削的臉龐,我發現我無法對他說。在成長過程裡,基於青少年的習性,使我無法跟小我兩歲的弟弟很親密。為了要跟我那些朋友更麻吉,我儘可能的避開我弟弟,而寇特也一樣。所以我跟他一年見面的次數,相處的日子,一隻手就可以數完。通常都是在耶誕節的時候。至於我們兄弟對於對方的生活情況,都是透過我媽得知,誰也沒有多探聽過對方,或多跨出一步。我想要跟寇特說。我需要跟他說,可是,問題是我不知道該怎麼開口說。我有一肚子的話,卻半個字也說不出口。我覺得很呆滯,很笨拙,完全像個無法跟父母溝通的彆扭小孩一樣。以前不是這樣子的。我記得以前我跟我弟弟常窩在我們家那輛淺藍色福特房車的後座,那時候,我們兩個是無所不談──像是秘密的躲藏地點(我房間的嵌壁式架子的後面),打算用什麼方法捉弄我們的妹妹麗莎(通常是抓住她,壓在地上,假裝對她吐口水),或是玩我老是輸的棒球紙牌遊戲。儘管成年後有這樣的疏離,但在我結婚前五天得知婚禮要被取消的時候,我頭一通電話打的對象是寇特。我打給他的時候是在我從我位於新港灘的家開上405號快速公路,往住在聖塔蒙尼卡安妮的租處去的路上打的。我不記得上次打電話給寇特是在什麼時候。應該是通知壞消息吧,像是通知我祖父去世的惡耗之類的事情。出社會後,我們就各奔前程,各分東西了。寇特在西雅圖從事房地產買賣仲介,我則是到華盛頓,還有加州往政界發展。接到我電話時,他似乎頗為驚訝。從他的聲音,我聽出他感覺出有事情不對勁。我需要他,我從來沒麼需要過兄弟的支持過。
「怎麼了?」他問。
「沒什麼事啊。就是天氣很好啊,前兩天去打了場高爾夫球啊,我的婚禮取消了啊。我有沒有提到天氣?」靜默。
「真的?」
「真的。我現在正在去安妮那裡的路上,要去被拋棄的。安妮的哥哥吉拉德剛剛打電話給我,說她撐不下去了,說她沒法進行婚禮。」
「老天,真是的。」寇特粗聲的說。
「出了什麼事?」
「說來話長。我改天再告訴你。」
「你打算怎麼做?」
「我不知道,一點頭緒都沒有。一切的費用都付了。親友這個周末也都訂了小木屋要來一起歡聚了,連遠在國外的,有的也已經在飛回來的路上了。真是一場夢饜啊。」
「嗯嗯。」
「我從來沒被人在禮壇前放鴿子過,而我唯一想到的,就是我明天有上百通的電話得打。」
「有夠,唔,機車。」
「我很不想麻煩你,不過,你能飛過來一趟幫我一下嗎?機票錢我付。」
「沒問題。」寇特一口答應。
「還有,三八兄弟,說那什麼話。我一確定好班機,就會到你的語音信箱上留言。」那之後,我簡短地跟我媽通了一下下的電話,告訴她婚禮很可能不舉行了。上星期就有成串的事情發生,我都沒告訴她,不過當人老媽的人都很精的,絕對可以從遲遲沒寄出的喜帖,沒戴上的婚戒嗅到不對勁的氣息。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其實,兒子,她這是對你好,要不然等到婚禮後才告訴你,更慘。兒子,這是件好事,過段時日,你就會看得出這對你是件好事。」我知道我父母會給我最大的支持。他們一向如此。有太多的時候,尚且是格外的支持。只是,那並不能讓我不覺得我不是個失敗的人。我知道我要是跟我爸一說上話,絕對會馬上崩潰。我不斷想到他們客廳架上的那些照片,有:他們四十年前的結婚照,有我妹妹去年的照片,有狗以前的照片,跟現在的照片,有我曾祖父在中國大陸期間的照片。就是沒有『濱海牧場』的照片。而我不知道我媽媽什麼時候才會拿下有安妮的照片。在我飛馳在405號快速道路的路上,我的腦海裡不斷播放過去這十年間我跟安妮的點點滴滴。別封殺我,安妮。別封殺我。我們孩子們的名字呢?我們都想好了的啊。妳忘了我們窮到只能共喝一碗豆子湯的那些日子了嗎?妳忘了我們那些嘻笑鬥嘴的情景了嗎?妳不記得我們在哈德遜谷最邊間那間房間瘋狂的做愛,狂野到兩人都必須抓著床柱的那個晚上了嗎?那個老闆娘在把房間租給我們之前,還躊躇了老半天。妳還記不記得隔天早上妳醒來的時候,發現我正在摸妳的頭髮,滿眼中看的都是妳?我們這些年在一起的那些點點滴滴呢?它們都毫無意義了嗎?安妮跟她的哥哥吉拉德住同一棟公寓,兩屋隔著走道遙遙相對。安妮穿了條破舊的牛仔褲,跟一件灰色開士米線衫,坐在吉拉德白色皮沙發上。我走進去的時候,她並沒有抬頭看我。我在她的面前坐下,彎下腰,審視她的臉。她的眼睛又紅又腫,我的心頓時難過到極點。為她,也為我。她纖細的小手捏捏折折著一張面紙,不時擦她毫無血色的臉。一旁的吉拉德結結巴巴的說著什麼這事沒有誰對誰錯,也沒有誰是壞人。我沒在聽,我的所有注意力全在安妮。我瞪著安妮,想著事情怎會變成這個樣子。妳怎不早幾個月就告訴我?算了,媽是對的。妳這樣做,是為我好,是在替我著想。我氣,我惱,我難堪,我痛到極點,痛到整個人都麻木……然後,我放下了。也是在當下,我領悟到我最佳的應對策略,就是以不變應萬變。有史以來的頭一次,我看清了,我跟安妮的這段情緣是完了,結束了,就像孩童手中飛往空中的氣球一樣,只會往上飄,往遠處飄,飄到看不見為止。安妮慢慢抬起頭,長吐了一口氣後,「對不起,我就是不能,就是沒有辦法。我努力過,可是我就是辦不到。」她看起來好小,一點也不像我所認識的那個能幹、優雅的女人。我拉過她的小手。
「沒關係。」我說。在回家的路上,我兩手緊緊握著方向盤,兩眼筆直看著前方,而那個安妮幾年前花了不少錢買給我的名牌手錶生日禮物,錶帶突然斷了。
“婚禮”照常舉行不是我的主意。我可沒那麼堅強。那是賓的主意。賓是我的好友。他取消了跟客戶的洽談,隔天一整天都在幫我打電話。寇特是在隔天近午從西雅圖飛過來。為了爭取時效,我們用了兩隻手機,還有我住處的有線電話通知親友。我們採取輪流接棒的方式,也就是一個打電話,說了個開頭,再由另一個接手把事情做個簡短的交代。我的第一通電話是最艱難的。那支電話我拿起放下,拿起放下,一連好幾次,最後我深吸了一口氣,才終於撥下我住在沙克拉門圖九十八歲的繼祖母。蘭露熱愛婚禮。還有安妮。我們上次去見她的時候,她們兩人光是聊位於舊金山市郊幾小時路程的濱海度假中心『濱海牧場』,就聊了好幾小時。蘭露什麼都想知道,連細節都不放過。
最後,她轉過頭來對我說:「我要幫你們做個最漂亮的結婚蛋糕。」我那才注意到一旁的茶几上有張結婚蛋糕的宣傳海報,海報上面有張利貼,利貼上面寫了數行的筆記。
「嗯,好。」當時我嘴裡應著,心裡卻在想,哪好讓一個九十八歲的老人家哈腰塗奶油、弄裝飾,累上好幾個小時。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跟我老弟度蜜月的圖書 |
 |
跟我老弟度蜜月 譯者:柴雲 出版社: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出版日期:2006-09-1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社會人文 |
$ 246 |
英美文學 |
$ 252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跟我老弟度蜜月
史上最悲情的真實蜜月旅行!帶出一段淚水與歡笑交織的奇幻之旅!當你正準備參加自己的婚禮,接受眾親朋好友的祝福,度蜜月的地點選好了,飯店、機票也都訂好了,只是……新娘烙跑了!你該怎麼辦?這個男人沒有取消婚禮,仍依照原計畫現身婚宴現場,向眾親朋好友說:「我不結婚了!我很好,只是很想哭!」在一場杯盤狼籍的、沒有新娘的婚宴之後,他決定和自己的弟弟去哥斯大黎加度蜜月,重溫那段哥倆好的兒時歲月。他這才發現,原來他的弟弟比他想像中的更了解他;而他卻一點也不了解他的弟弟。於是,一段奇妙的旅程,讓他走出了「被拋棄」的陰影,發現了兄弟之情,更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
作者簡介:
法蘭茲‧威斯納( Franz Wisner)他是一名作家,前世是個流浪漢,曾經擔任過政策說客、公關經理、政府發言人。在他環遊世界的期間,他將大量的旅遊札記與感想雜文付諸筆端,並被刊載於《舊金山論壇報》、《洛杉磯時報》、 A B C線上新聞及 Coast雜誌等。法蘭茲跟他的弟弟寇特正在遍遊全球各地,為他們下一本書做準備。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加州那座有著蒼鬱松林,有著碧海銀浪的『濱海牧場』,不失一個絕好的被放鴿子地點。那裡還有野紫丁香跟壞脾氣的海獅,可以分散你被你夢想中的女人丟在紅毯前的傷痛,分散個那麼幾分鐘。另外,再附上一大堆的酒精,就可以辦到更長的時間。我跟我弟弟寇特提早到潛水酒吧,那裡同時也是鎮上唯一的酒吧,裡面的酒保要是聽見你點 Mojito或是 Caipirinha,是會渾身抖一下的。我預付了二十元的美金給那名酒保,要他確保稍後抵達的客人飲料會持續的供應。蓄了落腮鬍的酒保立刻丟了數灌的啤酒進冰箱。這會是個漫長但愉快的夜晚。牧場內這座已...
加州那座有著蒼鬱松林,有著碧海銀浪的『濱海牧場』,不失一個絕好的被放鴿子地點。那裡還有野紫丁香跟壞脾氣的海獅,可以分散你被你夢想中的女人丟在紅毯前的傷痛,分散個那麼幾分鐘。另外,再附上一大堆的酒精,就可以辦到更長的時間。我跟我弟弟寇特提早到潛水酒吧,那裡同時也是鎮上唯一的酒吧,裡面的酒保要是聽見你點 Mojito或是 Caipirinha,是會渾身抖一下的。我預付了二十元的美金給那名酒保,要他確保稍後抵達的客人飲料會持續的供應。蓄了落腮鬍的酒保立刻丟了數灌的啤酒進冰箱。這會是個漫長但愉快的夜晚。牧場內這座已...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譯者: 柴雲
- 出版社: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出版日期:2006-09-13 ISBN/ISSN:9867088905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