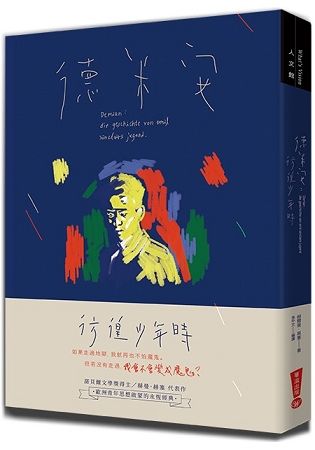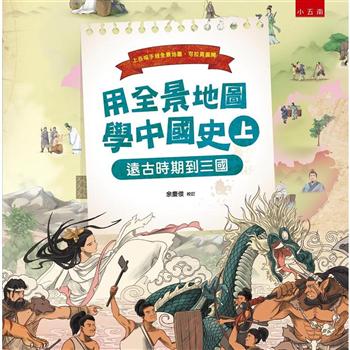如果走過地獄,我就再也不怕魔鬼。
但若沒有走過,我會不會變成魔鬼?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赫曼.赫塞 代表作
歐洲青年思想啟蒙的永恆經典
一隻鳥在孵化以前,蛋就是整個世界,牠得先毀了那個世界,才能開始飛。
在死去以前,你我身上無不沾著孵化那日的證明,黏漬、碎殼那些來自久遠時代的痕跡。有些從未蛻變為人,而是繼續當青蛙、蜥蜴和螞蟻;有些上半身有著人身,下半身仍是魚尾。
然而所有人都是源於大自然,源於自己的母親,以相同的方式來到世界上,甚至出自同樣的深淵。而當我們各自從深淵出走,努力邁向目的地,一路上或許能夠明白彼此,但真正能深刻了解的那個人,唯有自己而已。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德米安:彷徨少年時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15 |
二手中文書 |
二手書 |
$ 255 |
Others |
$ 262 |
德國文學 |
$ 263 |
世界古典 |
$ 276 |
中文書 |
$ 298 |
小說/文學 |
$ 308 |
德國文學 |
$ 308 |
Others |
$ 315 |
世界古典 |
$ 31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德米安:彷徨少年時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