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良心的詭異故事,只有神經的都市傳說!
日本文壇大師芥川龍之介的人間異語
收錄多篇芥川的短篇怪談,引發一瞬之間的顫慄。
你看不見的,不見得沒有發生;
你聽不到的,或許依舊唱著歌。
我不由得用恐懼的目光注視著這尊彷彿代表著命運的瑪利亞聖像。聖母穿著黑檀木外衣,那張美麗的象牙面龐上帶著惡意嘲弄的微笑,彌漫著永久的森冷氣息。──《黑衣聖母》
要問她這次是否記住了那個衝自己笑的紅帽腳夫的臉,她記憶裡依然是一片模糊。無論怎麼努力回想,能想起來的也只是那人頭上戴著紅色的帽子,五官卻早已模糊了。──《奇聞》
無視兩人的小花貓,好像看見什麼似的,猛地躥到了門口,隨後的舉動就彷彿在磨蹭某人的腳踝一樣。但是,彌漫在房間裡的暮色中,除了花貓的雙眼散發著令人毛骨悚然的磷光之外,看不到任何其他人存在的跡象……──《影子》
人間如地獄,鬼魅皆橫行。
為人一生,心緒無根,我們能否在人生中找到存在的指南?或者細觀荒謬怪談,還能尋得一絲真實與溫暖?你看不見的,不見得沒有發生;你聽不到的,或許依舊唱著歌。在這連靈魂都寒冷的世界上,我們搜尋細瑣,翻找蛛絲馬跡,魔鬼藏在細節裡,人生也不外如是。
本書收錄芥川龍之介〈黑衣聖母〉、〈影子〉、〈妖婆〉、〈孤獨地獄〉……等十六篇短篇怪談。妖異人間,經典再臨。
作者簡介:
芥川龍之介(1892-1927)
號「澄江堂主人」,俳號「我鬼」,日本知名小說家,博通漢學、日本文學、英國文學。1916年於東京帝國大學就學時,發表短篇小說,受到夏目漱石的讚賞。初期作品多以歷史題材為背景;中期則融入寫實,帶有自傳成分;晚期飽受精神及肉體的痛苦折磨,後期風格偏向黑暗、死亡及沉重。一生創作甚豐,卻於1927年仰藥自殺,得年35歲。好友菊池寬為了紀念這位文豪,於1935年設立「芥川賞」,現已成為日本最重要的年度文學獎項之一,並與「直木賞」齊名。
章節試閱
黑衣聖母
於此涕泣之穀,哀漣歎爾。祈我等之主保,聊以回目、憐視我眾……其寬哉,仁哉,甘哉,卒世童貞瑪利亞。──Credo
「你覺得如何?看這個。」田代君一邊說著,一邊將一尊瑪利亞神像放在桌上展示。
所謂瑪利亞神像,就是查禁天主教時期,天主教徒們經常用來替代聖母瑪利亞參拜的神像,多為白色瓷雕。但是這次田代君展示給我的瑪利亞神像,是即使在博物館的陳列室,或是頂級收藏家的藏品中也不曾出現過的。
首先,這尊一尺高的立像,除了面部,其餘地方完全由黑檀木雕刻而成。不僅如此,雕像頸項上十字架形的瓔珞頸飾也是由黃金和青貝鑲嵌的,做工極其精巧。聖母的面部由精美的象牙雕刻而成,只在唇上添加一抹如珊瑚般的朱紅色。
我雙手環抱胸前,沉默著,長久地凝視黑衣聖母那嬌美的容顏。凝目之時,我總覺得在那象牙面龐的某處,神情中透著古怪。不,僅僅說是古怪還不夠,用我的話說,那整張面龐上彌漫的表情,甚至可以稱得上是帶有惡意的嘲諷了。
「你怎麼看?就這個雕像。」田代君臉上浮現出所有收藏家共有的洋洋自得的微笑,視線來回穿梭在桌上的瑪利亞神像和我的臉上,又問了一遍。
「這確實是件稀世珍品,不過,不知怎的,那面相看起來總有些古怪呢。」
「說不上是盡善盡美的品相吧。不過話說回來,關於這尊瑪利亞神像還有一段奇聞呢。」
「奇聞?」我的視線不由得從瑪利亞神像上移到了田代君的臉
上。田代君帶著意料之外的認真神情,輕巧地從桌上拿起瑪利亞神像,卻又迅速將之放回了原處。
「是啊,和那種轉禍為福的聖母像不同,這可是一尊轉福為禍的不吉利的聖母像呢。」
「還有這種事?」
「事實上,她的擁有者確實遇到了這樣的事情。」田代君坐到椅子上,似乎若有所思,帶著陰鬱的眼神,
對我招手示意了一下,像是要我坐到桌子對面的椅子上。「真有此事?」當我在椅子上落座時,用自己都沒有想到的古怪腔調
問道。田代君比我早一兩年大學畢業,是有名的高等法學才子。而且,至少在我認知的範圍內,還沒有聽聞他對所謂的超自然現象有絲毫興趣和信仰。從一位極有教養的新思想家口中說出這種奇聞,僅就這一點而言,足見此事絕非什麼荒誕無稽的鬼話。
「千真萬確?」我忍不住再問了一遍,田代君一邊用火柴點燃煙斗,一邊回答:「這個嘛,就只能由你自己來判斷了。不過無論如何,這個瑪利亞神像確實有個不吉利的傳聞。如果你不覺得無聊的話,且聽我細細道來吧。」
在入我手前,這尊瑪利亞觀音的主人是新潟縣某村一個姓稻見的大戶人家。當然,那時候這雕像不是作為古董,而是作為祈求家族興旺繁榮的神像被供奉的。
那個稻見家的當家,正好跟我是同期的法學學士,不但與大公司有合作關係,還涉足銀行業,是相當厲害的實業家。因為這層關係,我也曾讓過他幾次薄利。大概是心存感謝吧,那年稻見來東京,順帶將這個家傳的瑪利亞神像送給了我。
我所說的奇聞,也是那個時候聽稻見親述的。當然,他本人對於這個不可思議的奇聞是談不上相信的,只是聽了他母親說的奇聞之後,將這尊聖母附帶的故事說給我聽聽而已。
那應該是稻見的母親十歲或是十一歲那年的秋天,說到年代,應該是「黑船」滋擾浦賀港口的嘉永末年。稻見母親的弟弟那時才八歲,名叫茂作,患了重症麻疹。稻見的母親叫作阿榮。自從兩三年前,雙親死於急性傳染病,阿榮和茂作姐弟倆就是由年過七十的祖母一手撫養的。因此茂作病重後,對於祖母這個已經切髮、心生歸隱之意的人而言,又是接二連三的打擊。儘管醫生拼盡全力,但是,茂作的病情只是一味惡化,在不到一周的時間裡,已經到了離死亡僅一步之遙的境地。
就是這種情況下,某天夜裡,祖母突然闖入了正在熟睡的阿榮的房間,無視阿榮還沒有完全醒過來,將之抱起,不假他人之手,利索地為阿榮穿好了和服。阿榮好像還在做夢般迷迷糊糊時,祖母已經牽著她的手,帶著她走過在紙燈籠微弱的光芒照射下顯得空蕩蕩的走廊,進入了即使白天一般也不會進入的儲藏室。
儲藏室裡有一座白木神龕,自古便供奉著防止火災的穀神。祖母從衣袋裡拿出鑰匙打開了儲藏室的門,但是透過紙燈籠的光看過去,在古舊的錦緞垂簾後面,端端正正擺放的神像不是別的,正是這尊瑪利亞神像。阿榮看到這尊塑像的時候,覺得深夜寂靜無聲的儲藏室突然陰森恐怖起來,不假思索地伏在祖母的膝頭,抽泣著哭出聲來。然而祖母卻一反常態,對於阿榮的哭泣不加理會,端坐在瑪利亞觀音的神龕前,恭敬地在額前畫十字,口中念起阿榮聽不懂的禱告詞來。
大約過了十多分鐘,祖母悄然抱起孫女,安撫地拍哄著阿榮的臉頰,並讓她在自己身邊坐好,然後再次向著黑檀木的瑪利亞神像祈禱,這一次說的內容阿榮也聽懂了。
「聖母瑪利亞,天地在上,我此番前來只為祈求您庇佑我今年八歲的孫兒茂作,以及就在我身邊的茂作的姐姐阿榮。如您所見,阿榮尚未到出嫁的年齡。如果現在茂作有什麼意外,稻見家恐怕就此後繼無人了。懇請您保佑茂作,不要讓那樣的不祥之事降臨。若嫌吾輩虔心未至,至少請在我一息尚存之時,保我孫子茂作不死。吾輩年事已高,雖一心虔誠侍主,但恐來日不多。不過在我離世前,若無意外的話,孫女榮兒也應到適婚的年齡了。蒙聖母垂憐,願那死亡天使之利刃在我長眠之前,遠離我的孫子茂作。」
祖母俯下那束成切髮式的頭,如此這般虔心乞求著。當話音落下之時,也許是心理作用吧,據說在一臉惶恐的阿榮眼中,瑪利亞神像好似面露微笑一般。阿榮輕輕地叫了一聲,再度伏在祖母的膝蓋上。但是祖母卻顯得心滿意足,一邊拍撫著孫女的後背,一邊反覆說著:「來,準備回去吧。聖母瑪利亞已經聽到我這老婆子的祈求了。」
待到天色變白時,也許果然是祖母的祈禱靈驗了,茂作的燒比起昨天要退了些。而且此前他一直是半昏迷的狀態,現在也恢復了意識。看到這一幕,祖母的喜悅之情真是溢於言表。稻見的母親說,那一刻祖母邊笑邊落淚的神情,她至今也無法忘懷。後來,祖母看到抱病的孫子熟睡的模樣,自己連夜看護的疲乏感突然湧來,就打算去稍事休息了。於是,她罕見地在與病房相鄰的房間打了地鋪,躺下休息。
根據田代君的描述,那時阿榮正坐在祖母枕邊,玩著玻璃球,看著年邁的祖母耗盡心神,筋疲力盡,彷彿死人般倒頭就睡。可僅僅過了大約一個鐘頭,照看茂作的中年女傭輕輕拉開了隔壁房間的隔扇,用略帶驚慌的語氣輕聲喚道:「小姐,請叫醒老夫人。」還是小孩子的阿榮趕忙來到祖母身邊,一邊拉扯了祖母棉睡衣的袖子幾下,一邊叫著:「奶奶,奶奶。」但是,平日淺眠的祖母,今天卻無論怎麼呼喚都不見回應。女傭此時也覺察有異,走了進來。一看到祖母的神情,她便好似發瘋般地突然拉扯著老夫人的棉睡衣,帶著哭腔高喊著:「老夫人,老夫人!」但是祖母眼周泛著彷彿凝固般的淡紫色,紋絲未動地安睡著。不一會兒,另一個女傭慌亂地拉開隔扇,帶著一臉的驚慌失措,用顫抖的聲音喚道:「老夫人──小少爺他──老夫人……」不用多問,即便是阿榮也能聽出,女傭口中的「少爺他──」是在告知茂作病情惡化一事。然而,祖母依然是那樣,對此時女傭伏在枕邊哭泣的聲音充耳不聞,始終緊閉雙眸。
那之後不到十分鐘,茂作也漸漸停止了呼吸。瑪利亞按照約定,一直到祖母離世,都不曾取走茂作的生命。
田代君的故事說到這裡,再次抬起陰鬱的雙眼,長久地注視著我。
「怎麼樣?你認為這個傳說是否屬實呢?」我遲疑著。「這個嘛──但是──該怎麼說好呢。」
田代君略微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再次點燃了已經熄滅的煙斗。
「我覺得是確有其事吧,但是,那是否為稻見家的聖母像作祟,我仍心存懷疑。不過話說回來,你還沒有看到這尊瑪利亞觀音底座的碑文吧,請看一看,在這裡刻著一行外文:DESINE FATA DEUM LECTI SPERARE PRECANDO(你的祈禱無法左右上帝的意志)……」
我不由得用恐懼的目光注視著這尊彷彿代表著命運的瑪利亞神像。聖母穿著黑檀木外衣,那張美麗的象牙面龐上帶著惡意嘲弄的微笑,彌漫著永久的森冷氣息。
奇聞
那是一個冬天的夜晚,我和老友村上漫步在銀座大道。「前段時間千枝子來信了,向你問好呢。」村上像是突然想到一樣,將話題轉到了現在住在佐世保的妹妹身上。
「千枝子身體還好吧?」「嗯,這段時間一直很健康,不像那個時候。你也有所瞭解吧?她還在東京的時候,神經衰弱的程度相當嚴重呢。」
「我有所耳聞,不過那時候也不太瞭解到底是神經衰弱還是什麼──」
「你還不清楚吧,那個時候的千枝子,真不知道是著了什麼魔,讓人以為她會哭的時候卻突然笑起來,覺得她要笑了,卻又開始說些奇怪的話。」
「奇怪的話?」
村上在回答我之前,推開了一家咖啡店的玻璃門,選了一張看得見馬路的桌子,與我相對而坐。
「還沒跟你說過吧?那些奇聞,也是她去佐世保之前才說給我聽的。」
你也知道,千枝子的丈夫在「一戰」的歐洲戰場中,是被派往地中海方面的「A—」艦的軍官。千枝子在留守的時候雖然來和我同住了一段時間,可是就在戰爭眼瞅著就要結束時,突然神經衰弱得越來越嚴重。要說引發病情的主要原因,大概就是她丈夫每週一次從未間斷的來信突然中斷了吧。
要知道,千枝子那會兒可是剛剛結婚才半年,就那麼和丈夫分開了,自然對於來信特別重視。可是那會兒我還對她毫不顧及地冷嘲熱諷,現在想想真是做得太過分了。
就在這麼個節骨眼上,某一天──對了,那天正好是紀元節,不知怎的,一大早就開始下起雨來,到了下午更是寒氣逼人。可是千枝子卻提出要到久違的鐮倉去玩,她那個嫁給鐮倉實業家做夫人的校友就住在那裡。雖說是要去找她玩,可是在這潮濕的雨天裡,實在沒必要跑到那麼偏遠的鐮倉去,一想到這兒,不僅是我,連我妻子也再三勸說她改日前往。可是,千枝子執意說,無論如何也要在那天去,就那麼生著悶氣,急匆匆地收拾了一下出去了。
「看情況當天是要在那邊留宿了,可能要到隔天早上才能回來。」她這麼說完就走了。只是沒過多久,她就渾身濕淋淋,一臉蒼白地回來了。問過才知道,她好像是一路冒雨從中央車站走回濠端車站的。你可能要問了,她這麼做到底是為什麼,這就引出了那件奇聞。
話說千枝子一到了中央車站,不,應該說在那之前還發生了一件事。她在乘電車前往中央車站的途中,因為車廂坐滿了人,她就拉住吊環扶手站在那裡。她說,就在那時,她透過眼前的車窗玻璃,隱約間竟望見了海。那個時候,電車剛開到神保町,要說看得到海,那怎麼也講不通啊。但是,她說在車窗外街道的間隙中,連海浪的波動也看得到,特別是雨水吹打到車窗上時,霧氣彌漫的水平線也隱約可見。照她的說法來看,千枝子怕是從那個時候起就不太正常了。
然後,車到了中央車站,入口處的一個紅帽腳夫突然向千枝子打了個招呼,還說了句:「您丈夫近來可好吧?」這已經夠奇怪的了,但更詭異的是,千枝子對紅帽腳夫的問題並未覺得有何不妥,而且她還回答了那紅帽腳夫的話:「感謝關心,只是因為音信全無,這段時間究竟境況如何我也無從得知。」這麼一說,那紅帽腳夫就接話道:「那我替您去看望一下他吧。」說是去看望,可丈夫遠在地中海,千枝子這時才開始覺得這個素昧平生的紅帽腳夫的話不免太過蹊蹺。可是就在她想著如何回應的時候,那紅帽腳夫對她略施一禮,悄無聲息地隱入人群之中。自那之後,千枝子無論如何搜尋,也再沒看到過那個紅帽腳夫的身影。不,與尋不見那個腳夫相比,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千枝子說連打過照面的紅帽腳夫的相貌也怎麼都想不起來了。
在遍尋不著那個紅帽腳夫的同時,千枝子覺得自己看到的每一個紅帽腳夫都像那個人,所以千枝子雖然找不到那個古怪的紅帽腳夫,卻總覺得他一定就在身邊監視著自己。這麼一來別說是去鐮倉了,光是留在車站就讓她覺得渾身不自在。於是,她急匆匆地連傘都沒打,冒著大雨夢遊般地逃出了車站。當然啦,千枝子的那些話也可以歸咎於她的神經質,那個時候她不是還得了很嚴重的感冒嗎?隔天開始,她整整三天持續高燒,還說了一堆好像在跟丈夫對話似的胡話,像什麼「老公,請原諒我」、「為什麼你還不回來」之類的。但是鐮倉之行的後遺症影響深遠,即使在大病痊癒後,只要一提到紅帽腳夫這個話題,千枝子仍會像回到那天一樣神情陰鬱,言語間也會變得不安起來。而且為此還有過這樣可笑的經歷:因為看到某個水路貨運行招牌上紅帽腳夫的畫像,她就放棄出行直接回家。
不過一個月後,她對那個紅帽腳夫的恐懼心理也大致消退了,還曾和我妻子笑談說:「嫂子,那個叫什麼泉鏡花的作家的小說裡,不是有一個長著貓臉的紅帽腳夫嗎?我偶遇的那些古怪事,可能是因為讀了那本小說後受到了影響吧。」可是三月的某一天,她又被紅帽腳夫給嚇到了,自那之後直到丈夫回來,千枝子是無論如何都絕不再去車站了。你出發去朝鮮的時候,那孩子沒來送行,也是因為害怕那個紅帽腳夫再出現。
三月的一天,她丈夫有個駐守美國兩年的戰友回國,千枝子為了迎接他,一早就出門了。你曉得的,那一帶因為地處偏僻,即使在白天也很少有人經過。就在那條空蕩蕩的路邊,有一輛賣風車的小貨車好像被遺忘般地丟棄在那裡。那天正好是一個大風的陰天,小貨車上插著的五彩風車令人目眩地轉動著。好像僅僅是看到這番景象,就足以讓千枝子心生不安了。她不經意地看嚮往來的行人,卻見到一個戴著紅色帽子的男人背對著她蹲在那裡。那自然應該是賣風車的人了,估計他是在抽煙吧。只是看到那頂紅色的帽子後,千枝子頓時產生了某種預感,覺得如果去車站的話,又會遇到什麼詭異的事情,以至於起了打道回府的念頭。
不過,最後她還是去了車站,順利地接到了人,接下來也都再無異常。只是當丈夫的戰友在前面隨著人群準備邁過光線昏暗的驗票口時,不知是誰在千枝子身後輕聲道:「您丈夫的右手腕受傷了,因此才沒能給您寫信呢。」千枝子猛地回頭看去,然而身後並沒有紅帽腳夫或是其他什麼人,有的只是相熟的海軍將校夫婦。這對夫婦自然沒理由突然說起這種事。雖說這句話真是有些詭異,大概是因為沒有看到紅帽腳夫的蹤影,千枝子也就放鬆了警惕,不再理會。她走出驗票口,便和其他旅客一起,在月臺目送丈夫的戰友搭車離開。這時候,從她身後再次傳來清晰的搭話聲:「夫人,您丈夫可能下月中旬就回來了呢。」千枝子再次四下張望,在身後送行的男男女女中確實沒有紅帽腳夫。雖然身後並沒有,在她面前卻有兩個腳夫正在往車上裝行李。不知怎的,其中一個在路邊看著千枝子,還咧嘴笑了一下。千枝子在看到那一幕的瞬間,彷彿是看到四周的行人都靜止了,刷地變了臉色。可是當她沉下心來想再仔細查看時,剛才清楚看到的兩個紅帽腳夫,此時卻只剩下一人在那整理行李了,而且剩下的那人與方才衝自己笑的分明不是同一個。要問她這次是否記住了那個衝自己笑的紅帽腳夫的臉,她記憶裡依然是一片模糊。無論怎麼努力回想,能想起來的也只是那人頭上戴著紅色的帽子,五官卻早已模糊了。這是從千枝子嘴裡說出來的第二件奇聞。
又過了一個月,你就奔赴朝鮮去了。我記得差不多就是那個時候,她丈夫真的回來了,而且右手腕還真的受了傷,所以紅帽腳夫的說法也與事實不可思議地吻合。我妻子和當時的一些人還笑她說:「千枝子是太過思念夫君,所以才有此心靈感應的吧?」又過了半個多月,千枝子夫婦就前往她丈夫任職的佐世保去了。大概就是將到未到的時候,我接到了她的信,信上令人吃驚地寫了她的第三件奇聞。內容是說,千枝子夫婦離開中央車站的時候,替他們搬運行李的紅帽腳夫突然靠近了已經開動的火車車窗,像是要打招呼般探過臉來。僅僅是掃了一眼那人的長相,就讓千枝子的丈夫變了臉色,似乎半是難以啟齒地道出了實情。她丈夫的艦隊靠岸馬賽的時候,他和幾個戰友一起去了一家咖啡廳。突然,一個紅帽腳夫打扮的日本人走到他們桌旁,自來熟地打聽起他的近況。在馬賽的大街上,有個日本的紅帽腳夫在閑晃,自然是沒有道理。但是她丈夫也不知怎的,居然沒有覺得有什麼奇怪之處,還說了自己右腕負傷以及歸期將至的事。期間,一個喝醉的同事把喝光的葡萄酒杯碰倒了。他受驚環顧四周的時候,那個紅帽腳夫不知何時已經從咖啡館裡消失了。那傢伙到底是什麼人物—時至今日他回想起來,雖然當時眼睛看得很清楚,卻還是分不清這是夢境還是現實,甚至連同事們對這個紅帽腳夫出現的事情,也表現得好像根本沒注意到一樣,所以後來他就沒再打算跟別人說起這件事。但是回到日本後,千枝子卻說已經遇見過兩次奇怪的紅帽腳夫。那麼在馬賽遇見的,要說也是這個紅帽腳夫吧?不過,這也太過奇怪,太過想入非非了。另外,他也怕被人嘲笑在榮譽遠征途中,盡想著老婆的事情,於是一直保持沉默至今。但是,看到剛剛那個探出頭來的紅帽腳夫,跟馬賽咖啡館內的男人長得竟然分毫不差—她丈夫說完這些,久久不能言語。隨後又不安地低聲道:「但這不是很奇怪嗎?雖說相似到連眉毛都不曾有出入,我卻回憶不出那個紅帽腳夫的長相。只是在隔著窗子看見那張臉的瞬間,覺得就是那個傢伙……」村上說到這裡,有三四個貌似他朋友的人進了咖啡館,走近我們桌邊,連聲向他打著招呼。我站起身。
「那麼我先失陪了。我回朝鮮前會再來拜訪你的。」我走出咖啡館,不覺長長吐出一口氣。三年前,千枝子兩次打破約定,沒來中央停車站和我私會,只簡單地寫信解釋說要做一個貞潔賢淑的妻子,直到今晚我才第一次明白了其中的緣由……
黑衣聖母
於此涕泣之穀,哀漣歎爾。祈我等之主保,聊以回目、憐視我眾……其寬哉,仁哉,甘哉,卒世童貞瑪利亞。──Credo
「你覺得如何?看這個。」田代君一邊說著,一邊將一尊瑪利亞神像放在桌上展示。
所謂瑪利亞神像,就是查禁天主教時期,天主教徒們經常用來替代聖母瑪利亞參拜的神像,多為白色瓷雕。但是這次田代君展示給我的瑪利亞神像,是即使在博物館的陳列室,或是頂級收藏家的藏品中也不曾出現過的。
首先,這尊一尺高的立像,除了面部,其餘地方完全由黑檀木雕刻而成。不僅如此,雕像頸項上十字架形的瓔珞頸飾也是由黃金和...
作者序
導言
文藝雜話.饒舌(代跋)
雖然海涅筆下的德國幽靈,和法國幽靈相比或許更加不幸些,但是日本和中國幽靈之間的區別卻更大。首先,日本的幽靈是非社交性的,即使是被人相對地靠近,也會感到不愉快。因為這一顯著特點,類似阿岩稻荷 的情況,人人皆敬而遠之。但是說到中國的幽靈,則傾向於受到過良好教育,通義理,達人情,有時結局也比較好。如果你認為我是在誆你,大可去翻閱一下《聊齋志異》,數百篇短文中隨處可見這樣的幽靈。女鬼的話,如泉鏡花先生筆下的身著中式服飾的女主人公也並不少見。
取材自日本怪談的作品中,《雨月物語》是頗為有名的,但就其文品而言,總令我覺得有些寒酸不足。就如曾我蕭白 的畫作一般,其筆下的險峰峭壁著實引人注目,但描繪起秋實春雨等景物來,卻比尋常畫家還有所欠缺。不過,《雨月物語》中的《血衣》、《海盜》兩則短篇,不論發表在哪裡都是名篇。文筆簡潔有力,甚至有些古雅的韻味。谷崎潤一郎還曾說過,遭遇瓶頸時讀一讀《海盜》,會令人的思緒倍感清晰。
※
若說是此類故事的合集,在已出版的書籍中,我覺得最為有趣的還是《今昔物語》。它文筆質樸而簡明,比起新發表的英文及中文的翻譯小說,我覺得《今昔》讀來收益更多。之前提到的《聊齋志異》,應該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發表的小說集,但與《今昔》相比,它已經算是很近代的文章了。說起來,《聊齋》和《今昔》之中有十分類似的故事出現。比如《聊齋》中《種梨》的故事主幹,就與《今昔》的本朝第十八卷中老翁用法術盜瓜的故事別無二致,只要把梨子換做是甜瓜,便幾乎完全相同了。這麼說來,也許是日本的故事流傳到中國去了吧。
但是,這樣的故事還是中國風太濃,或許這故事的原型本就是從中國傳入的也不一定。若有人得空做一番考證的話,也未嘗不是一件趣事。順便一提,《聊齋》中《鳳陽士人》的故事,也與《今昔》本朝第二十一卷常澄安永在不破關夢見留京妻子的故事十分相似。
※
另外再說一個,《聊齋》中《諸城某甲》的故事,寫了一個在戰鬥中頸部負傷的男人,在戰後因為笑得太用力以至於頭掉了下來。與其類似的故事在西方故事裡也能看到,阿普列尤斯 書中的開頭部分,無故將魔女斬首的男人,第二天在泉邊飲水時,自己的頭也掉了下來。只是《聊齋》中只選取了「斷頭」一說為題材。
※
翻譯中國的故事,是從明治時代起,由依田學海 、小金井喜美子 開始的。因為起步較晚,雖然這些中國怪奇小說集有署名,但是可以看出故事並非是同一人所作。即使在同一本書中,根據情節也可以看出誰勝誰劣。讀來有趣的部分,在泉鏡花先生的《櫻草》中雖有收錄,但並無可比性。印象裡《奇情雅趣》中的故事翻譯得還是比較優秀的。
※
雖然是翻譯中國書籍,也不能做那種生搬硬套成日文的事(因為雖說中文也是使用漢字,但在翻譯時卻並沒有幫上什麼忙)。最近出版的日文版《西廂記》等完全沒有體現出原作的風貌,也是因為生生把中文翻譯成七五調 之類的日文的緣故。像是「風靜簾閑,透紗窗麝蘭香散,啟朱扉搖響雙環。絳台高,金荷小,銀釭猶燦。比及將暖帳輕彈,先揭起這梅紅羅軟簾偷看」這樣的句子,生硬地翻譯成「廉下不走風」之類的句子,實在是無法表達原作之美。
話說回來,這原本就是相當棘手的事情,又屬於並非特別有趣的雜劇類,也沒有必要非得翻得與原作比肩,只在這裡順帶一提罷了。
※
總而言之,中國的幽靈都是比較可愛的,只是我對縊鬼卻同情不起來。他們會誘騙人們上吊而死,十分危險。說起來不知何時,我從《拍案驚奇》一書中看到過縊鬼變成動物。這種說法並不是指縊鬼化身成動物,而是叫作縊鬼的鬼怪原本就是動物。我想,應該就和俄羅斯民間故事《傻瓜伊萬》中出現的那種小妖怪一樣,只要它出現在身邊就覺得愉快不起來。
※
說到動物,像狐狸這般變化自在雖然不錯,但是如《夜談隨錄》中的能戴,也是不論到哪裡都會大受歡迎的吧。書中道:「通體烏黑無頭無面無手足,唯二目雪白,一嘴尖長如鳥喙。」常常被指派去酒鋪子買酒。因為能戴是怪物,只要讓它帶著酒瓶和酒錢,即使是深夜時分,也可以進入門窗緊閉的酒鋪,只把錢留下,把酒帶走。雖然不曉得它是參照什麼做的,倒是從來沒有拿來不符合要求的酒。
※
此動物雖然行動便利,但是如莊子那有名的怪物大鵬鳥卻因體格龐大而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一旦飛行在空中,據說排泄的糞便可以將一整個村子都埋住。不過,也聽說之後有人從糞便中將村子整個挖掘出來,而且大鵬鳥所吞食的魚蝦還都活蹦亂跳的,這樣說來,塞翁失馬,又焉知非福呢。但是與阿拉伯的象鳥 相比,大鵬鳥顯得要粗俗無禮得多了。
※
寫出大鵬鳥糞埋全村的是袁隨園,但是趙甌北筆下的通臂猿,其滑稽的表現也尤為出彩。它是一種手臂像晾衣竹竿一樣,可以向左或右延伸兩倍長度的猿猴,在手臂向一邊延伸時,另一邊的手臂則縮至肩膀。也許有人把長臂猿之類的動物看錯了吧。《水滸傳》中就有一人取了這個外號,眾所周知,那是叫作侯健的裁縫出身的角色。另外一個蠻僧的手腕也和通臂猿一般可以延伸縮短,他在書中的名字卻記不清了。
※
說到動物,我想起一件事。上小學的時候,老師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張紙,要求我們畫出「可愛的動物」和「美麗的動物」,因此我在前項要求下畫了大象,後項的要求下畫了蜘蛛。覺得大象可愛的人也有不少吧,至於蜘蛛,是因為當時看到巨大的女郎蛛,我真心覺得它很漂亮。但是那個老師卻責備我說:「大象那麼龐大一點也不可愛,蜘蛛有毒也根本說不上美麗。」我看那個老師若是活到現在,倒是可以去做個文藝評論家。
※
我開始寫小說也差不多是那個時候。那時我寫的所謂小說,充其量不過是模仿《魯濱遜漂流記》的文章罷了,都是些流落到無人島,射殺巨蟒,極其勇敢活潑的冒險故事。篇幅大概是十張日式白紙,卷首還有用紅色和藍色墨水筆描繪的無人島地圖夾在其中。這樣默默地過了幾年,在高一的時候—在平凡的五年左右的時間裡,我和朋友一起籌辦了一本內刊,每期都發表五六篇如春日郊遊散步、中秋賞月之類的文章。恰逢大彥家的少主 那時候和我同年級,高歌著「船兒已遠獨餘煙」之類的民謠,我也開始正式在《都々逸》上撰寫小說了。開始拜讀德富蘆花的小說,大概也是那個時候的事情吧。
※
那時我又讀了許多勵志故事,主人公多是窮人家的孩子,像是徹夜讀書卻苦於沒有燈油,以及因為父母負擔不起而每天早晨靠賣納豆維生,全是諸如此類的故事。因此那個時候的自己甚至覺得若是父母再窮困一點就好了。與此同時,我也模仿著勵志故事,做了諸如編草鞋、砍柴等等的事情。等到長大成人後,與人閒聊起來,曾這麼想的又何止我一個呢?大概每個人在小時候都會有這麼一段天真爛漫的經歷吧。
※
這種天真爛漫的情懷高漲的結果,是當讀到幼年的加菲爾德 曾吃雞蛋殼的時候,居然真的模仿著做了。還有和朋友兩人把學校的窗簾弄破的時候,獨自承擔罪名的事也幹過,說來好像很了不起,但要到老師面前說出「老師,窗簾是我一個人弄破的」這樣的話,還是會感到很羞愧。現在只要想起來,就覺得實在是不堪回首。與此相比,反而是每天從乾貨店裡偷點豆子帶到學校去撒 ,倒成了高尚的回憶。
※
後來,我受到租書店的照顧,從那時起到中學的短短三四年時間裡,甚至借讀了平田篤胤的《稻生平太郎某錄》 抄本,印象中倒不覺得怎麼有趣。至今為止,我覺得在日本妖怪的創新這一點上,那本書中出現的怪物是最非凡的。夢幻的虛無僧登記人來到家裡的橋段雖然有趣,但是更為令人敬佩的是那些從房間角落裡鑽出來的、有著無數節肢動物般手腳的奇妙生物,像是銜接曲尺般,關節相連成可以彎曲又可以延伸的手臂,名字應該是山本五郎右衛門吧。相似的還有神野惡五郎,這個就單純列舉一下名字,山本的讀音「SANMOTO」,和神野的讀音「SHINN」,都是魔界的發音。
導言
文藝雜話.饒舌(代跋)
雖然海涅筆下的德國幽靈,和法國幽靈相比或許更加不幸些,但是日本和中國幽靈之間的區別卻更大。首先,日本的幽靈是非社交性的,即使是被人相對地靠近,也會感到不愉快。因為這一顯著特點,類似阿岩稻荷 的情況,人人皆敬而遠之。但是說到中國的幽靈,則傾向於受到過良好教育,通義理,達人情,有時結局也比較好。如果你認為我是在誆你,大可去翻閱一下《聊齋志異》,數百篇短文中隨處可見這樣的幽靈。女鬼的話,如泉鏡花先生筆下的身著中式服飾的女主人公也並不少見。
取材自日本怪談的作品中,《雨月物語...
目錄
奇聞
黑衣聖母
影子
奇特的重逢
火神阿耆尼
妖婆
魔術
兩封信
春夜
孤獨地獄
幻燈
海邊
海市蜃樓
死後
夢
凶兆
文藝雜話.饒舌(代跋)
奇聞
黑衣聖母
影子
奇特的重逢
火神阿耆尼
妖婆
魔術
兩封信
春夜
孤獨地獄
幻燈
海邊
海市蜃樓
死後
夢
凶兆
文藝雜話.饒舌(代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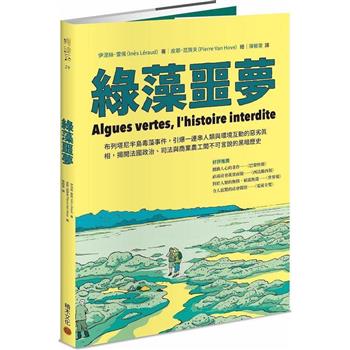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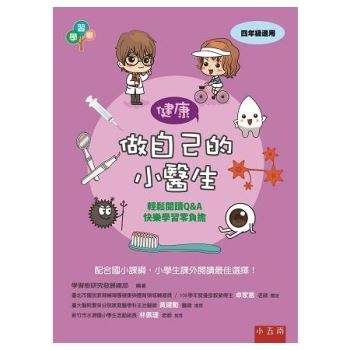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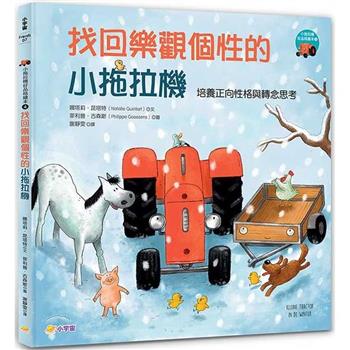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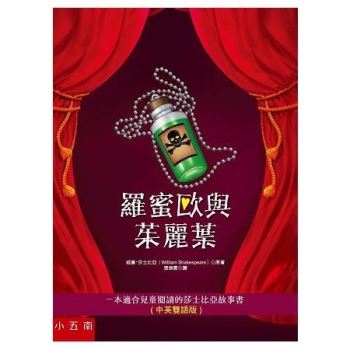







排版很糟 用了大量字體干擾閱讀,莫名的{ }、《》 翻譯也很有問題,魔術一文最後主人跟老婆婆說「客人今天不留宿」居然翻成留宿 日文原文漢字完全不一樣 真的很糟糕讓人不想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