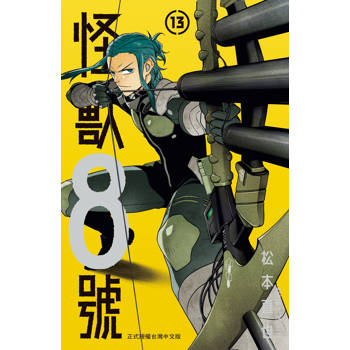〈自序〉適水適魚 /廖鴻基
每個人都有擅長,各有專精。有人記得天空飄忽的雲,有人著迷於花痕草跡,我專注的似乎是水域漂泊的漣漪。
對於人的記憶力很糟,好幾次對一位看似熟稔前來打招呼的朋友,尷尬失禮的想不起對方是誰;與人約了見面,進門前,一定得翻閱記事本,再三確認對方稱謂,以免失禮。對很多見過面的魚,不曉得為什麼,幾乎過目不忘。
這種魚、那種魚 … 只要見一次面,像底片感光,就記得了這條魚的身形、臉容和表情。寫過不少關於魚的文章,總有人問:不都一樣嗎,怎麼可能看見魚的表情或眼神。
某個冬日,和朋友去花蓮溪口,看見河口水面興起一波「異常」漣漪,我指著水面說:「看,魚。」朋友順著指尖看了老半天,也瞧不出所以然。他笑我神經質,說那不過是北風颳起的漣漪。但我十分肯定那是魚,而且,還能感受那魚因河口水域由污染而後恢復生機的喜悅。
「你又不是魚,怎知魚的快樂?」(有名的老故事)「你又不是我,怎會知道我不瞭解魚的快樂。」寫過幾篇關於魚的纏綿故事;有人懷疑,甚至說:「不過是作者穿鑿附會過度浪漫的想像。」
總難以明白解釋。或許有些浪漫,有些渲染,但情景確是親眼所見。
前陣子,媒體報導一對白頭翁殉情事件:這對白頭翁,其中一隻意外死亡,另一隻守著伙伴屍體終日徘徊不去;最後殉情而亡。這篇報導中,一位生物學家說:確實,許多種動物有類似的殉情行為。讀了這則報導後,鬆嘆了一口氣。世界寬廣,每個領域都無比深邃幽秘,都遠超過我們的理解和想像。何況水裡那看不透、摸不著的世界。
十數年前有次受邀參加營隊,對學員介紹花蓮環境。當我說:每當颱風靠近海岸,速度常會放慢,像是在和台灣高聳的山脈對話:凌越,或者,轉向。學員中出現幾個不以為然的訕笑。好多年以後,氣象報導提出,台灣山脈確是颱風行徑的路障,颱風在登陸前確有尋找缺口的「類似行為」。
當我主張為了挽回沿海生機,應該拒吃魩仔魚;因為魩仔魚是海洋食物鏈的基礎,也是兩百多種魚類的幼苗。有人提出學術資料反駁,指正魩仔魚並非如我所言是「兩百多種魚類的幼苗」。兩百多種,是根據一篇有關魩仔魚的研究報告。是不曾一一去計數魩仔魚到底包括幾種魚,但以我眼睛所見及海上現場瞭解,若長期採樣,再加上因拖網撈捕造成牠種魚苗的損傷,或於海上捕撈時就選篩掉的其牠種魚苗,恐怕不只兩百多種而已。何況,魩仔魚究竟包括幾種魚,並不是「拒吃」的重點。
當我講到黑潮的高溫特質,在台灣東部海域形成濕熱氣團,這氣團夏季時受東南季風吹拂上岸,並沿著東部陡峭山坡攀昇,形成凝結雨,像個園丁在我們高聳的山脈上辛勤澆水,使得陡峭山脈得以孕育森林奇蹟。有人來信指正:台灣氣象資料中根本沒有「東南季風」。
只好回信請這位先生,有空在夏季來一趟東部後山,感受一下旺盛而且自東南向吹來的海風;頂好出海一趟,檢證一下如花蓮漁民所言:「五月大南風;六月火燒埔」的後山夏季風情。一樣的,我所陳述的重點,並不在於這海域每年夏季吹拂的海風,是否被稱作東南季風。
不曾唸過生物、動物學,也沒受過任何生物特徵辨識訓練,但對於許多魚,僅憑一點邊緣跡象就可能猜出牠是誰。不一定直接叫出名字,但姓氏 (形樣分類或綱、目) 往往八九不離十。從事鯨豚調查時,船長和我總是比研究生們更遠的距離就能發現鯨豚。研究生若讚美眼力,我都這麼說:「你們書看得多,我們海看得多。」
有位熟識的朋友取笑我:「你啊,認識的魚比認識的人還要多。」
喜歡一個人到處走、四處看,也許恰如沈從文所言:「喜歡看東看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許多事情 … 讀一本小書,同時又讀一本大書 …」每次有趕稿壓力,不得不關起門來用功時,都會以「趕快寫一寫,就可以出去走走」來安慰及鼓勵自己。
回想與魚與水的相處經驗,多得是驚豔。潛水時偶遇一群游魚,如平靜的夜空一團煙火乍現,紛紛流轉。好幾次從甲板望著舷際魚體斑紋,感嘆這根本是武士才配得的勳章;而且是人眼無法捕抓的光、水調合。
寫作於我而言是生活記錄,儘可能一筆筆記下所見、所感、所想。因緣於適水適魚的個性,以多年累積的腳跡和船痕,一字字編織水和魚的風景。
這本書整理自2001-2005年間寫過三個有關海洋環境、生態、文化的專欄文章,穿插些關於水,關於魚的回憶。
當作是行腳、行船至此的紀念。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腳跡船痕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34 |
二手中文書 |
$ 253 |
文學 |
$ 281 |
中文書 |
$ 282 |
現代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腳跡船痕
以海水替換血液,將船痕過渡腳跡,尤有甚者,對魚比對人還熟,廖鴻基以懷抱海洋的深情,化為款款文字,搭配藍灩豔的照片,成為這本充滿自然詩意、體現人性魚格的作品。
這是一個把夢想和青春都獻給海洋的作家,對於台灣與海洋如何相處最深刻的祝禱……他既寫出了長年海禁之下台灣人靠近卻又陌生的海洋圖像,也表現了圍繞著台灣的大海的繁複面貌,以及海中生物,特別是魚類、鯨豚的生態現象,最後及於台灣海洋文化的整建理念──這樣的書寫企圖,如波濤之湧動、如水紋之綿密,不停不歇,因而使他的海洋書寫在台灣文學領域中建立了鮮明的特色,形成豐饒的海洋想像世界。──向陽
作者簡介:
廖鴻基
一九五七出生於花蓮市。花蓮高中畢業,三十五歲成為職業討海人,開始寫作。之後籌組台灣尋鯨小組執行「花蓮海域海上鯨類生態調查計畫」,並以關懷台灣海洋環境、海洋生態及海洋文化為宗旨,發起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http://www.kuroshio.org.tw),任創會董事長。曾獲時報文學獎散文類評審獎、聯合報讀書人文學類最佳書獎、一九九六年吳濁流文學獎小說正獎、第一屆台北市文學獎文學年金及第十二屆賴和文學獎。著有《討海人》、《鯨生鯨世》、《漂流監獄》、《來自深海》、《尋找一座島嶼》、《山海小城》、《海洋遊俠──台灣尾的鯨豚》、《台11線 藍色太平洋》、《漂島──一趟遠洋記述》、《台灣島巡禮》等。
作者序
〈自序〉適水適魚 /廖鴻基
每個人都有擅長,各有專精。有人記得天空飄忽的雲,有人著迷於花痕草跡,我專注的似乎是水域漂泊的漣漪。
對於人的記憶力很糟,好幾次對一位看似熟稔前來打招呼的朋友,尷尬失禮的想不起對方是誰;與人約了見面,進門前,一定得翻閱記事本,再三確認對方稱謂,以免失禮。對很多見過面的魚,不曉得為什麼,幾乎過目不忘。
這種魚、那種魚 … 只要見一次面,像底片感光,就記得了這條魚的身形、臉容和表情。寫過不少關於魚的文章,總有人問:不都一樣嗎,怎麼可能看見魚的表情或眼神。
某個冬日,和朋友去花...
每個人都有擅長,各有專精。有人記得天空飄忽的雲,有人著迷於花痕草跡,我專注的似乎是水域漂泊的漣漪。
對於人的記憶力很糟,好幾次對一位看似熟稔前來打招呼的朋友,尷尬失禮的想不起對方是誰;與人約了見面,進門前,一定得翻閱記事本,再三確認對方稱謂,以免失禮。對很多見過面的魚,不曉得為什麼,幾乎過目不忘。
這種魚、那種魚 … 只要見一次面,像底片感光,就記得了這條魚的身形、臉容和表情。寫過不少關於魚的文章,總有人問:不都一樣嗎,怎麼可能看見魚的表情或眼神。
某個冬日,和朋友去花...
»看全部
目錄
向陽序
適水適魚(自序)
海邊
布袋蓮
海防到海巡
東西海岸
輪迴
肉粽
糖果罐
滄桑
那是什麼
藍色公路
溪流
河口
錯亂
七星潭
海鮮
血脈裡的海水
翻車到曼波
釣魚
討海
鯨靈
空殼
想念
光光漁港休閒漁民
保護
夜生活
賞鯨
腳跡船痕
最後
適水適魚(自序)
海邊
布袋蓮
海防到海巡
東西海岸
輪迴
肉粽
糖果罐
滄桑
那是什麼
藍色公路
溪流
河口
錯亂
七星潭
海鮮
血脈裡的海水
翻車到曼波
釣魚
討海
鯨靈
空殼
想念
光光漁港休閒漁民
保護
夜生活
賞鯨
腳跡船痕
最後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廖鴻基
- 出版社: INK印刻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6-04-01 ISBN/ISSN:986710832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04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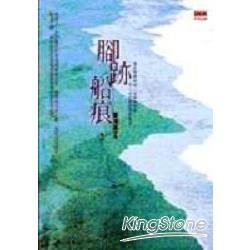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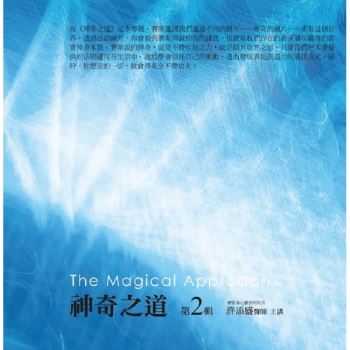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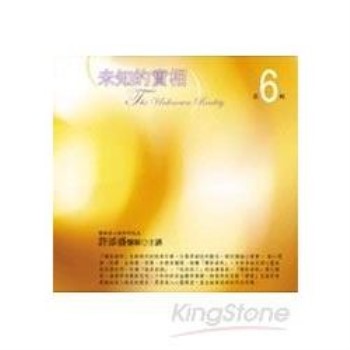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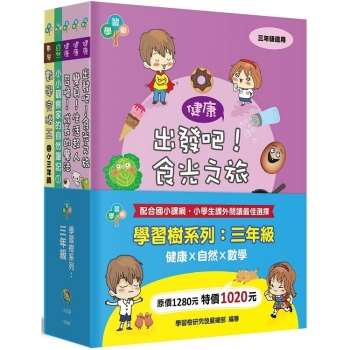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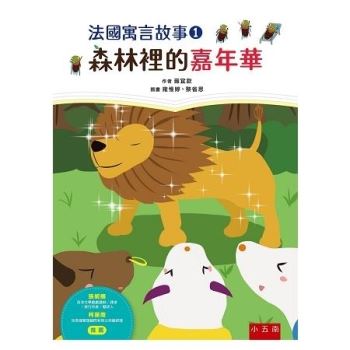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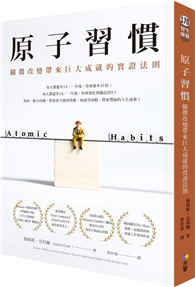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