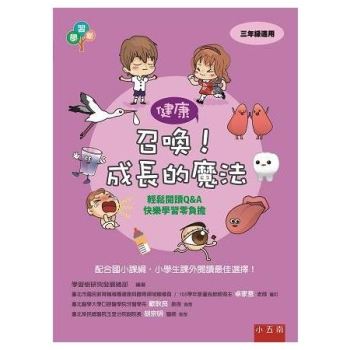抒情系譜的直裔 文字文明的貴族
古典靈魂與現代身體相悖相融的詩行風格
49首詩,49幅安靜無聲的畫面。詩人在學術的象牙塔與異境的風物間徘徊。閱讀時仿若一場旅行,在愛情、在鄉愁、在新舊文字靈魂裡迴蕩。以古典中文進入現代場景,以浪漫與風流的心情篤定安居。
此為作者的第二本詩集,年輕清麗的文字,專注真情,不只有我,「你」一直在,在所思所願,在眼前在遠方,有交融亦依靠,然無限情意卻在理性揮灑下顯出執?截絕的風格。
錘鍊,作為詩歌創作古老而核心的技術,在最新世代詩人當中,似有失傳之勢。獨有楊佳嫻,居然著魔一樣,迷戀著漢字的精魄與骸骨,時時展現錘字結響的工夫。
這個故作老成的靈魂,其實寄寓在一座狂野尖新的身體。在詩行推進的過程中,靈魂提倡著一種古典的理念,身體則綻放著一種現代的感性。兩者彷彿形成悖論,相互拉扯而形成一種特殊風格。
---唐捐
自我認識佳嫻與她的詩以來,倏忽也過了好些年;我有幸得見那斑斕的文明不再屏息,並為之欣喜。我期待在未來能看見更多的色彩、更新鮮的場景、不同的異地花園、爛醉的語言;那許許多多,原本不曾存在的節慶……---伊格言
詩使人與受過的傷害維持距離。長久掩埋對於記憶並非最好的處理,此時詩又是釋放。通過實境與幻覺,透過把握心上一點點愴然,雨中長窗與街道,眼前鋪陳著濕潤的屋瓦,彷彿看見新種下的九重葛青赭的銳葉如何突破陽台邊緣,完整形象漸次顯現,冥想成為實在,物也擁有了精神。
而在這沉浸乃至狂喜的過程中,我年輕了又老去了,唯一的聲音,乃是時間。
---楊佳嫻
作者簡介
楊佳嫻
一九七八年出生,台灣高雄人。台灣大學中文所碩士,現就讀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班。著有詩集《屏息的文明》(2003)、散文集《海風野火花》(2004),編有《臺灣成長小說選》(2004)。
定居台北已十年。歷居木柵、辛亥、東區、古亭,現在居住於日式房舍最密集之區域,同時與凋零中的優美和疊沓的市井共處,寫作讀書的窗外,咫尺處即是商家招牌、叫賣吆喝與縱橫之電線,但電線上常有白頭翁與燕子,聚簇昵語。正是俗塵與詩意的交界。
設有部落格http://blog.yam.com/chekh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