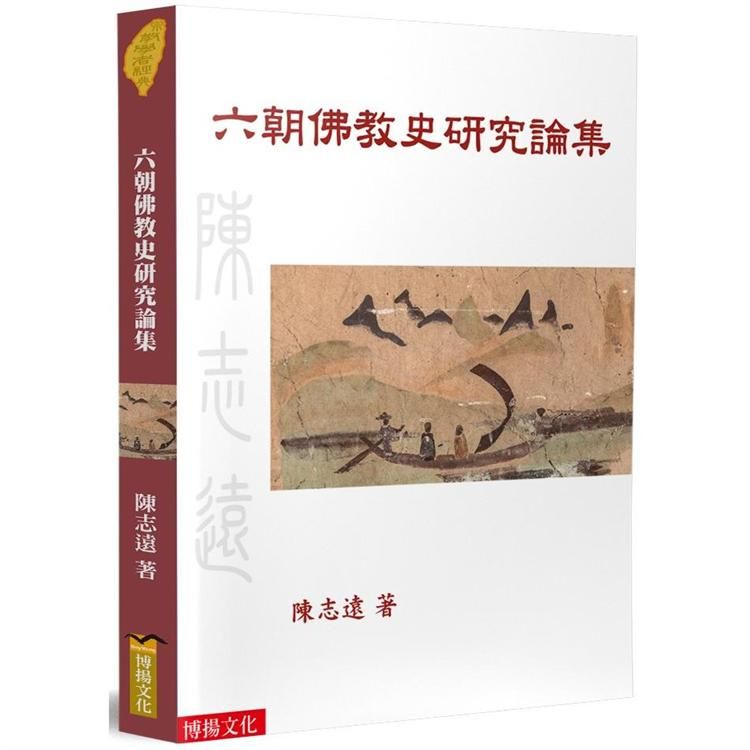卻顧所來徑(代前言)
是集收錄了我在六朝佛教史領域的若干論文。六朝既是時間斷限,也有空間的所指,對應中古史上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六個朝代。六朝定都建康,疆域大部位於長江以南,也正是在這一成期,江南成爲了一個文化地域的概念。
佛教史關心佛教的教理、實踐與現實的社會發生接觸的過程,關心二者的相互作用。佛教作爲思想、信仰,在歷史中傳播,作用於歷史;反過來,佛教自身也被外部世界形塑,歷史地展現出階段性的面貌。佛教在六朝江南的展開,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連貫的時空單元。本書所收論文,也都集中於此時空單元之內,故題曰《六朝佛教史研究論集》。
後漢至西晉中朝,佛教已有相當的發展,特別是隨著犍陀羅佛教寫本的研究推進,國際佛教學界也對最早期的漢譯佛經投以關注的目光 ,但由於史料的稀缺和我個人學力的限制,很難在這一領域有所貢獻,只好作爲“南渡”的背景略做追溯。永嘉南渡以後,南北對峙的局面持續三百年之久。北方的佛教形成了不同於南方的發展脈絡,深入研究且留待日後。
我從2010年起決定選擇魏晉南北朝佛教史作爲研究課題,迄今約有十年。起初想研究玄學,又想研究《文選》,玄學的興起和文學的獨立,二者相互關聯,對中古以降的中國文化影響至爲深遠。這種新的文化所塑造的自尊獨立的精神氣質,所開拓的疏離於此世生活的心靈空間,始終對我有極大的吸引力。博士階段放棄這兩個研究領域是感到對象的邊界太過模糊,學界的積累也比較薄弱,初學難於駕馭。選擇佛教,恰是基於相反的理由。佛教有大藏經,有明確的僧俗界分,人群和文本都是清晰的。
每個研究六朝佛教的人,都聽說過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這本名著。但我第一次閱讀的體驗糟糕之極,全書用和材料相似的文言語體撰寫,考證又極爲細密。我迷失在了細節和語詞的叢林裏。所以我決定暫時不看這本書,轉而去讀方立天先生的《魏晉南北朝佛教》,很快了解了這一時期教理學的基本線索,隨後又讀了許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國》。許氏此書是在湯先生研究的基礎上寫成,但卻有獨特的視角,例如他指出的佛教對社會階層流動的意義,佛教與印度、中亞世界的聯繫、佛道終末論等議題,和我在英語系學習所熟悉的問題意識非常貼合。
我最初的興趣點是政治史的,政教關係。從許理和的論述中,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東晉中期朝臣爭論沙門禮敬王者之時,建康的僧人紛紛退回會稽。局勢緩和之時,又紛紛返回建康。這和陳寅恪、田餘慶等魏晉南北朝史大家所描述的東晉僑人家族的出處進退如出一轍。我想搜集史料,從政治史的背景爲這個現象做一解釋。但當我逐漸深入,就意識到史料集中在東晉末年桓玄和慧遠的辯論,辯論中所展示出的問題的複雜性,遠遠超出了僧俗政治角力的解釋框架。偶然地,我在網上下載到哲學系李猛老師講解柏拉圖《會飲篇》的錄音。李老師的講解首先釐清在場諸人對愛(eros)的不同理解,然後分析了辯論發生的歷史情境。柏拉圖的文本不是簡單的哲學陳述,而是戲劇。劇中人物的思想交鋒,和戲劇發生的情境,二者是相互扭結著的。
李猛老師的這種分析方式,啓發我以類似的方法理解《弘明集》中的論辯,形成了本書第三編的諸篇論文。我逐漸領悟到,歷史的某個時刻,形成特定的思想,在佛教的語境裏,往往受到新經典譯出的刺激。也就是說,佛教是承載於特定文本的,隨著文本的移動、擴散而變化。核查論辯的典據,像同位素檢測那樣追蹤經典接受的歷程,就可以把思想史的內外連接起來。這種認識在我2012年到京都訪學,讀到船山徹老師的《佛典漢譯史要略》和《六朝時期菩薩戒的受容過程》兩文 之後,變得益發自覺。本書第一編的諸篇論文,大體是在這一思路下撰寫的。
六朝時期的辯論,有其鮮明的時代特色。不僅佛教在變,本土的傳統(儒學)也在變。本科時代起師從楊立華老師,博士導師陳蘇鎮老師精研《春秋》,本系的喬秀岩老師尤其強調義疏學是南北朝學術風氣的產物。耳濡目染,使我獲得了對六朝儒學的一些基本判斷,首先六朝絕不是儒學中衰的時期,玄佛之學,是儒學某些價值的擴展和補充;其次,儒佛交諍,焦點不在形而上的教義思辨,而在於實踐,是世俗禮儀與僧團戒律之爭 。即使相對抽象的討論,也有明顯的實踐指向。我曾經選取的個案,禮敬、踞坐、素食(未收入本書),莫不如此,未來還打算重談神滅論,也採取同樣的視角。
以上諸篇都採取思想史的路徑,在學界沒有什麼反響。一方面由於我理論分析和文章駕馭能力都很有限,一方面也是話題顯得比較陳舊,學界業已積累了大量同題論文,很難有人耐心閱讀我的新探。不過我珍惜研讀《弘明集》所獲得的認識,至今不變。
2013年,提交博士論文以後,我從思想史轉向了易於徵實的文獻學,關注點仍從之前的研究中生發。前面提到,禮敬問題是我思考六朝佛教史的起點,2011年提交博士中期考核的論文,也是我的第一篇佛教史論文,是《晉宋之際的王權與僧權》。許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國》,論述止於慧遠。塚本善隆的《中國佛教通史》第一卷亦以晉末爲斷。這個選擇不是偶然的。沙門不敬王者的討論在這個時刻爆發,意味著僧人作爲一個群體突顯在了世俗禮儀面前,皇帝要在佛教信仰系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說,僧俗關係經歷過幾次變遷。僧人起初局限於僑民群體,兩晉之際漸漸接近士人。名士先是以方外任誕之風來理解僧人出家生活對禮法的悖離,僧人與士人之間,是朋友關係。之後,士人意識到僧人出家是遵守另一套行爲規範的群體生活,僧俗之間,要建立一種類似師生的關係,戒律和禮法發生了正面衝突。我在文章中考證的論難發生的“八日”之所指,論難發生前桓玄與慧遠的關係,沙汰沙門的前奏舉措,都是末節,僧人形象的變遷,僧俗關係的調整,才是更爲本質的變化。爲了論述這種印象,我一改再改,一拖就是五年,始終感到力不從心!後來終於明白,我們對歷史的感覺像是眼前看到的風景,學術的語言則是一幅風景畫,構成風景畫的,是一些不規則的筆道和色塊。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以求音——我們需要用有形的、機械的東西支撐感覺。
圍繞這種感覺,我在博士論文開頭討論了佛教接觸士人的早期歷程,仍嫌蕪雜,最終提煉出材料比較集中,線索比較清晰的《般若經》作爲個案,寫成《般若經早期傳播史實辨證》。慧遠的廬山教團,具有高度的組織性,這一方式繼承自道安。對道安教團的南下路線和建寺歷程做細描,由此拓展,寫成《六朝前期荊襄地域的佛教》。
變化不僅體現在外部的組織形態,也發生在內部的知識形態。陸揚老師在討論鳩摩羅什傳時指出,寺院主義生活與經院主義學術二者相互表裏 。要有相應的知識和儀式,支撐一種生活。於是我嘗試用文獻學的方法呈現僧人知識管理的方式,具體而言,就是文本的編撰和注釋。本書第二編前三篇文章,都體現了這種關切。“合本子注”的問題,陳寅恪提出以後,受到普遍關注。我觀察到所謂“合本”,有對勘和拼綴兩型,前者是並列諸本,後者是首尾相接,分別有不同的產生背景。前者的重點是解讀《出三藏記集》中的幾篇經序,後者則需要調查不同版本大藏經中合本的綴接方法。博士論文的一節只是草稿,2014年到臺灣的法鼓佛教學院訪學,利用圖書館豐富的大藏經資源,大改了一次。在復旦大學的佛教寫本工作坊發表過。當時缺乏對大藏經的系統認識,對利用音義書復原藏經的方法亦不甚了然,後來僅僅發表了文章的前半,加了論“子注”一段,收入本書。
延續船山老師對佛典編撰現象的關心 ,我也關注齊梁時期繁榮的聚書和編纂活動。博士論文有一節考證定林寺經藏,其實是對《南朝佛寺志》的條目加以考訂、擴充,最終形成《定林上寺經藏考》。2014年,我在陳金華老師組織的暑期研修班結識了復旦大學李猛博士。李猛先後師承曹旭、陳尚君兩位中古文史大家,以考訂南朝、初唐文獻見長。內外史料交互爲用,考異繫年辨入毫芒,令我畏服。李猛考訂《蕭子良法集錄》 ,以蕭子良爲樞軸,帶起南齊一代之史。受其感召,2018年夏天,我也發意裒集史料,全面考訂寶唱著作,通過《歷代三寶紀》和《大周錄》佚文,復原《寶唱錄》的體例,寫成《寶唱著作雜考》。
也是在2014年,我去西安參加一個佛教石刻主題的會議,讀到魏斌老師的《南朝佛教與烏傷地方》 ,當時的震撼和感動至今記憶猶新。原來我所關注的建康宮廷、王府,大寺院裏的知識精英,政治上的那些派系、制度,都只是歷史的一個側面。在南方腹地的山坳裏,閉塞的金衢盆地,還有這樣一群人,那樣濃烈而卑微地生活著。他好像我碩士時代讀過的華茲華斯詩裏的老乞丐,又像侯孝賢長鏡頭中的臺灣,訴說著“永恒的人間悲曲”(the still, sad music of humanity)。2015年底,我工作的社科院歷史所派我到敦煌掛職。整個2016年,我都在敦煌七里鎮做鄉鎮幹部,切身地從首都走到了地方。遠離學術圈和朋友圈,晚上在我的辦公室兼宿舍,就在想,是不是要在文獻的考訂和思想的研討之外,對歷史上的人傾注某種同情?如何使研究具有靈魂?大概在那一年入冬的時候,孫齊發來了《六朝荊襄道上的道教》 ,初讀即可感受到魏老師的影響,史料運用嫻熟,佈局謀篇頗考究,關注歷史大勢中具體的人,又似乎有某種寄託。
對我來說,這兩篇文章都是神品,相當程度改變了我對學術人生的看法。但坦率地說,他們的精神魅力也對我形成了不小的困擾,或者叫“影響的焦慮”吧。我開始嘗試祛魅。首先是回到文獻。一位前輩坦言,歷史學始終是個靠天吃飯的學問,巧婦難爲無米之炊。情懷再動人,沒有材料支撐,沒有對文獻的細膩解讀,不過是一句叫囂而已。魏老師筆下傅大士的激烈與無奈,離不開四卷《善慧大士錄》,孫齊兄描述的荊襄道上的道館伽藍,離不開類書、道藏裏輯佚的材料。如果我也想講個動人的故事,材料在哪兒呢?
2015年,我寫了《干戈之際的真諦三藏》。真諦在梁陳易代的地方割據間輾轉漂泊,令人唏噓。要呈現這個故事,有賴於對真諦弟子所傳原始文獻、《歷代三寶紀》、《續高僧傳》層次結構的分析,有賴於聖語藏本《金光明經》僧隱序的發現,也有賴於《資治通鑑》梁陳段遠超正史的繫年資料之整理。同理,2018年寫作《六朝前期荊襄地域的佛教》,是利用了道宣《律相感通傳》的材料和《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才使敘事更覺豐滿。
史料匱乏是中古史的根本困境,突圍的路只有兩個方向,一是向外盡力搜討各類新材料,二是向內做嚴格的史料批判,對文本形成的機理和層次有更多的自省。受後現代史學思潮的影響,有研究者提出非常激烈的主張,幾乎否定了探求歷史真實的可能性。這類研究範式在佛教史特別是早期禪宗史研究中其實早有先例 ,將類似的方法引入六朝佛教史,也有一些嘗試。這給我帶來不小的刺激和不安。因此近年來我對六朝佛教史料做了一些專門的整理,既包括出土的石刻如僧尼墓誌、造像記,也包括輯佚文本如志怪小說、《世說新語》、十六國霸史中的佛教材料,也零散寫了一些考證文章,大體是本書第二編的諸篇,比如2016年完成的《謝靈運廬山法師碑的杜撰與浮現》,2017年完成的《六朝的轉經與梵唄》,在寫作過程中重新審視了以前比較熟悉的“高僧傳”類文體的形成機理,也考慮過後代禪、淨土等宗門文獻對六朝佛教史事的改竄。2017年4月,我在北大文研院做了“《高僧傳》的文本史”報告,系統地講述了我對六朝佛教史料學的整體看法。我認爲,六朝佛教史書的編撰,經歷了幾個階段。東晉中後期,主要是和傳主交好的文人寫作碑誌、行狀,劉宋時期代表性的體裁是類傳和感應故事的纂集,齊梁之際,出現了分科記述的高僧傳。史體的變化,反映了史書作者和記載對象關係的變化,前後形成一個連續的積累過程。
近年以來,史學界似乎形成了一種認識,認爲傳世的文獻,特別是卷帙浩繁,思想複雜的文獻,就是精英階層知識權力的產物,附著了他們的偏見,充滿了粉飾和欺騙,是認識歷史的障礙,爲了對抗權力,就要把目光投向散佚的、出土的、未經整理編排的史料,希望以此構建一個新的歷史敘事。關注下層、邊緣,發掘藏外材料,成了一種政治正確。這種二元對立的劃分,在我看來才是充滿偏見,它幻想了一個毫無思想輻射力的精英,和一個思想獨立自足的大眾。我甚至懷疑,如此主張某種程度上是在試圖解除研究者閱讀複雜文本的義務。在我處理過的案例中,我感覺傳世本和出土本,關係是柔和的,互動是複雜的。歷史上的精英與大眾,中心與邊緣,亦然。思想留下作品,事跡留下傳記,經歷漫長的時間,傳到我們手裏,有其內在的理由。將經典文本的形成全部歸因於歷史的偶然、後代的建構,是我不能接受的。
這當然已是世界觀層面的探討,我和幾位師友屢次激辯,很難求得一致。但重要的是我們按照各自的認識,在同一學術規範之下開展扎實的工作,貢獻出精彩的研究。於是我開始回歸基本的書目,把研究的重心轉到研讀道宣的作品上。這位7世紀的思想家和佛教史家,不僅在廟堂之上深度參與了唐初最高層的護教論爭,在鄉野之間,他又廣泛地記錄了南北朝後期到隋唐重要宗派形成時期多姿多彩的生存樣態。他的上百卷作品,可以說是中古前半期佛教史的全景展現。經池麗梅老師和易丹韻博士建議,2015年迄今,我比較仔細地閱讀了《續高僧傳》、《集神州三寶感通錄》、《集古今佛道論衡》,以及《廣弘明集》和《行事鈔》的部分篇章。在此期間,李猛完成了博士論文,討論初唐武德-貞觀年間的佛教政策和佛道鬥爭,王磊先後寫作三篇論文,考索唐代兩京、江南地區的東塔、相部律宗 。我討論慧光墓誌 、真諦行歷、智藏同梁武帝論難、寶唱的撰述,無疑都是閱讀《續高僧傳》的副產品。比起同輩的研究,這幾篇文章還顯得比較幼稚,不夠精彩。但我堅信道宣的作品是一個富礦,可以拓展的空間還很寬闊。
《續高僧傳》前後讀了半年,有一個困惑始終揮之不去。除了用寺院誌的方法整理僧人的住錫地和宗門譜系,用方鎮年表的方法整理僧人與政治有力者的關係,佛教史研究還能說出些什麼呢?這種痛苦在寫作《干戈之際的真諦三藏》時達於頂點,我一點都不懂真諦的思想,傳記材料又如此有限。類似的考證可以持續地寫,六朝完了寫唐代,唐代完了寫宋元,但自己都會感到乏味吧?
於是下定決心從史傳性作品進入比較“硬核”的佛學。其實在2014年,研究“合本子注”的時候,我就痛感解讀能力不足,跑到曹凌在通州的宿舍請教過一次。他勸我讀《俱舍論》。這本是佛學入門的通說,平川彰也是這樣告誡初學。2015年博士後出站之前,我和楊浩師兄等幾位學友組織了《俱舍論》讀書會,參照法譯本讀過《界品》和《根品》。此後買來新國譯本《成實論》研讀。至於《法華》、《涅槃》,從初學就喜歡其文字優美,反復翻閱。2018年,夏德美老師組織了《法華經》讀書會,每週幾位分任主講,解讀注疏。2019年,李薇老師在北大哲學系開設律藏選讀,帶我們精讀了諸部廣律第一波羅夷和受戒犍度。在此期間,經由胡曉丹博士,我和陳瑞翾、李燦等幾位研究早期大乘佛教的青年學者結識,先後做過《大般涅槃經》和《法滅盡經》讀書會,又時常在網上討論。在各位師友督責之下,我亦步亦趨地修習佛學,庶幾可以免於面墻。我承認大部分時間裏,我並不享受,因爲我並不是佛教徒,不希求在佛教的義理中尋求解脫塵世的出路,只在文化的意義上知道有必要努力理解。少數幾個時刻,當我能感知義理的實踐指向,找到了精緻複雜的名相和那些樸素的宗教情感的接合點,實在是法喜充滿,得未曾有。
以這種比較綜合的視角開展佛教研究,我選定了末法與孝道兩個主題,前者關注宗教對民眾歷史意識和時間感的塑造,後者則關注家庭倫理和兩性身體觀的一些話題。討論的範圍已不限於六朝斷代,甚至越出了傳統歷史學研究的範圍。
回顧本書所收錄的諸篇論文,總體來說都是不太滿意的。有從博士論文大幅修改發表出來的章節,也有新撰的篇章,帶有各個時段思想認識的印記,水平參差不齊。收入本書時,除了注釋格式和行文表述的修改以外,根據最新讀到的研究和讀者反饋做了訂正。需要說明的是,博士畢業前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梁武帝與僧團素食改革》,近年積累了更多材料,獲得了全新的認識,迫於交稿時限,實難草率成文,只好割愛。
六朝佛教史本來是學界深耕熟耘的領域,大師輩出。每個問題上先行研究的積累是不均匀的,我作爲初學,能有所推進的點因而也是不均匀的。本書沒有形成體大思精的著作,而僅僅是論文的匯集,維持一個相對發散的結構,這對我來說卻並不遺憾。頗感遺憾的是由於學術評價體制的壓力,不得不在今年倉促結集,六朝佛教史的若干問題本來積累了一些想法,未能深入探討,或者未及成文。比如,本書雖稱六朝,對開頭的孫吳佛教、東晉,以及末尾的陳朝著墨較少。孫吳佛教的受眾群體、信仰形態都迥異於後漢洛陽僧團,而東晉佛教受北方十六國佛教影響,僧俗關係經歷變遷,上文已經提及,尚待呈現。南陳一代,與北方周、齊成鼎峙之局。魏斌老師討論過的江南腹地傅大士教團,三國夾縫中的後梁荊襄佛教,由南入北的巴蜀佛教,猶有待發之覆。就算是學界研究較多的《弘明集》中幾場大辯論,《廣弘明集》中梁武帝的若干法會記錄,新出《大般涅槃經集解》和新出杏雨書屋羽271《雜義記》也值得一讀再讀。未來如有機會重版,我會把相關內容擴充進去。
本書能夠出版,感謝劉屹老師幫忙引薦,王見川教授慨允納入書系。兩位老師與我並無深交,卻對我勉勵有加。感謝在我求學的每個階段教誨我的老師,爲了避免名單過長,僅舉五位:楊立華老師、周小儀老師、高峰楓老師、陳蘇鎮老師、船山徹老師。他們有不同的人生觀和治學態度,如朗星麗天,我並不跟隨他們,而是參照他們走我地上的路。最後,感謝我的父母,他們不理解我研究的意義,卻默默包容我七轉八彎的學術經歷和並不成功的人生業績。過去這十年,應該是他們最困難的十年,也是衰老最迅速的十年。我對他們充滿了愧疚。希望未來十年,我能爲他們帶來更多的歡樂。這本小書,算是對我十年蹉跎所做的一個交待。
2019年11月25日
於錢塘江畔月輪山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六朝佛教史研究論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95 |
北傳佛教 |
$ 440 |
中文書 |
$ 440 |
佛教 |
$ 450 |
宗教類 |
$ 450 |
Religion & Spirituality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六朝佛教史研究論集
佛教史關心佛教的教理、實踐與現實社會發生接觸的過程,關心二者的相互作用。佛教作為思想、信仰,在歷史中傳播,作用於歷史;反過來,佛教自身也被外部世界形塑,歷史地展現出階段性的面貌。佛教在六朝江南的展開,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連貫的時空單元。
本書是作者近十年研究六朝佛教史的結集,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1)書物移動與佛教的時空展開:將佛教的傳播過程還原為書籍載體的翻譯和接受史;(2)聚書•抄撰•敘事:探析佛教史傳的衍生機理;(3)南朝教諍記:圍繞禮儀與戒律,觀察南朝的僧俗論爭。希望由各章節單篇考證,支撐起開放躍動的中古精神史畫面。
作者簡介:
陳志遠
男,1983年生於北京,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取得博士學位,曾到日本京都大學、臺灣法鼓佛教學院短期訪學。目前從事六朝佛教史、中古佛教文獻、儒佛交涉的研究,興趣集中於佛教末法思想的源流,佛教與孝道等問題。
作者序
卻顧所來徑(代前言)
是集收錄了我在六朝佛教史領域的若干論文。六朝既是時間斷限,也有空間的所指,對應中古史上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六個朝代。六朝定都建康,疆域大部位於長江以南,也正是在這一成期,江南成爲了一個文化地域的概念。
佛教史關心佛教的教理、實踐與現實的社會發生接觸的過程,關心二者的相互作用。佛教作爲思想、信仰,在歷史中傳播,作用於歷史;反過來,佛教自身也被外部世界形塑,歷史地展現出階段性的面貌。佛教在六朝江南的展開,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連貫的時空單元。本書所收論文,也都集中於此時空單元之內...
是集收錄了我在六朝佛教史領域的若干論文。六朝既是時間斷限,也有空間的所指,對應中古史上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六個朝代。六朝定都建康,疆域大部位於長江以南,也正是在這一成期,江南成爲了一個文化地域的概念。
佛教史關心佛教的教理、實踐與現實的社會發生接觸的過程,關心二者的相互作用。佛教作爲思想、信仰,在歷史中傳播,作用於歷史;反過來,佛教自身也被外部世界形塑,歷史地展現出階段性的面貌。佛教在六朝江南的展開,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連貫的時空單元。本書所收論文,也都集中於此時空單元之內...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卻顧所來徑(代前言)…1
引文凡例…13
圖表目錄…15
第一編 書物移動與佛教的地域展開…17
1-1 《般若經》早期傳播史實辨證…19
一、《道行經》在漢魏間的流傳…19
二、《放光經》的取得與流通…25
三、建康與會稽:東晉般若學的中心…29
四、道安掀起的般若新學風…33
五、般若學影響下的漢地撰述…39
六、結語…42
1-2 六朝前期荊襄地域的佛教…45
一、道安在荊襄地域之立教方略…46
1. 道安教團進入荊襄地域的契機…47
2. 襄陽、江陵兩地佛教寺院的建立…52
二、晉宋兩朝荊州佛教之繁榮…61
1. 慧遠教團在荊襄地域的經營…61
2. 江陵佛...
引文凡例…13
圖表目錄…15
第一編 書物移動與佛教的地域展開…17
1-1 《般若經》早期傳播史實辨證…19
一、《道行經》在漢魏間的流傳…19
二、《放光經》的取得與流通…25
三、建康與會稽:東晉般若學的中心…29
四、道安掀起的般若新學風…33
五、般若學影響下的漢地撰述…39
六、結語…42
1-2 六朝前期荊襄地域的佛教…45
一、道安在荊襄地域之立教方略…46
1. 道安教團進入荊襄地域的契機…47
2. 襄陽、江陵兩地佛教寺院的建立…52
二、晉宋兩朝荊州佛教之繁榮…61
1. 慧遠教團在荊襄地域的經營…61
2. 江陵佛...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