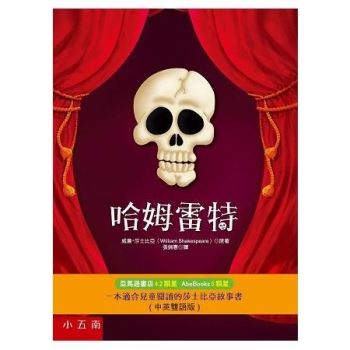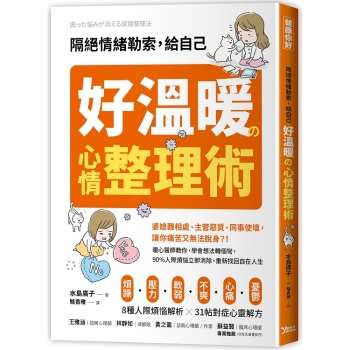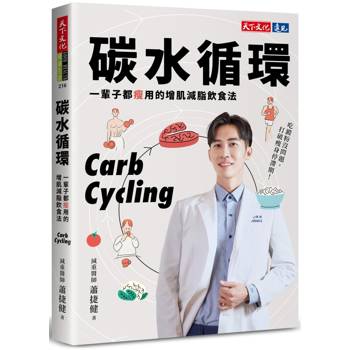我吃,故我在
我們在餐桌上認識整個世界
盤中物透露了人類過去和現在的祕密
食物的故事不僅和烹飪有關,也與文化有關。作者追蹤回溯當前的食物趨勢從何而來,也探究人們的口味和焦慮。故事的核心為食物史上的八大革命,揭示了以前隱而未見的關連:
*開羅街頭小吃的源頭為什麼在印度?
*素食主義者和食人族有多麼相像?
*吃微波餐的家庭和史前的原始人有哪些共通點?
*小麥如何成為征服全球胃口的主食?
*蝸牛怎麼會是人類早期演化的焦點?
食物是文化的指標,食物的歷史就是人類的文明史。最重要的是,食物是普天下皆感興趣、無法抗拒的話題,因此《食物的歷史》始終是一本理直氣壯講述人類樂趣的書。
作者簡介:
菲立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知名歷史學者,共有十多本著作,已翻譯成二十二種語言,包括Civilizations、Millennium、Truth: A History和Columbus。他自一九八三年起在牛津大學現代史系擔任教職,也曾任荷蘭高等研究院院士、明尼蘇達大學聯合太平洋客座教授。他有關海洋與殖民史的著作,為他贏得不少榮譽,包括一九九七年英國國家海洋博物館的凱氏獎章和一九九九年的約翰.卡特.布朗獎章。
《紐約時報》說,評論者將他比擬為吉朋、湯恩比、布勞岱爾等歷史學大師以及傳奇美食作家布伊亞─薩瓦蘭。
譯者簡介:
韓良憶,台大外文系畢業,曾在媒體工作多年,目前旅居荷蘭,右手翻譯,左手寫旅遊與飲食。近期譯作包括《第四隻手》、《心靈寫作》、《如何煮狼》、《牡蠣之書》等,不及備載。迄今在台灣出版的著作則有《青春食堂》、《鬱金香廚房》、《廚房裡的音樂會》、《我在法國西南,有間小屋》和《我的托斯卡尼度假屋》等八本。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費南德茲─阿梅斯托宛如行家吃龍蝦,津津有味地剝殼,剝開了食物歷史上的神話。——《舊金山紀事報》費南德茲─阿梅斯托替嚴肅的飲食寫作添加了人性與刺激,是傳奇美食作家布伊亞─薩瓦蘭之後的第一人。——《紐約時報書評》一本充滿知識的歷史書,但絕不枯燥:作者的看法雖強烈,但讀來極為興然有味。——倫敦《金融時報》具有高度的刺激與娛樂性……一本令人驚嘆的博學之書,許多趣味的內容讓人大開眼界。——《紐約時報》2003年國際烹飪專業協會最佳飲食寫作獎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最會說故事的歷史學家,寫出八段改變文明的飲食故事,同時顛覆你的味覺與歷史觀
得獎紀錄:費南德茲─阿梅斯托宛如行家吃龍蝦,津津有味地剝殼,剝開了食物歷史上的神話。——《舊金山紀事報》費南德茲─阿梅斯托替嚴肅的飲食寫作添加了人性與刺激,是傳奇美食作家布伊亞─薩瓦蘭之後的第一人。——《紐約時報書評》一本充滿知識的歷史書,但絕不枯燥:作者的看法雖強烈,但讀來極為興然有味。——倫敦《金融時報》具有高度的刺激與娛樂性……一本令人驚嘆的博學之書,許多趣味的內容讓人大開眼界。——《紐約時報》2003年國際烹飪專業協會最佳飲食寫作獎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最會說故事的歷史學家,寫出八段改變文明的...
章節試閱
火帶來了改變
牡蠣不是用來吃的。你在餐廳裡常可見到挑剔的吃客撥弄著牡蠣,要麼把包在棉紗布裡的檸檬擠出汁來,淋在牡蠣上,要麼在上頭澆點怪味醋,要不就灑上幾滴紅豔豔的塔巴斯可辣汁(tabasco),或別種辛辣得叫人雙眼發直、喉頭為之一嗆的辣醬。這可是存心挑釁的舉動,用意是要刺激這些雙殼貝,使牠們在臨死之前迴光返照。這不過是小小的一番拷打,你偶爾會覺得看到受害者的身軀扭動或退縮了一下。接著,吃客舉起匙和杓,撬開殼,讓牡蠣脫殼而出,滑進彎曲清冷的銀匙中。他舉起這滑溜溜的軟體動物,送至自己的唇邊,牡蠣的光澤和餐具的銀光相映成輝。
大多數人喜歡這樣吃牡蠣,然而這卻表示,他們因此喪失了完整且真實的牡蠣時刻。你應當拋開那些器具,將半邊殼舉至嘴邊,腦袋朝後一仰,用牙齒把這小傢伙從牠的巢穴裡一刮而下,嘗嘗牠帶著海水味的汁液,讓牠在舌上稍微停一下,以便味蕾玩味玩味,接著才將牠生吞下肚,你要是沒這麼做,可就硬生生錯失了歷史經驗。長久以來,吃牡蠣的人都是這樣來品嘗殼內那略帶腥臭的強烈味道,並沒有淋上可以去腥的芳香酸調味汁。高盧詩人奧索尼烏斯(Ausonius)就愛如此食用「這甘美的汁液,其中混合了妙不可言的大海之味」。有位現代的牡蠣專家則是這麼說的,你旨在接收「大海銳利的直覺,以及所有的海草與和風……你正在吃大海,就這麼回事,只不過在魔法的點撥下,有股奇妙的感覺自那一口吞下的海水中逸散而出。 」
在現代的西方烹飪菜色中,牡蠣有其獨特的地位,不用煮也不必宰殺即可食用。牡蠣可是我們最接近「天然」的食物,堪稱唯一足可冠上「天然風味」此一形容詞的菜色,而且這說法當中並無一絲嘲諷意味。當然,在餐廳食用牡蠣時,訓練有素的專家會運用全套的繁文褥節,外加合宜的技術、神聖不可侵的儀式和華麗優美的花招,替你處理好並撬開牡蠣殼。在那之前,牡蠣並不是天賜寶物,並非就生長在岩壁上水漥中任人摘取,而是被養在水底的石板或木頭棚架上,群聚於牡蠣床上,在專家的密切注意下成長,而後由熟手收穫採集。不過,牡蠣卻是把我們和我們的列祖列宗結合在一起的食物。一般認為自有人類以來,我們的祖先就生食牡蠣以攝取營養,而這也正是你吃牡蠣的方法。
有些人在一把抓起一顆梨子或一粒花生,直接生食咀嚼時,總以為自己聽到梨子和花生在哀叫。你就算跟這些人一樣,還是得承認在現代西方烹調中,除了幾種蕈菇和海藻以外,牡蠣其實可說是最「天然」的食物。我們所吃的蔬菜水果都經過千年萬載以來一代代人類的精挑細選、改良培育,就連直接從樹叢上摘下來的「野生」漿果也不例外。牡蠣則是經過自然淘汰過程留存下來的生物,品種未經人類染指改良,會隨著海域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而且,我們是趁牡蠣還活生生的時候就把牠吃掉。其他的文化還有更多這一類的食物,例如澳洲原住民愛吃木囊蛾幼蟲,趁幼蟲肥嘟嘟的,體內還有未完全消化的木髓,就將牠們自橡膠樹上刮下;北極圈內的涅涅特人(Nenets)把自己身上抓下來的蝨子放進口中咀嚼,「像在吃糖」 ;南蘇丹的努爾族(Nuer)的情侶,據說則會互相餵食從頭髮現抓下來的蝨子,彼此示愛;東非的馬賽伊人(Masai)生飲從活生生的牛隻的傷口擠出的鮮血;衣索比亞人愛吃裡頭藏有幼蜂的蜂巢;我們則吃牡蠣。小說家毛姆說過,吃牡蠣這回事,有種「討人厭的裝腔作勢」,是「想像力遲頓的人所領略不來的」 ,而且這鐵定會叫《愛麗絲鏡中奇緣》裡的海象發乎赤誠哀泣痛哭。更甚者,牡蠣算是相當不凡的一種生食,因為牡蠣一經烹煮便美味盡失。英國人會把牠們加進牛肉腰子派的餡裡,裹上培根肉串起來作串燒,或者澆上厚厚一層各種口味的乳酪醬汁,作成名為「洛克斐勒牡蠣」和「默絲葛雷芙牡蠣」之類的菜餚;再不,加進雞蛋裡,煎成中國廈門的名菜蠔煎;或將牡蠣剁碎了,作小牛肉或其他大菜的填料,凡此種種的作法都是為了掩蓋牡蠣本身的滋味。有時,創意食譜還比較成功,有一回我在倫敦的雅典娜神殿飯店吃到一道滿不錯的牡蠣菜餚,牡蠣用葡萄酒醋稍微煮過,上面澆了一點菠菜口味的貝夏美白醬。這類的實驗好玩歸好玩,在美食境界上卻難得能有所超越。
牡蠣是走極端的案例,然而所有的生食都有迷人之處,因為生食實在是反常的,這顯然是種返祖現象,返回文明前的世界,甚且回到演化史上人類尚未出現前的階段。人類所獨有的奇行怪舉並沒有很多種,烹調是其中之一,之所以稱其為奇行怪舉,是因為如果從自然的角度來看,以大多數物種攝食營養的方式為標準,那麼烹調還真是奇怪的舉動。史上最漫長且最不走運的探索之一,就是追尋人類本質的這趟旅程,人們汲汲於探究到底是什麼特質使人之所以為人,使人類在集體上有別於其他動物。這項追尋卻始終徒勞無功,迄今只有一項可被檢驗的客觀事實將人類與其他物種區分開來,那就是,我們無法和其他動物成功交配,其他一些所謂的人類特質,要不令人無法接受,要不就難以令人相信。有些說法聽來可信,卻不夠周全。我們大言不慚地表示「意識」乃人類所獨有,卻不很明白「意識」是個什麼玩意,也不知道其他動物是否擁有「意識」。我們宣稱唯有人類擁有語言,可是倘若我們有能力和其他動物溝通,牠們大概會反駁這個說法。我們在解決問題這件事上頭,算相對的有創意;我們算有適應力,能居住於不同的環境。我們使用工具︱︱特別是使用飛彈時,手還算靈巧。我們在創造藝術和具體實現想像力這兩件事上頭,算有雄心。就某方面來說,在上述這些事例中,人類的行為和其他物種之間的差距實在巨大,因此我們或可放心表示,兩者的特質確實不同。在使用火這件事上,我們的確匠心獨具,雖然有些猿猴經過教導也學會用火,招數卻很有限,就只有點煙、燃香或看著火不讓火熄滅等等,不過這些猿猴一定得經人指導才學得會。同時,自古至今也只有人類會主動地利用火 。有不少指標指出人類是具有人性的,烹調好歹也是其中一項不錯的指標,只不過箇中存有個嚴重的限制,那就是,在漫長的人類史上,烹調是晚期才發生的一項變革。根本沒有證據顯示烹調已有五十萬年的歷史,而烹調可能起源於逾十五萬年以前的證據,又無法令人徹底信服。
當然,這一切都得看所謂的烹調所指何意。正如古羅馬詩人維吉爾所說的「地煮」(terram excoquere),有人認為,耕作即是一種烹調的形式,在烈日下曝曬泥土塊,把土地變成烘烤種籽的烤爐 。胃夠強壯有力的動物經由咀嚼反芻來調理食物,又為何不能被歸類為烹調呢?在狩獵文化中,獵人在捕獲獵物後,往往會犒賞自己一頓,大啖獵物胃裡未完全消化的東西,如此一來,便可即刻恢復他們在打獵時消耗的元氣。這是種既天然又原始的烹調,乃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加工食品。包括我們人類在內的許多物種,都會先把食物咬碎了吐出來,餵給嬰兒或老弱者,以便後者攝食。食物不論是置於口腔中溫熱也好,用胃液加以分解也好,還是咀嚼咬碎也好,都應用到某種將食物加熱加工的過程。你一旦把食物放在水中漂一漂,便開始在加工處理食物了,有些猴子在食用堅果前就會這麼做。不過,確實也有真正嗜食生食的怪人,就愛把食物連同泥土一起吞下肚。小說《瘋狂佳人》(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裡的歐克農夫,便「從來不會為最純淨的泥土而大驚小怪」。
你一旦把檸檬汁擠在牡蠣上,便開始改造牡蠣,使得牠的質地口感和味道產生變化,廣義來講,或可稱之為烹調。把食物醃很久,就和加熱或煙燻一樣,也會轉化食物。把肉吊掛起來使其腐臭,或者索性置於一旁任其腐敗,都是加工法,目的在改良肉的質地,使之易於消化,這顯然是早於用火烹調的古老技術。風乾是種特殊的吊掛技術,它能使若干食物產生徹底的生化改變。掩埋法也是如此,這種技法以前很常見,能促使食物發酵,如今則少見於西方菜色中,不過gravlax(北歐式醃漬鮭魚)這個字倒還留有此一古風,它字面上的意思正是「掩埋鮭魚」。另外,有若干種乳酪以前也採用掩埋此一「類似烹調」的傳統技法,製作時須埋進土裡醃漬,如今則改用化學上色,使乳酪表面色澤暗沈。有些騎馬的遊牧民族在漫長的行旅中,把肉塊壓在馬鞍底下,利用馬汗把肉燜熱燜爛,以便食用。攪拌牛奶以製作奶油則簡直像煉金術,液體變成固體,乳白變成金黃。發酵法更是神奇,因為它可將乏味的主食化為瓊漿玉液,讓人喝了以後改變言行舉止,擺脫壓制,激發靈感,堂皇走進充滿想像力的領域。凡此種種轉化食物的方法既然都這麼令人瞠目稱奇,生火煮食這件事為何會顯得卓越出眾呢?
倘若真有解答,那麼答案就在於生火煮食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用火烹調堪稱有史來最偉大的革新之一,這並非由於煮食可以讓食物產生變化(有很多別的方法都有這個功效)而是因為它改變了社會。生的食物一旦被煮熟,文化就從這時這裡開始。人們圍在營火旁吃東西,營火遂成為人們交流、聚會的地方。烹調不光只是調理食物的方法而已,社會從而以聚餐和確定的用餐時間為中心,組織了起來。烹調帶來了新的特殊功能、有福同享的樂趣以及責任。它比單單只是聚在一起吃東西更有創造力,更能促進社會關係的建立。它甚至可以取代一起進食這個行為,成為促使社會結合的儀式。太平洋島嶼人類學先驅學者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特洛布里安群島(Trobriand Islands)研究時,有項儀式吸引他莫大的注意,那就是克里維那島(Kiriwina)上一年一度的番薯收穫祭,祭典中的大多數儀式都是在分配食物。人們一邊擊鼓、舞蹈,一邊把食物聚攏成堆,然後抬到家家戶戶,以便各戶人家私下進食。大多數文化都把真正開始吃東西當成祭典的高潮,但是克島的祭典卻「從未共同達到高潮……祭典的要素存在於準備的過程中」。
在有些文化中,烹調暗喻著生命的轉變。比方說,加利福尼亞原住民以前會把剛生產完的婦女和進入青春期的少女抬進地上挖的坑洞裡,然後把墊子和熱石頭堆在她們身上 。在另外一些文化中,調理食物變成神聖的儀式,不但促成社會的產生,獻祭時四散的煙和蒸氣也滋養了上蒼。亞馬遜人認為「烹調行動是在天地、生死、自然和社會之間從事仲裁的活動」 ,他們歸納出的這個觀念,大多數社會都至少在某幾項烹飪行為中有所體現。
日本人一般稱呼一餐為「御飯」,字面上的意思為「可敬的白飯」 ,這不但反映出白飯在日本是餐餐不可或缺的基本食品,也反映出攝食這件事的社會性質︱︱說實在的,應該說是社會地位才對。儀式性的餐食成為評量人生的尺度,有新生命誕生時,鄰居親友會致贈紅色的飯或加了紅豆的白飯為賀禮;小孩滿周歲時,作爸媽的會分贈被孩子的小腳踩過的米糕碎片給親朋好友。新屋落成時,得供奉兩條魚謝神,入住新居時,則得宴請鄰居。婚禮結束時,新人應贈送食品給觀禮嘉賓,往往是鶴形或龜形的糕餅或魚板,鶴和龜都是象徵長壽的吉祥物。葬禮和祭日時,則會出現其他種餐點 。
在印度社會中,有關食物的規矩極端重要,這些規矩標示並維繫社會界限和差異。不同的種姓純淨程度有別,這一點反映在食物上,有些種類的食物能和別的種姓分享,有的不能……生的食物可以在所有的種姓之間流通,熟食則不可,因為熟食可能會影響到種姓的純淨狀態。 熟食還有更精細的分類,用水煮的食物不同於用澄清奶油煎炸的食物。較多的種姓可以交換煎炸食品,水煮食品則受到較大的限制。除了食物能否共享與交換有一定的規矩外,某些特殊地位的人們還有特定的進食習慣和飲食規定。舉例來說,最高、最純淨的種姓必須吃素,「比較不純淨的種姓才會吃肉飲酒;而有些賤民吃牛肉的行為則明顯標示出其種姓的低下。 」尼泊爾唐區(Dang)第三階級的塔魯人(Tharu)不和種姓較低的人交換食物,也不讓低種姓者在自己家裡吃東西,但是他們吃豬肉和鼠肉。斐濟人禁忌之複雜,讓他們成為人類學家樂於研究的對象。在斐濟,某些特定團體一起進食時,只准吃彼此互補的食物;如果有戰士在場,首領吃捕獲的豬,而不吃魚或椰子,這兩樣必須留給戰士食用。 眼下,在自詡現代的文化中,我們所說的生食在上桌以前已經過精心調理。我們必須採用「我們所說的生食」此一明確用語,因為「生」實為文化所塑造的概念,或至少是經文化修飾過的概念。我們一般在食用多種水果和某些蔬菜前,都儘量不加以調理,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蔬果本就該生食,因為這在文化上是件正常的事,可沒有人會說這是生的蘋果或生的萵苣。只有碰到一般是煮熟了吃、但生食亦無妨的食物,我們才會特別指出這是生胡蘿蔔或生洋蔥等等。在西方國家,生鮮上桌的魚和肉實在太不尋常了,以致令人聯想到顛覆和風險、野蠻與原始等弦外之音。中國人傳統上會把野蠻部落依開化程度區分為「生」番和「熟」番,西方在分類世人時自也有類似的心態,西方長久以來的文學傳統把好吃生肉和蠻荒、嗜血以及一空腹便怒氣沖沖的惡形惡狀畫上等號。
西方最經典的「生」肉菜色就是韃靼牛排。菜名中提到中世紀時形象兇殘的蒙古人,又名韃靼(Tatars),這也是其中一支蒙古部落之名。此二字令中世紀的人種誌學者聯想到古典地獄觀念中的深淵「韃爾靼羅斯」(Tartarus),因此用韃靼二字來惡魔化蒙古敵人簡直再合適也不過 。然而我們今日所知的這道菜卻是經過千錘百鍊、膾不厭細的佳餚,肉被絞碎,變得又軟、又爛、又細,色澤鮮麗。好像為彌補它的生似的,這道菜在餐廳的調製過程被演化為一整套的桌邊儀式,侍者一板一眼、行禮如儀,把各式各樣添味的材料,一樣一樣拌進碎肉中,這些材料可能包括有調味料、新鮮藥草、青蔥和洋蔥嫩芽、酸豆、少許鯷魚、醃漬胡椒粒、橄欖和雞蛋。淋點伏特加雖非正統作法,卻能大大增添菜餚美味。文明社會所認可的其他生肉、生魚菜色,同樣也完全失卻其天然狀態,味道都調得很重,並經過精心調理,好脫去它野蠻的本色。「生」火腿經過鹽醃及煙燻。義大利式生牛肉(Carpaccio)要以優雅的手法切成薄如蟬翼,還得淋上橄欖油,撒點胡椒和帕馬乾酪,這才入口。北歐式醃漬鮭魚如今雖不再用掩埋法製作,但仍得抹上一層層的鹽、蒔蘿和胡椒,並浸在鮭魚本身的魚汁中好幾天才能食用。「如果說我們的遠祖吃的肉都是生的,」布伊亞︱薩瓦蘭(Brillat-Savarin)在他一八二六年的著作中寫道,「那麼我們尚未完全失去這習性,最細膩的味蕾仍舊能品味欣賞阿耳香腸和波隆納香腸、煙燻漢堡牛肉、鯷魚、新鮮的鹽漬鯡魚等等,這些東西通通沒有經過燒煮,卻依然仍勾起人的食慾。 」他的這本著作直到今日仍被美食家奉為聖經,被饕餮當成自我辯護的依據。
西方如今正時興的壽司就以生魚為材料,魚肉要麼沒調味,要不只加了一點醋和薑;不過這道料理的主成分卻是熟米飯,有時會撒點烤芝麻。「刺身」則比較復古,回到絕對的生鮮狀態,但還是有經過悉心的調理:生魚片必須用利刃切得薄透纖美,擺盤務必高雅,如此一來,生食的狀態反而更能令食者感覺到自己正在參與教化文明的過程。配菜必須分開來切成各形各狀,成碎末、細絲或薄片,同時得附上好幾樣精心調配的醬汁。丹麥人喜歡用生蛋黃當醬汁或盤飾,即使如此,還是得把蛋黃、蛋白分開,只有蛋黃才上桌。南非作家凡德波斯特(Laurens van der Post)曾在衣索比亞被款待以「生肉流水席」,食物本身雖未經多少調理,宴會過程卻充滿繁文褥節。 諸位賓客依序傳遞生肉,那肉剛從活生生的牲畜身上割下,不但血淋淋,而且仍然溫熱。每個男人用牙齒牢牢地咬住肉塊一側,然後用利刀往上一削,削下正好一大口的量︱︱在這過程中,一不小心,便會削下自己鼻頭的皮 。 肉片並非就這麼空口吃,而得蘸上貝若貝若醬(berebere),這種醬料熱辣得「叫人以為這肉已經燙熟了」。此醬也可把一鍋燉菜變得「火辣到令人簡直耳朵都要流血了」。三不五時,有人會隔著男人肩頭遞一片肉給默立在用餐者身後的婦孺。這些食物都只是狹義上的生食,大不同於其天然的狀態︱︱暫且不管那是個什麼樣的天然狀態︱︱因此我們想像中的原始人類祖先就算看到了,想必也認不出它們是什麼,這些祖先應當是手上有什麼可吃的就吃什麼。人類開始用火煮食後,生食在世上大部分的地方似乎都成為罕見之事。
在大多數文化中,烹調的源頭要麼可追溯至一項神聖的恩賜──「普羅米修斯之火」,要不就得歸功於某位幸運的文化英雄。古希臘人認為,火是逃離奧林帕斯的叛神者洩露給凡人的祕密。古波斯人相信,有位獵人射偏了石彈,從而自石塊中央引出了火。達科他的印第安人則認為,當初是美洲虎神的爪子不斷抓地而引起了火花。對阿茲特克人來講,第一把火便是太陽,是眾神在一片黑暗的太古時代中點燃了這把火。庫克群島人則認為,天神茂伊(Maui)降臨大地時,把火帶到庫克群島。澳洲有一族原住民則在一種圖騰動物的陽具裡,發現火的祕密;另一族人則認為是女人發明了火,她們趁男人出外打獵時用火煮食,然後把火藏在陰部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普羅米修斯」,幾乎每個文化也都有自己的普羅米修斯之火 。
人類究竟是何時開始使用火,不得而知 。所有的相關理論似乎都有如擦石取火,短暫地放出火花,其中最令人難忘、壽命最長的一項理論,乃「現代古生物學之父」布魯耶神父(Abb?Henri Breuil)所提出。一九三○年,則輪到布魯耶的年輕門生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揚眉吐氣,成為二十世紀知識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這位耶穌會神父兼考古學家一秉耶穌會結合科學和傳教的優良傳統,在中國一邊傳教、一邊考古,挖掘出「北京人」的洞穴居處。這種原始人生活在五十萬年前,照理講,當時應該尚未出現工具,人也還不會用火。德日進拿了一支鹿角給布魯耶看,請教老師的意見。「這支鹿角還新鮮的時候,」布魯耶答道,「被火烤過,而且被一種粗糙的石器切割過,可能不是燧石,而是某種原始的劈砍工具。」
「不可能。」德日進回答,「這是周口店出土的東西。」 「我才不管它是在哪兒出土的。」布魯耶堅稱,「有人製造了這東西,而且那個人會用火。 」一如其他有關人類何時開始用火的理論,近年來有越來越多人對上述理論存疑。不過,布魯耶仍自周口店出土的灰石堆中,架構重建了一個複雜的原始人社會,其理論固然引人入勝,卻難免包含了一些奇想的成分。他為北京人想像勾勒的生活畫面是這樣的:一個女人在磨燧石,一個男的北京人則在切鹿角,附近還有兩三個人在生火。男人一打出火花,女人趕緊用手中握著的一束乾草樹葉去接火,「接著她會把火拿到爐邊,這用小石頭堆砌成的爐子,就在他們兩人之間。他們身後還有另一堆火,熊熊的火焰上正烤著一頭野豬。 」事實上,相關的遺址一直未出現有製造燧石或用火的證據。
我們或可推論,人類會用火之後,接下來必然就會用火來把食物煮熟。現代西方社會有個最常見的迷思,英國作家藍姆的名作《論烤豬》(A Dissertation Upon Roast Pig)對烹調的起源有番想像,書中有段文字正足以勾勒此一迷思。有個養豬的農人粗心大意引起一場大火,把一頭乳豬意外燒死。 其中一隻早夭的受難者殘骸冒出濃濃的白煙。他不安地絞著手,正想著該怎麼對父親啟齒時,一陣香味撲鼻而來,他以前從未聞過這麼香的味道……就在此時,口水自他嘴角流出,濡濕了下唇。他不知該作何是想,緊接著,他彎下腰摸了摸豬,看看那頭豬是否還有一絲生氣。他燙傷了手指,卻仍傻勁不改,趕緊把手指塞進嘴巴裡,好涼一涼指頭。燒焦的豬皮屑隨著手指進了他的口,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嘗到了︱︱脆豬皮!(說實在的,是世界破天荒頭一遭,因為他是天下頭一個有此經歷的人。 ) 事情一發而不可收拾,直到一位賢明之士出面干預,「燒房子的習慣」才被淘汰。這位賢士「發覺不必放火燒掉整間房子便可烹燒(他們稱之為「燒灼」)豬肉︱︱說實在的,應該是任何一種動物的肉。 」耐人尋味的是,據藍姆說,這項重要的技術源自中國,而就整體而言,中國的確是有史以來世上技術發明最多的國家,只是西方一般並未給予適當的認可。至於藍姆認為用火燒煮乃是偶然的發明,這一點就比較是老生常談了。在史學著述中,「偶然」近來有復甦之勢,因為量子物理學和混沌理論顯示出,我們活在隨機的世界中,無法追溯的原因似乎的確會引起不可預期的後果。埃及豔后克莉奧派特拉的鼻子就像蝴蝶翅膀:在蝴蝶效應中,某地的蝴蝶翅膀拍動,可以在地球另一邊掀起一場風暴;而要不是埃及豔后那幾公分長的鼻子偏偏就那麼美麗挺直,說不定就絕對不會有羅馬帝國的誕生。「虛擬歷史」學家如今老是告訴我們,若非這件或那件偶然的事件,整個歷史的進程都會不一樣,某某王國就因為缺了根釘子而失敗。然而老實說,只有透過歷史的記錄才看得出來偶然的因素是否真的左右了事情走向。偶然提供了我們一個模型,使我們得以解釋「原始」社會的變遷,而我們往往自以為是,認為原始社會如一灘死水,愚昧且固定不變。可是創造發明並非在偶然間發生的,就算有,事例也極為罕見,發明的背後一定有想像力的實現過程與切乎實際的觀察。 早在人類學會用火以前,某種形式的烹調可能即已出現。很多動物會被吸引到自動燃起的野火燒過之處,在餘燼中翻尋被火燒烤過的可食種籽和豆類。今日仍不難看到野生的黑猩猩實施一種覓食的技巧,而我們可以放心大膽將此一技巧類比為原始人類強徵糧食的強橫作風 。對擁有足夠智力和靈敏度的動物來講,火燒後滿目瘡痍的樹林的幾項特徵,好比一堆堆的灰燼和傾倒半焦的樹幹,可能都看來像是天然的烤爐,雖仍冒著煙,卻不會燙得無法觸碰。硬殼種籽和豆子、無法咀嚼的豆莢和軟骨皮肉,這麼一來都吃得下去了。
烹調是人進行的第一項化學活動。烹調革命是破天荒的科學革命:人類經由實驗和觀察,發現烹調能造成生化性質的變化,改變味道,使食物較易消化。儘管由於現代的營養專家常針對肉類中的飽和脂肪酸提出恫嚇,而使得肉食失寵,肉卻仍是人體最好的蛋白質來源,只是肉實在含有太多纖維,也太韌了。燒煮使得肌肉纖維中的蛋白質融化,使膠原變成凝膠狀。如果是直接用火燒烤(最早的廚師們採用的大概就是這項烹調技術),那麼在肉汁逐漸濃縮時,肉的表面就會歷經類似「焦糖化」的過程,因為蛋白質受熱會凝結,蛋白質鏈中的胺基酸和脂肪中含有的天然糖分,就會產生「梅拉德反應」(「焦糖化反應」)。有史以來,澱粉便是大多數人熱量的來源,可是直到人類用火煮食後,澱粉質的攝取才變得有效率。熱度能夠分解澱粉質,釋放一切澱粉質當中都具有的糖分。同時,乾火能將澱粉中含有的糊精燒成棕色,我們看到這顏色,便感到安心,因為這代表食物熟了。在史上大多數的文化中,除了直接用火燒食物以外,另外一個主要的烹調法就是用水煮。水煮可以軟化肉類的肌肉纖維,使碳水化合物的粒子膨脹,當加熱到攝氏八十度時,粒子會破裂,擴散開來,湯汁就變得濃稠了。熱力改變了其他食物的質地,使食物變得容易咀嚼,或易於用手剝開,這是「在飲食習慣開化的過程中第一項重大的突破,要等到很久以後,才出現筷子和刀叉」 。由於加熱烹調使得食物較容易消化,人就可以多吃一點,現代人一生可以吃掉足足五十噸的食物。這多多少少促進了人類的效率,進一步也造成攝食過量的機會,從而對社會產生某些影響,我們稍後再討論有哪些影響(參見第五章)。
烹調除了能使可食的東西更易攝取,還會變更神奇的魔術,那就是把有毒的東西轉化為可口的食物。火能毀滅某些潛在食物中的毒素,對人類而言,這項可化毒為食的魔術尤其可貴,因為人類可以儲存這些含有毒素的食物,不必害怕別的動物來搶,等到人類自己要食用前再加熱消毒即可。這項文化優勢使得苦味樹薯成為古代亞馬遜人的主食,也使一種名叫「納度」(nardoo)的蘋屬植物的種籽成為澳洲原住民的佳餚。亞馬遜人當成主食的苦味樹薯是製作樹薯粉的常見原料,其中含有氰酸,只要一餐的分量就可以把人毒死,但是苦味樹薯經搗爛或磨碎、浸泡在水中並加熱等烹調程序處理以後,毒素就會被分解。印第安人當初怎麼會發覺樹薯的這項特性,進而種植並當成主食,至今都是疑問,惹人好奇卻也令人百思不解 。烹調可以消滅大多數害蟲,豬肉中常含有一種寄生蟲,人類吃了以後會得旋毛蟲症,但加熱烹調後就變得安全無虞。以快火將食物徹底煮熟可以殺死沙門氏菌,高熱則可殺死李斯特菌。有項例外應特別注意,大多數的烹調程序並不能殺死最能致人於死的細菌──肉毒桿菌,傳統烹調法中可以達到的最高溫度毀滅不了這種細菌,不過添加大量酸料倒是可以抑制它的生長。
人一旦親眼看到加熱對食物產生的影響,用火烹調這件事立刻就走上康莊大道。focus(焦點)一字不論照字面來講或探究其字源,都意指「壁爐」。人一旦學會掌控火,火就必然會把人群結合起來,因為生火護火需要群策群力。我們或可推測,早在人類用火煮食以前,火即是社群的焦點,因為火尚具有別的功能,使得人群圍攏在火旁:火提供了光和溫暖,能保護人不受害蟲、野獸侵擾。烹調讓火又多了一項功能,使得火原本就有的凝聚社會力量更形茁壯。它使進食成為眾人在定點定時共同從事的行為。在烹飪出現之前,人們沒有什麼動機共同進食。整備集合的食物可以當場吃掉,也可以隨各人意思私下食用。雖說我們可以想像原始人類聚集在一副生的獸體四周,好像禿鷹圍在骨頭旁邊,但是在人開始用火烹調以前,進食這件事卻未必能結合社群;狩獵、宰殺動物和維護集體安全等共同行動固然激發了群體合作,然而獵來的獸肉或拾來的腐肉卻可以分配下去各自食用。直到火和食物結合在一起後,大勢所趨,社區生活的焦點才沛然成形。進食以獨特的方式成為社交行為:共同進行卻不必同心協力。用火烹調賦予食物更大價值,這使得食物不再只是可吃的東西,而且開啟充滿想像力的新可能性:餐食可以變成祭品、愛筵、儀式,以及種種透過火的神奇轉化功能所促成的事物,其中之一便是將彼此競爭的人轉化為社群。
在現代社會,或至少可說是晚近以來,人仍可重拾或重新體會這種凝聚力所具有的原始感覺。有「農民哲學家」之稱的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在一九三○年代對童年往事有過以下一段追憶: 火比較像社會產物,而非天然物質……當熱騰騰的鬆脆烘餅在我的齒間嘎喳嘎喳作響時,我吃下了火,吃下它金黃的色澤、它的氣味,甚至它燃燒時劈劈啪啪的聲音。因此,帶著某種奢侈的快感……火總是如此這般地證明了它的人性。火不只能燒煮,還能把烘餅變得香脆金黃。它把物質形式帶進人類的節慶。不論追溯到多久以前的時代,食物的美食價值總是在它的營養價值之上,而人類是在喜悅而非痛苦中找到自己的靈魂……黑色的大汽鍋懸掛在鍊條上,這口三足的鍋子立在熱灰的上方,我祖母會拿著一根鋼管,鼓起雙頰吹氣,好搧醒沈睡的火焰。在這同時,所有東西都在爐上煮著,有餵豬的馬鈴薯,還有給一家人吃的上好馬鈴薯。熱灰裡頭摀著一只新鮮的雞蛋,那是給我吃的 。
火帶來了改變牡蠣不是用來吃的。你在餐廳裡常可見到挑剔的吃客撥弄著牡蠣,要麼把包在棉紗布裡的檸檬擠出汁來,淋在牡蠣上,要麼在上頭澆點怪味醋,要不就灑上幾滴紅豔豔的塔巴斯可辣汁(tabasco),或別種辛辣得叫人雙眼發直、喉頭為之一嗆的辣醬。這可是存心挑釁的舉動,用意是要刺激這些雙殼貝,使牠們在臨死之前迴光返照。這不過是小小的一番拷打,你偶爾會覺得看到受害者的身軀扭動或退縮了一下。接著,吃客舉起匙和杓,撬開殼,讓牡蠣脫殼而出,滑進彎曲清冷的銀匙中。他舉起這滑溜溜的軟體動物,送至自己的唇邊,牡蠣的光澤和餐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