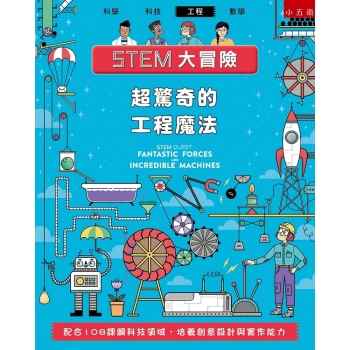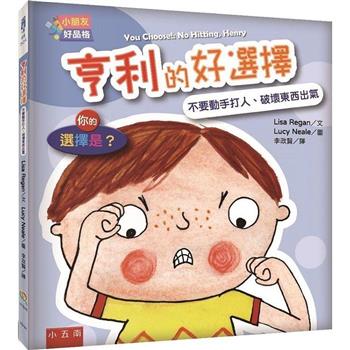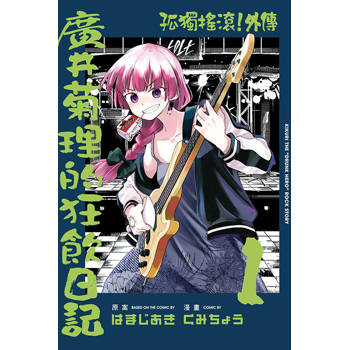本書源起於2002年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羅梅君策劃舉辦之「Women in Republican China」國際會議。由於中國史的社會性別研究,向來集中在與婦女相關的課題上,例如婚姻家庭、子女、纏足、性、人口發展,卻鮮少涉獵經濟、政治和國際關係等男性領域的歷史,因此,值得以社會性別的角度去發掘與探究這些尚待填補的部分。本書收錄的論文,橫跨了一九四九年前後兩個共和政權下的女性歷史,並涉及知識界、政治界、金融界、宗教界、政黨、報刊雜誌、商業廣告、近代小說以及漫畫,這原屬男性領域或由男性主導的區塊。
新時代來臨後,共和時代的女性,在論述中或現實情境裡受到的關注,更加多元,除了品貌、才德之外,還包括她們能否搭上新時代的列車,是否可以和現代性、西方文明、科學、商業廣告、民族主義、自主婚姻、女權主義這些流行話語或現象相互扣合,並且與男性一起建構新中國。這些研究更進一步指出,當女性要跨越性別秩序時,男性充滿不安,但在男性矛盾、游移的隙縫中,有的女性從客體轉為主體,儘管這其中有不少是經過妥協和退讓,女性仍為自己闖出一片天。
作者簡介
羅梅君(Mechthild Leutner),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歷史系教授。
顧德琳(Gotelind M?ller),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教授。
柯臨清(Christina Gilmartin),美國東北大學歷史系教授。
史明(Nicola Spakowski),德國不來梅國際大學歷史系教授。
李木蘭(Louise Edwards),澳洲雪梨科技大學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教授。
白露(Tani Barlow),美國華盛頓大學婦女學系教授。
梅嘉樂(Barbara Mittler),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教授。
顧德曼(Bryna Goodman),美國俄勒岡大學歷史系教授。
游鑑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臧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水鏡君,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瑪利亞.雅紹克(Maria Jaschok),英國牛津大學國際發展學學院國際性別研究中心主任。
楊海倫(Helen Praeger Young),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共十三位世界各地婦女史研究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