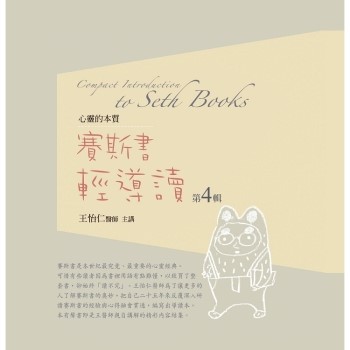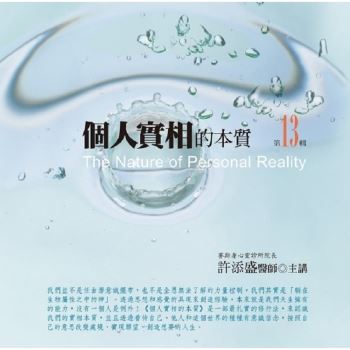〈01〉第一章 傷痕
凌晨,這裡是第一塊被太陽點燃的地方——依然淹沒在太平洋波濤中的太陽讓淡金色的光芒穿過殘留著黑暗夜色的茫茫雲霧,斜射向蒼穹之巔,將銀色的雪峰燒成火炭般深紅,那燃燒的雪峰呵,彷彿是浮現在時—空極致處的一團浴血的聖火;傍晚,這裡是留住太陽最後一片神韻的地方——大地已經彌漫起鐵黑色的蒼茫夜霧,而在峭立的黑暗之巔,被殘存的陽光映成金色的雪峰,猶如燦爛王冠的浮雕,隱喻著古老而高貴的精神原則。
這個地方便是地球崇高的極致,青藏高原。
這片高原以奔騰咆哮的冰山雪峰為銀色的骨架,以鐵褐色的無極的荒原為粗獷的肌膚,以聖潔的太陽為熾烈的靈魂。在荒野間漫遊萬里的青銅色的風是高原自由的激情;那將天空都燒成深紫色的雷電,是高原鋼藍色的狂笑;那能凍裂火焰的漫天暴風雪是高原潔白的悲愴;那裸露在荒涼大地上的風裂的岩石是高原堅硬的嚴酷;那貼著地面湧過的鉛黑色陰雲是高原蒼茫的哀愁;那能在鐵鑄的心上刻出荒涼痛苦的鷹嘯,是高原驕傲的歌。
或許是受某種宿命的召喚,在地球一次最富激情的震盪中,這片曾被囚禁在深海黑暗中的大地無可阻止地升騰而起,如同白銀築成的祭壇,托著頑強、壯烈的生命形式,托著金色的生命聖火,向太陽,這光明的根據獻祭;向藍天,這心靈自由的象徵獻祭。
這片高原上的太陽單純而熾烈得近乎蒼白,但蒼白的太陽卻賜給大地上所有的色彩以燃燒般的絢麗感,即使是鐵塊似的岩石也呈現出燦爛的黑色;這片高原上的天空藍得成為一種極致的優美,只有猛獸之血的殷紅波濤才配為那豔麗而純淨的蔚藍沐浴。
從這片離太陽和蒼穹最近的荒野間,從這踞於雲端的高原上,無數條雪水河閃耀著悲憫之情湧向低矮的地方,為東亞大陸、東南亞和南亞次大陸帶去命運的啟示。黃河金色的波濤和長江灰色的激流間浮現出古中華文明;會在落日下慢慢變成深紅的神聖的恆河與銀色的印度河孕育了古印度文明。但是,這片作為生命之源的高原卻一直高傲地堅守著遠古的青銅色荒涼;現代文明已經背棄了文明起步時的神聖感,而這片曾為在下的生命送去命運靈感的高原則依然冷峻地將神聖的靈魂舉向寒冷的燦爛。
萬年不停的狂烈的風撕碎了一切偽裝,像野火般在鐵褐色大地上掠動的雷電擊碎了所有的修飾,高原裸露出最深刻的自然的真實;熾烈如蒼白火焰的陽光使高原上的心靈得到淨化——只有火的沐浴才能使心靈淨化為聖潔。於是,在這裡,聖潔的心靈觸摸到了自然的終極真理。儘管那真理荒涼而悲愴,但聖潔的心靈卻從觸摸中領悟到了高於物欲的絕對價值。於是,聖潔的心靈與自然的終極真理重疊成一個塵世之上的信念,就像陽光滲入浩蕩的風一樣,融成同一個動盪的燦爛的意境。
高原南部,在印度平原上人們的仰視中,喜馬拉雅山脈宛似從藍寶石色的天空高遠處隱隱浮現出的銀色波濤;佇立在高原北緣的崑崙—巴顏喀拉山脈上,可以俯瞰亞洲大陸腹地無邊無際的大漠戈壁;高原西端之外的中亞大地和歐洲平原陷落為雲層之下的深淵,蹲踞在喀喇崑崙山岩石上的鷹群,常透過紫色的暮靄,被魅惑了般凝注血紅的日球漸漸在那深淵中熄滅;高原東部,雲霧彌漫的高崖深谷如同凝固的瀑布般陡峭,這被命名為「橫斷」的山脈酷似一個果決的意志劃出的斷然界限——峻峭、神聖的高原同卑下的低地之間的界限,而高原上那閃耀著冰雪魂魄的風,會越過東方潮濕悶熱的四川盆地和平庸的華北平原,在太平洋的波濤中找到自己命運的歸宿。
高原中部被稱為「無人區」的荒涼原野上,唐古喇山脈徐緩起伏,一片片雪水湖在藍天下波浪盈盈,有的似物欲之上的寧靜心靈;有的像永恆的哲學智慧;有的如少女聖潔的凝視;有的彷彿是晶藍、透明的沉思。
萬里「無人區」南緣和喜馬拉雅之間,是構成高原鐵背銀脊的岡底斯—念青唐古拉山系。在科學理性的視野中,珠穆朗瑪是地球之巔,但是,在宗教真理的古老凝注中,岡底斯的崗仁波欽卻是「雪山之王」,是世界之極,是純潔心靈的神聖歸宿。
神聖感是屬於高貴生命的感觸,他就在純潔的靈魂中燃燒。然而,作為某種精神神聖感的象徵的存在,卻往往離生命那樣遙遠,——他或是在生命無法企及的彼岸,或是在世界上最荒蠻的地方,在荒涼得連浩蕩長風都只會做千年悲泣的地方。這種神聖的象徵與塵世之間的需要用生命量度的距離,也許是精神信仰保持其魅力的根據——永不凋殘的魅力,往往在遙望之中。
崗仁波欽,這座佛教、印度教、耆那教、本教都尊崇為聖山的雪峰,就在最荒蠻的地方,就在離藍天最近的極致之處,就在茫茫冰雪覆蓋的青藏高原深處。
橫貫高原的岡底斯山脈氣質剛烈,風格銳利,無數座冰峰雪山猶如萬里波濤突然凝固在狂放激蕩的狀態中,崗仁波欽峰則以超群絕俗的王者氣概崛起於峻峭的波濤之上,那峭立千仞而輪廓渾圓的山體使崗仁波欽猶如巨大、美麗的日球沐浴在狂濤怒潮中——銀白色的日球。
崗仁波欽南面是聖湖瑪旁雍措。一位風姿綽約的美女正佇立在湖邊,讓目光越過碧藍的湖面,向聖山崗仁波欽遙望。在午後炫目的陽光中,聖山之巔的冰雪流盪起藍白色火焰般的光波,顯示出一種純潔的熾烈情調。
「聖山啊,你是來自遠古的潔白的呼喚——被雷電雕刻在陡峭而堅硬的藍天上的呼喚,你在呼喚什麼?⋯⋯噢,你是凍結在高空的燦爛,每當我離開你,就總想知道,總想弄清楚你在呼喚什麼,然而,一旦走近了你,一旦看到你雄偉奇麗的容顏,我卻又像一縷沒有思想的風,只願沉迷於你的燦爛之中⋯⋯。」美女在凝然不動的佇立中,用她遙望的目光向聖山傾訴心中飄過的縷縷紛亂的思緒。
她的眼睛顯示出康藏女性的特徵:眼睛秀長,如同明澈的水波,而眼梢又有一種銳利的妖嬈之美。只是,此刻她那如同高原墨玉色的夜空般給人以堅硬感的眼睛深處,卻動盪著無邊的迷茫,那迷茫的神情熾烈而又疲倦,熾烈得像被火焰灼傷的夢;疲倦得像乾熱的風中枯萎的花。她的兩彎彩虹似的長眉中間,有一顆沙粒大小的痣,那顆痣雖然小,但卻豔紅欲滴,在潔白的額頭上顯得十分觸目,這使她看起頗似寺廟壁畫上那些容顏秀美的天女或菩薩。她面容上的唯一修飾,就是將嘴唇塗成青灰色,這樣,她那輪廓優美、色澤陰鬱的雙唇就似乎隱喻著對動人死亡的追求,對美麗凋殘的嚮往。
美女的身後,在視野的極致之處,喜馬拉雅山脈的雪峰透過鉛灰色的雲霧暗淡地閃爍著銀灰色的光亮,從低垂的雲霧下伸展過來的原野呈現出沉重的鐵褐色,給人以堅硬的荒涼感;當原野終於越出烏雲的陰影之後,又在陽光下閃耀起刺目的蒼白色,那種無邊的蒼白似乎比死亡的意境更荒涼。雖然還只是九月中旬,荒原上低矮的野草卻都已經變成灰黃,而彷彿被野草染上枯黃色調的風,使美女的長髮以野性勃勃的情態飛揚起來。她那流溢著陽光的長髮,黑得有一種近乎美麗雌獸的、撩人的性感。
這位美女名叫珠牡,是北京民族大學舞蹈系的教師。她具有藏族的貴族血統。她的父親多仁.丹增班覺四十年代曾任西藏政府昌都地區總管。五十年代初共產黨軍隊進藏,丹增班覺率藏軍抵抗,戰敗後向共產黨投降。也許是出於在共產黨殘酷的專制政治下求生的本能,幾十年中丹增班覺一直對共產黨表現出寵物對主人般的絕對的忠誠,並無數次公開表示反對西藏獨立運動,他甚至還放棄了祖先對佛教的虔誠信仰,加入了唯物論的共產黨。丹增班覺的這一切努力終於使他又成為共產黨官僚體系中的新貴族。經過一系列升遷之後,他於十年前被任命為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按照共產黨的慣例,這個級別相當於副總理的官位,是丹增班覺這樣的投誠者所能得到的最高獎賞。
珠牡出生在北京,也生活在北京,可是,燃燒在她血液裡的屬於高貴祖先的古老戀情,卻從小就使她對青藏高原產生了熾烈的神往。從十二歲起,她每年都要到青藏高原上去度過幾個月。儘管每一次走上高原的具體目的可能不同,但每一次她都有一個不變的願望——拜謁崗仁波欽聖山,而且,隨著年齡的增大,她的這個願望也越來越堅硬,越來越灼熱,就如同野火燒成深紅的岩石,而那深紅的色調所蘊涵的,乃是一種對峻峭的神聖感的追求。
每當珠牡懷著被思念的火焰灼傷的靈魂,越過荒原上那萬年的沉寂,來到崗仁波欽聖山前面,生命的神聖感就如同高踞雲端的冰峰,以傲視萬物的王者氣概呈現在她的心中,而生命必須高貴、真實、善良、美麗的信念會於頃刻間化為沛然而降的急雨,為自己那落滿塵世灰塵的靈魂沐浴。然而,只要她將背影留給聖山離去,只要回到北京,回到那因中國現代思想專制而虛假化、物性化的人性氛圍中,生命神聖感便開始像風蝕的山崖一樣崩塌,而關於生命必須高貴,必須真、善、美的信念則漸漸變成垂死掙扎中的絕望的悲泣。最後,她的精神會在絕望和崩潰感中進入令人窒息的麻木狀態。當麻木到了極致,當麻木再也無法容納自身的規定性時,當麻木驟然破裂時,血淋淋的痛苦就迸濺而出。為了不被那種尖銳的痛苦將理智完全撕碎,為了免於進入精神失常的瘋狂狀態,她便只有再次走上拜謁聖山的遙遠旅途。
現在,一九九六年九月中旬的一天,珠牡已經使自己長久地沉迷在對聖山的遙望中。她總是以隔著瑪旁雍措湖的遙望完成對聖山的思戀。這一方面是因為,從這個角度望去,聖山正呈現出它最具個性魅力的形態:超越群峰之上的陡直而寬闊的石壁使崗仁波欽的山體顯得格外剛烈雄偉,崗仁波欽頂部不規則的巨大圓弧形稜線,則使這座聖山像是偉大日球的遺跡。珠牡喜歡向聖山遙望的另一個原因則是由於她不敢太靠近聖山,她不敢在近處仰視聖山——聖山的雄性之美太堅硬、太崇高、太銳利了,在逼近的仰視時,那種雄性之美會使她心醉神迷,會使她燃燒起來,會使她忘卻了對生命神聖感的領悟並迷失在燦爛的性感崇拜中。而個人命運的遭遇又將一種深刻的恐懼注入她的心靈,一種對雄性之美的恐懼。對她而言,那種輝煌的美似乎宿命地與豔麗而炫目的痛苦相伴。
在無數次遙望中,珠牡已經心靈震撼地領略過聖山的種種姿容:無月之夜,在燦爛的星空中,崗仁波欽圓弧形的、白雪覆蓋的山體,宛似藍白色的巨大的月球,周圍的雪峰像星雲一樣迷濛;凌晨時分,天空依然黑如墨玉,而天際已經泛起具有荒涼意味的淺黃色晨光時,崗仁波欽則呈現出剛毅的青銅色,彷彿是矗立在天地間的一面古老的銅鏡,鏡中映出的是生命虛無的意境;當高原上熾烈得近乎蒼白的太陽在東方升起時,崗仁波欽會被陽光燒灼成富麗而深沉的金紅色,似乎那高聳雲空的山體是用堅硬的火焰雕成的雄性美色的輝煌象徵,那種時刻,飄搖在聖山之巔的流雲則紅得妖冶,紅得豔麗;晴朗的白天,崗仁波欽頂部的弧形稜線猶如巨大彎刀的銀色鋒刃在親吻豔藍的天空,而在那銳利的親吻之處,藍天似乎就要被劃破,湧流出殷紅的血。不過,最令珠牡驚心動魄的魅力卻是聖山在夕照中變成燦爛金色的時候展現出來的——金色的聖山在她的視野中,是高貴而峻峭的真理,是用燃燒的金子鑄成的生命神聖的信念,是關於生命意義的金色之夢。
在向聖山的如醉如癡的遙望中,珠牡面容上浮現出的豐饒神情,顯現著她靈魂感觸的繁富:有時,遼遠而寧靜的憂鬱中會有長風般的動盪感有力地起伏;有時,豔紅的妖嬈中會閃耀起放縱不羈的野性;有時,燦爛的微笑中會飄過荒涼的悲愁⋯⋯隨著神情的變幻,聖山也在她的靈魂裡呈現出不同的意境。此刻,她覺得雪線以下裸露出的鐵黑色和紅褐色相間的岩層,使那峭壁看起來像是佈滿血鏽的鐵鑄成的祭壇,而聖山的山體猶如供奉在祭壇上的一顆猛獸之心,那彷彿被雷電刻出的猛獸之心是獻給荒涼蒼穹的祭品。
「噢,這顆雄烈的心中定然曾經有過能點燃萬里長風的遠古的火焰,定然曾經有過可以撕碎萬年沉寂的野性如狂的激情。可是,現在火焰和激情都已經在暴風雪中凍結成沉默的崇高與雄偉,凍結成高聳雲端的潔白的死亡。是的,火焰的靈魂一定是潔白的,因為,火焰最純淨,他不僅可以淨化萬物,而且可以淨化自己⋯⋯可是,那遠古的火焰還會為淨化現代人類墮落的靈魂而重新燃起嗎?那野性的激情還會使現代人類的生命意境中再度迴盪起屬於剛烈雄性的歌聲嗎?⋯⋯」思緒飄盪到這裡,珠牡的面容現出近乎煩亂的神情,而突然從旁邊傳來的格外尖利的風聲,完全劃破了她的沉思,使她不自禁地向風聲傳來的地方望去。
那裡是一座來聖湖沐浴的信徒堆起的「經石堆」。灰藍色的橢圓形石頭或蒼白的片狀石塊上,刻出了藏文的佛教六字真言,有的還刻出佛和菩薩的浮雕,那些字跡和浮雕被礦物顏料塗成紅褐色、灰綠色、土黃色、藍紫色等斑駁的色彩。在杳無人跡的原野上,這些色彩絢麗的精神的象徵給那遼遠的荒涼增添了神聖的意境,可是,不知為什麼,從那種神聖化了的荒涼中又飄盪出令人落淚的寂寞和悲涼。
珠牡的目光被「經石堆」頂部幾具野犛牛的巨大頭骨吸引了。在熾烈的陽光下,野犛牛的頭骨閃爍著令人心悸的慘白的光亮,刻在頭骨額際的「六字真言」不知為什麼被塗成了枯萎的黃色,而頭骨上堅硬彎刀般的長角卻呈現出深黑色,彷彿是生鐵鑄成的。那劃破珠牡沉思的尖利風聲,就是從鷹喙似的牛角尖上掠過。
儘管珠牡稍稍瞇細了眼睛,但那慘白刺目的野犛牛頭骨仍然使她覺得無法長久注視。然而,不知為什麼,就在她移開面容的瞬間,她視野裡的一切色彩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堅硬的慘白色,而尖利的風聲則在那慘白的背景上刻出一行字跡:「你不能在聖湖中沐浴,你會把聖湖弄髒!⋯⋯因為你的骨頭一定是黑的!」
珠牡的身體像風中的火焰一樣顫抖起來,彷彿被那片慘白、炫目的光亮刺激著,淡藍色的淚水從她深黑色的眼睛裡驟然湧出,那盈盈的淚影中動盪著無盡的茫然,閃爍著明澈的哀愁。
那句話是珠牡的一位女友對她說的。雖然她們從小一起長大,關係十分親密,可是,當得知她想要走入聖湖沐浴時,這位女友還是說出了那句令她的心受傷的話。珠牡知道,女友並不想傷害自己,她只是想要保持聖湖的純淨——這位女友是虔誠的佛教信徒,在她心靈的天平上,對佛教的責任重於私人的友誼。同時,珠牡也明白,這位女友為什麼會那樣說:按照藏族原始宗教本教的觀念,人的血肉來自於母親,人的骨頭來自於父親,而她父親的骨頭是黑色的,至少她的這位女友相信如此。在北京當局看來,珠牡的父親是背叛了原來的舊貴族的「反動」立場,並忠誠於共產黨政權的人,北京當局以顯赫的地位獎賞了這種背叛和忠誠,並將他視為可以用金鏈牽在自己手中的高貴的政治寵物,可以用來對抗西藏自由運動的政治宣傳品。不過,在許多西藏人的視野中,他則是一個背叛了祖先和神佛的罪人。這種罪人無論在焚身的火焰中,還是沐浴於聖湖中都不能得到淨化,他會使金色火焰變成鐵鏽色,會使清澈的聖湖被罪惡污染,因為,這種罪人的骨頭是黑的。
越來越茫然的神情使珠牡的目光宛似紛亂、蒼白的雪片飄落在聖湖盈盈閃爍的波光之上。她發現,映在湖中的對岸岡底斯山脈雪峰的倒影,比那沐浴在豔麗藍天中的雪山還要瑩澈,那由冰雪消融後的高山激流匯成的聖湖,則純淨得令人的心靈只能在高貴潔白的思想上棲息。
「聖湖呵,你這冰雪之淚,我真想讓靈魂永遠消融在你美麗的藍色中⋯⋯」珠牡無聲地自語道,她深黑的眼睛漸漸變得熾烈起來,將茫然的神情燒成了灰燼,並熔鑄出有幾許悲涼意味的高傲。她塗成青灰色的、輪廓秀美的唇邊忽然現出一個稍帶野性的微笑,高聲說:「不,不會把聖湖弄髒的——我的靈魂告訴我,我有玉石一樣潔白的骨骼!」
珠牡抬起了手臂,她解脫衣飾時的動作顯得從容而輕柔,只是纖細秀麗的手指在微微戰慄。一件件服飾脫落下來,就像深秋的紅葉或黃葉從枝頭上飄落一樣自然。
珠牡那舞者的裸體才會有的秀麗、明快而又豐饒、豔美的魅力,使浩蕩的荒野之風都垂下了翅膀,而在突然降臨的沉寂中,似乎能聽到岩石破裂的聲響。她身體的皮膚顯得有些蒼白,但那是一種能令猛獸心疼的、流蕩著誘人性感的蒼白,而且蒼白中有一種熾烈的情調,熾烈得能灼傷男人最堅硬的目光,能燒裂鐵黑色的岩石。不過,她胸前的皮膚卻白得耀眼,彷彿覆蓋著初雪的雙乳之巔,乳頭紅得有些妖豔,有些讓人恐懼;風韻妖嬈的小腹上,肚臍像是蝕刻在玉石上的一滴迸濺開的淚,那淚痕呈現出迷人的淡紫色——珠牡裸露出來的身體就像雷電之火在高原那寂靜、荒蠻的意境中燒灼出的一道美麗的傷痕。
珠牡那趾骨如淺紅色花瓣般的赤足,踏著湖邊橙黃色的石片,向湖中走去。她秀長的脖頸稍稍低垂,使沉迷的目光在湖面的波影間搖盪。每年七月和八月,都會有許多從遙遠的地方來朝拜聖山的信徒在聖湖中沐浴,希望能洗去靈魂的罪過。可是,一進入九月,湖水就會透出澈骨的寒意,也就不再有人前來沐浴。今天,珠牡剛走進冰冷的湖水時,身體不由自主地急速顫抖了一下,可是,在凝神注目中,她卻覺得那湖水呈現出的是一種燃燒的藍色,一種熾烈的藍色,一種純淨如火焰般的碧藍。
湖水在她胸前激起了細碎的銀色浪花,珠牡停下了腳步。儘管酷愛游泳,她卻不敢在此時游動,因為,沐浴於聖湖是一項聖潔莊嚴的典禮,游泳會顯得輕浮。於是,她雙手合什,低垂下頭顱,開始祈禱:「聖湖呵,請用藍色的火焰淨化我的靈魂吧⋯⋯。」同時,在冰冷的湖水中所體驗到的那種彷彿烈焰焚身的豔麗的痛苦,使沉醉的微笑盛放在她的唇邊。
在經過一段只能用心靈量度的時間之後,珠牡緩緩抬起因靈魂淨化而顯現出寧靜幸福的面容,向遠處的聖山望去。可是,她面容上那寧靜的幸福卻驟然被震驚的、恐懼的神情擊碎了,彷彿被利刃刺中心臟似的,她發出一聲喑啞的、慘痛的呻吟。
她看到,不久前還像銀色長蛇飛躍在豔藍天空中的岡底斯山脈連綿的雪山已經被狂濤怒潮般的陰雲所淹沒;從一道道岩石破碎的山缺湧出的鉛灰色濃霧,像陰鬱可怖的夢境迅速在湖面上迷迷濛濛地彌漫開來,在那濃霧中又有形態猙獰的鐵黑色雲影在動盪變幻;曾經如冰雪之淚一樣純淨,藍色火焰一樣燦爛的湖光波影,在低垂的雲層下呈現出死屍般的青灰色。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金色的聖山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76 |
二手中文書 |
$ 300 |
中文書 |
$ 300 |
中文現代文學 |
$ 334 |
小說 |
$ 342 |
現代散文 |
$ 34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金色的聖山
對生命真諦的追尋,交織著藏族在共產黨專制統治下逐漸漢化、失落心靈信仰的悲哀,譜成了金色聖山這一闕闕用鮮血謳歌生命極致之美的吟詠。一九五九年中共入侵西藏,藏軍浴血反抗;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對藏傳佛教進行滅絕性的毀滅;六十年代以來,共黨通過「漢化」以達到種族滅絕的真實目的。《金色的聖山》即是訴說藏民族如何橫遭共產黨殘害的故事。通過對一批藏族青年男女苦難命運的故事描繪,記錄著藏人真實的心靈歷程。作者袁紅冰以特有的小說藝術的形式,將藏人的美麗、高貴與真誠的民族風格得以體現與保存。
作者簡介:
袁紅冰,50年代出生在內蒙古高原,1979年考入北京大學,並於北京大學讀研究所,後任教於北京大學的法律系訴訟法教研室,1989年組織了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支持學生的民主運動。1994年被流放到貴州,在貴州省的師範大學10年,期間創辦了貴州師範大學法學院。創作《自由在落日中》,而後又創作了其他的三本小說《文殤》、《金色的聖山》、《回歸荒涼》,2004年攜帶著這四本小說的手稿流亡澳大利亞。
章節試閱
〈01〉第一章 傷痕凌晨,這裡是第一塊被太陽點燃的地方——依然淹沒在太平洋波濤中的太陽讓淡金色的光芒穿過殘留著黑暗夜色的茫茫雲霧,斜射向蒼穹之巔,將銀色的雪峰燒成火炭般深紅,那燃燒的雪峰呵,彷彿是浮現在時—空極致處的一團浴血的聖火;傍晚,這裡是留住太陽最後一片神韻的地方——大地已經彌漫起鐵黑色的蒼茫夜霧,而在峭立的黑暗之巔,被殘存的陽光映成金色的雪峰,猶如燦爛王冠的浮雕,隱喻著古老而高貴的精神原則。這個地方便是地球崇高的極致,青藏高原。這片高原以奔騰咆哮的冰山雪峰為銀色的骨架,以鐵褐色的無極的荒原為...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袁紅冰
- 出版社: 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09-03-10 ISBN/ISSN:9789867178817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611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