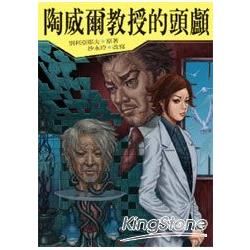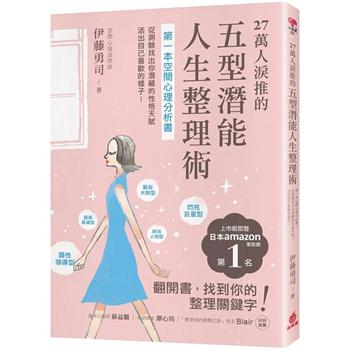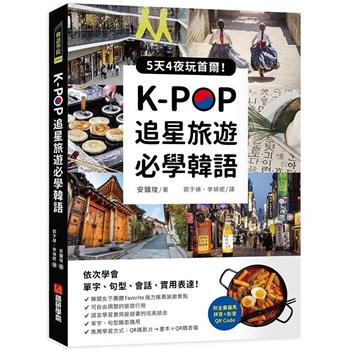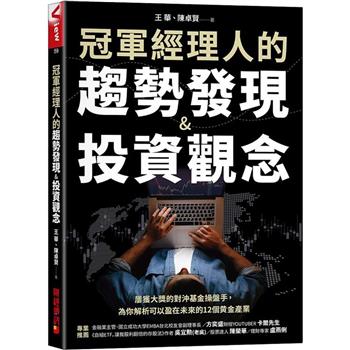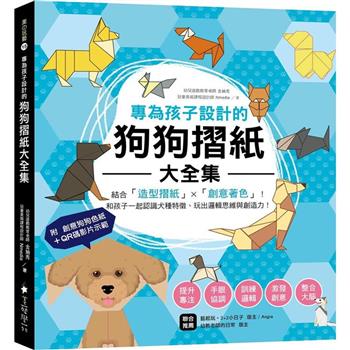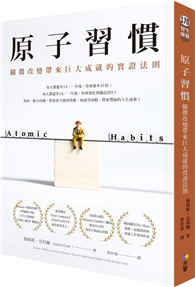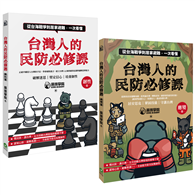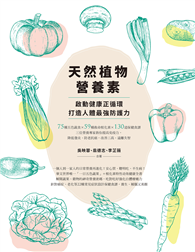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陶威爾教授的頭顱(新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80 |
二手中文書 |
$ 202 |
少兒文學 |
$ 207 |
兒童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陶威爾教授的頭顱(新版)
陶威爾教授是一位致力於器官實驗的外科專家,有一天氣喘發作,當他再度醒來時,發現自己居然只剩下頭顱……
柏麗克是在酒吧駐唱的歌女,在流氓火拚時被流彈擊中,當她恢復意識時,她發現自己已經成了一個沒有身體的女人……
杜馬離鄉背井到城市當建築工人,不幸出了車禍,當他再度睜開眼,他發現他已經和自己健壯的身體分離了……
羅蘭受雇於柯恩教授,她的工作就是照料只剩下頭顱的陶威爾教授、柏麗克和杜馬,當她發現陶威爾教授原來是被柯恩設計陷害,柏麗克和杜馬因為失去身體而鬱鬱寡歡,而柯恩野心勃勃想要進行更複雜的器官實驗時,她該如何保護,甚至拯救這三個科學的「俘虜」呢?
商品資料
- 作者: 別利亞耶夫
- 出版社: 小魯 出版日期:2007-01-01 ISBN/ISSN:9789867188861
- 語言:繁體中文 注音:內文含注音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4頁
- 類別: 中文書> 少兒親子> 少兒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