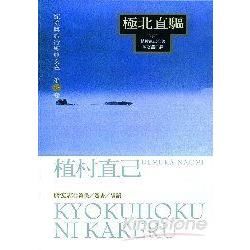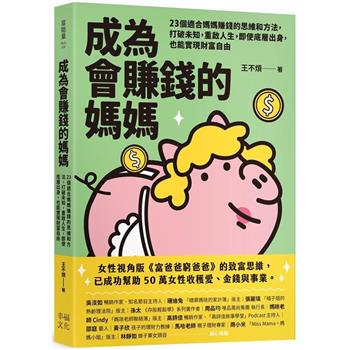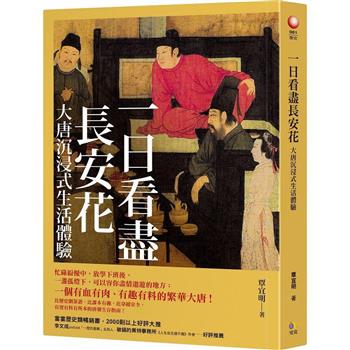導讀
極北直驅
詹宏志
當我們驅車來到阿拉斯加中部的丹納里國家公園(Denali National Park),時間已經是過午,天空還滴滴嗒嗒下著連綿不斷的小雨……。
等我們完成旅店的住宿登記,並在公園巴士服務處花了一番口舌才確定了第二天的訂位之後,時間已接近晚餐辰光,天色更是露出一種詭異的陰沈暗霾的灰黑顏色。公園出口附近的餐廳選擇不太多,有幾家好像是被荷美遊輪公司(Holland American Cruises)的團體遊客包走了,而我們看中的一家餐廳竟然已經排起了長長的隊伍。就在等待餐廳位子的隊伍行列中,我們看見淅瀝小雨的形狀與顏色彷彿逐漸起了變化,凝神一望,真的,雨滴轉白,下降速度變慢,落地前好像跳舞一樣,真的是下雪了,而這正是真夏的七月二十八日呢。
這就是美國最後的邊陲:阿拉斯加。即使是盛夏時分,天氣也是說變就變。早上啟程時天氣還是藍天高掛、萬里無雲,更兼涼爽宜人,馳騁在幾乎鮮少車輛的高速公路上,你就感覺到阿拉斯加與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比例與規格,群山的距離,道路的寬敞,平地的開闊,甚至是藍天與白雲的高遠,都讓你感覺到自然大地的巨大尺寸,以及個人存在的微不足道。
從資料上看丹納里國家公園也是驚人的,面積二萬四千五百八十五平方公里(超過六百萬英畝的土地),接近整個台灣的七成大小;當中只有一條未鋪裝的泥土路,像絲帶一樣在公園中綿延一百四十四公里。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護區不允許一般私人車輛進入,你只能登記預定每日一定容量的導遊巴士,或者你也可以申請徒步入園並自行露營的執照,那當然危險得多了。
第二天我們乘小巴士入園,天氣已經變好了,雖然地上的積雪還未融化,空氣也還冷冽刺骨,但陽光已經露臉了,視野廣遠遼闊,可以遠眺群山起伏。遠方壯觀的山脈,應該就是縱貫阿拉斯加中部的阿拉斯加山脈(Alaska Range)。其中一座高高聳立的巨大白色山峰,正被朝陽照耀得金碧生輝,果然臨時被找來充當自然導遊的女駕駛就指著它說:「看哪,那就是麥金利峰,北美洲的最高峰。」 這當然也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從遠處「觀看」這座海拔六千一百九十四公尺的北美洲第一高峰麥金利(Mount McKinley)。——從前我看到高山就想登頂,後來年齡漸增體力漸衰,慢慢覺得從遠方眺望也就可以了。——美國登山者常愛說,麥金利峰比喜瑪拉雅山的埃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或稱珠穆朗瑪峰)更崇高壯麗,因為珠穆朗瑪峰的基座是將近六千公尺的喜瑪拉雅高原,而麥金利峰則從七百公尺左右的基座丹納里山脈直拔雲霄,看起來或爬起來都高遠得多。
但即使是遠眺美麗的麥金利峰,對我這位大部分時間都在做一個「讀者」的人而言,心情也是複雜的。麥金利峰以氣候、山況多變聞名,是出了名的「殺手」,一流的登山者在這裡失足的不少,愛讀強.克拉爾(Jon Krakauer)的書的人,應該讀過登山高手對這座山的殘酷描述。而在諸多葬身麥金利雪峰的名人當中,日本探險家植村直己(Uemura Naomi, 1941-1984)是我目睹山峰真面目這一刻,最令我覺得感傷的人。
植村直己生也晚,當他有志於做一位大探險家時,探險時代已經大致上是過去式了。植村在一九六○年進入明治大學,參加了登山社(日本人稱為山岳部),剛剛成為登山界的新人,但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瑪峰已在一九五三年由紐西蘭人艾德蒙.希拉瑞(Edmund Hillary, 1919-)和雪巴人嚮導丹增(Tenzing Norgay, 1914-1986)成功聯手登頂了。而當植村一九六七年初訪格陵蘭(Greenland)思索極地新探險的可能性時,距離世人矚目的北極、南極探險競賽完成的一九○九年與一九一一年,也已經過了半個世紀了。
儘管有點不合時宜,但植村直己仍然以他極獨特的個人風格(害羞、敏感、喜歡孤獨),成為二十世紀幾位最偉大、最受尊敬的探險家。特別是對於二次大戰後亟需重建信心的日本人,植村的勇氣與成就,大大地振奮了同世代以及後來的日本年輕人。
在探險史上,植村創造了好幾個第一,其中尤其以他獨特的「獨自一人」的探險風格最為人稱道。生於日本兵庫縣的植村直己,真正開始他的「探險生涯」也許要從一九六六年算起,這一年,他在歐洲最高峰白朗峰(Mont Blanc, 4807公尺)獨自登頂成功,隨即又一人登上高難度的馬特杭峰(Matterhorn, 4,478公尺)。然後他乘船到非洲,先登上五千一百九十九公尺的肯亞山(Mount Kenya),再獨自登上非洲最高峰吉力馬札羅山(Mount Kilimanjaro, 5,895公尺)。這一系列成功的登山行動,後來造就他成為史上第一位登上五大洲最高峰的登山者,也突顯了他後來的行動特色,對於那些其他人習慣團隊完成的探險行動,他卻傾向於一個人孤獨完成。
一九六八年,他出發到南美洲,獨自完成南美最高峰阿空加瓜山(Aconcagua, 6,962公尺)的登頂,隨後他又用了兩個月的時間,獨自一人完成亞馬遜河六千公里的木筏溯源之旅。同年他本來想繼續前往美國,嘗試麥金利峰的攀登,但因為美國不肯發給他獨自登山的許可而放棄。 經過這一連串的探險行動,植村已經成了日本山岳活動的英雄,一九七○年日本再度籌組珠穆朗瑪峰登山隊時(前一年日本剛組過一次不成功的行動),就爭取他成為隊員。植村也不負眾望,他和同隊隊員松浦輝夫兩人負責攻頂,在五月十一日成功登上珠穆朗瑪峰,成為第一位登上世界最高峰的日本人。完成珠穆朗瑪峰的登頂之後,植村再次前往美國挑戰獨自登頂麥金利峰,那是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的事,而植村也同時成為世界第一位曾經登上五大洲最高峰的人。
完成五大洲高峰之旅,植村直己開始把眼光轉向極地探險,為了練習南極大陸的橫斷探險,一九七一年他試著從日本頭走到日本尾(從北海道的稚內走到九州的鹿兒島,因為距離和橫越南極洲相似);一九七二年他又移往格陵蘭北端與愛斯基摩人同住,希望熟悉狗與雪橇的操作,並學習愛斯基摩人的極地生活智慧,也是為了後來的探險做準備。 一九七三年,植村在格陵蘭獨自駕駛狗雪橇往返三千公里旅行成功。一九七六年,他再接再厲獨自駕狗雪橇繞行北極圈一萬兩千公里。一九七八年,經過前面多次嘗試與努力,植村終於駕狗雪橇獨自一人到達北極極心,成為歷史上完成此一壯舉的第一人。植村直己從此不再是日本人的探險英雄,他是世界性的人物了。
植村寫書很遲,一九七一年他的處女作《賭青春於群山》出版,記錄他多彩多姿的登山生涯,從大學時期的自卑寫到世界最高峰的登頂,他的熱情浪漫,以及說故事的能力立刻風靡了全日本。極地冒險之後,他又出版了他的「極地三部曲」的代表作,一是記錄他格陵蘭三千公里雪橇之旅的《極北直驅》 (1974),二是《北極圈一萬二千公里》(1976),三是《北極心格陵蘭單獨行》 (1978)。三本書共同燃起了日本全國上下瘋狂的探險熱,也鼓舞了日本年輕人對冒險的大膽夢想,以及對理想的勇敢追求,影響至今不衰。
一九八二年,植村想完成他以狗雪橇獨自一人橫越南極大陸的終極夢想,結果英國與阿根廷的福克蘭戰爭正巧同時爆發,他人雖然已經抵達南極大陸,卻苦等不到阿根廷軍方本已允諾的援助,他在南極陸地獨自度過冬天,但未能進行破紀錄的橫跨大陸壯志,失意而返。一九八四年,他試圖獨自一人完成冬季登頂麥金利峰的高難度冒險,二月十二日他在自己的四十三歲生日當天登頂成功,二月十三日他與外部最後無線電通訊之後,再也沒有蹤影,沒有人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此刻我看著麥金利山峰泛著金色陽光的雪白頂蓋,沈默安靜,彷彿什麼事也不曾發生,我想著讀過的植村留下來的情熱之書,忍不住想著:「植村先生,那裡會冷嗎?」
編輯前言
詹宏志
探險家的事業
探險家的事業並不是從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才開始的,至少,早在哥倫布向西航行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大探險家法顯(319-414)就已經完成了一項轟轟烈烈的壯舉,書上記載說:「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編按:指今日的中印度),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法顯旅行中所克服的困難並不比後代探險家稍有遜色,我們看他留下的「度沙河」(穿越戈壁沙漠)記錄說:「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這個記載,又與一千五百年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穿越戈壁的記錄何其相似?從法顯,到玄奘,再到鄭和,探險旅行的大行動,本來中國人是不遑多讓的。
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探險旅行,多半是帶回知識與文化,改變了「自己」;但近代西方探險旅行卻是輸出了殖民和帝國,改變了「別人」。(中國歷史不能說沒有這樣的例子,也許班超的「武裝使節團」就是一路結盟一路打,霸權行徑近乎近代的帝國主義。)何以中西探險文化態度有此根本差異,應該是旅行史上一個有趣的題目。
哥倫布以降的近代探險旅行(所謂的「大發現」),是「強國」的事業,華人不與焉。使得一個對世界知識高速進步的時代,我們瞠乎其後;過去幾百年間,西方探險英雄行走八方,留下的「探險文獻」波瀾壯闊,我們徒然在這個「大行動」裡,成了靜態的「被觀看者」,無力起而觀看別人。又因為這「被觀看」的地位,讓我們在閱讀那些「發現者」的描述文章時,並不完全感到舒適(他們所說的蠻荒,有時就是我們的家鄉);現在,通過知識家的解構努力,我們終於知道使我們不舒適的其中一個解釋,就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說的「東方幻想」(Orientalism)。這可能是過去百年來,中文世界對「西方探險經典」譯介工作並不熱衷的原因吧?或者是因為透過異文化的眼睛,我們也看到頹唐的自己,情何以堪吧?
編輯人的志業
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探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大內容;不了解近兩百年的探險經典,就不容易體會西方文化中闖入、突破、征服的內在特質。而近兩百年的探險行動,也的確是人類活動中最精彩、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當旅行被逼到極限時,許多人的能力、品性,都將以另種方式呈現,那個時候,我們也才知道,人的鄙下和高貴可以伸展到什麼地步。
西方的旅行文學也不只是穿破、征服這一條路線,另一個在異文化觀照下逐步認識自己的「旅行文學」傳統,也是使我們值得重新認識西方旅行文學的理由。也許可以從金雷克(Alexander W. Kinglake, 1809-1891)的<日昇之處>(Eothen, 1844)開始起算,標示著一種謙卑觀看別人,悄悄了解自己的旅行文學的進展。這個傳統,一直也藏在某些品質獨特的旅行家身上,譬如流浪於阿拉伯沙漠,寫下不朽的<古沙國游記>(Arabia Deserta, 1888)的旅行家查爾士.道諦(Charles Doughty, 1843-1926),就是一位向沙漠民族學習的人。而當代的旅行探險家,更是深受這個傳統影響,「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行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旅行內容發生在內在,不發生在外部。現代旅行文學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深刻而豐富,因為積累已厚,了解遂深,載諸文字也就漸漸脫離了獵奇采風,進入意蘊無窮之境。」這些話,我已經說過了。
現在,被觀看者的苦楚情勢已變,輪到我們要去觀看別人了。且慢,在我們出發之前,我們知道過去那些鑿空探險的人曾經想過什麼嗎?我們知道那些善於行走、善於反省的旅行家們說過什麼嗎?現在,是輪到我們閱讀、我們思考、我們書寫的時候。
在這樣的時候,是不是<旅行與探險經典>的工作已經成熟?是不是該有人把他讀了二十年的書整理出一條線索,就像前面的探險者為後來者畫地圖一樣?通過這個工作,一方面是知識,一方面是樂趣,讓我們都得以按圖索驥,安然穿越大漠?
這當然是填補過去中文出版空白的工作,它的前驅性格也勢必帶來爭議。好在前行的編輯者已為我做好心理建設,旅行家艾瑞克.紐比(Eric Newby, 1919- )在編<旅行家故事集>(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 1985)時,就轉引別人的話說:「別退卻,別解釋,把事做成,笑吠由他。」(Never retreat. Never explain. Get it done and let them howl.)
這千萬字的編輯工作又何其漫長,我們必須擁有在大海上漂流的決心、堅信和堅忍,才能有一天重見陸地。讓我們每天都持續工作,一如哥倫布的航海日記所記:「今天我們繼續航行,方向西南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