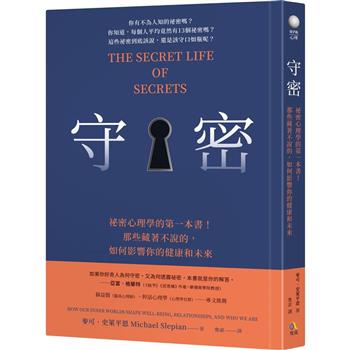一部當代書寫布拉格的經典作品
冷戰之後,班維爾首次進入布拉格,由於涉入一項藝術品走私的計畫,開啟了他的布拉格之旅。布拉格是歐洲的魔幻之都,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魯道夫二世於1575年就位,這位星相愛好家與鍊金術的庇護者,將來自全世界的鍊金術士與魔術師召喚到他位於山丘上的布拉格,如今那裡已成為神秘與陰謀的集散地。而戰爭、革命、洪水、蘇聯入侵,甚至是1989年絲絨革命之後接踵而來的觀光客人潮,都無法摧毀這位位於伏爾他瓦河畔,充滿美麗、驕傲而憂鬱的城市。而作者爬梳布拉格悲劇般的歷史糾結,不論是皇帝、王子、天才、騎士、英國或是惡霸,這些創造歷史的人物都將進入讀者眼簾。
卡夫卡住在這裡
作者出身於愛爾蘭,他在寫作本書特別關心布拉格的小酒館,或許是因為這兩地愛喝酒的作者相當不少吧!班維爾在比擬兩地的小酒館時,將本書也變成一座歷盡繁華的布拉格小酒館了。
在這家小酒館∕這部作品裡,我們將會見到知名的文學家、藝術家,他們訴說著布拉格過去的壯麗,光榮之後的灰燼、被罷免主權的王朝,歷史與作者的想像力並馳,傳說在文學的筆觸下發光,這些故事在愛爾蘭威士忌的輔助下,聽起來特別動人:卡夫卡住在這裡,曾算出納粹會倒台的捷克算命大師底比斯夫人也住在布拉格,這個城市的風景如此美好……。除了歷史上的知名人物,班維爾還以攝影家、魯道夫皇帝、市井小民、克普勒、異議份子、扒手等人物為對象,為布拉格做出萬花筒式的導覽,讀者能感受布拉格的層次多變,並且經由班維爾的古怪、黑色幽默,彎曲蔓延的敘事路徑,隨著他進入了宛如布拉格迷宮般的小巷。
這是這座愛之城的醉人讚美詩,按照他的描述,她是位喜怒無常的淫蕩女妖。「在古董商的名義掩護下,千嬌百媚的她將自己偽裝成一幅靜物圖,一段對過去光榮歷史的沉默繼承,一個在玻璃球中的死寂景觀,這一切更增添了她的邪惡魔幻感受。她狡猾地運用她的特有方法,進入到受詛咒的靈魂,深入到只有她擁有鑰匙的謎團當中。」
魔幻之城,魔幻之筆
布拉格是歐洲三大魔幻城市之一,作者藉由四次造訪的追憶,加上個人的想像與文采,描述他與布拉格的關係;這種文風呈現出來的「魔幻感」讓人分不清布拉格的真實虛假,加上班維爾強烈的個人風格與幽默感,本書正是讀者能藉由布拉格的「真」,進入班維爾的「虛構之城」的最佳入門。
儘管我在寫作的時候,並沒顧及其實我是在發明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城市,更具挑戰性的是,我得重新創造十六世紀早期的生活——所有的故事都是發明,所有的小說都是歷史小說——但我感興趣的,是如何達到逼真,或者至少達到某種可信度。許多讀者恭維我的小說準確地「掌握那個時代」,我實在不好意思問他們如何知道這一點;但我知道他們是在讚許我的想像巧藝,他們被我的描述所說服,好樣情況真的就是那樣。不過有時幻想真能化為具體事物,那些曾有夢境成真經驗的人,便能理解此點。
作者簡介
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
2005年曼布克獎得主,被譽為最有可能為奪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愛爾蘭作家,他最喜歡的作家是貝克特,其作品同時兼有喬伊斯與納博可夫的特色。
班維爾1945年生於愛爾蘭,曾任《愛爾蘭時報》文學編輯,也長期為《紐約時報副刊》撰寫書評。自第一部作品《人魔龍狼金》(Long Lankin)於1970出版以來,他已寫了十九部小說,最近一本是用筆名Benjamin Black寫的犯罪小說《克莉絲汀驚魂記》(Christine Falls);「科學革命三部曲」特別能見出文學特色,並獲獎連連:《哥白尼博士》(Doctor Copernicus)獲布萊克紀念獎(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克普勒》(Kelper)獲衛報小說獎(Guardian Fiction Prize),《牛頓書信》(The Newton Letter: An Interlude)被改拍成為影集。
他另一部「三部曲作品」《證據之書》(The Book of Evidence)、《鬼魂》(Ghosts)、《雅典娜》(Athena)則以藝術為焦點;他亦喜愛戲劇,多次擔任改編劇本的工作。2005年班維爾以《大海》(the sea)獲曼布克獎,本書《布拉格》以厚重、魔幻、古怪與黑色幽默,彎曲蔓延的敘事路徑,敘寫了布拉格迷人的風景。最新的小說作品是《遮蔽的過去》(Shroud)。《波士頓環球報》讚譽他是「當今最偉大的英文作家之一」。
譯者簡介
耿一偉
花蓮人,台大哲學系畢,布拉格音樂學院研究。目前擔任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與華梵大學哲學系兼任講師。曾獲倪匡科幻獎首獎,著有《動作的文藝復興──現代默劇小史》、《誰來陪我跳恰恰──澎恰恰傳》,譯有《給菲莉絲的情書》、《恰佩克的秘密花園》、《哈維爾戲劇選》(與林學紀合譯)等作品。